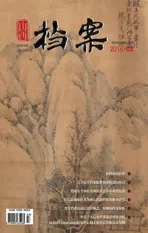规范与自治:近代山西忻县商会组织演变探析
2016-02-03张玉莲唐庆红
文/张玉莲 唐庆红
规范与自治:近代山西忻县商会组织演变探析
文/张玉莲 唐庆红
处于社会基层的近代县级商会,虽未在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政局变动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其展示出的中国近代商会发展的纵向连续性与横向地域性差别,却为我们理解近代商会在地域社会的建构及其组织演进开启了一扇窗。考察《商会法》与忻县商会的组织演变,有助于透视近代中国基层商会组织演进机制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近代;基层商会;忻县;组织演变
一、自治走向规范:新旧兼容的忻县行会、商会
明清以来随着区域间贸易的扩大,业内激烈的竞争与身在他乡的孤寂、无助,商人们日渐注重群体力量的联合。忻县离邑从商者多活动于内蒙古和新疆,塞外荒凉、恶劣的生存环境、长途跋涉的艰辛以及商业竞争的激烈,促使他们注重同乡间的联络,并逐渐形成团队。正是同乡相互提携扶助,忻州商帮日渐成为晋商中活跃于塞外边境的一支劲旅。
忻县商人虽以外出经商者居多,但多与本县商业有连带关系。一般总号设在忻县,分庄沿商路分散各地。如忻县六大财主郜、王、张、陈、连、石家在“小西商路”密布着他们的店铺,贸易的品类举不胜举。发达后的忻商积极投资家乡工商业,曾推动了忻县城内和四大集镇的繁荣。民国十九年《新兴》半年刊曾载,“清前忻人尽管贫瘠,然极少有外出行乞者,必以学商立足,白手起家者不胜枚举。本地商业在昔颇殷实,城内商号林立,鳞次栉比,市肆连瓦,街巷如织,门庭峥嵘,檐牙高啄,偎依井然,百货绚丽,客栈联袂,一望而知繁荣之区。”[1](p341)
为协调行业内部的竞争,同一城镇的经营者多以同一行业或几种相仿行业为基础建立了各种行会。忻县境内主要分为绸、布、纸、钱、粮、铁、药、估、木、当10大行。各行对内自成体系,均有自己的头目,头目由资金多、有声望的掌柜或财东担任,主要办理本行内事务。对外则十行又相互联合为一大行。因绸缎行为各业之首,所以绸缎行头目亦为大行之总行头,统领其他各行业头目集体协商办理对外社会事务。此时忻县商业行会是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商业自治组织。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使现代工商业组织商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渐为士人所识,由此呼吁向西方学习,设立商会之声鹤起。
1904年1月,晚清商部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劝办商会。该《章程》的颁布,从国家政策层面引导了国内传统商业组织—行会向新型工商业组织商会的转型。但政府的这种政策规范旨在“劝办”,给予了各地极大的自主性。如《章程》第一款明言,“本部以保护商业、开通商情为一定之宗旨。惟商民散处各省,风尚不同,情形互异……自应提纲挈领,以总其成。”[2](p22)也就是说商会章程、商会选举、商会何时何地成立及如何运作,只要“有裨商务,无背本部定章”即可。地方商会内部拥有极大的自治空间。
在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很多地域商会多于该时期由当地的行会、会馆、公所直接转变而来。这也决定了近代中国商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行帮组织作为基础和支柱。而在尚未成立商会的区域,其原有行会组织中也开始出现了新趋向。就忻县而言,虽无法考证忻县商务会形成的具体时间,但可以明确的是,在忻县商务会成立之前,忻县商业组织——十大行会以总行头召集各行头共同议决的形式与商会民主议事有异曲同工之处,已具有近代商会的雏形。1907年山西总商会成立,晋省各县商会也相继成立。忻县商界也组织成立商务会,初期仍沿用行头议事的办法,会长由各行会大、中、小商会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商务会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各行业开展商业活动,调息纠纷,和解事非,摊派税款,支应地方公益、社会福利开支等事务。
二、规范与自治:同步转型的忻县商会
民国初年,鉴于清廷商会法规对商会的权限定位不明,多项规定模糊不清、不合时宜之处,1914年9月,北京政府参政院议决新的《商会法》及施行细则。然该《商会法》及细则因细节问题尚未推行即被重新修订。直到1915年12月为大总统申令重新公布。要求各地商会依法进行改组,将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改称总商会和商会,领导人改称正、副会长。该法最重要的变化在于从法律的角度加强了政府对商会的规范性约束。如其首次对商会的选举制度做了明确规定,使商会选举的运行成为考核其民主与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忻县商会虽直到1919年才改组商务会为商会,设会长制,并从10大行候选人中选出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会董若干人。此次商会选举具体是如何进行的,虽不得知,但从名称变更可以看出忻县商会已向1915新《商会法》规范的体系靠拢。这一方面道出商会选举章程已被基层商会所贯彻,即政府的规范性得到认同与实践。另一方面忻县商会的延迟改组,及其行、商新旧兼容状态则反映了该时期商会具有相当的自治、独立性。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革命目标由“破坏”向“建设”的转换,也使民众组织以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被整顿改组。具体到商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8月15日颁布《中华民国商会法》,要求各地商会依法整顿改组,重新登记。1930年7月25日又出台《中华民国商会法实施细则》协助实施。1929年,忻县商会下属行会改建为同业公会。1931年,忻县商会改组为委员制时,并由各行业推选代表,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再从常务委员中选出主席。[3](p36)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商会的整顿改组,有力地促进了基层商会由新旧兼容状态向近代商会的转型。忻县商会、山西省商会联合会、全国商联会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商会等级体系。而忻县商会改组与政府改组令的首次同步性,亦说明该基层商会组织变迁已由前期的诱致性转为强制性。可以说,《中华民国商会法》及其《实施细则》不仅在制度层面推动全国商会体系的健全与基层商会组织现代化,且实现了国民政府对整个商会体系“法”的规范与管理。
三、强权与自治:日伪政权下的忻县商会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1月侵占忻县的日军强令忻县商会恢复为日军及伪政权做应急性后勤服务,并名为自治会。其组织功能已完全不同于真正的商会。随着战事转变与占领的长期化,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始注重利用沦陷区社会组织来控制地方社会。改组沦陷区商会、同业公会组织即为日军控制沦陷区经济的策略之一。由此,日伪政权下的忻县商会改组提上日程。
1940年11月,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通知各省、特别市对各级商会、同业公会进行改组。要求查明各辖区内工商业组织,已设立公会、商会者应重新登记上报。尚未组织者,则应劝导迅速依法成立。1941年3月,在忻县公署训令督促下,[4](p3)忻县商会改组随即展开。
值得关注的是,日伪政权在华北沦陷区推行商会改组时所依据的商会法及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都是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整顿改组商会时颁布的。甚至连改组中所需的相关文书格式、手续说明,也都沿用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商会时印制的。如忻县公署转饬商会山西省公署训令时,提到“依法成立的商会、同业公会上报的职员、会员名册,多数不合格,为求一律起见,将前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之商会,及工商同业公会呈报组织或改选时应具手续说明书,暨会员名册、职员名册,随令印发。除分令各县外,合行令仰该知事转饬所属商会及工商同业公会。”[5](p4)由此,忻县商会根据上述商会法及实施细则制定了《忻县商会章程》以及所要求的手续,完成了在日伪政权下的第一次改组。
日伪政权对忻县商会的改组是通过选举实现的。而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说1941年日伪政权下的忻县商会改组,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改组的重演。尽管此次忻县商会改组中出现选举在先,会员注册在后等不符程序之状况,但忻县商会的改组民主与否、规范与否,并不为日伪政权所关注。日伪政权对商会改组,不过是借商会为商家之领导机关,商业活动之总枢纽,对商家业务深明洞悉的特质,对沦陷区尚存工商业进行调查,以藉此重建沦陷区工商业组织网络的手段而已。同时,改组后的商会与同业公会通过《商会法》与伪政府建立起的“法律”关系,又为日伪政权通过法律来管理、控制商会及其整个组织体系所辐射的商号与地域社会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同时也侧证,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的规范,令这一新型工商业组织的民主性、现代性深入基层。但日伪改组商会的真正目的,毕竟是欲将商会变为其控制地域社会的工具。
为适应日伪统制经济需求,华北政务委员会对《商会法》即(1929年《中华民国商会法》)做了一定的修改。其变动主要在于各级主管官署名称、严格经费和会计以及细化经营业务及会员的资格的变更,对商会选举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有趣的是,尽管实业总署训令,“所有各省各县之商会,均应按照新商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于一年内依法改组。”但忻县商会却“因种种特殊关系,竟超法定限期,未按期进行改组。”[6](p92)
依照《忻县商会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董事及监事之任期均为四年,每二年改选半数不及连任。[7](p23)1941年3月忻县商会董监自前届选任以来,已逾四载,按章应行全体改选。于是1945年3月27日,忻县商会召开了第一届理监事选举大会,亦为沦陷后的第二次选举大会。这次理监事选举大会虽有“政府”代表临场监选,但各位代表均表态为“改选事宜如果得大家之同意,变通办理。”“官厅绝不参加意见”[8](p80),对于新就任的理监事的履历虽档案中没有详细记录,但从选举时会员一人一票,以实票当场公众的选举记录看,此次选举是较为民主的。另外从当选者的年龄、所代表的行业比例看,大致是均衡的。
综观忻县商会的上述两次选举,如果第一次改组法令、人员的沿用是日军出于在战事变化急于控制地方商业组织的策略的话,那么,1942年新修正的商会法出台却一直未被地方商会所实践,则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沦陷区基层商会组织的自治空间。1945年3月,已经进入中日战争的决战阶段,山西各地商会仍相继进行换届选举大会。特别是忻县第一届理监事大会中,在大会及会员代表的沟通中,因时制宜、变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换届选举,也彰显出其因地制宜的自治行为。两次选举实践中以“通官商之邮”的实力与资望为准的选举结果,亦道出忻县商会在人员组织结构上的自我处理空间。
通过上述层层递进式限制,日伪政权将忻县所有的工商业者强行纳入其统制经济体系内,也使改组后商会的功能与性质变得复杂化。为求得生存,商会向县公署上呈请求,请求其与“友邦机关”交涉。拟将忻县商号自行组织棉布、谷物、砂糖等相关组合,组合应行一切规定章程,均遵崞县机关指示办理。显然,商会领导明白,如果单提出不入组合是不可能的,但若可以自行组合的话,除可以省去摊派的13,7500元外,还可加强本会内部成员的联合经营。然遭拒后,忻县商会只得一面着令各同业公会按照商号等级摊派,一面又函致山西实业银行贷款融资入股,以不使本县主导商业完全退出晋北市场。
藉此物资配给组合事件,可以看到忻县商会面对日伪损害工商界利益的若干政策,仍以行业发展和团体利益为取向,积极发挥其维护工商业利益职能。然若由此评议忻县商会是日伪政权的御用组织,显然过于片面。近代商会作为政府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人社团,于任何政体下都不可能完全丧失其独立自主权,即便是在日伪政权强压下的忻县商会也从未放弃过其自治诉求。
综上可见,自清末新政推动近代中国商会成立以来,政府与商会的关系便处于规范与自治的互动中。清末民初政府规范引导与商会自治独立,具体到组织形式上呈现为商会、行会兼容。这种状态不仅存在,而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近代中国基层工商业组织由传统的行会向新式工商业组织商会的转型是缓慢渐进的过程。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商会的整顿改组,推动了商会、行会兼容到完备现代商会组织体系的彻底转型,也是近代中国商会制度确立及其落实基层的一次重大变革,以致于日伪在沦陷区对商会的控制也须仰赖于选举重建。而对于这种自上而下层级商会在强权政府下的自治权,则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层商会研究(1937—1949)—以山西忻县商会为个案”,[项目编号:11YJC770086]、井冈山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民国时期山西忻县商会研究”[项目编号:JRB11018]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杨秋梅)
[1] 曹利军.忻县商业文化之浅析[A].忻州市忻府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忻商史料辑要[C].2007.
[2]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3] 于颖.建国前忻县商业综述[A].山西省忻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忻州文史(第六辑)[C].2006.
[4] 忻县公署训令(44)号.1941年3月5日[G].日伪忻县商会档案(以下简称日忻商档)103-8-18,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档案馆藏(下略)
[5] 忻县公署训令(169)号.1941年6月20日[G].日忻商档103-8-18.
[6] 为呈报理监事改组情形并当选名册及就任日期敬请核转备案由.1945年5月[G].日忻商档103-8-01.
[7] 山西忻县商会章程.1941年3月[G].日忻商档103-8-03.
[8] 忻县商会第一届理监事选举大会记录.1945年3月27日[G].日忻商档103-8-02.
Norms and Autonomy: Evolution of Xin County’s Commerce Chamber in Modern Times
Zhang Yu-lian Tang Qing-hong
F727
A
1005-9652(2016)02-0024-04
张玉莲(1980—),女,山西太原人,井冈山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唐庆红(1980—),男,江西吉安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