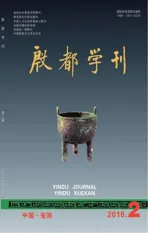不同语境下卞之琳诗歌的阅读接受
2016-02-02张文民
张文民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不同语境下卞之琳诗歌的阅读接受
张文民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根据时代语境的变化,卞之琳诗歌阅读接受史分为3个阶段:20世纪30—40年代,卞之琳诗歌引起朱自清、李健吾等人的解读讨论,诗名初显,但也不时受到左翼阵营批评;50—70年代,卞之琳受到政治批判,其诗歌不见容于主流文艺规范,渐渐被淡忘;80年代以来在诗歌现代性话语背景下,卞之琳诗歌的独特品格、价值被重新发现、论说。卞之琳诗歌阅读接受史折射出由诗歌、诗人、读者、诗学话语、时代语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参与的中国新诗意义生产与形态建构过程。
卞之琳诗歌;阅读接受;诗学话语;时代语境
卞之琳作为中国新诗现代派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为人熟知,然而80多年来对其诗歌的阅读、接受历经起伏,不同时代语境下读者、批评家、文学史家对卞之琳及其诗歌的阐释与评价大相径庭,这种言说反过来也影响到卞之琳的诗歌创作。本文通过梳理卞之琳诗歌的阅读接受情况,揭示出中国新诗自身品格、价值的生成与不同时代语境下读者阅读、阐释、接受、评价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因与徐志摩、闻一多的师生之谊,卞之琳最初以新月派成员身份跻身诗坛,早期诗作《望》、《黄昏》、《魔鬼的夜歌》、《寒夜》入选《新月诗选》,陈梦家说:“卞之琳是新近认识很有写诗才能的人。他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1]透露出卞之琳诗歌有别于新月派的另一种诗风。随着《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30—1939)》(1942)等系列诗集出版,卞之琳诗歌以其象征色彩浓厚的意象、幽深玄妙的构思与新月诗歌拉开距离,而被划入戴望舒主导的现代派阵营。
卞之琳诗歌问世之初便受到名家青睐。朱自清率先敏锐觉察到《三秋草》与新月派诗歌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爱情诗极少”、“说得少,留得可不少”、“这个念头跳到那个念头”、“联想出奇”、“比喻别致”等。[2]也就是说卞诗吝于抒情,善于“留白”,思维跳跃,联想、比喻奇特,与抒情浪漫、婉转秾丽的新月诗风大异其趣,由此确立自身独特艺术价值。后来朱自清《新诗杂话》对卞之琳《距离的组织》、《淘气》、《白螺壳》等诗作了细致解读,认为卞诗是“零乱的诗境”又是“复杂的有机体”,是“一种解放,一种自由”,又是“一种情思的操练”[3](P19),朱自清赞赏卞之琳能够在微细琐屑的事物里发现诗并致力于形式试验。卞之琳指出朱自清对其诗作的“误解”,而后朱自清在序言中对自己的解读作了更正。
李健吾认为《三秋草》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言近而旨远”:“那样浅,那样淡,却那样厚,那样淳,你几乎不得不相信诗人已经钻进言语,把握它那永久的部分。”[4](P138)《鱼目集》唤起“一个完美的想像的世界”,“在字句以外,在比喻以内,需要细心的体会,经过迷藏一样的捉摸,然后尽你联想的可能,启发你一种永久的诗的情绪。”[4](P144)关于《圆宝盒》等诗的解读问题李健吾与卞之琳展开反复讨论,先是李健吾《鱼目集》尝试对卞诗做一解读,接着卞之琳《关于<鱼目集>》对李健吾的解读做出回应,然后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再回应,最后卞之琳《关于“你”》再解读,两人的讨论无不才气横溢,洋洋洒洒。[5]
朱自清、李健吾、卞之琳之间这场解诗讨论为后世史家乐道,这场讨论扩大了卞诗的声望,其艺术探索、形式创新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另一方面确也昭示出卞诗的复杂、多义、难懂,易被“误解”的审美特质,为后来卞之琳及其诗歌的命运起伏埋下伏笔。
经过这次解诗论争,卞之琳诗名日隆,在20世纪30—40年代,除朱自清、李健吾外,其他人也对卞诗给予好评。沈从文说卞之琳“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6]。除了这种印象式、点评式的褒奖,李广田《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从“章法与句法”、“格式与韵法”、“用字与意象”等3个方面深入解读《十年诗草》的艺术成就,作为《汉园集》的合作诗人,李广田的论析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袁可嘉《诗与主题》谈到卞之琳善于将微细琐屑的事物里发现的诗意透过感觉富于变化而技巧娴熟地向广处深处伸展,卞诗这种特点要求读者既要有敏锐的感觉,还要深谙隐藏于诗中的各种技巧,惟其如此才能捕捉到诗的美质。废名《谈新诗》对卞之琳的推崇与其诗歌观紧密相联,他认为诗之为诗重在内容是诗的而形式可以是散文的,但新月派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诗的形式建构上,以致诗的内容有些空泛,而卞之琳的诗既在形式上兼顾新月的格律,内容又是诗的,与自己的诗歌观暗合。
而鼓吹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左翼诗歌阵营批评现代派搬弄西方象征主义等“没落形式”,宣扬空虚、颓废、伤感、逃避现实等“消极情绪”。他们指责《鱼目集》充满“睡眼朦胧”、“孤独”、“暮色苍茫”、“坟墓”、“孤泪”、“真愁”等灰色字眼和“有微毒的叹息”[7]。左翼诗歌阵营看出卞诗与时代的疏离,却忽视了卞诗的艺术价值。
抗战爆发后,卞之琳创作《慰劳信集》努力拥抱时代、服务现实,写法上追求浅白。但时代风云从根本上改变了诗歌接受语境,倾向于个体内心抒写的卞诗越来越受到批评,其“朦胧”、“晦涩”的特征一再为人诟病,阿垅说:“诗底写法不应该是谜面,内容不应该是谜底;然而卞之琳,恰好是要猜的。一猜,就一塌糊涂了。”他批评《断章》“故求炫丽,故作聪明,故寻晦涩”,是“绝望的诗”、“愈艳愈毒”的“罂粟花”。[8]在对卞诗简单化批评中蕴含着从“晦涩”走向“浅白”的期许,也昭示出卞诗在下个时期的命运。
二
20世纪50年代以后,解放区文学作为“新的人民文艺”样板在全国推广,其中包括改造民歌资源而成的解放区诗歌。与此同时,一切西方的、中国的现代派文艺被冠以“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艺”而受到批判,许多与之有关的文艺家急于清算或者撇清自己。卞之琳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诗时批评中国新月派、现代派诗歌“颓废”、“晦涩”、“逃避现实”,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一派”[9]。但两年后《文艺报》上一组总题为《对卞之琳的诗<天安门四重奏>的商榷》的文章逐字逐句批评卞之琳的《天安门四重奏》,指责诗人没有走进新时代,没有摆脱旧的创作方法。这次批评表明新中国主流文艺界对“晦涩难懂”、“迷离恍惚”的现代派诗歌的高度警惕。卞之琳为此作出检讨,主动拥抱时代,到江浙地区参加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创作诗集《翻一个浪头》,里面的许多作品采用新民歌体,即便如此,仍难逃“晦涩”的声讨。原本就“小处敏感,大处茫然”[10](P4)的卞之琳面对急遽变化的时势想努力追赶却又无所适从,此后文艺界对他的批评不绝于耳,诸如“不清晰”、“模模糊糊”、“朦胧不明”、“百思不解”、“晦涩”等成为卞诗的标签。
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颇能反映新的政治话语、文艺规范重塑中国新诗形象的努力。长篇序言《“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站在“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文学”立场构造一个二元对立的新诗史叙述框架:“五四”时期的郭沫若、20年代的革命诗歌、30年代左翼诗歌与抗战诗歌、40年代国统区讽刺诗与解放区颂歌构成革命、进步的“诗歌主流”,“五四”时期的胡适、20年代的新月派与象征派、30年代现代派等则构成与“诗歌主流”对立的“诗歌逆流”。在这种框架下,臧克家批评卞之琳所属的现代派逃避现实斗争、抒写个人主义的“没落的悲伤”和“颓废的哀鸣”,《中国新诗选(1919—1949)》收录卞之琳《远行》、《给一位刺车的姑娘》、《给西北的青年开荒者》3首相对“思想进步”、“手法明朗”的诗歌,对《断章》及其他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弃之不顾。
在50年代末“新诗发展问题”大讨论中,卞之琳一不小心又撞到批判的风口浪尖,就连在30年代与卞之琳同属现代派阵营的徐迟此时也批评卞之琳“写起诗来,文字总是别别扭扭的,也是有几个外国诗人的魔影在作祟”[11](P66),透露出对卞诗醉心于西诗格调而没有继承民歌传统的不满。这场大讨论是在“新民歌大跃进”背景下展开,民歌被视为新诗发展的“正途”,而卞之琳委婉提出学习民歌并不是“依样画葫芦来学‘写’民歌”,而是以民歌为基础,结合旧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传统、外国诗歌长处来创造更新的更丰富多彩的诗篇”[12];其次,诗歌的民族形式不应只是民歌形式,还应包括“五四”以来受外国诗歌影响形成的新诗形式;第三,为了便于记诵,应追求“新格律”,追求精炼。卞之琳这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被指责为“轻视新民”,甚至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与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倾向”,众多论者对卞之琳、何其芳所谓“轻视民歌”、提倡“新格律诗”的观点展开围攻。[13]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对卞之琳诗歌经历一个从“批判”到“遗忘”的过程。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指出卞之琳等汉园三诗人的诗歌讲究文字瑰丽,注重想象、感觉、暗示,表现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自沉于艺术美的情感,批评卞诗晦涩、难懂的形式特征以及消极、苦闷的人生态度。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同样批评卞诗感伤、忧郁、晦涩等“最触目的特点”。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7月版)、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 年7月版)、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8月版)、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现代文学组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4年4月版)、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1980年12月版)则只字未提卞之琳。
在50—70年代的中国,民歌与古典诗词的融合被视为新诗发展的新方向,像卞之琳这样有西方诗歌背景的诗人哪怕小心维护西方近现代诗歌艺术与“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努力都会受到严厉批判;此外,卞诗的“晦涩”、“多义”造成阅读接受上的困难以及不见容于主流诗歌规范也是导致卞之琳先被批判再被遗忘、淡出诗坛与文学史的重要原因。
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卞诗为人诟病的“晦涩”一转而为“智性”、“哲理”的正面论说,其丰富的内涵和高超的诗艺不断被批评家开掘阐释,卞之琳也由此前“资产阶级颓废诗人”而变为“智慧诗人”、“学者诗人”、“感觉诗人”。
这一时期卞之琳的诗歌价值最先在港台得到重新肯定。1980年2月,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2辑刊出“卞之琳专辑”,除卞之琳旧作新论还有张曼仪《“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试论卞之琳早期新诗(1930—1937)》、《卞之琳著译目录》和黄维梁《雕虫精品——卞之琳诗选析》。余光中对戴望舒批评甚多,而说卞之琳“绝对是一流的诗人”[14],香港版《雕虫纪历》封底对卞之琳评价甚高。港台地区对卞之琳诗歌的重新认识影响到大陆诗坛、学界,1981年第4期《诗探索》以《谈卞之琳的诗》为题重刊废名40年代北大讲义《谈新诗》中有关卞之琳部分,后记谈到:“此文既会有助于读者欣赏卞诗,也会有助于读者理解废名。这两位作家都是很有独创性的,也都是较难为多数读者理解的,特别是今日读者。”[15]预示着被埋没30多年的卞之琳及其诗歌重新浮出水面。
着眼于“新诗现代性”时代命题,探讨卞之琳诗歌融汇化合中西诗艺终成一家的独特创造,及其对中国新诗的贡献,是这一时期学者言说的重点。袁可嘉说卞之琳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推动新诗从早期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到达中国式现代主义。唐湜说卞之琳是新诗“五四”创始期到30年代成熟期、新月派到汉园一代的桥梁。两人都指出卞之琳在新诗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中国新诗重建自身艺术传统必然面临如何沟通、融汇中西诗歌艺术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实践显现出特有的价值,成为支撑这一美丽想象的重要支柱。唐祈说卞之琳吸收化合法国象征派诗歌、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与艺术凝成“诗的结晶”。[16]孙玉石说卞之琳达到“化古”与“化欧”的统一,是“沟通中西诗艺的寻梦者”。[17]两人均强调卞之琳“沟通中西诗艺”的独特贡献。
此外,卞之琳诗歌的“智性”与“哲思”特征也被反复论说。早在30年代,金克木将新诗分为“智的”、“情的”、“感觉的”3类,“智的诗”就是“以智慧为主脑”,是文学中的“僻路”,“如明珠之不可多得”,金克木没有提到卞之琳,但很有可能受到卞诗启发而作此论。“智慧诗”概念经常被用于对卞诗的论说,龙泉明认为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一系列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王泽龙将卞之琳的这种“新智慧诗”特征概括为感性与智性的融合、宇宙时空的艺术变奏和“非个人化”的艺术,卞诗的“智性之美”是理性美、想象美、意象美的融合。早期白话诗尝试说理但词浮意浅,卞诗融合智性与感情、哲思与诗美,成为中国新诗由主情到主智转变的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对卞之琳的处理也发生变化。唐弢主编、出版于70—80年代之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3卷本及其后的简编本难脱“政治—文学”一体化文学史观与阶级论述史模式,两书均未提及卞之琳。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脱去阶级论话语,从艺术层面剖析卞之琳所属“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象征、暗示、朦胧多义等审美特性。该著把《汉园集》诗人视为中西文学结合的新生一代,称卞之琳是一位对诗歌艺术“高度敏感而热情”、“最醉心于新诗技巧与形式的试验的艺术家”,强调他“化古”、“化欧”而形成的“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着意克制感情”、“追求思辨美”等独特风格。[18]10多年后该著修订本把卞之琳与戴望舒并列为现代派代表诗人,认为卞之琳对中国新诗做出两大贡献:一是“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及与之相连的“语言实验”,二是“诗的非个人化”及由此形成的“诗人主体的退出与模糊”。[19]此后的文学史对卞之琳诗歌的论述大都没有脱离“主智诗”或者“智慧诗”的定性。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卞之琳诗歌借鉴艾略特“思想知觉化”和“非个人化”倾向,并以《断章》为例证明卞之琳贡献了一种“情境的美学”。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也把卞之琳与戴望舒并称,以3页多篇幅评述卞诗,强调卞之琳在“知性与感性结合”基础上“开辟了以冷静的哲理思考为特征的现代智慧诗”。[20]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同样将卞之琳与戴望舒并提,也是以3页篇幅解析卞诗,概括其特点是“诗情的‘智性化’和‘非个人化’”,在卞之琳这里“诗歌不再是一种情感的体验和抒发,而是变成一种诗化的经验,一种情感的思想,一种智慧的结晶”。[21]
卞之琳曾谦虚地说:“我可以说是个小诗人,一个Minor Poet,我喜欢精雕细琢,可以说是雕虫小技吧,不管怎么成功也是Minor的。”[22]他的诗名与影响确实很有限,其诗歌独特品质造成的阅读阐释困难是首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时代政治、文学语境、诗学话语的沧桑巨变造成新诗“非连续性”发展。80多年的卞之琳诗歌阅读接受历史表明:中国新诗的品格、价值并不是自足生成的,而是由诗歌、诗人、读者、诗学话语、时代语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是意义生产与形态建构的过程。
[1]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A].新月诗选[C].上海:新月书店,1931:28—29.
[2]朱自清.三秋草[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1期,1933-05-22.
[3]朱自清.新诗杂话[M].上海:作家书屋,1947.
[4]刘西渭.咀华集[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5]李健吾.鱼目集[A].卞之琳.关于《鱼目集》[A].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A].卞之琳.关于“你”[A].以上收入:咀华集[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127—182.
[6]沈从文.《群鸦集》附记[J].创作月刊:创刊号,1931.
[7]李磊.《鱼目集》和《孤帆的诗》[A].洪球编.现代诗歌论文选:下册[C].上海:仿古书店,1936:683、687.
[8]阿垅.人生与诗[J].希望,1946(1).
[9]卞之琳.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J].文艺报,1949(4).
[10]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A].雕虫纪历:增订版[C].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11]徐迟.南水泉诗会发言[A].《诗刊》编辑部.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12]卞之琳.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A].《诗刊》编辑部.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201—202.
[13]参阅:宋垒.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A].萧殷.民歌应当是新诗发展的基础[A].卞之琳.分歧在哪里?[A].宋垒.分歧在这里[A].张永善.民歌在发展着[A].陈骢.关于向民歌学习的几点意见[A].李晓白.民歌体有无限制?[A].晏明.不要在空中建造楼阁[A].等文,《诗刊》编辑部.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14]余光中.新诗的赏析——“中文文学周”专题讲演[J].中报月刊:创刊号(香港),1980.
[15]冯健男.废名遗作《谈卞之琳的诗》后记[J].诗探索,1981(4).
[16]唐祈.卞之琳与现代主义诗歌[A].李青松主编.新诗界:第2卷[C].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76.
[17]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9.卞之琳:沟通中西诗艺的“寻梦者”[J].诗探索,2001(1—2).
[18]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56—357.
[1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7—368.
[20]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3.
[21]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80—82.
[22]古苍梧.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J].编译参考,1979 (1).
The Reading and Accepting Process about Bian Zhilin’s Poetry in Different Contexts ZHANG Wen-min
[责任编辑:舟舵]
I206.2
A
1001-0238(2016)02-0075-05
2016-01-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项目编号09BZW052)。
张文民(1976—),男,河南浚县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中国新诗传播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