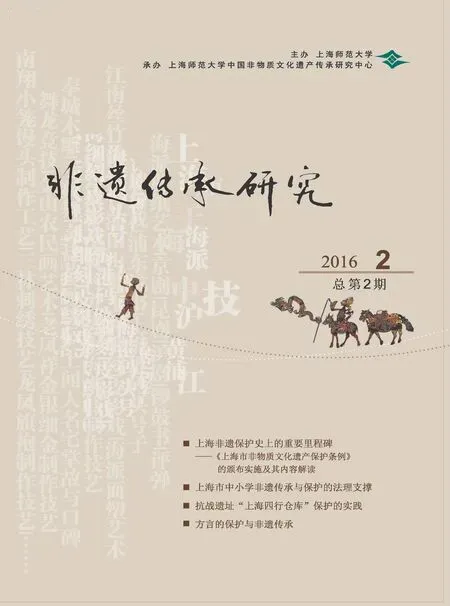吴宗锡与新中国评弹(上)
2016-02-02吴宗锡口述王其康毛信军整理
吴宗锡口述 王其康 毛信军整理
吴宗锡,诗人、作家、戏曲曲艺理论家。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曾任上海评弹团团长,中国曲协副主席,上海市曲协主席,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组长。日前,笔者就上海评弹团的前世今生,对吴宗锡老先生作了专访。以下是采访整理稿。
一、新中国评弹开拓者和建设者的由来
讲新中国评弹开拓者最早是原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唐家璇提出的。有一次唐家璇同志到上海评弹团一起吃饭时,邀请我参加,过去我从未与他碰过面。唐家璇同志向我敬酒时说:“你是评弹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我听了吓一跳,觉得评弹开拓者应是过去清朝的事情。我说不、不、不……。他补了一句:“你是新中国评弹开拓者和建设者。”
二、为什么能接受新中国评弹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讲法
我后来想了想,这个开拓者我是能接受的。讲到开拓者,有些情况可能大家不太了解。1949年前,我没有接触过评弹艺人。后来听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刘厚生同志讲,周恩来同志在国共和谈破裂离开上海前交代给上海地下党一个任务:派一些作风正派的同志到旧日的戏曲界去。像刘厚生搞话剧的,后来派到越剧界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文委也就是上海地下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上海当时地下党搞文艺工作的同志,到戏曲界去。当时的看法是北方南下干部不一定了解上海的戏曲界,上海的同志进去后工作比较方便。当时我在地下党是搞文艺的,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找我谈,要我转为搞戏曲。找我谈的地方是现在的静安公园,当时是静安外国公墓。那时地下党碰头,要么找非常热闹的地方,要么找非常冷静的地方。那时的外国公墓谁都能走进去的,但是没有人进去的。约我在公墓里面一边散步一边谈,希望我去搞戏曲。当时我不大愿意,因为那时看不起戏曲,总觉得沪剧、越剧要比文艺界低一些。但这是党的任务,只好接受。接受后,刘厚生同志来联系我们这批人,我与另外三位同志成立了一个小组,讨论如何去搞地方戏曲。要开始分工了,我当时不愿去搞沪剧、越剧,那时还有维扬戏。我想我是苏州人,而评弹比其它戏曲文学性要强一些,比较高雅一些,还是去搞评弹吧。所以,我主动提出来,我去搞评弹。其他同志就分工搞沪剧、滑稽戏等。1949年初,上级就确定了我去搞评弹。这个阶段一直到上海解放,除去地下党给我的其它任务,包括发信要求文艺界人士留在上海等工作之外,我就是对评弹进行调查研究。那时候去跑书场、收集资料,包括评弹的报纸、书场阵容表,演员不认识,我就通过评弹小报的一个作者去认识评弹演员。1949年初,我就开始接触评弹了,所以可以说我是开拓者。
三、1949年5月28日首次接触评弹界人士
我接触评弹人士是哪一天?上海市是5月25日南部地区解放,5月27日全市解放。5月28日,我代表领导去参加上海演艺协会评弹分会在泥城桥大中华大陆电台做的特别节目。这个特别节目宣传解放军进城,老百姓欢迎,解放军是不扰民的,以稳定人心。所以上海一解放,第二天电台就有特别节目,有戏曲、评弹、滑稽戏等。那时,评弹在电台做特别节目很多,因为评弹主要是听的,电台都有评弹节目。5月28日上午,我就到大中华大陆电台,电台有地下党同志来组织和安排节目。我带了些宣传材料去,那时我是不大听评弹的,也不知写出来的东西是否像评弹,总的都是一些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扰民,解放军是为人民的等。我记得来的评弹演员很多,都比较有名。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个见到的是赵稼秋。那时我是没有单位的,就说我是上面派下来的,要你们宣传,他们也心照不宣,你是上面派下来的,是代表共产党来的。随后我就把开篇给赵稼秋,说你们可以唱吗?赵稼秋善于唱白话开篇,连说“好唱,好唱,我好唱”。所以,我接触评弹演员是上海解放第二天的5月28日。自此之后,地下党通知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报到,以后就到军管会文艺处,作为军管会文艺处的干部。我原来搞评弹就仍然搞评弹。
四、初期怎样开展评弹工作
那时的工作倒不是领导与被领导,跑进去是联络、交朋友、去组织他们学习等工作。我后来就到现在的寿宁路民生里评弹协会去了。著名评话演员金声伯最近还讲起过我去报到的情景。他说,你进来时(那时有一个工会干部陪我进去),你们两人年纪很轻,穿了套西装。金声伯那时17岁,坐在门口,他说看见你们进来的。开始工作还是照地下党联系群众的办法,一是联系年纪轻的,当时认为年纪轻的比较好,思想进步;还有是发现比较正派、积极的一些演员。所以最早我联系的、把他选择作为骨干的是潘伯英,后来他到苏州评弹团去了。接着还组织所有演员学习,那时主要是学习“工人读本”。那时没有什么学习材料,“工人读本”是比较浅显的,里面讲劳动创造世界等内容。当时帮助他们成立了许多小组,妇女有妇女组,年纪轻的叫青年组。有人对我说响档他们喜欢睡懒觉,不大肯来,每个星期有一次在南京路成都路有个叫大观园的地方,那儿是个商场,有个可喝喝茶、布置得蛮好的地方,那些响档在那里唱京戏,每周有一天像票友那样,学唱京戏。你这时候去,就能见到这些响档。于是,我就找了个时间去大观园,到了后也不去打扰他们唱京戏,唱好京戏再请他们坐下来学习。后来就比较正规了,妇女组摆在沧州书场,我就去和他们一起学习,那时就这样领导的。潘伯英也有个小组,他们在福建路汇泉楼。潘伯英与我关系比较好,向我表示拥护共产党。我觉得他人比较热情,也比较正派。他对我说,我们组织一个小组在汇泉楼,你可以过来。我就去了。那时汇泉楼有朱慧珍、唐耿良等人,与潘伯英一个圈子的。那时我一是组织他们学习,二是推动他们说新书。那时认为评弹是旧的封建文艺,要改造。我就与潘伯英商量着要说新书。有这么多艺人,这么多拼档,你叫他们说新书,他们又没有新书。这时潘伯英出的点子,我们来组织一出书戏。书戏是化装上台的,可以把上海比较有名的艺人全部都包括在内。那么说什么内容呢?研究下来决定说新书《小二黑结婚》,是从解放区来的。于是,由潘伯英执笔,写了《小二黑结婚》这出书戏。演出在南京大戏院(后改为上海音乐厅)进行,演出的剧照资料评弹团内应该还有保存,评弹词典上也有一张剧照。蒋月泉演小二黑。那时最红的是范雪君,她演小芹。刘天韵、朱耀祥、张鉴庭、张鸿声等当时在上海的(严雪亭当时不在上海,有些人出去了)全部都上台了。当时的影响是蛮大的。这等于全体评弹响档亮相,表示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是要说新书的,就像是个宣言似的。这大概是1949年6、7月份的事。接下来再联系他们,推动他们学习,这的确是新中国评弹的开拓工作。
五、从创建评弹改进协会到领导上海曲艺家协会
在国民党时期有一个评弹界协会,到解放后全部要接受改造,我帮助他们筹建了评弹改进协会。开会就在军管会文艺处大礼堂,就在同孚路(现石门一路),现在的民立中学隔壁。后来因为评弹属于曲艺,中央成立曲艺协会,上海就成立了分会。当时分会主席是刘天韵,我是副主席兼秘书长,实际上分会是我筹备开始的。到1979、1980年“文革”后,分会都改成协会了,开始叫曲艺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曲艺家协会。这些协会的成立都是我经手的。后来上海评弹团党支部实际上是领导上海评弹界的。我也做了很多评弹界的工作,评弹团当时认为我们是整个上海评弹界的核心,上海评弹界归我们支部领导。我们搞过中青年演员培训班,很多工作都是由评弹团出面。所以,现在评弹界一些年岁老一点的演员都和我关系很好。
六、评弹团成立和赴治淮工地
我最早是写诗歌的,那时要题个笔名,我父亲启发我,他说用“弦”。诗歌古时叫“弦诵”,后来我题了个笔名叫“左弦”,左当时表示进步、革命,所以我是革命的诗人。后来我搞评弹了,有人问你是否早就搞评弹了,笔名中用“弦”字。其实不是的,但很奇怪,我像是命中注定要搞评弹工作的。“文革”后一次开会时,见到读大学时的一位教授对我说,我们大学里没有“评弹”这一课程,你怎么会搞“评弹”的。后来军管会文艺处改成上海市文化局,我在文化局文艺处工作,联系评弹少了。有一段时间我在编审科工作,管戏曲剧本,联系戏曲编剧和导演,与评弹的联系比较少,所以成立评弹团时,派的干部不是我,是一个叫何慢的同志兼的,他是创作室主任。实际上他也没有去评弹团。团长是演员刘天韵。所以有人讲我是第一任团长,其实是讹传。但是事情也是蛮巧的,那一年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要派知识分子干部去参加土改,我原来是被派去参加四川土改的,后来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治淮委员会说上海文艺界应该派些人去参加治淮工作,这也是接触工农改造思想的好机会。所以1951年下半年就派我去参加文联的治淮工作队。文联治淮工作队有三个队长,一个叫杨村彬,话剧编导,写《清宫外史》的。还有一个是搞音乐的司徒汉,再有一个就是我。三个人中司徒汉是搞音乐的,他管美术、音乐、新文艺界,一个是管话剧,我当时分管戏曲,那时有很多戏曲编剧和导演。这时正好成立了评弹团。评弹团成立第二天,领导就决定评弹团也去参加治淮学习。这一决定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好的。过去评弹艺人都是单干从未参加过集体生活,下去参加治淮接触工农,为评弹团打下了很坚实的思想基础。评弹团11月20日成立,上面决定第二天就参加治淮学习,11月23日就参加治淮工作队,我们一起出发,由我分管领导评弹团。所以评弹团成立我没有参加,但实际上评弹团成立第二天起,我就带他们这个团了,一起到治淮工地去了三个月又二十多天。这时与评弹演员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原来与他们熟悉的,现在又进一步联系和熟悉了。那时的生活比较艰苦,与民工及团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治淮工地回来,当时上海在搞三反、五反运动,我被调到戏改整风领导小组。
七、被派往上海评弹团工作
1952年3月从治淮工地回来后,5月份上级领导考虑到评弹团当时没有驻团干部,原来的何慢是兼任的,但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记得有一次与刘厚生一起吃饭时讲起这件事,当时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因为那时在机关里工作,每天上班下班较枯燥。到评弹团去,可出去巡回演出,到外面跑跑。我对刘厚生同志说,评弹团要人,我去吧。就这样,组织决定派我去评弹团了。那时的评弹团团长是艺人刘天韵,驻会的干部也不能叫党代表,叫政委好像又太高了,所以最早叫教导员。起初我是教导员,刘天韵是团长。后来觉得艺人当团长,分散他的精力,他还是搞艺术比较好,所以后来是我做团长。我不是评弹团第一任团长,但评弹团干部当团长,我是第一个。
八、年轻人怎样当评弹团团长
我到评弹团28岁,上海解放时我25岁,当时评弹演员年龄都在35岁以上,年纪较大的都是40好几岁了。我28岁,大学毕业,其它社会经历不多,后来做军管会干部。而他们年龄比我大,甚至要大一倍,都是社会经历丰富的。以前讲起来叫跑江湖,评弹艺人比一般跑江湖层次要高一些,但实际上也是在江湖上生活的。我与他们有一个极大的反差,我年纪很轻就进去了,所以后来陈云同志说,他们是五颜六色都见过的,鉴貌辨色的。陈云同志说,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我那时去评弹团也有点糊里糊涂,没有觉得一点怕。而且在治淮时与他们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些评弹演员待我都比较好,当然后来也有各种矛盾和意见,但他们总有个思想你是党派来的,是与我们一起为搞好评弹来的。所以就这样来到评弹团,一直干到1984年,搞了三十几年。
九、五四新文化对旧文艺的改造
我觉得当时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派我们地下党一些懂文艺的同志去文艺界,与一般派个行政干部去不一样。解放后,党的方针政策是要为人民服务、推陈出新。说我是新中国评弹的开拓者和建设者,那么什么是新中国的评弹呢?我总结了两条,一条是演员懂得了为人民服务,当然也是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旧中国的演员是为自己个人名利、为生活、为衣食。新中国的评弹艺人,就是要懂得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国家剧团、人民评弹团。第二条是对书目要推陈出新,进行整旧和创新。老的书目中工农大众做主人翁是没有的,都是太太小姐老爷少爷。新社会既有整旧,也有创新,有了以工农大众为主人翁的新书目。我现在想一想,当初我们进入戏曲界,也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搞评弹团,要改人、改书、改戏,要推陈出新,评弹团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实验示范。实验是在书目中、艺术上要创新实践。示范就是要推动其他团,带动其他团。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做到了。比如说,评弹团搞中篇。现在有人讲以中篇为主是不对的,评弹应该演长篇。其实评弹团从未讲过以中篇为主,但是评弹团创作出中篇适应了当时人民的需要,现在群众仍然蛮欢迎中篇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一公演,听众反应极其强烈,而且吸引了新的听众。于是,整个评弹界成立了八九个小组都演中篇。中篇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示了范,结果推广出去了。所以上海曲协副主席周介安讲我是根据党的战略要求,用五四新文化和党的文艺政策来推动评弹的传承和创新。所以说建设者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
十、与评弹演员的关系
一个搞新文艺的青年,结果打入当时所谓的旧艺人里面去,且一些当时还是响档。这是因为当时我是党员的身份,他们比较尊重。此外,我也的确是虚心向他们学习的。后来到团里工作也有好处,与他们完全打成一片。很多演员对我有非常感人的事情,甚至于我不在评弹团后也这样。去年我90岁,他们一批演员要为我祝寿,一道吃顿饭。我说倘然一般人请我过90岁生日,我是会拒绝的。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不是为了奉承拍马,而真正是一种感情,一份情意,这份情意我要领的。结果大家买了蛋糕,还为我唱了生日歌,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人与人的感情,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的感情是建立在评弹基础上的。他们觉得我对评弹艺术是一心一意的,是在帮助他们搞评弹艺术。
十一、进行评弹艺术的研究
我搞评弹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到评弹团后,当时觉得评弹要宣传,要让更多的人喜欢评弹。所以写了《怎样欣赏评弹》等,目的是要让更多听众理解评弹,不是要做什么理论家。后来文化大革命把评弹说得一文不值。当时我想,评弹不好,怎么能吸引这么多的听众。我就想评弹为什么这么美,到再后来想许多老艺人的经验,包括我的经验能够对下一代演员的创作演出作些参考。所以,我就写了这些东西。我觉得理论一定要从实践出来的。我到了评弹团,开始改编了几出短篇,就是按毛主席说的若要知道梨子是啥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不会唱,我唱出来不入调,但我会写,我开始学着创作。后来做了艺术指导,帮助他们改进艺术。我觉得真正的理论必须来自实践,是实践经验的提升。当然,这个实践不是我一个人的实践,是与演员们共同的艺术实践、创作实践。所以,周介安同志说:“整旧的过程是吴宗锡所代表的新文艺思想对传统评弹艺术实行渗透的过程,是令评弹艺术清新化、去俗化、趋雅化的过程,是上海评弹团整体风格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吴宗锡本人也在整旧的过程中对评弹的艺术规律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和把握。”我是接受的。
有关上海评弹团的群体风格,文艺戏剧理论家沈鸿鑫等同志也是肯定我的。也有人现在提出来,这是“左”的东西。怎么可以有“群体风格”,“个人风格”发挥怎么会有“群体风格”,这是他们没有理解。过去,上海评弹团跑出去无论到码头演出或书场演出,老听客都讲他们听得出这是上海评弹团,那不是上海评弹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追求一个艺术的格调,艺术的品味,而且在台上不滥放噱头、不庸俗化,这就是上海评弹团的风格。这些艺人有自己的风格,像蒋月泉有蒋月泉的风格,张鉴庭有张鉴庭的风格,杨振雄有杨振雄的风格,严雪亭有严雪亭的风格,不是把他们抹杀了,而是在他们的个性中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追求艺术不要庸俗,要高雅,也就是艺术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在台上我要卖噱头吸引听客。所以,这就是群体风格。这个群体风格不是很容易培养出来的,是大家在实践中互相切磋,互相展开批评,逐步达到的。
十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评弹大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有人说:“你做团长时我们要听评弹,你现在不做团长了,我们评弹也不听了。”这当然是说笑话。但是我讲这不是吴宗锡的功劳,主要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来讲,最主要是新中国。地利是上海的环境。人和当然有很多的好演员。对评弹的发展,有人讲评弹发源地是苏州,发祥地是上海。这种说法可能与评弹的两次繁荣有关。一次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如果不到上海来,评弹不会有这样的兴旺。那时好多艺人来到上海,一个是上海有许多唱片公司和电台,那时上海有五十多家电台,没有一家电台没有评弹节目。还有一个是海派的艺术环境,评弹很善于吸收,吸收了很多戏曲甚至电影的精华,蒋月泉曾说他的唱还是学的平克劳斯贝的发声。现在说起来是吸收了戏曲的先进一面,包括各种文艺。如果不是新中国,不是在上海,不是上海评弹团,就不会有今天的评弹,这是第二次繁荣。所以我讲是天时地利人和。我看到一些资料,评弹刚进上海时,上海没有评弹听众。因为上海人说浦东话,不习惯听评弹。评弹进上海,是与滑稽、杂技等节目放在一起演的。所以说对听众一个是要适应,一个是要培养,再有一个是要争取。起初评弹在上海是没有人要听的,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评弹听众多得不得了。解放以后,也是顺应了时代,发展了评弹。既是培养了听众,又是争取了听众,也是适应了听众。这个适应包括像在交易所等工作的每天来听的老听众,但新听众没有时间每天来听,对这部分听众他如不听中篇,他更没有时间听长篇。后来我们到北京去演晚会,都是一段一段的书,人家要来听。一段一段的都是精品。所以说,我们不是一定要搞中篇,不搞长篇。长篇也搞的,在一般老的书场内照样说长篇。但是没有中篇,就没有这么多新听众,包括现在的一些六七十岁的干部,当时的中学生、大学生欢喜听评弹,就是我们顺应了听众,适应了听众要求,所以评弹得以兴旺。评弹最早的书场都是茶楼书场,如上海城隍庙的茶楼书场,是茶馆店改的。到解放后是舞厅书场,舞厅都改成书场,可以容纳一二千人。那时的西藏书场,最早叫米高梅舞厅。还有新成书场、大沪书场等都是千把人的。一直到评弹进入到文化广场,我看到有资料讲一共演了13场。现在讲评弹团到文化广场似乎是轻而易举的,六七千人的座位客满,都是外面排队买票的,且上台演出时下面凝神静听。这样六七千人的一个文化广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应该讲是评弹的一种兴旺。这是评弹艺术适应了上海的听众,上海听众需要这样的艺术,而且很多听众是我们培养的,我们培养了一批我要听评弹、我愿意听评弹的听众。所以说没有上海就没有上海评弹团,没有上海评弹团也就没有中篇等形式。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共同结晶。最近上海评弹团演了一出中篇《林徽因》,听说票买到五场了。我们那时演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那时叫“放票板”的,开始想能演五天就蛮好了。到第五天,还有不少人来买票,于是再放。包括后来的中篇《王孝和》,我记得我有一本台历,在上面记数字的,票务组每隔两天要对我讲,现在卖掉多少了,数字不断地增长。有几出中篇卖了三个多月。最长的一出中篇是《芦苇青青》,那时是“四清”期间,许多演员下乡了,不是主要演员演的,演了七八个月。我们的演出在艺术上适应了这些没有时间每天来听的听众,反过来听众也支持了评弹的许多改革。所以说不是不要长篇,而是有许多新的东西是适应了时代,得到了听众的支持。我觉得艺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深入群众,还要跟上时代。
十三、搞评弹的人必须懂文学、戏剧和音乐
我再补充一点我的认识:评弹有文学性、音乐性、戏剧性;搞评弹必须要懂文学、懂戏剧和懂音乐。一般的行政人员和懂文艺的人看似是一样的,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