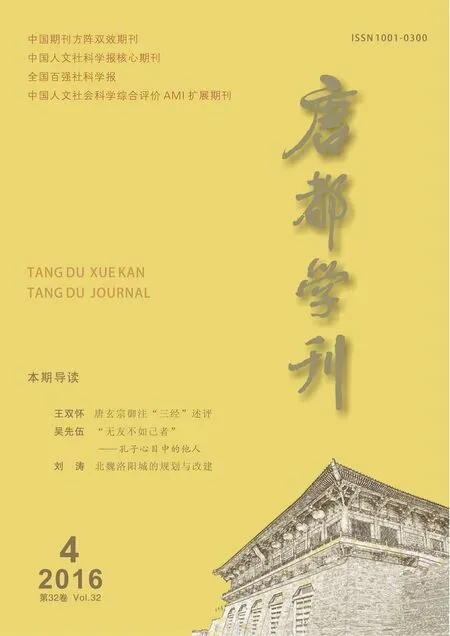《冷山》的深层生态解读
2016-02-02付小兰
付小兰,夏 喆
(空军工程大学 理学院,西安 710051)
【文学艺术研究】
《冷山》的深层生态解读
付小兰,夏喆
(空军工程大学 理学院,西安710051)
查尔斯·弗雷泽在作品《冷山》中,以逃兵英曼艰辛漫长的回家之路为明线,描绘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同时又以艾达与鲁比相互帮助,在农场中求生存的故事为暗线,深刻地表现了人与土地的交融共生关系。从深层生态学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在探索作者渴望人类融入自然、返璞归真,实现人性“归化”的生态追求之外,呼吁人类学习印第安先民朴素的生态智慧,以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查尔斯·弗雷泽;《冷山》;深层生态思想;印第安人
夏喆,男,陕西西安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军事文学研究。
《冷山》是美国作家查尔斯·弗雷泽的处女作,该书于1997出版后便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在当年以“描写了人与土地复杂感情与关系”[1]341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次年又成为全美十大畅销书之一。各大报纸杂志、知名作家更是不吝溢美之词,《纽约图书评论》评论其为“一部绝佳的小说,令人惊异”[1]1,《华盛顿邮报》赞誉其为“一本令人激动的小说”[1]1,两届“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得主里克·巴斯则认为它“是美国文学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1]2。小说中,作者以诗意般细腻的笔触,以双线式的叙事结构,穿插讲述了内战末年,身负重伤的南方士兵英曼逃离战场,历尽千难万险,回归家园冷山,与爱人艾达团聚的传奇,以及艾达·门罗在孤女鲁比的帮助下辛苦劳作,等待心上人归来的故事。
深层生态学作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其概念最早由挪威哲学家伦·奈斯1972年在《浅与深——长期的生态运动》一文中提出。作为一种生态智慧,深层生态学要求深入到人类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的价值体制进行根本改造,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积弊,并最终建立一种无等级差别的和谐生态文明。因此,深层生态学的“目的不是为我们现存社会的轻微改变,而是对我们整个文明的根本性转向”[2]。为了寻找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及工具理性价值观的精神资源,深层生态学者们转而将目光投向土著文化、东方文化等一切被西方现代文明边缘化的传统文明,如印第安人生态智慧、东方佛教文化等,而这些正是深层生态学智慧的直接思想来源。弗雷泽在《冷山》中并未过多着墨于战争,而是通过对战争中生态、人性危机的描绘来表现其反战主题与生态追求,因而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深层生态思想。正因如此,弗雷泽在小说的卷首特别引用了中国唐代著名隐逸诗僧寒山的诗句:“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1]3,不仅暗含了自己对田园生活的追求,使全书带上了东方禅宗的意境和生态观,更表达了对战争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不再的失落无奈与对战争血腥暴力的强烈批判。
在人类文明的畸形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枯竭日益加剧的今天,品读弗雷泽的《冷山》,领悟小说中的生态智慧,对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关系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作家的深层生态思想来源
弗雷泽成长于北卡罗来纳州山区,即小说中冷山的所在地。儿时的山区生活赋予了弗雷泽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也使他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与依赖。成人后,他依旧憧憬着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渴望着在原始自然之美中“诗意的栖息”*“诗意的栖息”: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其著作《环境伦理学》中将生态伦理最后归结于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息,即心怀热爱与感激之情地去融入自然,将个人的生命融合进自然整体之中。。然而,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他却目睹着青山绿水被钢筋水泥所替代,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在灯红酒绿中纸醉金迷、在利益驱使下变得谄媚贪婪。虽然这些都使人们获得了短暂的感官愉悦和满足,但是信仰的缺失、心灵的空虚与道德的沦丧却弥漫于整个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愈发疏远和对立。面对着令人失望的现实,作者怀着对自然原始之美的热爱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向往,毅然决然地带着全家人离开城市,回到故乡,回归自然,从此以牧马为娱,以写作为生,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作者的家乡风景独特,一直以来都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印第安人按照古老的方式生存繁衍、生产生活,虽然土地贫瘠,但仍过着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弗雷泽从家人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个从高祖父起就世代相传的故事:一个叫英曼的逃兵在内战中拖着受伤的身体踏上漫漫回家路,最终却惨遭民兵枪杀。为记录下这个奥德赛式的伤感回乡之旅和当年家乡的风土人情,作者亲自上山去寻找英曼及其他遇害者的坟墓,并重温了英曼当年走过的艰辛历程。小说中,作者把目光聚焦在原始的自然之美,追忆那个时代朴素、天然的生活方式,怀念人与人之间的纯真善良;在批判人类社会文明中的积弊与血腥的战争对自然与人性的摧残和破坏、在表达对先民生活方式逐渐消逝的遗憾的同时,也抒发了他对人类回归本性、融入自然,共同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生态追求以及对人类如何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诗意的栖息”的深刻思考,而这正是对深层生态学思想的思考与回应。
二、《冷山》中的深层生态思想
(一)人类精神的“异化”
人类因为贪婪而发动战争,参战者以主宰者的姿态,在疯狂蹂躏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之时,也给卷入其中的人们带来无尽的苦难。小说中,弗雷泽多次将镜头聚焦至战争摧残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支离破碎关系的现状:环境受到污染,原本和谐美丽的自然家园不复存在,野战医院外一片灰蒙的天空、充斥着泡沫垃圾的污浊河流——“这条宽阔的水沟,只是大地上的一条污渍……堆满了泡沫的黄色垃圾……和茅坑一般肮脏”[1]63,被焚毁后房屋的断壁残垣等。战争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更导致了人类巨大的精神危机,它激发了人类内心潜藏已久的征服欲,使人失去了理智与人性,成为一台台冷血的杀人机器;它侵蚀着人的精神,泯灭着人的善良,扭曲着人的精神,迫使卷入其中的人们终日被血腥与死亡围困。小说中多次出现了描绘战场上惨烈场面的情节,如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北军一整天都在进攻,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但仍旧前赴后继,“北军尸横遍野,到处是一堆堆血肉模糊的尸体”[1]8;受伤的士兵也未能幸免一死,被排列整齐,一锤一个砸死;即便是号称正义之师的北军,也因吃了败仗而气急败坏,到处烧杀抢掠,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战争中的征服与统治行为,会使人获得暂时的感官刺激与欲望满足,但却加剧了人类精神生态的“异化”,强化了人对人、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欲,导致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被割裂,人身心的内在自然与作为生存家园的外部世界被隔绝,使人类丧失对信仰和对生命的敬意,从而带来最终的结果:人类与自然在文明发展道路上愈加疏远并逐步走向对立。
(二)人类精神的“归化”
“只有实现了价值观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向,才能有效解决生态危机。”[3]人类的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圈的最高组成部分,因此,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协调一致才是生态和谐的理想境界。弗雷泽敏锐地觉察出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化”,因此,他强烈渴望将人类文明中的积弊进行彻底清理,使人类精神生态得到新生,实现内心世界自然回归,重返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人类精神世界的“归化”。
1.回归荒野
在深层生态学学者们看来,荒野是生命的源头,也是人们找回在文明劣根中丧失的自我的场所,只有在荒野中,人类才能恢复真正的自我。弗雷泽将英曼的回家之旅描绘为他心灵的救赎之路:厌倦了冷酷的杀戮与毁灭后的英曼逐渐从最初对战争的盲目狂热中清醒过来,怀着对心上人无尽的眷恋,最终选择逃离战场,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重返家园之旅。他的返乡之旅凶险异常,危机四伏,他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在忍受着饥饿、病痛的折磨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山林猛兽的袭击、民兵的屠杀、同伴的背叛与恶霸的迫害。因此,他本能地渴望在大自然中,在心上人浓烈的爱里寻求庇护,获得慰藉。对记忆中冷山上自然之美的眷恋和与艾达未来生活的憧憬,成为了他苦难返乡路上唯一的心灵寄托与精神家园。“凭记忆勾画家乡熟悉的绿色田野。……生长着水晶兰的潮湿的小河岸,……聆听牛蹄踩踏尘土发出的噗噗声,直至消失在蝈蝈儿和青蛙的叫声里。”[1]2英曼向往着冷山上的一切,憧憬着与家乡的自然美景融为一体。深层生态运动最终要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它的任务是“把人类文明重新放置于自然的母体中”[4]37,使人类重获内心世界、文明观念与外在生态韵律的和谐统一。而正是这种渴望回归自然的和谐之光在抚慰着英曼的心灵创伤,减轻其精神折磨的同时,也让他始终保持着人性的善良。
回归荒野、融入自然使英曼在其心灵救赎之路上得到重生,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生态则与艾达和鲁比的生存息息相关:她们在森林里打猎;在农场中养殖牲口;在周边的田地上耕耘,“田垅上的卷心菜、萝卜、芥蓝菜和洋葱还很稚嫩,艾达和鲁比在给他们锄草,这些就是他们过冬的主要蔬菜了。几个星期前,她们开始精心准备,先用犁耕一遍,然后用炉灰和牲口粪施肥。”[1]101艾达和鲁比在农场中生产生存,依靠自然所赐予的生活所需免遭饥饿与寒冷。在这里,人与自然合二为一;人与土地浑然一体;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睦融洽。虽然艾达拥有农场,但她和鲁比之间并没有主仆关系,她们彼此尊重、相互关爱、同甘共苦,像姐妹一般亲密。鲁比教会艾达认识土地,获得求生技能;艾达也会在闲暇时为鲁比阅读小说,丰富她的精神生活。同时,土地上收获的一切也使她们有能力去给予更多身处困境中的人无私帮助。
2.返璞归真与“自我实现”
与很多生态作家一样,儿童承载着弗雷泽对人类善良本性的赞美,依托着自己所追求的和谐生态世界。儿童形象以及儿童的视角,既是作家追忆逝去的美好童年的生动文学再现,更具有深刻的生态隐喻及内涵。
小说中的二号女主角鲁比,从小就被毫无责任心、懒散无能的父亲抛弃,整日处于“放养”的状态。“在野外觅食,挖掘草根,用柳枝编网捕鱼,并用类似的方法捕捉飞鸟。”[1]267特别是一天夜里,小鲁比被困在森林里,起初,她对周围陌生的一切都充满了惶恐,然而,渐渐的,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在自然之美的感召下,她感受到了温暖与慰藉,变得不再恐惧。而且从那以后,她在大自然中“能知道别人永远不知道的东西”[1]81。作家笔下的小鲁比向往自然、热爱自然、亲近自然,更沉醉于其中,沉醉于细腻地聆听自然万物的声音,敏锐地感知生态野性之美。孩子保有着人类最本能的纯真善良,这也赋予了其与大自然超验沟通的能力,他们能用感官与心灵体验自然,避免了用理性来分隔自然。而这正是鲁比能够敏锐地洞察自然界的规律,获得人类最原始的宝贵生存技能的原因。弗雷泽通过对鲁比童年时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描绘,以儿童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呼唤人类天性复归的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
童年时期的鲁比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也传递了奈斯深层生态学的智慧——“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论,它是深层生态理论的基点,也是深层生态运动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实现途径为“通过自我与多样丰富的生命世界的认同,从而超越人类个体小我的局限性,在广博的生命世界融合的过程中获得个体生命的拓展和心灵世界的超越”[4]14。在奈斯看来,“自我实现”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范畴,达到了人与生态中所有存在物的认同,因此“自我”应是大写的(Self)。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人类需要“自身内在潜能的激发”[5]18。小鲁比那晚在荒野中富于神秘色彩的“顿悟”经历,激活了她在生态中“自我实现”的潜能,使小鲁比对自我与广袤自然中一切存在物的认同范围不断扩大与加深,对它们的恐惧感与疏离感逐渐缩小,最终达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5]31的“自我实现”心理状态与精神境界。在奈斯看来,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自我实现”。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鲁比在面对被传统定义为邪恶与死亡象征的乌鸦时,却对其有着特别的亲近与崇拜之感。作为艾达的精神导师和最好的朋友,鲁比在帮助她恢复农场生产,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也使她逐渐认识了土地,融入了自然,获得了感悟自然之美的能力:“逐渐地她开始感觉到不可计数的细小生命在忙碌着,从一簇簇的花冠……他们对能量的积聚是生命善良的律动。”[1]106因此,鲁比在小说中也扮演着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生态意识的角色。
(三)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
弗雷泽描写了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生活方式。生态思想家克里考特指出:“在生态文学思想普及和环境危机的意识深入人心的时代,传统的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成为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我们失去了但还没有忘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6]在生态方面,美国印第安文化近乎“成熟”,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他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遵从自然的规律进行生产生活,仅向自然索取自己的基本生活所需。这正是今天深层生态学学者们所追求的,他们渴望从这些原著居民那里汲取营养,获得智慧。
1.生态中心主义
印第安人将自己视为生态之网中的一部分,这种朴素原始的自然观为与自然矛盾越发尖锐的人类和被人类中心主义支配许久的西方文明指明了一条自我拯救之路。正因如此,奈斯在其深层生态学思想中将印第安人朴素的自然观作为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理论来源。在《西雅图宣言》中,印第安人向世界宣告了他们传统的生态中心自然观:“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7]印第安人从未将自己放置于自然界的中心位置,认为自己有优于其他物种的任何特权。在他们看来,自然生态中的一切都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万物互相联系,互相连结,彼此平等,统一于一个和谐整体之中。他们认为尽管杀生是必须的,因为人类的生存需要食物,但是人类必须要尊重动物的生命,对其心存感激之情。这一思想可以从一位印第安老妇人杀羊的情节中看出:“老女人继续挠着它的下巴,抚摸它的耳朵……一眨眼便深深地割开了山羊额下的动脉……她继续挠着它的毛,抚弄它的耳朵。羊和女人都凝神看着远方。”[1]208老妇人杀羊的过程平静而详和,更像是一场神圣的宗教仪式,表现出了印第安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尊重。这也是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Land Ethic)中所追求的重要生态思想之一,“大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8]。而与印第安人对生命的敬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暴虐的民兵在抢夺了寡妇家的牲口后,却进行了一场屠杀,“他们必然要饱餐一顿,哪怕把那头猪的腿生生割下来……拧断两只鸡的脖子,拔掉鸡毛,掏出内脏”[1]244。在战争摧残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征服、杀戮的邪恶观念再度占据了人类心灵。他们疯狂地藐视,践踏着自然,以征服者的姿态高唱凯歌,残暴地宰杀生灵,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狂妄。弗雷泽渴望人类向古老的先民学习,恢复对自然界中一切生命的敬畏之心,并与其休戚与共,以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和谐关系。
2.尊重自然,简单生活
印第安人的作息方式并不像所谓的文明人认为的那样是野蛮和愚昧的。相反,印第安人创造了一种和谐美好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也拥有了人类宝贵而深远的生态思想。他们的劳作仅仅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他们自由地生活,拥有心灵的安宁祥和与精神世界的丰富完整。小说中,那位印第安妇人住在简陋的帐篷里,饿了,就吃自然赐予的食物;渴了,就喝饲养的羊奶;病了,就用山上的草药。即便是将要死亡,她也希望重新归入自然,“往石崖上一躺,让渡鸦把她的尸体啄碎,带着她飞向远方”[1]207。同样,鲁比在帮助艾达经营农场时,也始终沿袭着印第安人的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一切事情——给篱笆打桩、做泡菜、杀猪——都得听从天意的指示”[1]102。“很少有她想要,而自己又不能制造,种植或在山上找到的。”[1]189鲁比所遵从的这种天然生产与生活的方式加深了人类对土地与自然万物的依赖,并且以生存需要为指向的物物交换将生产从金钱利益的铁链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关系,更促进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危机日趋严峻的今天,深层生态学学者们更加确信,把人类的物质需求限制在生态的可承受范围内,并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是人类应尽的责任。人类对物质的强烈追求是以内在自然的极度萎缩,自然资源的加速耗尽为代价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将物质享受的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要求人类重新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混沌状态。“我们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拆除高楼而重新搬到山洞里去住,抛弃钟表而重新滴漏计时,销毁电脑而重新结绳记事。”[4]78朴素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回归,一种生态思维模式的回归:像那些原著居民一样,不再热衷于物质需求的满足,日益关爱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树立人类应有的生态责任意识。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弗雷泽亦将艾达与英曼这对患难情侣的重逢设定在了印第安人的古村落,暗示着只有人类融入自然,简单生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时,才会得到幸福。
三、结语
弗雷泽在《冷山》中展示了自己渴望人类融入自然、返璞归真,实现人类精神“归化”的生态追求,呼吁人类向古老的先民学习,尊重自然,简单生活,与万物休戚与共。然而,由于长期深植于人类内心的征服、占有的劣根,人类要真正实现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很漫长的一段“奥德赛”之路要走。正因如此,弗雷泽并未给小说设置一个圆满的结局:英曼在与民兵枪战时,对一位男孩心怀怜悯却最终惨遭其杀害,这也呼应了作品的卷首语——“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1]3。
[1]查尔斯·弗雷泽.冷山[M].周玉军,潘源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4.
[2]Eric Katz,Andrew Light,and David Rothenberg.Beneath the surface[M].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5:8.
[3]Berry T.The Viable Human[G]∥ in G.Sessions,eds.,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5:18.
[4]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雷毅.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6]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203.
[7]Lisa M.Benton,John R.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 Reader[M].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12-13.
[8]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慧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2.
[责任编辑张敏]
Interpretation of Cold Mountain
FU Xiao-lan, XIA Zhe
(CollegeofScience,AirForceEngineeringUniversity,Xi’an710051,China)
ColdMountain, written by Charles Frazier, is about Inman’s long and hard walk home as an army deserter, describes the ravages of the war to human nature and natural ecology. Besides, the novel tells of the mutual help between Ada and Inman, and their survival in the countryside, portraying the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ecology, the pursuit of the writer’s eagerness to blend into the nature and recover the original simplicity, and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pursuit of human naturalism, this paper aims at appealing us to learn Indian ancestors’ simplicity so as to seek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themselves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harles Frazier;ColdMountain; deep ecological thought; Indians
I106.4
A
1001-0300(2016)04-0124-05
2016-02-28
付小兰,女,重庆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军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