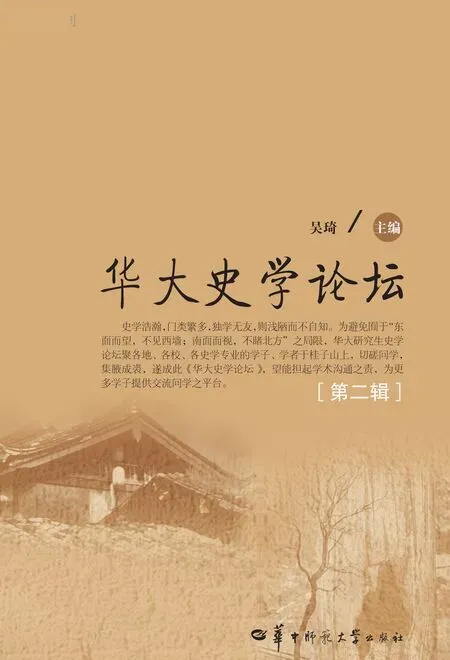读书与回归史学传统:读《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有感
2016-02-01李佳衡
李佳衡
桑老师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一书中探讨了很多方面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在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和富强趋势的余波下被西方的分科治学强行打散,并在西方的学科框架下对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进行解构和重组,带来了很多深刻的问题和矛盾。
问题之一在于分科治学使得历史学人的眼光囿于一时一地,以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为历史研究的全部。分科治学的本意原来是为了研究学问的方便,使得所研究的领域能够精进深入,从而与其他领域合成一个一贯的系统。然而现今历史研究的问题在于个人各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其他领域不管不顾甚至于文人相轻,这样造成的问题就是限制了学人的研究范围从而限制了眼界和境界,最后的成就也难以望前人项背。中国历史的研究传统一向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名家精译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3页。,讲求通达的境界,而要达到通的地步则必然要广博,博则需心胸宽阔、无所窒碍,方能以众家之长铸一家之说。而在当今这个时代,各种史料的获取成本大大降低,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大家获取史料的机会和成本相差不大,那么这个时候能判断学人水平高下的就是学人的层次了——能“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注]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者,方有史才。
应该说在现今史料爆炸的年代想要达到通达不易,尤其是治近代史者可供参考的史料汗牛充栋且在不断扩充,史料的边界模糊不清,一个问题穷尽所要看的史料尚且不能,而要以通达为目标,那史料要看多少才是个头?每思及此,常有“以有涯随无涯”的无力感。那么是否现今学人对通达只能是抱有“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情呢?实际上中国史学发源甚早,早已有自己的系统与流派,若学人能追寻发源、辨析源流,则通达可待。否则不问其他只是一味看文献,恐怕多少都达不到通达之结果,甚至连登堂入室都算不上。
因此拙见以为,历史研究内部可以划分研究范围,但是学人不能给自己限定研究范围,否则作茧自缚,受害的总是自己。清代政治家陈澹然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注]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577页。历史本就是事关时间与空间的学问,以万世、全局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方才是大手笔。历史研究内的领域划分本是在西学框架下对中国史学研究传统的强行拆分和机械架构,时至今日已弊端丛生。吾等也许无力改变,却也不能以此自缚手脚以致动弹不得,当勉力作为以求徐图改进。
在史学求通达的路上,学人的求学历程或者可以先从广览资料和群书开始,这样一方面能使自己的眼光不囿于一隅、不断了解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从而成为自己的志业。而在找到自己的方向后,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专,专到“唯我独尊”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也不能放弃打通全部历史的努力,或可从一些自己做的小题目当中见到大历史,或者可考虑做通史,也或者可以考虑做一些时间跨度长的大题目。对通达的历史境界的念念不忘或许不能成就一个大历史学家,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见贤思齐总是可以做到的。
问题之二在于不读书而专注于找新材料。传统的史学方法在于读书,书读得越多,对于历史学本身的了解、对于历史的感性认识也就越多,也就能慢慢进入所研究的时代,慢慢了解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从而在某种层面上觉察历史的真相。这种通过广泛的读书来做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中国古代历史学者所推崇的,只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人正确的历史观,建构起学人敏锐的历史感觉。这样的观念与感觉一旦建立起来,那么学人可以说是在历史研究的殿堂中真正登堂入室,无论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都不会跑偏、无论研究怎么样的问题都能开辟自己的一方天地。
然而这种历史研究的模式在现在看来好像不大行得通。以往治史者往往有家传,饶是如此,能在史学上有一番成就也要积累多年功力方能崭露头角——历史研究不讲究智力超群,而更青睐功力深厚者。然而现如今中国历史学科的设置以及学术环境貌似对于培养学生深厚的功底不大有利:历史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都要有毕业论文这个枷锁,而且往往是有限的学习时间内重重加码的毕业要求,很多时候给人以“以有涯随无涯”的无力感,于是等而下者选择抄袭、剽窃等不入流的行径,中者则是挤干肚中笔墨勉而为文,有追求者无力也无暇读书积累,但却知道在史料上面做文章。
治史的首要在于占有和运用史料,傅斯年曰“史学即史料学”虽值得商榷,却也离事实不远。我们平日所见的史料大部分都是可以找得到的、用得上的,那么一般而言,占有相同史料的史学学人想要一较高下的话,就要看谁的史料了解更为深刻、谁能更好地运用史料说明、解释问题,这是一般正统的做法。然而这就要求史学功底的深厚,非一日可成。一些希望能够做出超过前人成就且不屑于采取鸡鸣狗盗方式以获声名的学人则将目光投向了一些偏僻、长期未引人注目的史料,并以此做出了一些成就。长期看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既不利于学人的成长也不利于学界研究的突破。要知道新材料不是时时有,一个学人如果高度依赖于发现新史料而不培养对于一般史料的深入解读能力,那么长此以往没有了新材料,学人的学术生涯何以为继?再者,一般而言,新材料的发现集中在一些不是很受重视的历史问题上,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意义和对于学人达到通达的境界的帮助都不是很大,会使学人陷入一个狭小的范围且与其他更为宏大的历史问题无法产生联系。
2012年《近代史研究》期刊举行过一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的专题讨论[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系列文章,《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5期。,其中很多意见都很有见地,也引发了笔者个人的思考。笔者认为,“碎片化”实际上是历史研究中逃不开、避免不了的问题。原因在于史学的目的是从各个不同层面还原历史真相,所依赖的不外乎各种史料。然而,一个时代能流传下来的史料至多也不过当时那个时代资料数量的十分之一而已,更别说越往前推史料越少。因此,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时代所遗漏的史料碎片中工作,将看似不相关的史料按照某种联系拼接起来从而显示过往岁月的轮廓。“碎片化”的研究不要紧,很多小问题的解决促成中问题的解决,很多中问题的解决促成大问题的解决。然而现在大家担心的不是研究的“碎片化”,而是研究方向似乎跑偏。大家都去研究一些很冷很偏的小问题,而这些小问题无法促成中问题、大问题的解决,无法使其贯通起来,史学研究的风向也因此而改变。长此以往,大家都满足于挖一个池塘自给自足而非疏通河道、建设水网的过程,那么历史研究无疑就成了作茧自缚、自娱自乐了——病的根子,还是不读书的问题——不读书,所以要找新材料;新材料不好找,只有向冷门领域进发;冷门问题的研究,无助于史学的贯通,也引来了对于历史研究过于“碎片化”的非议。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有多读书了。
桑兵老师在书中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背后实际上是中西两种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系统和逻辑。然而自近代史发端以来,从器物的西方化到制度的西方化再到文化的西方化,中国传统史学受到的冲击虽然晚,但也是实实在在地来了。最大的冲击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框架完全被打散并且以西方历史学科的框架进行重构。这种重构的过程与其看成是史学的“进化”,不如说是史学的“重构”,打破一种系统兼容另一种系统。现在历史研究的很多问题可以看成是中西文化不兼容的一个投射,也说明了中西文化的整合还在进行中。中外文化的融合最成功的莫过于佛教的本土化,来自印度的僧人和中原的知识分子一同努力,使得佛教完全适应了中国文化(或者说被中国文化吸收为自身的一部分),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宗教流派:禅宗。而现在史学方面的中西融合,实际上是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传统而完全倒向了西方史学体系,然而却尴尬地发现了各种水土不服的症状。桑兵老师对此颇有微词,强烈批判史学的全盘西化,并且认为必须在坚持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营养,以中国文化格义印度佛教的方式来定义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关系。桑兵老师的见地颇为深刻,但是史学研究的西方框架已经形成,想要扭转过来绝非易事,而且学人在这个体系中浸淫已久,早已“错把他乡认故乡”,不知传统史学为何物了。而作为个体的学人来说,以一己之力扭转现状或者促成东西方史学的融合都是不现实的想法,面对现在史学研究的状况,想要在中西史学的矛盾冲突中左右逢源,可能要在几个方面精进。
一是多读书,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的都要读,这个功夫不能不下。但是,既然知道中西史学的融合尚未完成,那么在读书过程中对于所谓范式、框架、体系等方面的东西要极其谨慎地对待才行。二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寻找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一些有共性的东西,寻求二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东西方史学尽管有矛盾、分歧和冲突,但是也一定在“历史研究”这个框架内存在一些堪称“共识”的东西,把握了这些东西也就把握了史学的要义,可以在研究中找对方向、避开歧路。三是在自身的写作过程中不要照搬框架、范式,这些东西好看好用,却是一个个陷阱,限制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同时很容易用结论来裁剪材料和论据,最后反而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而笔者个人认为,范式的作用类似于地图,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解决就像寻路一样,需要一个特定的地图来指引;而如果所有问题都用一张地图,问题比没有地图还严重。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懂得别人绘制地图的方法,然后自己绘制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