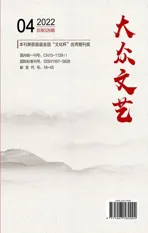《冤报冤赵氏孤儿》复仇情节研究
2016-01-28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院100000
孙 畅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院 100000)
《冤报冤赵氏孤儿》复仇情节研究
孙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院100000)
摘要:复仇情节是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的高潮情节,主角赵武的矛盾性格既为复仇提供了可能性,又为他的复仇方式做出了解释;程婴等人为赵氏一族所做出的牺牲,则为最后一折的复仇情节做了充分铺垫。此外,联系作者纪君祥所处的时代背景,这部杂剧中也存在着反元复宋思想与忠君思想的微妙对立。
关键词:赵氏孤儿;复仇;情节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后在《史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元人纪君祥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敷衍而成的。与史书所载不同,戏剧尾声隐去了程婴自杀这一堪称悲壮的情节,改以赵武复仇,功成受赏作结,全剧的高潮因此完全集中在了复仇情节上。复仇的直接动因当然是赵氏孤儿与奸臣屠岸贾之间不可化解的家族仇恨,但除此之外,背后也有赵武本人、他人以及时代背景的因素。
首先,赵氏孤儿的矛盾性格既为复仇提供了可能性,又为他的复仇方式做出了解释。赵武的成长过程中,“这壁厢爹爹是程婴,那壁厢爹爹可是屠岸贾”,这两位父亲给赵武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他的两个名字屠成(屠城)、程勃(“勃”有兴盛之意)就是这种矛盾的缩影。一方面,屠岸贾身为一员武将,给予他的是过人的武力与胆气。赵武在全剧第四折出场时就是在教场中演习弓马,而他的话语也仿佛是屠岸贾的翻版:“引着些本部下军卒,提起来杀人心半星不惧”“这一家若与我关系呵,我可也不杀了贼臣不是大夫”“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把他九族屠”。这些极具杀气的话语集中显现了赵武在屠岸贾影响下不惧天地,好勇斗狠的性格特点。同时,屠岸贾栽培赵武,是要“早晚定计,弑了灵公,夺了晋国”的,忤逆纲常的枭雄本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因而在得知灭门之仇时,赵武未经丝毫犹豫便能将一直视如亲父的屠岸贾当做仇敌对待,并要求诉诸暴力,血债血偿。另一方面,程婴作为一个大夫,在赵武面前始终是“拿一手卷”的形象。赵武在程婴处习文,被灌输的是极为正统的忠君报国思想。他的终极愿望就是“扶明主晋灵公,助贤臣屠岸贾”。两种不同的思想汇集于他的头脑深处,导致了他的矛盾性格:尚文而又嗜血,忠君而又不惧权威。因此,本该是极为血腥的复仇情节,复仇者本人的双手却并没有沾染鲜血。即使处于愤怒的顶点,赵氏孤儿仍是以王命和国法为先。事前奏请君王,事后则将仇敌交予王法定夺,君王意志始终处于他的私人情感之上。
其次,他人因素在赵氏孤儿的复仇过程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复仇的动因除了家族仇恨,也有程婴等人为赵氏遗孤所作出的牺牲。杂剧前三折所描写的公主自缢、韩厥自刎、程婴献子、公孙杵臼受刑等情节都为第四折赵氏孤儿的复仇做了充分的铺垫。为守护赵氏孤儿而死的人或为将军,或是能臣,原本都应有一番大作为,但全部为了救一个孤儿毅然舍命。自出生起,赵武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这些人雄图壮志的寄托。随着牺牲者的不断增加,他的人生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唯有完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复仇才能真正实现这些义士的人生价值。而复仇的同时,他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晋灵公铲除权臣的武器。本剧中君主的形象虽然始终模糊不清,但两位权臣先后被杀,坐享其成的都是君主。赵盾虽是忠臣,但功高震主。与屠岸贾不睦只是赵氏家族满门被斩的表面原因,实际上整场杀戮都是在君主的默许下进行的。而当屠岸贾势力独大,渐生反心时,灵公又允准了赵武对他的清算,还派亲信魏绛跟随在后,特地叮嘱“道屠岸贾兵权太重,诚恐一时激变,着程勃暗暗的自行捉获”。由此可见,从政治层面上讲,赵武是步了屠岸贾的后尘。
以上所讲的,是“复仇”并不完全是赵武的个人行为,而是众人意志的结果。从戏剧角度看,复仇这一情节是合理的,但从赵武个人来讲,则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这主要体现在赵氏孤儿对自己的身份转换接受过于顺利,情感变化过于迅速上。从赵武的言行上可以看出,他与屠岸贾其实更加意气相投些,提到这位“父亲”时尽是赞美之辞(“俺父亲英勇谁如,我拚着个尽心儿扶助。”)相比之下,他与另一位“父亲”程婴对话时,则有着武夫与文人间的隔阂。但在得知自己身世后,赵武对屠岸贾的感情骤然消失,丝毫没有出现“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而是即刻要“把铁钳拔出他斓斑舌,把锥子生跳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把钢锤敲残他骨髓,把钢铡切掉他头颅。”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赵武并无家族惨遭灭门和义士赴死时的悲壮感的记忆。由第一折到第四折所跨越的二十年间,仇恨情绪的积累、发酵过程,是由程婴、观众和作者本人完成的,而非赵氏孤儿,最终急于“挥剑”的也是故事之外的看客。这种缺陷既有元杂剧篇幅的限制,也有作者对于人性和人物心理的思考不够深入的原因。整部剧的结尾固然大快人心,但赵武的形象却十分单薄。此外,赵武在复仇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一点抵抗,这一点也值得斟酌。正义与邪恶交锋时若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就难以显现正义一方的强大。枭雄屠岸贾面对复仇者时,下意识地想到“我只是走的干净”,畏首畏尾的形象与前文中志在弑君的豪迈形象形成了极大反差。而赵武在一句戏词间就擒住了对方,也使得复仇的过程过于形式化而缺乏实感。
最后,《赵氏孤儿》中的复仇情节还与时代因素密不可分。整部剧的主题是邪不胜正,联系其时代背景,邪恶一方似是在隐喻元朝,而正义一方,即赵氏遗孤则是代表了赵宋王朝,“复仇”就变成了“恢复宋室”。“虽然难以考察纪君祥撰写此剧的真实动机,但在宋亡不久的元代舞台上演这一历史故事,而且让主人公高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流芳’等曲辞,至少在客观上与当时广大汉族人民普遍存在的反元复宋的思想情绪是相吻合的。”1然而在剧作中,“复仇”这一行为又被刻意地与“忠君”联系在了一起。赵氏孤儿决心复仇的时候,说“我拼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只要他偿还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属”,先说屠岸贾对于国家造成的危害,后说自己与屠岸贾的血海深仇,把朝廷社稷放在了家族恩怨之前。复仇便不再只是由于血缘上的情感了,更有为国家失去良臣而产生的痛惜之情。为了强调这一思想,作者在史实的选取与剪裁上十分具有倾向性,力图将赵盾塑造成一个不容置疑的忠臣形象,先后以鉏麑不愿刺杀赵盾和赵氏遗孤屡次被救侧面证明了赵盾的忠心,历史上赵盾纵容其弟弑君的情节则被删去。作者还几次提到屠岸贾在灭掉赵氏一族后想要弑君的意图,让赵武的复仇同时具有救主的意义。而昏庸的灵公被当成了本剧的背景模糊处理,使得赵武和程婴等人不至于沦为“愚忠”之徒。隐含着的“推翻新君”的思想和剧作中宣扬的“忠君”思想虽然会形成冲突,但又是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对于广大汉族人民的压迫使得灭元复宋的思想在民间滋生起来,因此称“元朝是儒家思想依然笼罩朝野而下层人民日益觉醒,反抗意识日益昂扬的年代”2。《赵氏孤儿》之前,也有如《窦娥冤》等控诉黑暗社会的杂剧,但复仇终究是通过鬼魂和神明的力量完成的,悲剧性压过了抗争性。直到纪君祥所作的《赵氏孤儿》,才第一次把现世的报复写的如此酣畅漓淋。纪君祥其人生平不详,但想必他也和当时许多志在朝堂而身在市井的汉族士人一样,面对外族统治者时有着复杂的心态。
《赵氏孤儿》一剧虽然是以赵武成功复仇,赵氏一族沉冤得雪结束,但仍被广泛认为是一部悲剧。复仇并不能挽救几百条无辜的生命,一直以来复仇这一行为也广受争议。因为当正义一方选择利用暴力方式复仇时,就意味着他已经被邪恶一方所同化了。然而在这部剧中,复仇却成为了死者生前的唯一企盼,生者活着的唯一意义。程婴苟活于世是为了确保赵氏孤儿能够复仇,赵氏孤儿生来则背负着必须要复仇的命运,他们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人生百年,仅仅因为身份而放弃自我,是非常不值得的。赵武是如此,有元一代的汉人亦是如此。
注释: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52.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12
孙畅,女,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