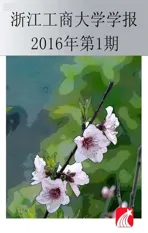重新发现中国:论列奥·施特劳斯与当代思想大解放
2016-01-24杨子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杭州310018
杨子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杭州310018)
重新发现中国:论列奥·施特劳斯与当代思想大解放
杨子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杭州310018)
摘要: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规模宏大,并且注定影响深远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其主旨在于: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与跟随中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中国。列奥·施特劳斯站在“西学东渐”历史洪流的终点,为这一解放运动提供了关键性的思想动力:通过重审施特劳斯开启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再一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文明的可能性、特殊性与优越性才重新被发现。
关键词:施特劳斯;思想解放;发现中国;古今之争;中西之争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即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固步自封,而是确信自己正走在一条正确的而非错误的、独特的也是普遍的道路之上。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第二个三十年,基于文明自信的道路自信将成为标志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最大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信并非仅仅表现在官方的言行中,同样表现在日益多元化的学术界。我们发现,不管是哪种政治立场或学术背景的学者们,他们都在或多或少地回归中国。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落后”,而是“中国为什么强大”;不再是“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些什么”,而是“中国可以向西方乃至世界贡献些什么”。[1]学术界正在用宣言般的语气宣告中国的自信,比如“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2],再比如我们已经迎来了“即将结束的开始”(许章润语)。
这些现象恰恰启发我们去思考:弥漫在当今中国上下的自信心理绝非仅仅源于中国今日之崛起,它一定与我们思想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其深远的影响正逐步显现出来。可以说,没有这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就不会有中国的真正崛起,更不会有对中国道路的真正自信。因为这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主旨(也是它区别于以往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特色)就是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与跟随中解放出来,并且重新发现中国。
要深切地理解这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就必须把它放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中来认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养成了凡事向西方看齐的心理习惯,我们总是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中国,以至于我们怎样理解西方,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怎样理解中国。我们发现,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中,在二十一世纪初,有一个西方思想家来到了中国,他不仅像其他思想家一样掀起了规模庞大的思想潮流,更重要的是,他终结了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同时又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了中国。他就是列奥·施特劳斯,可以说,施特劳斯是一块中国藉以找回自身的西学跳板,他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改造国家的主义或方案,却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
本文的任务就是:理解施特劳斯在西学东渐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并进而解释施特劳斯的思想主张如何帮助我们开启了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
一、当代思想大解放运动——重新发现中国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不断证明:中国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不会有实践上的突破。可以说,思想解放是改革进程的“总开关”,难怪约翰·奈斯比特会感叹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3]
中国最早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从晚清时期谈起。当时中国人面临着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之所以号称“三千年所未有”,显然不是因为我们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败了。因为历史上中国并非第一次被异族打败,而是因为我们在心理上被彻底打败了,我们不仅开始怀疑我们的军事能力、政治制度,而且进一步开始怀疑我们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当我们被蒙古等少数民族击败的时候,中国人还是依然坚守着夷夏大防,华夏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文化上依然是先进的代表。以前我们碰到的敌人要么是有武力而没有文明的民族(比如蒙古人),要么是有文明而没有武力的民族(比如印度),但是西方人是既有武力又有文明的民族。[4]这就迫使中国人开始整体性的反思,尤其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中国人终于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在经济的、器物的、制度的层面)对自己的文明失去了信心。因此,中国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从天朝上国的自信中解放出来,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学习西方、追随西方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首场集中演出,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高表现。
一九七八年开始的历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从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而所谓的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新观念实际上依然是基于对西方的某种认识抑或想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要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与晚清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本质的差别,最多只是在理解西方上有所不同。甚至到后来我们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究其根本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西方普世文明的中国版,即将西方普遍化建构的现代之路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贯彻与实施之后的产物。[5]中国的主体性地位依然是缺失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追求的中国崛起仅仅是“作为西方文明模范生”的崛起。
也就是说,从晚清以来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是连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把古老的中国文明当作沉重的包袱,必欲弃之而后快。解放是从中华文明中解放出来,运动是迈向西方文明的运动;它们都把一个独特的西方理解为一个普遍的西方,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从中国古老文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6]。拜其所赐,中国人在西方化的过程中开创了高速现代化的历史伟业,奠定了中国今日之崛起。
但是,晚清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一直有一个未曾解放的思想包袱,那就是对于西方的迷信以及相应的对于中国自己的鄙夷乃至漠视,这个包袱一直隐藏在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它的后果就是我们在学习和追随西方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自己。一个丢失了自己的国家,只会一个劲地与国际接轨,而不知道这样的接轨要把自己带往何方;一个缺乏了主体性意识的国家,虽然它会宣称要走自己的路,但它所能够设想的未来以及所能够行走的道路骨子里依然是别人的。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注定是走不长远的。
而新世纪以来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就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晚清以来历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反向运动”,它的根本主旨就是要摆脱对西方人的迷信,并且重新找回我们自己。这种思想努力最重要地体现在关于“中国道路”这一总体性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中国道路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这可以被称为“弱意义上的道路自信”,因为它的姿态是消极的辩护),而且进一步上升到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这可以被称为“强意义上的道路自信”,因为它的姿态是积极的期许)。中国不再充当西方文明虔诚的追随者,转而寻求自身的道路,这条道路绝非特殊的道路,而是普遍的道路,是可以让西方“道法中国”的道路。中国也不再被看作是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远大前程的“文明国家”,它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文明的使命,承载着世界性而非地域性的责任。
笔者做完自我介绍和简单的开场白,考虑和新员工年龄差距较小,设计的PPT可以自动播放和用激光笔远程控制,对于所讲内容成竹在胸,于是就尝试走进新员工中间去说,拉近了彼此之间的物理距离。这个尝试,有比较好的收效,全程半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基本没有看到新员工们有低头看手机的现象。
我们看到,自主性是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议题,而中华文明是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资源,对中华文明的自觉意识(文明自觉不同于文化自觉)①“文明是一个整体”,它既有主观的层面,比如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等,也有客观的方面,如经济制度、习俗、法律、建筑等。虽然文化是文明非常核心的构件,但是文明绝不局限于文化,相反“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也是实体化了的文化,我们只有从文明这个包容广泛、涉及全面的视角出发,文明内部的任何构成单位才能被充分理解。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正是道路自主性的前提,没有自觉,就不会有自主,更不会有自信与自强。总而言之,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重新发现了中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如何重新发现中国的?要解释这一重大问题,当然会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但是笔者认为,只有当我们把它放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中来审视时,才能比较清楚地理解它。因为受晚清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影响,我们在看待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我们总是借助西方人的视野来打量自身。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当代思想大解放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正在流向何方?一旦我们尝试这样去努力了,我们势必会发现,列奥·施特劳斯以一种迥然不同于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独特身姿出现在我们眼前。
二、西学东渐中的列奥·施特劳斯——走向起点的终点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在不断地分化,知识界从原先还具有的“态度的同一性”逐渐进入了一个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代。[7]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众声喧哗、主义纷争,像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思潮纷至沓来,每一面旗帜都代表了一两个被我们引进的西方大师。
正是在这个“道术已裂”的时代,德裔美籍犹太人列奥·施特劳斯被引进中国。①列奥·施特劳斯的名字中国最早出现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政治理论的译本〔詹姆斯·古尔德、文森特·瑟斯比主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商务印书馆1985年〕之中,但是很长时间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施特劳斯思想的独特价值,包括1993年翻译出版的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也没有引起中国学者应有的关注。直到2002年刘小枫在《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中选编了施特劳斯的五篇论文和两篇导论,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真正意识到施特劳斯的思想价值,并开始有意识地大规模译介施特劳斯的其他著作。因此我们可以把2002年定为施特劳斯登陆中国年。很多时候,人们把他与其他西方思想家同等看待,并且也给他头上安放了新保守主义、绝对主义等头衔,这样人们就可以免去深入细致地阅读施特劳斯的辛苦,还可以比较容易地批判施特劳斯的政治不正确。但是,这样急切而肤浅的口水之争只会进一步误解施特劳斯的意图,更不可能恰当地理解施特劳斯在一百多年西学东渐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实际上,施特劳斯跟其他西方大师的最直接差异即在于他没有提供任何主义或方案,因而也根本无法用他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相反,我们越是深入地阅读施特劳斯,我们越是会惊讶地发现施特劳斯所谈论的问题与我们中国人没有太多的关系。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在施特劳斯所描述的现代性危机中,现代人不仅杀死了上帝,而且也杀死了沉思的古典哲人。但是中国文明自古就没有上帝,也没有所谓的古典哲学,那么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讨论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呢?![8]如果这里所说的“借鉴意义”只是用施特劳斯所恢复了的古典视野来看待我们自己,那么答案当然只能是否定的。但是,这种心态实际上正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对待西方思想的惯常态度的一个延续,我们要真正理解施特劳斯之于中国的意义,就必须首先跳出这种心态。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都是以弱者向强者学习的心态来追随西方的各种先进思潮,这是一种极其自卑的心态,中国人引介西学是在向西方人寻求救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而中国人自己(尤其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聪明智慧,因此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名目繁多的主义就被当作救治古老中国的社会改造方案引进中国了。所谓的“西学东渐”实际上含有这样的假设前提,即西学是主,中学是客,西学是启蒙者,中学是被启蒙者。而所谓的中外文化交流几乎已经到了“文化臣服”的地步,甚至有学者把一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比喻为“精神在押的巴比伦囚”。[9]自卑的心态导致了“自我囚禁”,而我们所“臣服”的即是现代西方文明,这是百余年来西学东渐的主要关注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之争实际上是古今之争,[10]而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以现代西方的视野来认识和改造自己的。
但是改革开放让我们初步品尝到了现代化的果实之后,我们突然间发现现代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于是“现代化问题”变成了一个“现代性问题”。于是我们又开始学习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身上看到了对于现代性的激烈批判,并且还初步认识到了在现代西方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不甚熟悉的古典的西方。
但是施特劳斯进入中国之后,不仅告诉我们百余年来我们所认识的西方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西方、现代的西方,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认识到的对于现代西方的反思以及对于古典西方的回归存在着根本的局限,因为尼采、海德格尔的反思是在现代西方的视野之内进行的,因此他们所尝试回归的古典世界也是被扭曲了的古典世界。[11]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非但没有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反而越来越将现代性推向极端。施特劳斯告诉我们,我们只有获得一个超越于现代性之上的整全视野,才有可能清楚而准确地评价现代性的得失,这个视野必须在真正的古典传统中寻找。施特劳斯区别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我们能够如其所是地返回到古典世界,其方法就是通过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一步步爬回到古典哲人所面对的那个自然的洞穴。[12]这代表了人类的原初境况,代表了我们最根本性的问题以及呈现这一问题的整全的视野。
因此,引介施特劳斯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就是对于所有先前的西学引介的不满,正如甘阳所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是对自由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双重批判,[13]他把我们引向的是一个古典的、完整意义上的西方。这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对于我们的直接意义。
但是这绝非意味着我们要把施特劳斯所恢复的那个古典西方重新作为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而是要像施特劳斯重新找回西方人的整全视野那样重新找回我们自己的整全视野。只有重新找回我们自己的整全视野,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反思和改进现代性中的中国问题的最终根基。[14]因此我们可以说,施特劳斯对于我们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需要盲目地跟随西方,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源头。用张志扬极富哲诗意味的话说,“西学的夜行”注定是一场“走向起点的夜行”①请参见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我们长期跟随着西方,当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跟他们一样迷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返回各自的起点。[15]
综上所述,施特劳斯的进入中国,绝不能看成是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简单延续,而更应该看成是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终点。这个终点并非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引介西方学术,而是意味着一种自卑心态的终结,意味着迷信西方的终结。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信奉盲目的“拿来主义”,不再被动地充当全球文化霸权体系中的“搬运工”角色,我们将坚持主体性的地位,有意识地从浩瀚的西学海洋中“取”我们之所需。[16]
那么,具体而言,施特劳斯的思想学术是如何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中国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到施特劳斯的思想深处,详细探查一番。
三、从“古今之争”到“中西之争”——照亮中国
事实上,在施特劳斯所有著作中,只有两个地方明确提到了中国:一是他有关自由教育的演讲,他说“有一种必然的不幸使我们无法倾听印度和中国的伟大思想: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我们又不可能学会所有语言。”[17]另外一处是他在讨论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提到“科学的观念迫使他坚持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的科学作为科学都是独立于世界观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西方人与中国人,即对那些‘世界观’尖锐冲突的人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有效性。”[18]38前面一次提到中国,施特劳斯语气中充满了向往和无奈,后面一次提到中国,施特劳斯仅仅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例子与西方对举,但不管是哪一次,施特劳斯印象中的中国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既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又如何能够从施特劳斯所描绘的西方文明中找到中国的身影呢?
我们的回答是,不管中西文明之间存在多少异同点,施特劳斯没有也不会用中西比较的方式来理解西方,因为长期以来中国都没有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西方人更不会以中国为背景打量自身。但是,施特劳斯在西学的视域内重启了“古今之争”,无意中却为中国人重启了“中西之争”,正是在“中西之争”中,我们重新发现了中国。
之所以说是“重启”了“中西之争”,是因为早在晚清时期,当中国人第一次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中西之争”就是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基本问题。在中西文明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激进的保守派依然沉浸在“夷夏之辨”的古老思路当中,把西方当作夷狄,中国人只不过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罢了。就算是温和的改良派,也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文明的主体地位从未丧失。但是,随着国势的日益衰微,使得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彻底瓦解,“中西之争”逐步演变成了“古今之争”,中国代表的是落后的“古”,西方代表的是先进的“今”,整个近现代历史演变成了如何摆脱古老中国的束缚,如何向现代西方学习的过程。
但是,施特劳斯首先告诉我们,那个曾经被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现代西方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相反,今天现代西方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当中。西方的危机就在于它丧失了信心,即“西方的决心已经动摇”。所谓“西方的决心”,就是现代启蒙运动以来建设普遍同质世界的美好蓝图,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都是自由平等的国家,而且每个国家都由自由平等的男女构成”[19]3-4。曾几何时,这个伟大的理想不仅征服了西方人,而且还征服了全世界,中国的现代化不就是要努力成为普遍同质世界当中的一员吗?但是现在,西方人自己对这个理想失去了信心,作为曾经的追随者的我们不应该警醒吗?
现代西方的危机意味着普遍同质的现代启蒙理想的失败,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施特劳斯认为普遍同质的现代理想是纯粹的乌托邦,是不可行的,因为任何政治社会都是特殊的“封闭的社会”,“如果说真正的统一只能通过对真理的了解或者说通过对真理的探询才能得到,那么人类真正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哲学最终大众化的基础之上(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或者让所有人都成为哲学家(而不是PHD等等)的基础之上,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存在的只能是封闭的社会,即国家。”[20]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个现代理想也是不可欲的,因为“一个开放的或包容宏富的社会会在比之封闭的社会更低的人性层次上存在着,封闭社会经历许多代人,在趋向人的完善方面做出了无可比拟的努力。”[19]133既然任何人类社会在事实上都是封闭的、特殊的,那么宣称普世的西方文明就脱去了普世的外衣,它实际上只是被普遍化建构起来的特殊文明,这样一来,长期被普遍化建构所遮蔽了的西方文明追随者(尤其是中国)就浮出了水面,它们根本没有必要为自己不西方进而不普遍、不正常感到丝毫的羞愧,相反,它们应该坦荡地承认和接受自己的特殊性身份,因为西方自身就是特殊的。
当然,仅仅从西方的危机中发现中国是十分脆弱的,只是一味唱衰西方并不能够唱响中国。而且,讨论西方危机的人并不限于施特劳斯,像尼采、海德格尔等伟大西方思想家都从不同层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是从尼采、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中国呢?这只能从施特劳斯对西方危机的独特诊断中寻找答案。尼采和海德格尔把西方危机归结为起源于苏格拉底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施特劳斯认为他们的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而且给出的药方非但不能救治西方现代性的弊病,还进一步推进了西方现代性的浪潮滚滚向前,加剧了病情的恶化,最后导致了历史主义、虚无主义。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理性主义并非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到现代都是一以贯之的,相反,西方理性主义在近代曾经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正是现代的理性主义导致了现代西方的严峻危机,而要救治这种弊病,就必须要重新回到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当中。这就是施特劳斯重启的“古今之争”,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西方远没有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战胜了古典西方,一度被废弃的“古今之争”需要被重新审理。
简单一点说,“古今之争”的症结在于如何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现代理性主义认为哲学可以与政治结盟,所谓普遍同质的启蒙理想实际上就是把政治社会建立在哲学真理基础之上的产物,所谓的“开放社会”就是让真理的光芒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政治社会之所以是政治社会,就在于它一定是由意见甚至是教条组成的,普通百姓也不可能都变成哲学家,这是政治的常识,也是无法改变的政治铁律。现代理性主义是癫狂的理性主义,强行把哲学与政治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现代西方的危机就是它的典型体现。而古典理性主义坚持认为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哲学对真理的追求会危及政治社会的稳定,而政治社会的教条主义本性又倾向于迫害哲学家。因此成熟的哲学家(就像老年苏格拉底一样)出于自我保护和社会责任的考虑,必须学会谨慎的言行,当然同时又能保持思想的锋芒。最高的哲人(必然是政治哲人)能够实现思想的无所畏惧和言行的谨慎中道这两者的完美统一。[21]也就是说,现代哲人试图通过改造社会来实现哲学与政治的融合,而古典哲人则只是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平衡哲学与政治的冲突;现代哲人的眼光是向外的,古典哲人的眼光是向内的。
这样一来,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中国的传统智慧,因为不管是儒释道哪一家,都主张我们把目光专注于自身德性的提升,而不是专注于外部社会的改造。更重要的是,正如西方古典哲人强调人类灵魂的等级差异不可磨灭一样,中国儒家也强调君子小人之分,西方古典哲人强调言行上要谨守中道,中国儒家也把中庸之道提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施特劳斯通过对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重构,在很多方面走到了非常接近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智慧的地方。[22]既然西方的古典理性主义可以用来救治现代性的弊病,那么同样面临现代性困扰的当代中国人也可以向自己的老祖宗寻求思想资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曾经被我们唾弃的传统,竟然又再一次拥有了用武之地,而且还是借助西方人的思想努力。
当然,受施特劳斯思想深刻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探索停留于此,事实上他们还从施特劳斯那里接收到了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当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西方古今理性主义会有如此根本性的差异时,施特劳斯把我们引向了西方文明的至深根基之处,而正是在这个根基之处,我们看到了中国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古今之争”表面上是如何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对待“理性与启示之争”的问题。现代哲学认为理性已经一劳永逸地战胜了启示宗教,哲学可以在排除启示的前提下获得完满的真理,这样哲学就能够与政治结合,一如以前宗教与政治结合一样。但是施特劳斯认为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现代哲人对启示宗教的批判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它的自信只不过是建立在教条主义基础之上的,而它也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古典哲学认为理性与启示之争是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选择,这两者谁都驳不倒谁。[18]75这就意味着哲学最多只是对真理的热爱,而不可能获得完整的真理,哲学永远处于不确定性当中,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哲学就不能用来指导政治。施特劳斯认为理性与启示之争是西方文明的活力源泉[23],要自觉地接受甚至是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才有可能避免西方文明走向衰亡。
一旦深入到这个地步,深受施特劳斯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与施特劳斯分道扬镳了。他们认为理性与启示之争仅仅是西方人的根本问题,中国人既没有希腊意义上的哲学,也没有希伯来意义上的上帝,更没有上帝与人(哲学)的“天人永隔”。这不是我们的短处,恰恰是我们的长处,因为“希腊的理性与希伯来的神性,使人要么物化,要么虚无”[24]。施特劳斯为了克服相对主义、超越虚无主义,将自己的立场停留在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但是中国传统智慧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人们在对人与事持一种开放性理解的同时,能够坚守某些确定的道德原则,这一点恰恰是施特劳斯没有意识到的。[22]尽管笔者认为前面这两种判断还有待商榷,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施特劳斯对“古今之争”的深入挖掘,重启了一百多年前潜藏在中国士大夫意识中的“中西之争”,[25]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智慧独特而优越的一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的中国才真正被发现。
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就在施特劳斯的指引下,逐步从现代西方启蒙理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不但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可能性,而且看到了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因此我们说“施特劳斯照亮了中国”。
四、结语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之上,一个历经一百多年埋首学习西方的中国正在逐渐找回自身,一场深刻而又迥异于以往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各个领域蔓延开来。
当然,重新发现中国,绝不是要排斥西方,更不是要闭关锁国,相反,我们还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因为在一个事实上已经被西方化了的世界中,了解西方已经成为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逃避的历史命运,“只有在真正进入了西方以后,了解得越深,才能够从西方文明中解脱出来,进入中国文明的理解。这是个漫长的过程。”[26]实际上,重新发现中国就是要培养一种健康的心态,在对待西方的时候,既没有低人一等的自卑,也没有天朝上国的自大,而是介乎其中的自信。
参考文献:
[1]玛雅.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66.
[2]姚中秋.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J].文化纵横,2013(3):75-80.
[3]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M].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9-26.
[4]许纪霖.富强还是文明:崛起后的中国走向何方[J].贵州文史丛刊,2012(3):8-14.
[5]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道路论纲[J].思想与文化,2008(1):32-64.
[6]甘阳.文明国家大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25.
[7]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M].吉林:吉林出版社,2007:40.
[8]邓正来,曼斯菲尔德等.从施特劳斯学派源流看新保守主义[N].社会科学报,2008-09-04(07).
[9]张志扬.“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西学东渐”再检讨[J].现代哲学,2007(2):39-45.
[10]甘阳.古今中西之争[M].北京:三联书店,2006:35.
[11]LEO STRAUSS.German Nihilism[J].Interpretation: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1999(3):353-379.
[12]STEVEN B SMITH.Leo Strauss's Platonic Liberalism[J].Political Theory,2000(6):787-809.
[13]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后记[M]//徐戬.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9.
[14]刘小枫.前言[M]//吴雅凌.俄尔普斯教祷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
[15]ALLAN BLOOM.Leo Strauss:September 20,1899-October 18,1973[J].Political Theory,1974(4):372-392.
[16]张志扬.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C]//萌萌.“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
[17]LEO STRAUSS.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C]// Leo Strauss.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New York and London: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68:7.
[18]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38.
[19]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133.
[20]LEO STRAUSS.Letter to Karl Lowith,10 January 1946[J].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3,4:107-108.
[21]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C]// LEO STRAUSS.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30.
[22]唐士其.中道与权量——中国传统智慧与施特劳斯眼中的古典理性主义[J].国际政治研究,2011(2):101-119.
[23]列奥·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M]//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29.
[24]张志扬.生活世界中的三种哲学生活——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选择[J].世界哲学,2002(1):52-59.
[25]徐戬.高贵的竞赛——施特劳斯与主义的彼岸[J].开放时代,2009(9):63-78.
[26]甘阳,刘小枫.西学源流丛书“总序”[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
(责任编辑陶舒亚)
Rediscovery of China:On Leo Strauss and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Yang Zif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Since the 21st century,China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a sweeping and far-reaching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whose substance is emancipation from blind worshiping and following West,and rediscovery of China.Leo Strauss who stayed on the end point of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provided the most important ideological motivation for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by reopening the argument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the argu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ome into Chinese sight again,so that the possibility,particularity and superior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ld be rediscovered.
Key words:Strauss;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discovery of China; argument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rgu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作者简介:杨子飞,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仅启蒙运动的启蒙——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16CBZZ05)
收稿日期:2015-11-30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1-00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