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别
2016-01-18走走
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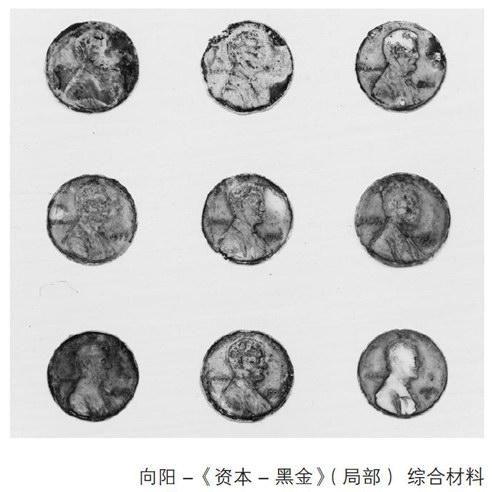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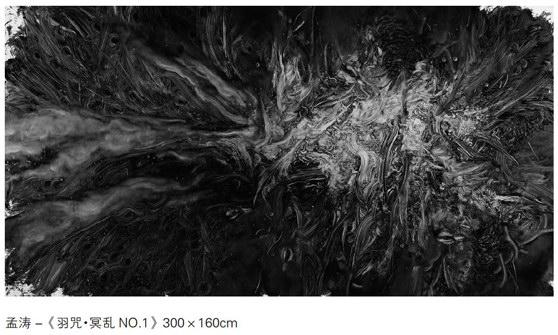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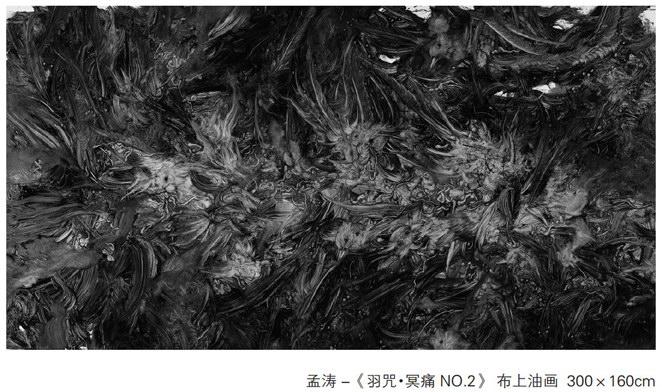
我坐在出租车副驾驶座上,三月底的傍晚,单看天空算是晴好。手机一查,空气质量指数却在101,橙色的轻度污染。就在这时,接到了一个号码完全陌生的电话。
“喂?”我一边应答一边伸出左手,调低收音机音量。
“我是章琳,刚到上海,有空见个面吗?”
把手机放回口袋后,我的脑子有点乱。不管怎样,章琳在上海只待一星期,一星期后,她就要回她的慕尼黑了。
“你现在怎么样,还在杂志社?你妈妈怎么样,她身体还好吗?”
她问了我一堆问题。我说很好。实际上,我刚经历了不算顺利的本命年,有点意气消沉。至于我妈妈,她当然也挺好,生过一次带状疱疹,疼痛也就几个星期。疱疹总会慢慢干瘪下去的。
餐厅里,男男女女三五成群。我往里走了几步,没错,她就在那儿。一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瓶巴黎水。她其实背对着我,我们之间隔了好几张桌子,服务员还在当中穿来穿去。我没有想到我能一眼认出她来。
她留了披肩发。看见我,她立刻站起身,似乎想要拥抱我一下,但我把手里提着的一只纸袋递给了她。一点小礼物,我说,你的气色真好。她身上穿的裙子我没见过。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她穿裙子。是一条黑色的珠片裙,闪闪发亮。脖子上挂着一条绕了三四圈的珍珠项链。两只胳膊晒得黑黑的,整个裸露在外。我注意看了看,曲线紧致,没有“拜拜肉”的迹象。看上去,她过得很好。
我们已经十几年未见。曾经,她生活里发生的那些事,在我听来像是新闻。她和我在同一片棚户区长大,可我直到念中学才认识她。她家在棚户区的最北边,紧挨着建于1930年的“步高里”,那是一片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七十九幢整齐的二层楼房,一水儿红砖外墙。
她父亲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学教授,她母亲却是一个四十不到的年轻裁缝。(比我妈整整年轻了八岁。)她的爷爷奶奶住在太原路的别墅里,他们一家三口却挤在她母亲娘家的小屋里。第一次去她家,我的注意力就被桌上的画册吸引了。色彩艳丽的画册看起来精致极了。旁边堆着剪了一半的布料。下午她家总是没人。我们穿过马路走进“步高里”,曲曲弯弯,一路上看到的全是自行车,靠着墙根。每扇大门上都挂着信箱,用毛笔写着好几个姓氏。我们靠在最里面某扇紧闭的后门上,隐约能闻到厨房里饭菜做完,剩下的余味。光线洒在红砖墙上,镀成一种美丽的金红色。猫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又消失。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红牡丹”,“来,抽一根。”她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小太妹。香烟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捻着,我们对着地上的青苔弹下烟灰。煞有介事。和“步高里”相比,我们住的房子像是随便用砖堆起来的,逼仄、低矮,毫无生气。冬天寒冷而乏味,夏天闷热又潮湿。黄梅天一到,墙壁就弥漫起一股霉味,整个七月逗留不去,直到八月酷暑到来,被热烘烘的空气蒸走。我那时开始在纸上写下一些自己也不太明白意思的句子。用工整的钢笔字抄在草稿本上,拿给她看。“我看不太懂”,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她的眼形有点凹,里面流露出惊讶,接着是迷惑,最后是一点点不以为然。“你想做诗人?”她指了指竖在她面前的本子。“怎么可能,”我说,“我就写着玩。”
服务员来了,递给我们一人一本黑皮菜单。你看上去有点疲倦,她一边打开菜单,一边说道,还是整天写东西吗?写东西的人心事重,你睡眠一定不太好。
“你真是一针见血。”
“你知道吗?某某生癌去世了,听说是骨癌,据说她是我们同学里最早去世的。”
太可怕了。我说。
“我一直以为生癌的都是老人。”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得不得癌症全靠运气,变异随机发生。”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床上度过。要静养,医生说。自从去年十二月底做完手术,我做到了“尽量不想不愉快的事”。一上来就谈癌啊死的,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你呢,这次怎么想到回来了?”
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她离开上海,也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十年前的章琳,头发剪得短短的,身上穿的是牛仔裤和圆领T恤衫。十四岁时她身高超过我,此后一直比我高小半个头。虽然和我记忆中的样子相差不大,但披肩发和碎刘海使她显得比实际岁数年轻。桌上的小蜡烛闪闪烁烁,她的脸在昏黄的光下看不出一丝皱纹,乌黑的头发还是那样浓密,脸上带着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笑。她越来越像她妈妈,据说她妈妈活泼好动,还当过长跑运动员。这使她在整个中学时代,面对八百米跑神态自若。而我显然已露出老态,总要刻意收一下小肚子。
那天,我们之间没有出现尴尬的沉默。她的两只手动个不停,她几次三番提到她儿子,说他已经会说三国语言,平常爱弹吉他。说到他的一些趣事时简直绘声绘色。从照片上看,是个瘦巴巴、长得还不错的男孩,我注意到,他的下眼皮长了颗痣,有点突兀。“他现在迷上了重金属,卧室墙上贴满了罗柏僵尸的海报。”看来我们喜欢同样的乐队,我心里嘀咕。
“你能相信吗?我儿子已经十五岁了。”她说。
真是难以置信。我想起那年夏天,她告诉我她决定休学一年时的情景。“看来你从来没后悔过,”我说,“如今大家一定都很羡慕你,那么早就当了妈妈。”
“是啊,”她赞同地点点头,“你说得一点没错,有时别人把我们看成姐弟。”但她突然摇了摇头。她显得若有所思。但是很快,她又露出微笑。
她还说了说她的新男友,一个喜欢拍狗的摄影师。说到他时她拿起手机,给我看了那男人给狗拍的好几张照片。我微笑着点头,对每张照片都给了几秒钟的注意。我只说生活中好的一面。我没有孩子但我出了好几本书。我都去过哪些地方玩。
感叹、赞美来来回回了好一会儿。无关痛痒的话题而已,我们之间的气氛却很活跃。她聊得那么起劲,没有喝酒脸却越来越红。我不记得她有过这副样子。那些年,她话不多。有一次,她用大拇指甲沉默着掐自己,掐得那么厉害,为了一件什么事呢,我已经不记得了,竟然掐出了血。
我们都考上了复旦大学,我在外语系,她在高分子科学系。据说那是她父亲的意愿。她总在教室里埋头学习,因此我很少见到她。即使在食堂见到,她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我经常去图书馆,找一个靠窗的座位,看一整天的书。小说是读不完的。很快我交了新朋友,写诗的、玩音乐的、画画的。晚上一群人经常一起涌进国定路上的酒吧,酒吧墙是砖砌的,贴着外国乐队的大幅海报,音乐响极了。大家一边喝便宜的啤酒,一边讨论某个自以为至关重要的话题。他们身边总是围着许多女生,他们知道怎么和我们说话,说些什么。每个女生手里都拿着烟,没完没了,谁也不关心烟是从哪来的。烟头被揿灭,被掐灭,被踩灭。在烟缸里,在木头桌上,在水门汀地上。可是面对那些话题我既没有立场,也没有观点。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争吵,而我没法谈论的东西太多了。我努力跟上他们的讨论,很多夜晚都困得要死,另一个我浮在半空中看着我:你真的觉得这些很有意思?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一开口说话,语速就很快。这只能暴露出我的紧张、兴奋。(自认有身份的人,总是把语速控制得极其缓慢。)每段话开始之前我都加上一个疑问句。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后来的男友喜欢这样反问我。)渐渐地,我喜欢上了几个玩摇滚的学生说话的方式。他们说话全都以“操他妈的”开头,没有诗社那些人抽象的用语,或者含义不明的措辞。和他们比比,我的想法也没有那么不成形。“操”,真是一个清晰的表达方式。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经常重复这个字。
不上课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他们的地下排练室。我在那里看书,慢慢喝我的啤酒。有天下午,只有吉他手在。他自己弹了一会儿,突然探过身来吻我。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疲惫还是厌烦的神情。(毕业后我去听的摇滚演出多了,发现那样的神情简直是随处可见。)他解开我的牛仔裤时,我没有拦他。我们在一堆用来消音的泡沫板上做爱。我很快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屋子里漆黑一片,伸手一摸,发现身边空着。我坐起来,还是感到困倦。角落里,音箱灯一闪一闪,他戴着耳机坐在那里。红色的光一闪一闪。某个我听不见的旋律在一闪一闪。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几次。每一次,我都坐在泡沫板上,赤裸着身体,注视着他在黑暗中,一个人听着打过口的唱片。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在校园里碰见章琳。我们站着简单聊了几句,她说真羡慕我的生活。“你们系就几个女生,我觉得你可以恋爱了。”我说。她摇摇头,低头看着脚尖。“晚上我们要在相辉堂排话剧,你来玩嘛。”出乎我意料,她来了,远远地站在那里,冲我笑了笑。比我高一个年级的男生走向她,毫不费劲地和她搭上话。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露出整个额头。他们要我介绍她。我看见她两只手绞在一起。“他们都是食肉动物。”她在我耳边悄悄说道。她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我目送着她的背影,感到如释重负。
有天晚上她来寝室找我,告诉我她开始画漫画了。这是她来看过我们排话剧之后几个星期的事。“画漫画?”我惊讶地反问。“嗯,功课太无聊了。”我们坐在下铺同学的床上,屋里很安静。可能期末考试快要到了,大家都去了自修教室。“好吧,”我说,“我记得你妈妈画的那些时装画很漂亮。”“怪就怪在这里,我一直以为我更像我爸。”她那身为教授的父亲,总是在学校,总是在工作。中学七年,我只在放假时见过他几次。圆圆的脑袋,粗粗的胳膊,相貌平平。我还记得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喜欢化学吗?”
“我现在越来越不想去上那些专业课了,我想换个系,重新开始。”她随手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涂涂画画,勾出一个九头身的长发美少女。“你说,我是不是失去了理智?”美少女笑得很美丽,没有一点迷惘的表情。我放下本子,叹了口气。中学七年,我一直觉得她的生活大体上比我有规划、有条理。“你都读了那么多小说,应该可以建议我点什么……”我摇摇头。她打量着美少女,美得真是没啥特点,然后看着自己的手,看了似乎很长时间。
屋子里有点冷,我们越坐越冷,于是一起下楼,去东门那里买酸辣粉丝汤。“我现在有点明白你写诗时的感觉了,”她对我说道,“是不是每一笔下去,都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已经不写诗了。”我说。那时我正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可我身边所有朋友都在写诗。我把话题转到玩摇滚的男生身上。她说她觉得他们任性、傲慢,换女孩和换首歌一样。
“你现在还画漫画吗?”
“早就不画了,有数学就够了。统一、对称、简单。关于这个世界,数学足够表达。”
儿子两岁时她突然决定去德国念数学,一直念到获得博士学位,进了一所地方大学,做起了助理教授。
接下来她问起我的写作情况。有大半年,我几乎什么都没写。我心里还有什么能展示出来呢?我用一些工作掩盖这一事实:在一本纯文学杂志做编辑;指导一些年轻的写作爱好者;参加各种读书会;研究一些历史人物……
“真不错,”她说,“我还记得你发在复旦校刊上的一篇散文。那时你喜欢用寂静、阳光明媚、烟雨迷蒙那些词儿。”
这个夜晚不需要回首往事的。我们的情况都不错。
吃完甜品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总是说回她儿子身上去。她拥有我所没有的,但我总是觉得,等待孩子长大的过程更是一个负担。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从来没在乎过,不是吗?
在餐馆门口分手时,她突然提出,明天想带儿子和我见见,一起逛逛我们少年时逛过的那些地方。身后传来一些人分手前醉醺醺的说话声,我感觉有什么在戳我的太阳穴,duang,duang,duang。
四月一日,愚人节。在“步高里”门口,我见到了一个鸭舌帽少年,即使长长的头发把他的眼睛挡住了一半,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章琳看见了我,朝我挥手。前一天晚上,在出租车上,我已经在脑海里制定了计划。我要带他们去一下尚街LOFT。我们曾经住过的棚户区被夷为平地后,建起了这样一个时尚生活园区。百度百科对它的描述是:国际时尚中心地标,“上风上水”之钻石地段。然后,沿着建国路,可以一直走到“田子坊”。气温高到了二十五摄氏度,在这样的大白天,牢记着“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的我,还穿着呢子外套。太阳高挂空中,阳光热昏昏的,天上完全没有云,光影在地上刺目地流动。为了打破我们三人之间的沉默,我没话找话问那男孩,“这里怎么样?天气真不错,是不是?”他礼貌地点点头,把长袖T恤的袖子卷到了肩膀上。章琳走到了我身旁,黑色的长发盘在脑后,她的样子跟我记忆中她母亲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我注意到,过了一会儿,男孩偷偷地戴上了耳机。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想他听不见我说话了。但是过了几秒钟,他又偷偷地摘下了一边。那一半耳机线在他胸前一跳一跳。
我努力把注意力放在此时此刻,章琳在我右手边走着,而我尽职地指出一些变化,像是真有什么人会感兴趣。但我的眼角余光忍不住向后瞟去。男孩的T恤,一半塞在牛仔裤里,一半荡在外面,看起来整个人都松松垮垮。我带他们看了我们曾经流连忘返的几个角落,告诉他们梧桐花园里发生的一些故事,以及嘉善路上,哪家馆子适合吃夜宵。章琳不时插上一两句,让谈话顺利进行。男孩对一切都似看非看,不像他妈妈,不时对一些东西大加赞赏。我们逛进“田子坊”的时候,男孩问,他可不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冰的饮料。
我们选了一家二楼有露台的餐馆,可以俯瞰下面的街道。他们在我对面坐下。“你还好吧”,章琳一边翻看饮料单,一边头也不抬地说,“你看上去有心事。”
“有点怀旧吧,”我说,“没什么。平时我太忙了,都没来过这里。”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
“我都想不起来以前这里是什么样了,不过总觉得天要更蓝一点。”
男孩点完可乐,把手伸进自己的斜挎包,从里面掏出一台KINDLE,低下头开始看起书来。他会喜欢读哪一类书呢?看着章琳和儿子一起,我心里开始产生动摇,她的选择,无疑不是错的……一切都表明她过得非常幸福,这多少打破了我内心的平衡。我以为我三思而行、仔细考虑了。我找人算过命,看过手相。星盘或者塔罗牌,也都一一试过。我总是想知道,未来会怎样。可是十几年前的我不会想到,我还在这里。自己现在拥有的,到底是该为之高兴,还是黯然神伤呢?直到放了柠檬片的苏打水端上来,我才把自己拉回这个让人热昏头的日子。
“只待一星期,时间太紧了。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你打算带他去哪里看看?”
“外滩、东方明珠,有这些就够了吧。”
我们从外滩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讲到了德国的教堂,每周一次的自由集市,啤酒和肉肠。男孩已经喝光了可乐,把空杯子推到了桌子的中间。“要不要再来一杯?”我问他。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一摸他的头发。他摇摇头,“我想下去逛逛。”他把手搭在他妈妈的肩膀上按了按,噔噔噔地下楼了。
章琳探出脑袋,打量了一下街景,突然回过头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大学的那段日子?”
“当然想过,但不会经常想。”一种焦虑的情绪从胃里泛了上来。
“有时我会变得很怀旧。”她一边说着,一边转动起桌子中间那只空杯子,“昨天见到你后,想起了很多事。心里很乱,也很激动,不过,真的很高兴见到你。”
我不知怎么说下去。确实,她也把我带回到了从前。那时候,一切都那么简单。
“我那时……走得很艰难,我已经把自己连根拔起了,就只能换个地方再把自己种下去。”
“你现在很好,真的。”
“也许吧。”
短暂的沉默。
“那天你为什么不等等我?我想和你一起走的,但是我喝得太多了。”她越过我的肩膀看着我身后的某个地方,然后把目光又转向我,“我醒来时,他已经不在了。他们都不在了。”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十五年前的盖子就被揭开了。也许我将永远背负那种内疚感,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到我。脑袋开始一跳一跳地疼。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好像从接到电话起就知道她想说什么了。露台背光,有点太阴凉了。外面阳光那么好,但我没法起身离开,走进那片阳光里。于是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等。
那天晚上,是那几个玩摇滚的学生第一次登台的日子。其实只是作为暖场乐队,表演了三支曲子。但我们都很高兴。我叫来了章琳。她刚洗完头,散发着草本植物的清香。她现在走到哪儿,随身都带着她那本素描本。在酒吧里庆功的时候,她一会用它懒洋洋地给自己扇风,一会又掏出铅笔,草草画点什么。
闹到近午夜,酒吧要关门了。一多半人先回了宿舍,我和章琳跟着剩下的一些去了排练室。烟、酒、灯光、暖意,让我瘫在了椅子里,昏昏欲睡。这时章琳捅了捅我,将翻开的素描本推给我看。
“他和他们都不一样。”她说完,期待地看着我,似乎该轮到我点评了。
我扫了一眼。画面上的男孩,耳朵里塞着耳机,闭着眼睛。
“是啊,他总是在听音乐。”我说。我注意到,她把他下眼皮上的那颗痣,画成了一颗星。
我把本子合拢,推还给她。
“要是能让他摘掉耳机,听我说话就好了。”她出神地看着他。我把一瓶刚打开的啤酒递给她。总是有人拿来刚打开的啤酒。酒瓶子握上去冰凉冰凉。我问旁边人要来一支烟。我一边抽烟,一边努力让自己去看鼓手,去看主唱,去看键盘手,去看贝斯手。他们在屋子里窜来窜去。
“真奇怪。”我说。
“奇怪什么?”
“他们怎么就那么高兴。”
“你不高兴?”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口香糖,撕掉了包装,塞进了嘴里。
持久香气,祛除异味。她停止咀嚼的几个瞬间,嘴唇微微分开,我感觉到她清新的呼吸。清新又急促。就像春耕时节雨后泥土的气息,渴望着被翻动。我怎么会突然想起鲁藜的诗来: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房间里弥漫的烟气让我全身无力,只想回到自己舒服的上铺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去食堂打几个好菜,然后再喝点儿可乐,也许再去图书馆翻翻最新的杂志。
但她留在了那儿。
我是把她留在了那儿。
然而。
没有人送我,没有人和我告别。我顺着马路朝东区的女生宿舍走去。头开始疼,好像一头撞上了墙。我在路灯下用手捂住了脸。
我睡醒起床,发现才早上十点。洗漱完,吃了一个蛋饼,在修车摊上让人给自行车打足气,我骑了上去,沿着国定路、邯郸路、曲阳路、东体育会路,一直骑到了甘河路岳阳医院。
前几天,我向章琳借了几百块钱。“你要用这笔钱做什么呢?”
“马上要二十岁了,我想给自己买件礼物。”
“想买什么呢?”
“还没想好……”我说。
她没再问什么。
在那几十分钟里,我忘记了章琳,忘记了凌晨的悲伤,我把心思集中在双腿上。暖融融的阳光晒在我的背上,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棵阳光开朗的向日葵。这片刻的阳光给了我勇气和决心。
事情最后总会过去的。
那之后,我没再找我的那些朋友。我不再记得他们的脸,即使我在梦里梦到过,他们都只是模糊的、若有若无的影子。我开始用功读书,大清早就离开宿舍,穿过整个校区,步行到燕园,一路背诵单词。
我再次见到章琳是在三个月后,她因病申请休学一年。那时棚户区已经拆迁,他们一家没要房子,拿了补偿金,搬进了太原路的别墅。那次我没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一直笑眯眯地,说整天忙着做小衣服,还说读书急什么,任何时候,想读都可以再读。这时,章琳从一本《育儿指南》上抬起目光,对我礼貌地微笑,说谢谢我来看她,然后让我保密。我很快就告辞离开了。那之后,我没再见过她。我们的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十几年。
“哪天来德国玩吧。我们开车去黑森林。”
“好的。”我说。
她笑了。
“你看上去,真不错。”我由衷地说。
她的儿子还没影子。她从包里掏出一包烟,一只打火机。我想告诉她,我刚做完手术,不能闻烟味。她把一绺掉下来的散发拢到耳后,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大口淡蓝的烟雾,探过身来,像二十几年前一样,不容置疑地,把它递给了我。我犹豫了一秒钟,还是接了过来,轻轻地,把它放进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