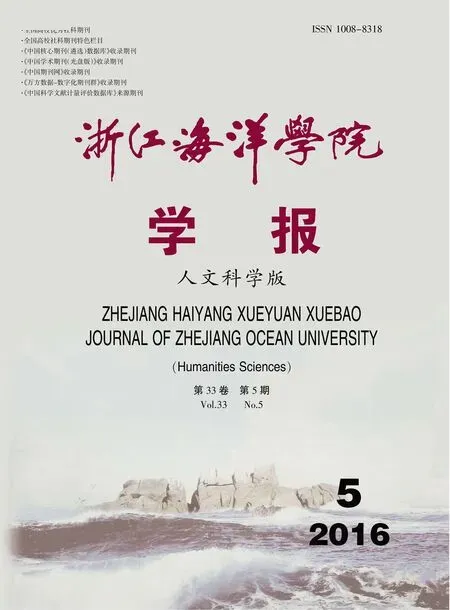异质同构的自然与女人
——论萧红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蕴
2016-01-16岚张雅芳
张 岚张雅芳
(1.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舟山316000;2.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浙江舟山316000)
异质同构的自然与女人
——论萧红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蕴
张 岚1张雅芳2
(1.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舟山316000;2.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浙江舟山316000)
生态女性主义虽然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又是来自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但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萧红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与自然相同的生命节律,女性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女性与自然互喻性的苦难形象,以及“自然化”的文本特征等,都显示了萧红的小说内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蕴,这使得她的作品超越了其身处的时代,具有鲜明的先锋性。
生态女性主义;同质异构;自然;女人;萧红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它是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最早由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尼在1974年出版的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她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父权制的世界观。这一观点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并为女性的社会存在以及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虽然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又是来自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但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一位年青的女作家就以她身为女性的独特人生感受、对故乡东北农妇们的深切悲悯之心,以及童年时亲密触摸自然的经验,写出了自然和女性双重苦难的悲壮史诗——她就是萧红。萧红小说内涵的多义性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已被学者们不断挖掘,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更是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阐释。但是今天,当我们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解读萧红时会发现,萧红小说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女性或北方农民的苦难,而是对自然和女性命运的双重关怀,是同时为自然和女性立言。她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对立思维统治下的对自然、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压迫,向往建立一种男人和女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互相依存的新型关系,其内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蕴使萧红的小说超越了她身处的时代,具有鲜明的先锋性。
一、自然的“女性化”和女性的“自然化”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一样,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源。女性天生比男性更容易亲近自然,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女性的心灵也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笔者认为,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保有着自然的、情感的、天性的东西,与自然更为接近,也更容易感受到自然的脉动和天籁之音,所以女作家常以她们迥异于男性的“自然思维”和“自然语言”来描绘绚丽多彩的大自然,使得自然在她们笔下呈现出女性化特征。总之,女性与自然互相依存、互相慰藉,正如苏珊·格里芬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①这种女性和自然的联系在东西方文化中随处可见。西方有“大地之母”盖亚女神的传说,中国有女娲补天的神话;埃及人常把女性的子宫当作生命复苏和谷物丰收的象征,中国人也有“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的女性生殖崇拜……。女性养育着人类,正如大自然哺育着世间众生,女性与大自然之间息息相通,共生共荣。
女性与大自然的这种息息相通的依存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作家萧红的笔下表现得非常典型。她笔下的女性是“自然化”的,自然也是“女性化”的。她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有许多诗意的段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而充满生气的自然生态景观。作家以一个女童的视角感知自然的活力,通过幼小心灵与自然的亲近和友爱,呈现了一个与荒凉冷漠的体制文化相对立的灵性化的生态空间,以她的后花园为例:
“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②
在后花园里,自然的一切都是活的,是自由自在,随性而生的:倭瓜爬上架或爬上房,黄瓜开谎花或结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蝴蝶、小鸟随意的飞,在这样的生态空间中,“我”完全融入其中,“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③觉得“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④,生命的顽强与欣悦尽现天地之间,“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⑤。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天地里,“我”和“祖父”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欢欣和自由:“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踢飞了。”⑥在这里,后花园、小女孩和老人三位一体地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画面。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人即自然,自然即人,虫鸟蝴蝶、花草藤蔓都有灵性和自由的意志,人与天地融为一体,能够互相交流,融洽而默契:“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⑦儿童视角和女性视角的双重叠合将人与自然纯净的乡土关系诗意化地呈现,田园牧歌的情调中洋溢着生机勃勃的生命色泽。在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天性呼唤中,萧红不自觉地发掘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女性亲和自然的特质,表现了生命的、和平的生态女性观。
如果说对美好大自然的喜爱和向往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勿论男女不分性别,那么从女作家萧红的视野中看到的则更多的是女性生命过程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律动,她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将人类以外的动物放在与人类平等的位置,使自然成为了言说的主体。在萧红那片充满了苦难的乡村大地上,生命不分人类与非人类都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第六章有一段生生不息的生命景象的描述:
“小风开始荡漾田禾,夏天又来到人间,叶子上树了!假使树会开花,那么花也上树了!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
……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⑧
在写完了叶子上树、树木开花、大狗生了小狗,母猪即将生育小猪之后,小说才写到五姑姑的姐姐、金枝、二里半的婆娘和李二婶子生小孩,期间还穿插了窗外墙根下,母猪生下了小猪。
生育本是哺乳动物的繁衍方式,尤其对于雌性动物来说,简直就是推不掉的使命和天职。尽管生命的诞生过程充满着血污和苦痛,但萧红是从天职的意义上来写生育,她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在完成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她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将女人的生育与动物的繁殖、土地的收获及自然轮回看作同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人的生命与宇宙万物的其它生命协调一致,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跟生态女性主义者把生态系统看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且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生死场》中,不仅生育过程中人和动物一样,而且那里人们的所有活动也都是动物性的。人以动物的方式支配着生命活动的方式,如成业和金枝河边幽会时没有花前月下的诗情画意,只有姑娘“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⑨,二里半“伏身到井边喝水,水在喉中有声,像是马在喝”⑩,王婆的“头发毛乱而且绞卷着。朝晨的红光照着她,她的头发恰像田上成熟的玉米缨穗,红色而且蔫卷”⑪,麻面婆“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⑫,说话“总是发着猪声”,取柴的时候像“母熊带着草类进洞”⑬。……总之,“他们的欢乐是动物性的,除肉体的欲望外没有欲望,他们的痛苦是动物性的,只有肉体的苦难而没有心灵的悲哀,他们的命运是动物性的,……他们的行为、思维、形态也近于动物,他们像老马般囿于习惯而不思不想,秋天追逐,夏天生育,病来待毙。”⑭在这种动物性的生存状态中,他们的情感显得冷漠而粗糙,唯一细腻动人的感情不是给人,而是给了牲畜和庄稼。《生死场》中金枝因为踩坏了庄稼挨了母亲的打,之后作者这样写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⑮书中老王婆与即将走进屠场的老马相依难舍的场景更是让人动容、催人泪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把动植物当成家庭一份子的那种难以割舍般的亲情。
在萧红的小说中,不仅女性的生命与自然众生平等,而且“自然”也成为女性的精神家园。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生态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家园意识,它是对人类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真诚眷恋与祈愿,而“自然”在这里就成为这种家园意识的载体,成为人们(尤其是女性)的精神避难所和心灵栖息地。女性的痛苦心情往往在自然中能够得到感应和抚慰,同样,对自然的礼赞和诗性表现,也可以实现对沉重现实和女性苦难的暂时逃离。短篇小说《牛车上》中,饱受了失去丈夫痛苦的五云嫂坐在牛车上,远道去看望做学徒的儿子。在开满野花的旷野上,“五云嫂下车去给我采了这样的花,又采了那样的花……她几乎是跳着,几乎和孩子一样。回到车上,她就唱着各种花朵的名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像这样放肆一般的欢喜。”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五云嫂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的苦难,忘却了人世的悲凉,短暂地绽放着生命的自由和诗意。同样,在《呼兰河传》中,当“祖父”和“我”挨骂时,“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够止住,不知哪里来了那许多的高兴”。⑰在这里,“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⑱现实中的恶与后花园百花盛放的热情拥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后花园成了童年的“我”摆脱孤独和亲情冷漠的精神百花园,正如法国作家莫罗阿所说:“最广阔最仁慈的避难所是大自然”。⑲
从具体的文本特征上看,萧红的自然书写也迥异于男性作家。首先,与大多数男作家的理性思维不同,萧红的小说大多以一种充满感性和温情的“自然思维”来描绘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她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自然,把自然当作想象中的“他者”,而是最大限度地打开各种感官,直接参与或感受自然,使叙述者本身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她也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使自然成为“为我之物”,而是把自然当作“自为之物”,正如作家白桦所评价的:“萧红完全用感性的、女性的、细腻的眼光,而且充满了情感来表达出她的很高的理念。”⑳小说《旷野的呼喊》中这样描写小村庄夜的宁静:“脱落了草的房脊静静的在那里躺着。几乎被(风)拔走了的小树垂着头在休息。鸭子呱呱的在叫,相同喜欢大笑的人遇到了一起。白狗、黄狗、黑花狗……也许两条平日一见到非咬架不可的狗,风一静下来,它们都前村后村的跑在一起。”㉑这里的自然万物都具有了灵性。同样,《呼兰河传》中后花园的生物也成了自我言说的主体:“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来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㉒在这些自然书写中,萧红都从书写对象的视角体恤它们的境遇,让自然万物尽情地言说自身,由此打通了物我界限,达到了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境界。
萧红小说“自然思维”的另一个特征则表现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她试图改变以往将环境仅仅作为场景、背景和事件的附属而存在的习惯,不是以“人”及人的活动作为结构轴心,而是以一座小城或一个村庄为主轴来安排故事,于是她笔下的这块土地不再是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而是变成了故事的一个角色,甚至是主角。将非人类的自然当作故事的主角,是自然言说的一种方式,这也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一种叙述方式。《生死场》以东北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山村为轴心,依次写了“麦场”、“菜圃”、“老马走进屠场”、“荒山”、“羊群”、“刑罚的日子”、“罪恶的五月节”、“蚊虫繁忙着”、“传染病”……。从各章标题可以看出,小说的主角并不是单个的人或人类群体。在这里,人类并非万物的中心。作者把小山村里的动物、植物、环境及人的活动都纳入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万物一样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这与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不谋而合。同样的,《呼兰河传》以萧红故乡呼兰河小城为主角,写了小城的气候、地理、天象、风俗和人物,全书也没有通贯紧密的情节,没有中心人物。人物的活动与自然万物的律动放在同一层面上展开,各章独自成篇,结构松散,但连缀在一起却又像生命一样和谐。用非逻辑的、直觉的散文化方式,将小城的各个方面连缀在一起,同样体现了萧红创作的“自然思维”特征。
其次,萧红小说的这种“自然思维”是通过她独有的“自然语言”得以表达的。这种“自然语言”在萧红笔下具体表现为感性的、孩童似的语言风格,它与男性作家理性的、规范化的语言不同,充满了返璞归真的自然野趣: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
那拉磨的,夜里打着梆子通夜的打。”㉓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㉔
这种直白而稚拙的语言表达更接近女性生存体验的本真状态,使得女性所特有的诗性气质与自然万物毫无痕迹地融为一体。
二、自然和女性的“边缘化”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自然和女性有着大致相似的命运。在人类文明的原初阶段,由于自然知识的严重缺乏及生产力的低下,使得人类对自然极尽敬畏之心;此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对自然认识的加深,人类开始征服自然,发出“人定胜天”的狂妄叫嚣,于是自然被粗暴践踏、蹂躏。与此相似,女性的地位也经历了由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女性崇拜,到农耕社会备受奴役和压迫的发展历程。自然和女性有着类似的命运,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男性统治女性和人类统治自然之间具有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道德危机之间具有同步关系。这种统治关系的根源就是父权制文化,它具体表现为二元制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在父权制二元对立的统治逻辑下,人类居于自然之上,可以肆意掠夺和践踏自然;而在人类内部,男性居于女性之上,可以任意支配、统治甚至蹂躏女性。所以,在父权制视阈下,女性和自然都被当作“他者”而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则反对将生命作等级划分,反对二元对立理论,提倡生命的平等观。他们认为地球上的生物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完整的生命网中,没有上下高低贵贱的等级之分,所以他们积极声援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萧红的作品就处处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维护。
作为一名饱受男权压迫和摧残、饱受性别屈辱和苦难的女作家,萧红的小说常常充溢着对生命等级制的不平和愤懑之情。女作家临终时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㉕这句话沉痛地道出了萧红孤苦一生的缘由,也表达了她对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的反抗和呐喊。在《呼兰河传》中,当她写到年轻女子不堪夫家的虐待而跳井自杀,认为这种行为比男子要勇敢时,有过这样一段议论:“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性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㉖又比如在写到老爷庙和娘娘庙里,老爷像被塑得威风凛凛而娘娘像则非常温顺时,作者又发出这样的感慨:“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所以她断定:“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㉗这些感慨凝聚了萧红在两性生活上诸多难言的委屈和不平,是她个体人生经验的伤痛总结。
或许正是出于作者个体独特的人生经验及女性集体被边缘化的现实,萧红的作品常常充满了对父权制二元对立文化下弱势群体,包括女性、孩子和自然的同情。在她的笔下,自然往往呈现出一种苦难负重者的形象:
“风陵渡侧面向着太阳站着,所以土层的颜色有些微黄,及有些发灰,总之有一种相同在病中那种苍白的感觉。看上去,干涩,无光……”㉘
“大树林子里有黄叶回旋着,那是些呼叫着的黄叶。……凄沉的阳光,晒着所有的秃树。”㉙
这一片寒冷、肃杀、枯燥、衰败、凄凉的自然景象成为萧红所有故事的背景:春季狂风肆虐,盛夏蒿草杂乱,秋天枯叶飘零,冬日酷寒漫长。不仅如此,在她笔下,自然的负重者意象与女性个体或群体的悲剧人生还常常相互隐喻,女性与大自然常常融化为同一种惨淡悲凉的意境。
女性主义学者李银河曾经对自然和女性所受的欺凌和屈辱作过形象的比喻:“对地球上一切形式的强奸,已成为一种隐喻,就像以各种借口强奸妇女一样。”㉚确实,在世界各国的文学语言中,有许多女性与自然同受欺凌的互喻性词语,诸如“对大地的强暴”,或者“开垦处女地”等等,这些与女性和自然相关且带有性别歧视特征的语言,不仅反映了女性命运与自然命运的紧密关联,同时也反映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与凌辱。萧红笔下的自然意象就常常与女性的苦难人生相互对应和观照,比如《呼兰河传》一开篇就是一段严寒大地被冻裂的自然描写:“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㉛,在《旷野的呼喊》中,陈姑妈的双手就烙上了这种土地的印迹:“冬天因为风吹而麻皮的手,一开春就横横竖竖的裂着满手的小口,相同冬天里被冻裂的大地,虽然春风昼夜的吹击,想要弥补了这缺隙,不但没有弥补上,反而更把它们吹得深陷而裸露了。”㉜小说将旷野、大地、山林、人声、风声、家畜声以及被旋风横扫过的柴栏,被暴雨洗涮过的庭院都纳入陈姑妈这一女性人物的视线之内,与女性人物的命运相互映照。女性的苦难与土地的沧桑相互交织,女性成为母性大地的符号载体。
不仅严寒冻裂了大地,呼兰河小城的街道上还有个一年四季都开着大口的泥坑。小说第一章用近六千字的篇幅描述了那给人带来许多烦恼和消遣的大泥坑,写那些掉进泥坑的猪、马、鸡、鸭们如何在里面绝望挣扎,而坑边看热闹的人却不断喝彩叫好,这与第五章小团圆媳妇被摁在大缸里用滚烫的热水泡身、浇头,拼命挣扎却得不到围观者的一丝同情和帮助何其相似(见《呼兰河传》)。“裂口”和“坑洞”成了女人受难的载体、见证和象征。在萧红的小说里,我们随处可见女性身心被撕裂的痛苦:女人们生育时的生死挣扎,金枝被成业粗暴地压在身下泄欲,老王婆死而复生又被丈夫用扁担“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㉝,月英病瘫在床,丈夫不闻不问,身体成了蛆虫的洞穴(见《生死场》)……。
正是由于女性在人类世界中的卑弱地位和在男权社会里的失意处境,使她们更容易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动物产生同病相怜的情感,也更能感受到弱势群体的苦难。《生死场》中,当王婆牵着马去屠宰场时,那不得不卖马的无奈,对马的眷恋不舍,和为马儿送行时锥心般的痛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动物相依难舍的悲情画面:“王婆的手颤抖着”,“什么心情也没有”,当看到老马的“眼睛哭着一般,湿润而模糊”时,“悲伤立刻掠过王婆的心孔”,她“哑着嗓子”了。这中间还穿插着萧瑟的自然环境描写:“深秋秃叶的树,为了惨厉的风变,脱去了灵魂一般吹啸着”,“深秋带来的黄叶,赶走了夏季的蝴蝶。一张叶子落到王婆的头上,叶子是安静的伏贴在那里。王婆驱着她的马,头上顶着飘落的黄叶;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㉞这里,动物的苦难、大地的苍桑与一个老女人的悲伤融为一体,难以剥离。老王婆即将失去老马的痛苦融入了黄叶飘零的萧瑟情境中,构成了一幅悲戚的离别画面。
总之,在萧红笔下的那片乡土世界里,不管是女人像动物一样生产,或者孩子不如牲畜、庄稼般宝贝,或者人与动物相互温存的画面,都凸显出弱势个体或群体的低微、渺小与无奈。
然而,在父权制文化下,不仅女人和动物、和自然一样都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女人的境遇在许多时候还不如动物。猪、狗们在生育时还能得到人类的帮助和照顾,至少没有同类的欺侮,而女人生产时,不仅要忍受上苍给予的自然痛苦,还要承受来自同类男性的欺辱和打骂。当五姑姑的姐姐被难产折磨得死去活来时,酗酒的丈夫却还使唤她伺候自己,得不到回应就用长烟袋砸女人,并将大盆冷水泼向女人(《生死场》);王阿嫂临产前还要给地主干活并遭地主踢打难产而死。除了女性的身体和生命遭受男人的摧残与折磨,萧红的作品还进一步揭示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自然天性和女性人格的压抑、摧残与异化。《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本是个“脸长得黑忽忽,笑呵呵的”健康活泼的少女,可到了老胡家后,却因她“十四岁会长得那么高”,“坐在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㉟而遭致邻居们的非议,也促使婆婆对她毒打:拧她的大腿,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用针刺她的手指,最后被折磨而死。害死小团圆媳妇的凶手(婆婆)和帮凶(邻居们)大多是女人,但是她们代表的却是父权制下夫家的权威,她们本身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同时又成为男权思想的自觉遵从者和执行者。这样,男权思想不仅无情地践踏摧毁了女性的肉体生命,而且压抑和摧残着女性的自然天性,异化了女性正常的思想和情感。萧红以入木三分的笔触揭露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男权家长制罪恶,写出了她对不平等两性文化的愤怒,潜在地表达了回归正常自然的性别精神生态的强烈诉求。从性别上对二元对立的不合理价值观进行消解,显示了萧红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对性别精神生态的思考同样表现在萧红对待战争的态度上。生态女性主义者竭力推崇那些洋溢着关怀、同情的文学作品,指责或批评充盈着权力、功利性的话语。萧红的作品属于前者。小说《生死场》长期以来被归入抗日文学之列,但是当我们去意识形态化后重新解读这部作品时,可以发现萧红对战争的看法更接近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小说后半部分在写到日本人打进东北这个小山村后,李青山组织村里的年青人去打鬼子。北村一个寡妇的儿子被日本人打死,寡妇疯了似的哭着向李青山要人,之后和三岁的小孙女一起上吊自杀了。小说这样写道:“三岁孩子菱花小脖颈和祖母并排悬着,高挂起正像两条瘦鱼。”㊱这里萧红没有把抗战放在固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没有同类作品歌颂抗日英雄的陈词滥调,更没有像男性作家那样肆意渲染暴力和血腥,而是以温情悲悯的女性情怀,从一个老寡妇失去儿子的悲痛,从老人与孩子鲜活生命的无辜逝去,来表达她对战争的抗议,对暴力的痛恨。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崇扬那些充满温情、护佑万物的女性生态伦理,用这种女性的生态智慧消解男性的好勇斗狠与热衷武力,也许世间可以多一些和平与安宁。
总之,萧红的小说通过对自然、对女性权利的认同,体现了她对人类的生存性关注。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在萧红去世30多年后才出现的,但是当我们今天将女性视角与生态视角有机结合重新解读萧红的小说时,可以发现,她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热爱自然、崇拜自然的女性精神,同情弱者、护佑万物的女性伦理,洋溢温情、充满感性的女性思维,都表明萧红的小说早已触及甚至突破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全球生态问题愈加严峻和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的今天,萧红的这些文学思考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生态建设乃至女性解放,对于人类寻求诗意化生存之境的努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苏珊·格里芬著,毛喻元译:《女性与自然:她内心的呼号》,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
②③④⑤⑥⑦⑰⑱㉒㉓㉔㉖㉗㉛㉟萧红:《呼兰河传》,见《萧红小说全集》(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554-555,558,557-558,552-553,554,557-558,565,554-555,587,682,542,549,499,597-599页。
⑧⑨⑩⑪⑫⑬⑮⑯㉑㉘㉙㉜㉝㉞㊱萧红:《生死场》,见《萧红小说全集》(上),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416,407,413,405,406,424,142,305,212,427,304,456,427-428,493页。
⑭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⑲[法]莫罗阿著,傅雷译:《人生五大问题》,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0页。
⑳冯羽:《呼兰河畔访白桦》,转引自张抗:《萧红小说全集·序》,见《萧红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㉕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㉚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The Nature of 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 and Women——On the Ecological Feminist Implication of Xiao Hong’s Novels
ZHANG Lan ZHANG Ya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s’Education,Zhejai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00)
Although the ecological feminism,a trend of cultural thoughts from the west,came into being between the 1970s and 1980s,but in China,as early as in the 1930s and 1940s,Xiao Hong’s novels had already reflected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feminism,embodying the same life rhythm of femininity and the nature,the interdependence of femininity and the nature,the intermetaphorical miserable image of the femininity and the nature as well as the text features of“naturalization”,and so on,all of which enable her works to surpass the age in which she lived and to be of remarkable pioneer spirit.
ecological feminism;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the nature;women;Xiao Hong
I207.42
A
1008-8318(2016)05-0042-07
2016-08-23
张岚(1964-),女,江苏宜兴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