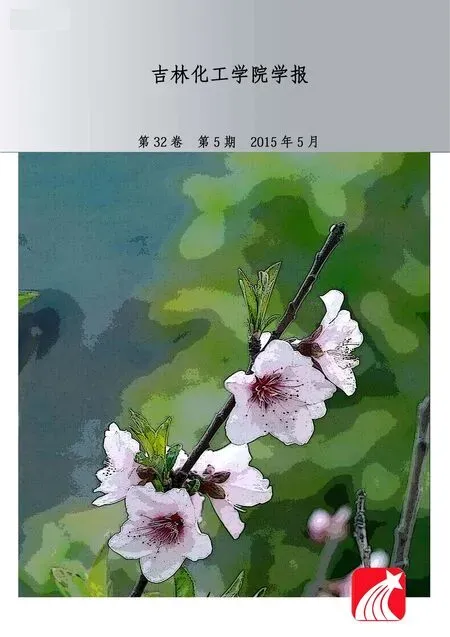“为人生而艺术”——茅盾早期(1919年~1927年)文艺思想探析
2016-01-08曲立斌
“为人生而艺术”——茅盾早期(1919年~1927年)文艺思想探析
曲立斌
(吉林女子学校 女性研究中心,吉林 吉林 132108)
摘要: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生而艺术”,以要求“怨与怒”的文学,要求“血与泪”的文学,要求同情“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文学为基本特征,一九二五年实现了其文艺思想的转变,为人生的文艺思想是在同各种文艺流派的斗争中发展、完善起来的。
关键词:茅盾;为人生;新特质
收稿日期:2015-03-11
作者简介:曲立斌(1962-),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女子学校女性研究中心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文章编号:1007-2853(2015)05-0028-09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一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意义不仅是时间上的,它标志着在布满青苔的驿道上蹒跚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对“五四”运动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有着重要影响的爆炸事件,刺激着中国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神经。李大钊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①的开拓贡献;茅盾则从文学对社会革命积极影响的角度,在世界的背景上探讨了托尔斯泰和十月革命的关系,字里行间蕴含着“为人生而艺术”文艺思想的萌芽。他指出:“今俄之Boi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尔斯泰实其最初之动力”。把托尔斯泰看成是俄国革命的“最初之动力”,显然是幼稚的。但可喜的是,茅盾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对托氏的作品能够触及人生的重大问题,能够把“处于全球最专制之政府下,逼压之烈,有如炉火”的俄国“社会之恶现象”、“发为文字”,表示了极高的赞许。托氏言社会之恶,不仅能“破其假面具”,还能“确立救济之法”。也正是在“于人生之究竟,看得极为透彻”②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才引起茅盾的强烈共鸣。这种文学精神的感应,正是茅盾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原始引点。
茅盾明确地提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是在《现在文学的责任是什么?》一文里。在文学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中,茅盾鲜明地提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绝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接着,茅盾在以后所写的文章中,对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作了一步的阐述。
其一,茅盾认为为人生的文学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要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③的能力。而他的目光所注,主要是当时国民的劣根性。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有一种极不健全的人生观,因此,文学家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描绘生活的表层,而应把“全社会、全民族”的“普遍的弱点”④指出来,从而“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⑤这种认为文学应有“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生的缺陷”⑥的功利启蒙思想,是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潮影响下形成的。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出发,把文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把改变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同小说的社会地位相提并论,他所提出的“欲新一民之国,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对“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形成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人论文,也都是从民众思想的启蒙入手。鲁迅因家庭变故,由小康之家落入困顿以后,接触到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由此产生了“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⑦的“张灵明”、“任个人”⑧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在这里,茅盾和鲁迅的文学主张是相通的。他们对几千年来在以封建思想为主宰的政治经济关系统治下所形成的国民的弱点深感忧虑并痛下针砭,两者的区别在于:鲁迅是在得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⑨这一结论之后弃医从文的——改造“国民性”,不仅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也是作家战斗一生的锐意追求;茅盾则是在为人生的统摄下,在对中国历史进行“探本溯源”的基础上对国民的弱点进行理性的审视——他把对这种弱点的否定和对“善”和“美”的肯定包融在一起的。
其二,茅盾认为新文学是和贵族文学相对立,“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⑩“文学既为表现人生,岂仅当表现贵族阶级之华贵生活而弃去最大多数之平民阶级之卑贱生活乎”?他认为,文学不能只是贵族阶级肆意“感物吟志”的工具,不能只“载”封建统治者之“道”,而应使其“社会化”。基于此,他把世界“文学进化已见的阶段”概括为“个人的(太古)、帝王贵阀的(中世)、民众的(现代)”。而新文学正处于“帝王贵族”向“民众”的过渡阶段。近代俄国文学为“平民的呼吁”和反映“下流社会人的苦况”这一特色,也为新文学性质的根本改变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因此,茅盾呼吁:我们应该“在极短的时间内赶上去”。茅盾在这里表露的“平民”文艺思想,既不同于周作人倡导的以“普通”、“真挚”的文体,写“普通”、“真挚”的“思想与事实”的“平民文学”,又有别于李大钊以资产阶级博爱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写实”文艺观,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朴素的阶级观点,但这仅仅表明茅盾对封建旧文学反叛的深刻性以及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在他身上的积极影响,说茅盾这时就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来指导文学活动还为时尚早。
其三,茅盾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提出文学应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认为文学“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他精细地考察了先秦以来的文学传统,发现“我国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不晓得有人类的共同情感”。茅盾有时幻想文学能够超阶级超民族超时代地去表现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情感”,“在非常纷扰的人生中搜寻永久的人性”,从而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民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我们知道,在“五四”运动初期,无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力量还很薄弱,因此,当时新文学运动主要是以一些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为骨干的。茅盾虽然那时已经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接触,但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欧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如社会主义一样,对他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人道主义在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中曾经起过促进作用,流传到我国以后,在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以及恢复人的价值等方面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它还不是一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尤显得捉襟见肘,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它也就成了茅盾前进中的羁绊,因此,茅盾很快就和它分道扬镳了。
其四,茅盾认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在考察西洋文艺时,他始终强调的是“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而这种“系统的经济的介绍”,又是以不应“忽略了文学进化的痕迹”为其出发点的。首先,茅盾把文学史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流动”的历史,充满着无限生机。这样,以进化论的尺度来考察西洋文艺,就清晰的昭示出其嬗递更迭轨迹。其次,茅盾认为文学史上的每一次“进化”,绝不只是名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是文学观念的更迭,期间每前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并且把文学的使命也重新估定了一个价值”。所以,他希冀“西洋文化进化途中所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的必要”。再次,“进化”的观点,赋予茅盾以史识和史感。因此,茅盾认为“新”和“旧”在性质,不在形式。正因为文学史上每一次“进化”都是对前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否定和抛弃,从而使文学发生质的变化,他才颇为大胆的把新浪漫主义尊奉为文学的圭臬。虽然新浪漫主义是文学的极致,但中国的新文学还留在写实主义以前,距新浪漫主义还有一个过程,如果“为将来自己创造先做系统的研究打算,都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正是这种“进化”的观点,使茅盾没有超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而以清醒的理智正视现实,提倡写实主义。
以上四种观点杂揉在一起,一方面构成了茅盾“五四”初期为人生文艺思想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茅盾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复杂矛盾程度。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时代对文学发展的需求和制约以及他本人清醒严峻的性格特征和对祖国命运的急切关注。正是这种决定性作用,使茅盾没有“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而是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从一九二一年,茅盾完全把主要的注意力倾注到下层的劳动人民身上。他认为“真的文学”必然是反映时代的文学。“由浅处看来,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呵!”他呼吁有出息的文学家应把反映“第四阶级”的疾苦作为己任。茅盾正是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要求出发,把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又注入了新的因素:要求“怨与怒”的文学,要求“血与泪”的文学,要求同情“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文学。他以俄国文学为例,指出从果戈理一直到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不是描写黑暗专制,同情于被损害者的”。他认为“怎样的社会背景产生出怎么样的文艺,怎么样的文艺是怎样的人生反映”。凡是“处中国现在这政局之下,这社会环境之内”的文学家,“但凡不曾闭了眼,聋了耳,怎能压住我们的血不沸腾?从自己热烈地憎恶现实的心境发出呼声,要求‘血与泪’的文学”。茅盾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种,把“丝毫不曾受着西方文化影响的纯粹中国的老百姓”列为首,虽然他们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们有自己的信仰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观”,因此,“他们的思想很可以代表部分的中国式的思想”,而现在“描写此流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小说”,都把他们“描写成蠢物”,因而配不上“成为真的文学作品”。这实际上就是茅盾后来民族化文艺思想的雏形。虽然新文学的创作“并不以民众能懂为唯一条件”,但茅盾在思想内容上要求新文学为“第四阶级”服务的同时,也并未忽略创造民族的艺术形式。茅盾是把对民众思想的启蒙和其鉴赏力的提高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当时的某些新派作品之所以脱离人生实际,是因为这些作品仅从思想上认识到应该注意社会问题,反映“第四阶级”疾苦,但政治上的理解和掌握并不意味着就是艺术上的掌握,由于他们只注重于思想意念的表述,忽视了艺术形象的塑造,作品中人物不过是作者主观意念的传声筒,“结果思想上虽或可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未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像高尔基之做过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流过西伯利亚”,“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似乎是问题的症结。为此,茅盾号召有志于新文学创作的青年,“到民间去”,“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这也是茅盾倡导自然主义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三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现实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文学阵营内部继续分化,茅盾则以坚实的步伐,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由于党的活动日益增多,使茅盾的文学活动不得不成为“副业”。同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上海全体党员会议上,他担任了中国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的国民运动委员、委员长等职务,同时还和向警予同志专门分管妇女运动方面的工作。直接的革命活动和党的杰出人物的影响,给茅盾带来了思想上的飞跃,思想的飞跃又促进了文艺观的深刻变化,发表在一九二三年《文学》周报上的《杂感——读代英的<八股>》和《“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端倪。当时的文坛受唯艺术论的影响,刮起了一股颓废的唯美主义文风,而且颇有泛滥之势。恽代英、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以其敏锐的嗅觉,纷纷著文,对这股文化逆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中夏认为新文学应该“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量披露”。恽代英希望新文学担当起“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茅盾积极地响应了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他说:“喜欢躲避在幻想的世界里”,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快乐”的文学青年,不要再“逃避现实,借文字以自麻醉”,应该“从空想的阁楼中跑出来,看看你周围的现实状况”。他在全然反对那些脱离人生而且滥调的中国式唯美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对托尔斯泰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采取了保留。他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要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显然,这时的茅盾已经不满足于以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下层人民为主要特征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而应更多地提倡以“唤醒民众”、“激励人心”为己任的“肯定的文学”,揭示中华民族所蕴含的美的特性,这无疑又给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他的文艺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茅盾曾认为,在作家思想时代的划分上,决不能简单、机械地搞一刀切,如果我们观其“来龙”,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就指出:“世间万象,人类生活莫不有善的一面与恶的一面”,正因如此,古来对文学的功用就有“美”、“刺”之说,而浪漫派文学与自然派文学就是各走一端的,这“只代表人生的一边,到底算不得完美无缺,忠实表现”。“刺”的文学固然不可缺少,但“美”的文学更为重要。他确信:“一个民族既有了几千年历史,他的民族性里一定藏着善美的特点;把他发挥光大起来,是该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创作的前途》中他说,当今除了描绘现实以外还要“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一九二二年他又说:“我们要以我们那几乎不合理的自信力,去到现代的罪恶里看出现代的伟大!”,“我诅咒悲观的诗人,我甚至于诅咒赞叹大自然的伟力以形容人类的脆弱的文学!乐观!乐观!让我们扬起迷信乐观的火焰呵!”以上论述尽管是零散的、片断的,但却显露出茅盾文艺思想发展中的可喜迹象。从一九二三年以后,茅盾的文艺思想就由革命的民主主义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过渡,特别是经理了五卅运动和亲自领导商务书馆工人罢工的斗争实践,终于使他的文艺思想出现了质的飞跃,其标志就是《现成的希望》、《论无产阶级艺术》、《告有志研究文学者》、《文学者的新使命》的发表。在这些文章中,茅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对为人生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某些充实和修正,扬弃了先前文艺思想中的不合理因素,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作了明确的阐述。他的文学见解,已明显地具有了社会主义因素。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他摈弃了先前所倡导的文学应超阶级地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思想。他说:“在我们这世界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不分阶级的全民众?”据此,他明确提出,应该“抛弃了温和性的‘民众艺术’这名儿,而换了一个头角峥嵘,须眉毕露的名儿,——这便是所谓‘无产阶级艺术’。”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对于文艺的选择,都是以本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为前提的。无产阶级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之所以在苏联能够“茂盛”,能够有“传播之可能”,是因为在苏联“无产阶级由被治者地位,一变而为治者”。这既肯定了政治对文学绝对的制约,又指明了文学作为上层建筑而对政治社会所具有的反作用。
其次,茅盾认为文学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我们读高尔基的作品,仿佛“走进了贫民窟,眼看着他们的污秽褴褛,耳听着他们的呻吟怨恨 ”,这种身临其境的效果所以能够产生,茅盾认为,是因高尔基不是以局外人来表述自己对生活的评判,而是亲身经历了无产阶级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他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战斗的一员。当然,他也并不“承认‘此实事也’的小说方为可贵”。他举例战争小说,“既以描写人们在战争中所起的心情变幻为主要目的,那么作者的曾经身列戎行就算是唯一重要的条件了”。在这里,茅盾把亲身经历看成是文学创作的“唯一重要的条件”,固然有些偏颇,但对文学和生活关系重要性的强调,却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三,茅盾认为揭露现实的黑暗,并不应简单地复制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而应“在现实的丑恶的世界里,创造些美的东西出来,以抵御卑贱痴呆残忍无耻的侵略,而在人心上保留下一些高贵的思想,温和的同情心,进取的志气来”,从而达到“以求生活的进步”的目的。茅盾后来曾总结说:“攻刺生活的脓疮,暴露社会的丑恶”,并不是写实主义的全部内容。为人生也绝非是机械反映人生,而是“指导人生向更光明更美丽更和谐的前途”,“文学决不可仅仅是一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指南针”。正是在“创造生活”这一点上,茅盾的文学主张才跳出了旧写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窠臼。另外,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及互相关系,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形成及产生的条件等诸问题,茅盾都表示了很好的见解。
综观上述,说在一九二五年,茅盾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分析文学现象,明确提出了为人生就是为无产阶级人生。这不仅在自己文艺思想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关键的一步,而且这种转化在客观上对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过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当我们对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一番鸟瞰式的巡视以后,就会发现茅盾的文艺思想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上的,并和以对社会现象“应该否定的予以否定”为主要特征的旧现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阐述如下的事实也许会加深我们对茅盾早期文艺思想更深刻的认识:茅盾在所有新文学作家中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他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总是考虑是否和党的利益保持一致,这是其一;良好的家庭影响、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和商务书馆浓郁的学术空气赋予茅盾以翔实的理论储备和活跃的思维习惯,这是其二。茅盾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上来建造其文艺思想的理论框架的,因此它的文艺思想显现出许多新的特质,正是这些新特质,确定了茅盾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中文艺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一)虽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和其文艺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对照关系,但任何一种文艺思想的建立不能不依附于一定的哲学根基。茅盾正是以唯物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把反映“时代精神”当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这就给他的文学主张奠定了良好的基调,使它能够高屋建瓴,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把握文学的趋势。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能在他的文艺思想发展中折射出来。如俄国十月革命,他就从托尔斯泰对十月革命影响的角度,考虑了文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他认为,“醉心于‘艺术独立’的人们,常常诟病文学上的功利主义”是“很可怕的”,而尤其可怕者,是“把凡带些政治意味社会色彩的作品统统视为下品,视为毫无足取,甚至视为有害于艺术的独立”。他以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为例,证明文学趋向于政治社会的原因。第一,由于当时俄国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因此他们只能在文学里折射出对政治的看法。第二,由于十九世纪俄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而“作家大都受其苦”,“所以更加要诅咒这政治这社会”。正是十九世纪的俄国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现状有些相似之处,因而茅盾提出文学一定要干预生活,“趋向于政治的或社会的”。又如,茅盾曾经直接参加了五卅运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作家“突破了自设的忌禁”,他觉得“政论文已不足宣泄自己的情感和义愤”,而采用散文这一最迅速最直接表达思想情绪的文学样式,来控诉反动军阀对爱国学生的迫害。可以设想,如果茅盾不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实践,仅从本本出发闭门锁居,是不可能实现其文艺思想“质”的飞跃。鲁迅一登上文坛,就把中国现代小说的水平提到了迄今无人逾越的高度,茅盾不仅把文学观念亦提到了相应的高度,而且这种文学观念真正体现了时代对文学的需求,在客观上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同步。他们分别代表着第一个十年创作和理论的最高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坦率地讲,茅盾对中国社会现实洞察的深刻程度,远较鲁迅逊色,只是他能够以先进的哲学思想为指南,并且和实际革命斗争的关系最为密切,才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而那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周作人,就因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终于戏剧性的在新文学史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可见,先进哲学思想的接受,对文学家的发展道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茅盾是以唯物主义作为其文艺思想的理论支柱,因此,显著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一直贯穿其文艺思想发展的始终。比如,他基本上能够用阶级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一九二〇年,他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他认为文学应该努力反映“第四阶级”的疾苦,申诉他们的喜怒哀乐;一九二三年,他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普通人的人生,还要表现他们的理想,起到“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作用;一九二五年前后,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况,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有些研究者认为是在《论无产阶级艺术》这一篇文章中完成的,而是在这前后一系列文章中体现的。事实上,任何思想的转化,都要经过历史的演变并有其承继关系,都要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远非一篇文章所能奏效的。
(二)“印象式”批评和理性批评的融合是茅盾为人生文艺思想的又一特色。茅盾的“印象式”批评显然暗中师承了中国古典文论感悟评点的思维模式,他善于从自己的独特感受出发,心地爽直地喊出“他从某作品所得的印象”,然后在这种独特“印象”的基础上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于是我们看到,作品中的一个细节、一段对话、一种情绪……都可以作为茅盾建立自己批评观念的逻辑起点。如茅盾就从一九二二年男女恋爱小说大都在公园相见的细节中,引发出当时恋爱小说雷同化概念化的弊端,进而告诫作者于创作之前应“实地观察后方描写”;从中国近代言情小说每每喜加“此实事也”一句,引发出“实则全篇无一处令人感到真实”的慨叹,进而提出新文学发展过程必须经过自然主义洗礼的进化文学观;从“豆腐西施”对“迅哥儿”与“闰土”的情绪差异上,引发出《故乡》的意趣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进而提出封建式的宗法血缘关系和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是造成这不了解的直接原因……
“印象式”批评赋予茅盾把握当时文坛趋向以开放意识和宏观眼光,茅盾始终注意把纷杂的文学潮流和文学事实“化”为自己的主体感受。正是“化”的过程,培育了茅盾自身的理性品格,显示了理性对个别事实材料的逻辑统摄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茅盾这时期的文艺批评最具文本意义。茅盾的超前意识太强烈了,他无意之中充当了俄国别林斯基的角色:经常对一个时期的创作情况进行综述,准确地反馈现实对文学的各种需求,按照现实对文学的需求和文坛的实际情况来引导批评的导向。在理性的制约下选择“印象式”批评,使茅盾基本上能“完全脱离感情作用而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的”。茅盾说:“安得列夫的著作,我是倾倒的,然而其中如‘Souoo’(《萨瓦》)如‘The B LaCKmaSR’(《黑面人》)……等,我都认为给现在烦闷而志气未定的青年看了,要发生大危险——否定一切”。茅盾一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鲁迅的《故乡》算不上“规模宏大”,而《狂人日记》也谈不上“文笔恣肆绚烂”,但两篇文章发表不久,茅盾便独具慧眼,著文称妙。广泛地涉猎使他能够取精用弘,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扶持鲁迅等作家已取得的现实主义成果,在发掘中国古典文学养料,摄取西洋文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本民族特点的崭新文学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即以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揭示理想,指明前途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茅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建设民族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论家。
(三)由于茅盾的批评多是针对文坛的实际,有的放矢,因此形成了鲜明的倾向性,具有明确的战斗方向。“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想也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文艺流派的斗争中发展、完善起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首先遭到了鸳鸯蝴蝶派的围攻。鸳派作家们就曾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有口不谈国家,任他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找囊鱼生活”。其浮靡颓废文学观在此略见一斑。茅盾一经接管《小说月报》就开宗明义:“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既是《小说月报》的办报宗旨,也是对鸳派进行反攻的战斗宣言。从此以后,茅盾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鸳派的斗争。首先,他扣下了足够一年之用尚未刊出的全部鸳派稿件,并且提出馆方不能干涉和修正编辑方针,这就保证了《小说月报》始终掌握在研究会同仁手中。其次,茅盾对鸳派消极颓废的文学观进行了攻击。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鸳派作家“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茅盾不仅在思想上指出鸳派作家的最大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推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而且在艺术上他批评他们颇多纰漏,以主观的向壁虚构,代替客观的实地观察,“以至连篇累牍所载无非是‘动作’的‘清帐’,”使人无法卒读。茅盾就是这样挥汗泼墨,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对鸳派乖谬的言论进行反击,在斗争中捍卫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茅盾同封建复古派的斗争主要是针对“学衡派”而言。“学衡”诸将居南京东南大学一隅,以“学贯中西”自诩,主张白话不能代替文言,高呼语文不能合一,对新文学表示了极端的仇视。梅光迪就曾漫骂:“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就“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他更反对文学进化论,“西国名家。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何吾国人童騃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针对这种陈词滥调,茅盾批驳说:“他们自己也研究西洋文学,他们似乎也承认中国旧书里对于文学的研究不及西洋人那么精深;但是他们竭力反对白话。他们忘记了自己所钦仰的英美文学大家原来都是用白话做文章的”。“学衡”干将吴宓较之梅光迪更加阴险,他把茅盾介绍的西洋写实主义同中国的黑幕小说、“礼拜六”相提并论,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为此,茅盾写了《写实主义之流弊》,对吴宓的鬼蜮伎俩予以揭露。茅盾指出,吴宓对欧洲的写实主义只是皮相的了解,因为欧洲写实主义“把人生看得非常严肃”,“描写非常认真”,并且“不受宗教上理论上哲学上任何训条的拘束”。黑幕小说及“礼拜六”则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任何活动都当作笑谑的资料”,“马车直达虎邱”这样流水账式的描写:“称赞张天师的符法,拥护孔圣人的礼教,崇拜社会上特权阶级的心理”,这都和西洋写实主义相悖,而吴宓却认为它们和西洋写实主义相埒,“实在是和它们开玩笑了”。
尽管茅盾对复古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他并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对于我国古代丰富灿烂的文化,他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一向反对侈言作家独立创作而全然忽略了古人成功的著作的研究。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要得到世界的公认,首先必须是民族的。实际上,他的为人生的文艺思想正是吸收民族精华和借鉴西洋理论“合力”的结晶。
茅盾和创造社的论争,孰是孰非,历来聚讼纷纭,这场争论的全过程,应另文专述。在此想说明的是,这桩文坛公案,称它是“人生派”和“艺术派”的争论也好,称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艺思潮的论辩也罢,究其实,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文人相轻的恶习和狭隘的门户之见。茅盾和郭沫若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过,为人生并不排斥艺术,为艺术也须以人生作基础。况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前者是以现实为基础,但不否定理想;后者是从理想出发,也针对现实。因此,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争,不过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郭老坦荡的表白,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这场论战的真谛。正因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没有本质的分歧,最终也就捐弃前嫌,握手言和了。
茅盾在同鸳派、复古派和创造社的论争中,并不以打笔仗这种运动式的抨击为满足,而主要是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自胡适在《新青年》上燃起“发难”的信号,以其“八不主义”开文学革命之先河,封建旧文学才被全面否定,但那时还是过多的从形式方面着眼,即文白之争吸引了人们的主要精力。“‘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整个新文学家作家这时都面临着文学观念的更新。有人虽然在批判封建旧文学的同时,试图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但都如昙花一现,远没有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产生那么深远、广泛的影响。当时在文学研究会周围形成了以茅盾为首的强大的人生派。当然,由于这些作家生活经历禀性气质和外来思潮影响的差异,因而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格调和为达到这种格调所采取的途径又是各异其趣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总的倾向的一致。叶绍钧、谢婉莹、黄庐隐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客观地去反映乡镇小市民的迂腐守旧的劣根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一是以敏锐的感觉和清新的情调,在残酷的社会中,用“爱的哲学”来普度人生;一是穿着恋爱的外衣去苦索人生的真谛。尽管他们的作品纷呈出五彩缤纷的个性差异,但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确是他们总的方向。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之所以没有滥觞的可能,固然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缺乏浪漫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但为人生艺术思潮所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也是不可低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朝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跟茅盾的理论主张和以后的创作实践是密不可分的。鲁迅、茅盾,并立为新文学现实主义道路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当之无愧。
注释:
①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以下所引《文学运动史料选》版次相同。
②《托尔斯泰与今日俄罗斯》。关于茅盾的第一篇文学论文,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一九二O年一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有人认为是一九二O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乐黛云同志认为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学生杂志》连载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本文采用乐黛云同志的说法。
④《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第4页。
⑦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茅盾文艺杂论集》卷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以下所引《鲁迅全集》版次相同。
⑧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1,第46页。
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卷1,第417页。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曹万生.茅盾艺术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丁尔纲 李庶长.茅盾人格[M].河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5]钟桂松.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6]周兴华.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Art for Life’s Sake”:Insight into Mao Dun’s Early
(1919-1927) Literary Ideology
QU Li-bin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Jilin Municipal Girls’ School,Jilin City 132108,China)
Abstract:The core of Mao Dun’s early literary ideology is “art for life’s sake”,whose features are fundamentally the literature to require “resentment and anger”,to require “blood and tears” and to require to sympathize with “the injured and the insulted”,and his literary ideology,which derived and improved from the struggle of diverse literary schools,was not transformed until 1925.
Key words:Mao Dun;for life’s sake;new tr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