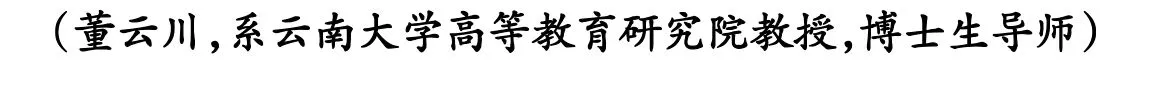明德的先生与新民的教育
2015-12-27董云川张琪仁
董云川,张琪仁
明德的先生与新民的教育
董云川,张琪仁
一
20 世纪是中国大灾难、大动荡、大变化、大转型的时期,从被外强疯狂宰割的封建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100年里,为倡文明之繁荣、国家之昌盛,一批灿若星河的先贤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
涂又光先生1927年生于河南光山,他那一辈人是最能体会个体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人,也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体会最深的一辈人。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要有真意、有见地,最关键在于“背景”的洞悉,这个“背景”就是问题浸润其中的“文化”,好比涂先生泡菜理论中的“泡菜汤”,泡菜味道如何,实际是泡菜汤决定的,我们分析问题的外环境实际就是使问题成为问题的真原因,然而,道理浅显,却不是人人通达,正如陈丹青在“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莫不如说是一个人的“一生之和”,涂先生一生经历整个大时代的动荡、转折,又师从冯友兰先生研习哲学,久历时事,孜孜以求,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观中国高等教育之“众相”,见解独到而深刻。这与涂先生在整个人生历程中所感受的中国文化、所体悟的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涂先生高屋建瓴的感性基础,这个东西“临摹”不来,是个人人生经历之独有。我们现在的很多学生甚至老师,研究“乡村社会”、“农村教育”……连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更别说晓其文化、知其风气,这样的缺憾绝非三五个月的“田野蹲点”就能弥补。唐代诗人韩愈在《送进士刘师服东归》一诗中,言:“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有良知的学者重在求“智”。深厚而至通、广博而至简,这样的“智”是褪去了繁华的包裹,如一本牛皮纸装帧的旧书,着最朴素的外衣,却有最耐人寻味的意涵。智是“容”,口是“形”,心是“气”,如三者能合一并做到“天下为公、道法自然”,便是“公心、公口、公智”。涂先生一生为学,即如此番。
二
我们当前的学科建设、专业研究、工作总结……各业各界,总想在一件事、一类事、一档子事中倒腾出个“规律”来。“规律”是个好东西,“规律”是源、是本,把握了规律,就抓住了“命门”。因此,我们在关于某个学科的定义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阐述:“XX学,是以XX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出……规律的一门科学。”对于这样的表述,笔者并无异议,任何学科,归根结底,都是要揭示该学科研究对象以及发展规律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所有待揭示的东西都是未知的东西、都是新东西。其实,“未知”和“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其实在“我们”之前就昭然若示,甚至已被揭示出来,或者,不管是否已被“揭示”,它都已是事实性的存在。对于这些“未知”,我们都仅算是“后者”。通过探索这个“未知”、挖掘这个“未知”、最后发觉这个“未知”,其实仅是一个将“新的命题”和“旧的答案”完型匹配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本源”,而只是找到了与命题或现象相对应的“本源”。正如涂先生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以下引用同此)之于“大学之道”,我们所言的“高等教育”是个后来词。我们寻寻觅觅、蓦然回首的“总规律”,涂先生亦是用老祖宗的“智慧”来揭示。
涂先生总结,“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历称“三纲领”,称之为“纲领”,是说中国高等教育在实现它。称之为规律,是说中国高等教育在遵循它。因其是贯穿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全过程的规律,故为“总规律”。规律是矛盾运动发展过程当中总结出来,故有找到规律还得抓住矛盾。涂先生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是‘道’与‘艺’的矛盾,现在叫做‘人文’与‘科学’的矛盾。”其实,观之中西,近30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与讨论无不基于两者地位与关系的论争,先生寥寥数语,却将这一问题说得清清楚楚、通透明白,“在传说阶段,道艺同一;在人文阶段,重道轻艺;在科学阶段,轻道重艺;在人文·科学阶段,复归道艺同一。”先生在总规律与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再度深入,提出“当前对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研究,有人区分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若区分内外,则‘明明德’是内部规律,‘新民’是外部规律,‘止于至善’是内外合一的规律。”先生在此基础上,生发“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总规律,实现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旧称‘八条目’”。这在西方文化下来审视这样的步骤,是很难理解其先后与主次的,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简直找不到更为契合的总结。敬瞻先生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学术研究的中心论题为分段,前期是以哲学为中心的文化研究阶段,后期是文化视野中的教育研究阶段,这也就决定了先生之观点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现实的契合性。当前数量惊人、眼花缭乱的研究,往往繁华过后即是烟云,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两层皮”,为了问题而问题,为了对策而对策,为了建议而建议,为了总结而总结。而先生这云淡风轻、三言两语,却是句句要害、字字真意。
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论点下,对“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者进行释义,提出,“明明德”是修养人格整体,人格整体就是“人之性”。先生用《中庸》之言阐释,“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以,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个人自我,又是宇宙一分子而“与天地参”。“参”即“叁”即“三”,这里的“参”相当于西方的trinity,即天地人三者合一。所以不论古今、中西,往“根”上溯,其实都是殊途同归。我们之所以更多看到差异、不同,是因为还没到“高屋”,遂未能“建瓴”。“新民”在先生看来,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最佳关系的规律。其表现,先生概括为,大学新民,则大学与社会俱兴;大学不新民,则大学与社会俱衰。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时兴‘适应’说,要高等教育适应社会,这只算维持平常关系,不算最佳关系。”对“止于至善”,先生则言:“现在常说办世界第一流大学,标准为何?亦曰‘至善’而已矣。”
先生释义“大学”一词,一为“大学问”,一指“大学校”。在先生看来,两者是远远不能对等的,“大学校”办得再好,也不等于全部的“大学问”。先生言,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十五岁以后,“死而后已”的终身教育。而这漫漫“终身教育”路,所学之内容,概括而言,即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遂先生慨叹:“这岂是高校教育所能担当的!”现在,我们在象牙塔的围墙之内讨论教育的无限与有限,其实,所谓“有限”,不就是先生这一句慨叹!“近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过是高等学校研究,这是关系中国文化文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哪有这么严重?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能在高校中开个头就很不错了。高校毕业后还有大半辈子,这大半辈子的持续教育怎么落实?不说落实,有人还没提上日程。不说提上日程,有人想也没想过。不管这个大头,就算把高校办得锦上添花,花开花谢,又该如何?这个问题,用西方大学观,看不出来,提不出来;只有用《大学》大学观,才能看出来,提出来。”这样的通达,不至深处不可寻,不至远方难看清。若说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如先生所言,高等教育也只是为成人之独立生活开了个头而已,而这个头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大学是否能够“明明德”、实现“新民”而达“止于至善”,这个头实在是关键。
三
涂先生晚年不带研究生,他说:“我是到60岁以后才学会拒绝,人生苦短,应该抓紧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波澜不惊的话却是铮铮风骨。其实,这何尝是60岁以后的事呢,学问人是一个社会“文明的良心”,“文革”后期,有人批判冯友兰,凭借只言片语质疑其学术和研究成果。涂先生说先别忙着批判,“瞎子放响鞭,乱缠一股烟”,待把冯先生的全集出完后再说。于是,毅然放下自己的研究,将冯友兰先生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翻译为中文,并笔记冯友兰先生的口述自传《三松堂自序》,参与冯先生最后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讨论与写作,独立编纂14卷本、400万字,历时10年才出齐的《三松堂全集》,多年辛苦为一人!人正、诚心!现在人文社科研究有一个不好的趋势,认为可与自然科学一样,从方法到观点都不受人为影响绝对中立,实际呢?人文社科的研究是以“人”为微观单位的,人是有缺陷的,由人构成的国家、社会、政府因此有了天然的生理、心理、文化上的不完美。由此推论,不论个人研究个人、个人研究集体、集体研究个人,这个观点都是会出现偏狭的,所以才有了“研究伦理”。而遗憾中国当下“研究方法”中的“研究伦理”是从西方学过来的,直接从操作层面谈问题,而中国老祖先则早早说了学问之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学,即为人。人们经常问“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大师”,眼下这位令人敬仰的先贤的一生就是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