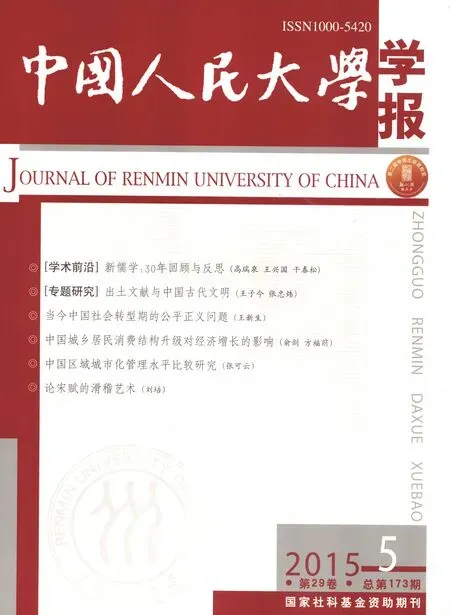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
2015-12-27张忠炜
张忠炜
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
张忠炜
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这主要是因为其内容可大大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缺憾。但是,学界很少考虑出土文献的性质:即以出土文献作为随葬品的用意所在。秦汉之际,今湖北江陵地区发掘的墓葬中,以律令为随葬品的现象不止一次地被发现。它们能否被称为“明器”,从“名”与“实”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均可存疑。结合楚地的丧葬习俗及众多的考古发现,我们充分留意到随葬器物的空间布局,并尝试探寻“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重申并拓展冨谷至提出的假说,认为以律令文献为随葬品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
律令文献;性质;明器;布局;功能
关于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但对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的性质,关注者寥寥。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多是基于以下认知背景:研究者立身于讲究史料的时代,研究重心自然落在以甲骨、金石、简帛为载体的文字内容方面,而且多数情况下对之信而不疑。比如学界一般认为金文是用语言记录历史的真迹,是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实录。[1](P107)诸如刘起釪等学者则认为,金文多局限于较狭隘的范围内,其本身多是孤立的、片断的,不具有连贯性,故需要以文籍考辨学的方法进行“批判地审查”工作。[2](P51)
近几十年来,松丸道雄、伊藤道治、夏含夷、罗泰、巫鸿、风仪诚、李峰等海外学者,对西周金文的性质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被忽略且有价值的重要问题,他们讨论的着眼点在于:铸造金文的目的以及此类铜器的使用场景,由此重新审视铜器铭文的价值。
譬如,罗泰强调西周铭文并不是单纯的文本而是宗教文书,只有将其与器物的用途相结合,才能理解铭文的全部内涵。在他看来,铭文并不是精确的历史记录,它们主要还是礼仪活动遗留下来的产物。[3](P343、353)李峰则从“多重的社会背景”出发,提出金文铸造目的是“无限制的”的论断,其使用并不局限在“宗教—礼仪”祭祀的范畴;铭文虽是为了记录并传承作器者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并不一定常常记录真实的历史。[4](P13-23)之所以如此,借用夏含夷的话说,是他们或多或少地考虑到铭文的“主观创造背景”[5](P213)。换言之,铭文撰写者是基于何种立场、如何选择性地记述事件*夏含夷指出:“新出土文物的价值当然不须我现在再来鼓吹提倡;学术界早有共识。然而,治西周史的学者也不应过于轻信,对铜器铭文所记载的史实之可信性不加分析,便用来重新论述西周时代的历史演变,骤然地形成新的史观。我们须知,尽管这种新史料未经后人删改润饰,可是对史实也并非都是客观公允的加以记载,因而不能看待为档案或客观史实。”参见夏含夷:《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前言4页,150-151、157-158、165页,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如何通过“修辞”来达意[6](P34、39)等等,都是利用金文做研究时不得不考虑的。这些讨论对加深金文的理解大有裨益,也对我们探讨出土简牍的性质有所启发。
就秦汉时代而言,简牍依据其出土地域及遗址性质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屯戍遗简,主要见于西北塞防等遗址中,内容以行政文书为主;墓葬简牍,出土地域较为广泛,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多,内容相对驳杂,以古书为大宗,兼有遣册、行政、律令等内容[7](P72-114);古井简牍,主要见于今湖南地区,出土地在当时均为官署遗址,绝大多数是档案。*古井所出简牍,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为始,后又有湘西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西汉武帝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益阳兔子山简(年代跨越较长)等大宗发现,此外尚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等小宗发现。新近披露的湘乡三眼井遗址古井中,亦有千余枚战国楚简出土。简牍发掘或整理者据出土地点,断定这些简牍性质为官署档案。为节省篇幅,此处不一一指明出处。屯戍遗简的性质相对单一,多是定期销毁或废弃的文书(一般文书保存十年左右即被销毁,诏令等文书多被长久保存),汪桂海对此已有深入研究[8](P227-232);古井遗址所出简牍,大概也是定期销毁或废弃的文书,但文书保存期有待进一步研究。墓葬遗址所出简帛古书,论者观点大同小异。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事死如生,与个人的爱好关系比较大,同身份地位的关系则略有争议。[9](P97、100)[10](P81-82)那么,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是否也是如此?是否还有我们未曾注意到的其他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墓葬出土文献的性质,涵盖通常所说的抄录、归属(如归入《汉书·艺文志》的某略某家,主要针对典籍而言,律令不存在此类问题),但更多的是旨在探讨以律令等作为随葬品的用意所在。以下,先从学界对随葬书籍的认识出发,再逐渐尝试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镇墓说”与“明器说”
文献中记载以书籍随葬的事例,比较可信的是东汉时的周磐。他曾命二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11](P1311)。对此现象,海外学者格罗特很早就注意到[12](P414-417),但因材料有限,论者多从事死如生的观念着眼。随着楚缯书的发现,中外学者对之以及汲冢书所见《穆天子传》作为随葬品的意义展开积极探讨。安志敏、陈公柔认可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楚缯书很可能是具有保护死者的巫术性的东西。[13](P48-60)[14](P1-48)何四维关注问题的视野尤开阔,不仅关注传世文献所载,也将当时考古所见简帛均涵盖在内。针对楚缯书,何氏认可Alfred Salmony、饶宗颐及安志敏、陈公柔的意见,认为具有避邪或镇墓的功能。对于汲冢书中所见《穆天子传》,他认为正如古埃及的《亡灵书》,起到引导死者通往天国的作用。[15](P78-99)后来,吉川忠夫认为东汉至六朝时代以《孝经》为随葬品,究其实是《孝经》被寄托了巫术力量(魔力)。[16](P425)
墓葬出土文献的性质,因内容不同而或有别。纪安诺认为,墓葬出土文献或有宗教意义(如告地策、买地券),或为墓主遗愿(如皇甫谧随葬《孝经》),或填棺以防出殡、埋葬时尸体移动(无例证,但认为睡虎地秦简有如此功能),等等。[17](P409-438)对墓葬所出古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对书籍或文本本身的研究,主要涉及文本结构、内容(文字、图像)、形制、文本性质。譬如,李零认为楚缯书分甲、乙、丙三篇,甲篇、乙篇互为表里,丙篇(及所附神物图像)则是帛书用途之所在,从而推断帛书是一部与古代流行的历忌之书有关的著作。[18](P29-48)今日看来,这一层面的讨论日趋翔实、完善,并成为《日书》等文献讨论的范式。其二,对书籍作为随葬品性质的探讨。国内外学者对之均有关注,相较而言,海外学者似更关注这一点,亦即探讨随葬品本身可能被赋予的意义,从而导向信仰方面的研究,上引楚缯书的讨论即如此。
就随葬律令简来说,不过是墓葬出土简牍的一个方面;从出土数量及地域看,也很难称为一个普遍现象。虽如此,学界对其性质依然展开讨论,冨谷至、邢义田是代表性的论者。
2005年,由内田智雄编、冨谷至补的《译注中国历代刑法志》出版。冨谷至在书中简要介绍相关出土法律资料,着重说明这些文献对法制史研究的贡献并进而提出问题:为何法律方面的书籍或条文、记录会从墓中出土?他认为有待更多的简牍、纸质文书出土,但亦提出假说:
法律文书、律条文乃至律的注释作为殉葬品埋入墓中,不正是作为赶走妨碍墓主长眠于地下的恶魔、邪气的避邪物吗?[19](P365)
2006年,冨谷至在《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汉律令研究》一书“绪言”中,重申上述观点:
律令是以镇墓、辟邪的目的被随葬的,如果说与法律有关系的话,那么在现世社会中具有作为威吓恶行为效果的律与令,转而用于对黄泉世界的邪气、恶鬼进行威吓。即,作为随葬品的法律,其目的就是除魔、辟邪。
兵法书、医书、经书、道家的书,还有关于授予王杖的文书等亦然,可以说都是有赶走妨碍墓主之眠、除魔作用的简牍。[20](P16)[21](P309-310)
冨谷氏的上述提法,似可被概括为“镇墓说”。
邢义田依据简牍的体积、重量、编联及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曾有如下推测:“墓葬中出土的简册,凡一册多达数百简者,都比较可能是为陪葬而特别抄制的明器,非供实用。”并举随州孔家坡汉墓日书简为例(七百余枚简编为一册),参照居延简而推测孔家坡简册的长度、重量:
这份出土日书册,全长四、五公尺,重达2.6公斤以上。试想这样的简册,卷成一卷,直径约24.88厘米,如果不置于几案,而是单手持握,不论坐或站,边展边读,将是何等不便?[22](P22-23)
据此标准,由500余枚简构成的《二年律令》当属“明器”了。紧接着,邢义田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更明确说道:
我估计西汉墓,甚至秦墓出土的竹木简文书和帛书,基本上都不脱明器的性质。由于是“貌而不用”的明器,不免露出他们的“不实用性”,例如不顾使用上的困难,将数百简编连成一册(如随州孔家坡日书简);内容有错误脱衍,却不见任何在使用过程中应有的更正痕迹。[23](P85)
较之早先的提法,此处“明器论”所指,实际上又有所发展:文书、书籍乃至地图,都不脱“明器”性质,具有“貌而不用”的象征性。此即所谓的“明器说”。
墓葬所见律令文献若诚然如此,更棘手的问题将随之而至。冨谷至说道:
如果古墓出土的法律是面向冥界的东西的话,将其无条件地视为现实世界的资料,或者将其作为与埋葬的时代相同时期的资料来利用,是否完全没有问题呢?[24](P366)
换言之,作为“明器”而面向冥界的出土文献,所记载内容的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
不论冨谷至还是邢义田,在表达上述疑问的同时,又试图打消这种顾虑。冨谷至说道:
为了避免误解,在此必须申明,我并没有把出土的法律资料走极端地论证为是虚构的、非现实的拟制文书的意思。本来,它们在现实世界中被执行、被运用的概率就极高。当法律成为殉葬品时,转用现行法不用说也是最便利的。只是,现行法如果被说成仅具有厌胜驱邪的效果将会怎么样呢?还有,当初殉葬的是现实世界的法令,之后逐渐演变为非现实的内容的现象,这种倾向目前已经可以从买地铅券中看到。在现阶段所发现的法律方面的出土资料,尚未见到这一特征,但今后发现的,也许有包含拟制文书的可能性。果真如此,那将是现实世界实施的公文书的符号化所致。[25](P366-367)
邢义田也说道:
虽为明器,内容上却又绝不是如魏晋以降地券之程式化。迄今所知,除了类别大体相近,没有任何内容重复或据同一范本复制的迹象。它们比较像是据墓主生前所用,真实的文书抄录或摘节而成。内容上包括地方性的户口、赋役簿籍、律令、历谱以及和个人相关的“大事记”或典籍等等。[26](P85)
他们的补充说明,或许可消除学者对出土文献可信性的顾虑,但一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乱花钱,会“剥夺”孩子们掌控钱的机会。比如要买什么东西,统统向父母伸手要,孩子们得到了压岁钱,家长们也会说:“压岁钱由父母来帮你保管”,全数地将压岁钱收回去。这样做的弊端是,孩子们会因此养成要花钱就伸手,一有钱就赶快花光的习惯,而缺乏对消费的规划意识。
二、“明器说”辨析
对于“明器说”可能存在的问题,我已有相关论述[27](P380-388)[28](P263-266),今以旧文为基础,重新修订,叙述如下。
古代礼书经传中,分丧礼用器为生器、祭器和明器三类;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尤其是明器、生器,不仅要充分结合当时的历史场景,还要注意其内涵可能发生的变化。
生器,系生人日常生活所用之器,故或又称作养器、用器;祭器,用于宗庙祭祀等特定礼仪活动,又称人器、礼器。从形制、制工、质地看,生器必能合乎实用且可在市场上交易,祭器、明器虽模仿之,但又有本质上的差异:祭器或礼器,体现着重要礼仪意义和政治权力,而且是无法出售或赠与他人的,其由技艺高超或娴熟的工匠用珍贵材料制成,器形虽与日常用器一致,然故意抹杀实用之功能;明器或鬼器,一般来说质料、制工较粗糙,或不堪使用,或仅为象征。[29](P119、173)[30](P23、86-87)三者作为随葬品,不同时代各有侧重,也有合并使用的现象。[31](P119)[32](P203-204、206)
巫鸿在《“生器”的概念与实践》一文中指出,《仪礼·既夕礼》中的“明器”是指祭器以外的所有陪葬器物,也就是汉代郑玄经注中的“藏器”。荀子以“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区分生器、明器[33](P369),前者虽是生时所用之器,其形状和装饰已无法改变,但在葬礼中通过取消其实际功能“明不用”而突出“送死”的象征性,明器则被清晰地界定为供丧礼和墓葬专用的“鬼器”;相应地,对“明器”的关注,已从实用的功能、陈放的位置等转向器物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34](P87-89)
巫鸿的论断与林沄早先的观点有一致处,即均认可郑玄“明器,藏器也”的论断[35](P191);“明器”可以是实用器,并不一定都是非实用品,故又与“生器”并非截然有别。[36](P20)若以“貌而不用”为衡量“明器”的依据,实际上与“祭器”的主要特征相吻合。[37](P73、77)若以“明器”来统称谓之,似乎又未注意到彼此的异同,以及考古发现中的大量实例。[38](P203-204)故而,从“名”的角度看,将随葬品泛称明器,恐怕是不合适的。
考古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也对我们认识“明器”有益。从广义来说,明器可泛指陪葬器物。《中国明器》是国内学者最早研究明器的专著,书中认为明器为陪葬器,用以供死者神灵之用[39](P8)。研究汉代墓葬及丧葬礼俗的学者,如王仲殊、李如森,在其研究中也是将简帛视为随葬品。[40](P97-104)[41](P182-188)狭义的明器,似有特定所指。《中国明器》书中论述,秦汉以来的明器,通指瓦器而言,有俑(人像俑、动物俑)、仓、灶、井、杵臼,等等。[42](P33)此书实际收录的明器,大体以上述所列为准。此似本于罗振玉《古明器图录》:此书收录、影印的明器,分俑、器物、家畜等类(另附圹砖),并非将随葬品泛列于间。[43](P2417-2420)考古发现丰富了人们的认知,即瓦器为明器殆无疑,木器或少数石制、铅制器物,亦可归入明器。[44](P130-164)
从汉代以来的相关记载看,明器并非随葬品的泛称,仅是其中的一个类别而已。《续汉书·礼仪志》记有汉代皇帝大丧所用明器的种类及数量,《通典》中亦有古往今来关于明器及饰棺的记录,文繁不引。[45](P3146)[46](P2321-2328)唐代典章中对明器的使用有较为扼要的叙述,时代虽晚,但对理解狭义的明器颇有益,故引如下:
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47](P597)[48](P690)[49](P55-58)

将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视为“貌而不用”之物,可能与简牍外在的书写特征也存在着矛盾。

其二,从《东观汉记》所载光武读桓谭《新论》事看,即“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53](P548),或可旁证当时确实有大型简册存在,尽管此类现象可能并不常见。而且,从学者复原的走马楼吴简简册看,超过百枚简的简册并不罕见[54](P100),甚至规模更大。*大型简册的存在,与载录内容似有一定关系。譬如,经传诸篇长短有别,篇短者用简少,篇长者用简多。武威《仪礼》简七篇,少者如“士相见”共十六简,多者如“泰射”用百余简。似乎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篇幅太长的文字,或亦可分册书写。那么大型简册是否因此而少见?若对书写史进行系统考察,或许会有益于问题的解决。另外,侯旭东认为吴简中大型简册的存在,可能是册书的构成与规模会随着用途与保管方式的变化而变动不居所致,存档时可能会按照一定规矩将相关册书编联在一起而形成超大简册。凌文超亦认为,大型简册有可能不是一次成形的,很可能是出于诸如存档等需要,将不同乡里的簿籍进行再抄写、编联的结果。这或许是随着其用途及保管方式的变化而形成的,但亦可说明,孙吴的时代仍有超大型的简册存在。
最后,尚未公布的张家山336号汉墓简,确确实实地揭示出简牍文本的实用性。若干不合时宜而废弃的法律,如“肉刑”、“刖刑”,校雠者则括去“肉”、“刖”字[55](P97),此例系整理者所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目前虽为孤证,未必能印证他类简牍,但表明张家山336号墓汉简并非“貌而不用”,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事实。换言之,是称之为“明器”,还是称为“生器”,难有明确定论。
此外,简牍上的符号标识,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多被整理者忽略不录,无疑是个疏失。[56](P225、251、255)[57](P43-44)[58](P158-160)这究竟是抄写者抄录时所为,还是阅读者诵习时所加,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均有待进一步思考。*韩国学者金秉骏认为简牍上的符号,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按照个人的关注点标入的,而不是作者或抄者在书写过程中因虑人误读而标记的。结合熹平石经所见章节符号,则可知金氏之言有武断之嫌。虽如此,仍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作者、抄者、读者三者间的关系。参见金秉骏:《如何解读战国秦汉简牍中句读符号及其与阅读过程的关系》,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四辑),403-4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这些符号标识的意义,如陈梦家所言,或表明篇、章、句所在,或是诵习者所作之钩识;陈槃据汉简句读、标识,论及古人之“离经辨志”,虽未提及陈梦家,但彼此暗合处,或可揭示文本实用性之一斑。[59](P308-309)[60](P100a-101a)
简言之,从“名”与“实”的角度看,将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也包括律令)视为“明器”,似乎都有扞格不通处。
三、再论“镇墓说”
对冨谷至的“镇墓”说,李力曾提出质疑*具体论述可参见李力:《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236-240页,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9。,若结合律令简牍的出土地及年代,或许对重新认识冨谷至假说有益。今所见墓葬出土律令文献,除西北地区所见三批王杖诏书令(年代集中在西汉末、东汉前期)外,主要见于今湖北地区,且主要存在于秦末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参见表1)。大概与西北地区汉墓埋藏王杖诏书令册现象相似,以大宗律令文献为随葬品可能是特定地区、特殊时段存在的现象。若着眼于楚地丧葬习俗的转变,以及汉代“告地策”文献的兴起,可知以大宗律令文献为随葬品,极可能还有观念方面的考虑。

表1 墓葬出土大宗律令文献表
注:此表相关信息据发掘简报或正式出版物而定,简省起见,不一一注出。青川郝家坪秦墓出土有秦统一前颁布的“为田律”,荆州松柏一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令丙第九”,扬州胥浦汉墓出土的“先令券书”,材料有限;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所处军法军令类资料,严格来说,与一般律令文献有别;岳麓书院藏秦简购自文物市场,有不少法律文献,极可能也出土于湖北地区;荆州印台九座西汉墓中,也出土不少简牍,其中也包括律令,除《荆州重要考古发现》略有所述外,具体情况不清;故均未列入。
如果说敬奉鬼神是古代民族普遍存在现象的话,则楚人此风更盛[61](P112-120、283-289),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楚墓随葬“镇墓兽”正是突出表现。今楚墓所出镇墓兽,一般为木质,个别为陶制,头似兽(典型者为虎首虎面),头顶两侧对称插鹿角,身长方形,直立于方形底座正中的孔眼中,身与座为套榫结合。[62](P63)[63](P54-60)多出自一椁一棺的士级,或士以上的大夫级墓葬中。[64](P66)[65](P24-25)以之为随葬品,一般认为具有镇墓辟邪的功能(或以为早期多镇墓说,后期多升天说)。[66](P64-67)[67](P54-61)楚地随葬镇墓兽之风于战国晚期骤止,楚人敬奉鬼神的观念是否也随之消失?若未消失又会通过何种方式表达?毋庸置疑,楚人敬奉鬼神的观念并未消失:楚式镇墓兽虽骤然消失,但俑葬之风渐盛,两者应存在某种关联,松崤っ权子的研究已揭示此点;今所见汉初吕后至汉文帝时江陵等地区出土的“告地策”,学界一般认为是为了保护死者,亦可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此点。[68](P5-12)
对“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的关注,新近尤值得注意的是沈睿文的提法。他指出,任何器物都是因为它的功能而存在的,毫无意义的器物不具备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同的语境决定了器物存在的原因,是确定器物功能最为重要的因素。[69](P178)这对我们思考问题无疑有启示意义。
秦汉之际江陵地区既未见镇墓兽也无埋藏“告地策”的墓葬中,却不止一次地出现以大宗律令为随葬品的现象,这恐怕不能孤立视之。根据巫鸿对部分墓葬生器摆放位置的研究可知,或是靠近尸体,或是围绕“灵座”。[70](P94)[71](P509-522)无独有偶,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律令简是典型的示例,律令简正摆放在尸体周边,与前者所述现象吻合[72](P13);后者所说“灵座”,就马王堆一号、三号墓来说,正位于椁室的头箱,而张家山二四七、三三六号墓律令简恰恰也位于头箱,尽管这不一定能证明它们就是生器。有趣的是,镇墓兽也多搁置于椁室的头箱部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即头箱象征前朝(堂),棺室象征后寝(室)。[73](P64)既然搁置镇墓兽具有镇墓辟邪的功用,则湖北尤其江陵地区秦汉墓以律令为随葬品,使之具有或发挥与镇墓兽相似的功能,也完全不是不可能的。毕竟,随着秦厉行“法治”的传统被推广,律令在现世中所拥有的强烈震慑力,是有可能被移置于冥间且被赋予特殊功能的。从这个角度看,冨谷至的假说尽管没有文献支持,但从楚地丧葬习俗的演变看,完全是有可能成立的。
不过,律令简即便是有这种假想的功能,也无法确定其他墓葬简牍文献,如兵书、医书、经书、道家等,也具有类似功能,至少当下似乎还无法如此断言。吉川忠夫对《孝经》具有“宗教性”的论断,放在佛教盛行的六朝时代可以成立[74](P419-435);但恐难由此引申:《孝经》或《老子》本身就具有某种“宗教性”的功能。随葬此类典籍,多为个人遗愿。上引东汉周磐事例如此;与其相近,西晋皇甫谧安排身后事时,有“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75](P1418)。从这两个事例中无法看出经典具有“宗教性”,至少在佛教盛行时代来临之前是如此。随葬典籍的原因无法一概而论,但就周磐、皇甫谧等事例看,借用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话说,应为“文化展示(display culture)”[76](P34-37)。用以表示个人对某种观念或学说的认可,不仅生时如此,死后亦如此。
四、余论
就墓葬出土的简牍文献,包括本文讨论的律令简,除去我们此前揭橥的几点外*其一,研究思路的转化,不再停留在是此非彼的层面,强调实证与解释的办法相结合;其二,注意秦汉时代的法律编纂、书写及传布;其三,律令简的校读。参见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268-2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一,简牍在墓葬埋藏空间中的位置。如考古学、艺术史学者揭示的那样,不同的布局及器物组合,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77](P204-227)[78](P509-522)当古人将简牍作为随葬品放入墓中,既讲求摆放的位置,又选择不同的内容,多属有心之举。尽管我们对此未必清楚,但这方面的解读不可或缺。有些简牍的出土位置,因自然或人为的原因,确实与最初状态有别,也是无可奈何事。一般来说,根据所在的空间位置判定其性质与用途,是解读墓葬简牍文献的关键一步;再结合墓葬形制、墓主身份、地域葬俗等情况,进一步考虑其与墓主人的关系。我们认为以简牍为随葬品,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且与身份还密切相关。此外,通常强调的文本研究,尤其是深入发掘文本的内涵,仍有待加强。
第二,留意文本抄录中存在的诸问题。写本、刻本的时代,校雠有其存在必要,甚至成为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之一;以简牍帛书为书写载体的时代,书于竹帛是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口耳相传的作用亦不容否认。如此,口述、书写及彼此间的相互转化,作者、读者与抄录者之间的关系,对文本的流动与固定均产生重要作用。*关于战国至秦汉文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参见来国龙:《论战国秦汉写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动与固定》,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二辑)》,515-527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在以单篇律、令为法律存在形态的秦汉,律令由朝廷制订、颁行自不待言;问题在于,如何参照、呼应是个根本问题。李零认为,越是文件才越是一条条书写,然后才往一起攒,“编辑的问题比写作的问题更突出”*笔者就汉代章句问题请教李零先生,他在复信中提到此点。。睡虎地秦简中,仓律与效律的部分条文相同或相近[79](P328-333),不同抄本所见效律的文字、接续亦有异同[80](P48-55)[81](P154-162、120-122),学者新近揭示秦律中“有罪”的指代问题[82](P103-110),以及《二年律令》中“死罪”的替称问题[83](P18-21),似均可从文本的流动与固定考虑之。*江村治树是从增补角度入手,即效律的编纂是将相关已有的仓律原样截取;佐佐木研太的论说从不同抄本所见效律的比较研究入手,认为竹简上的黑墨点不是表示前后条文的区分,而是对律文所做的补充;我们是从章句角度入手,进行书写接续及律章句学的考察。我们最初在进行讨论时,未曾留意到江村治树、佐佐木研太的论说。不过,彼此论断各异,不妨相互参看。
第三,文本价值的认定离不开史料批判。材料有限素来是古史研究的制约因素,故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借此,我们可以反思疑古思潮中存在的理论和方法上缺陷,也可以反思前辈学者对古书真伪、年代、作者等方面的具体论断,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史料批判。[84](P5-16)尹湾汉墓简牍经科学发掘而面世,绝无后人篡改之嫌疑,但“集簿”所见幼龄、老龄人口比重甚至超越当下,显现并不因其出土于地下而完全属实可信。[85](P110-123)[86](P557-561)又如,银雀山汉简《孙子》之《九地》篇,各个片段并不衔接,内容也十分冗杂凌乱,且前后篇屡有重复。[87](P364-367)所以,面对简牍帛书之类的出土文献,我们不能因为其从墓葬出土,而忽略对其进行史料审查的必要性。
对于今所见秦汉出土律令文献,这种态度也是不可少的。暂且不论“正本”、“抄本”的关系(也许今后能发现“正本”),也不论及文本抄写中的人为衍讹(无意,有意,或兼有之),我们还不得不留意的是条文规定与法律实践。规定可能是面向普天之下,也可能是针对局部;可能具有长久的法律效力,也可能是行用不久即废止。从秦汉之际到汉武帝时代,律令修订增删频见于典籍,尽管已不清楚变更的具体内容为何。身处混沌状态中,却依旧满怀期望: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律令简,睡虎地七七号汉墓律令简,加上此前已经公布的睡虎地秦简,以及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律令简,会让我们构建出由秦至汉的文本序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则让我们有可能窥视当时的法律实践。文本也罢,实践也罢,史料批判依旧不可或缺。
引用池田知久的论断,以结束本文:
出土资料也好,文献资料也好,都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并不是说出土资料讲的就是纯粹的事实,没有任何的加工成分;同样地,并不是说文献资料描述的历史就容易出问题,引用出土资料就可以反映真确的历史了:出土资料并没有这种特权。这一点容易被误解。总之,出土文献不见得比传世文献更可靠,尽管它是数千年前的东西,但它只是将数千年前的思想面貌呈现了出来,并不等于所反映的数千年前的历史事物就真实可靠了。[88](P29)
[1] 王晖、贾俊侠:《先秦秦汉史史料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3] 罗泰:《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4]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起的官僚国家和制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 夏含夷:《从驹父盨蓋铭文谈周王朝与南淮夷的关系》,载《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10]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9]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45]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九《周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 J.J.M.DE.Groot.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Vol.2.Leyden: E.J.Brill,1894.
[13] 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缯书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63(9)。
[14][18]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A.F.P.Hulsewé.“Texts in Tombs”.AsiatischeStudien.Vol.18-19,1965.
[16][74]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7] Enno Giele.“Using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as Historical Source Materials”.MonumentaSerica,2003 (51).
[19][24][25] 冨谷至:《论出土法律资料对〈汉书〉、〈晋书〉、〈魏书〉“刑法志”研究的几点启示:〈译注中国历代刑法志·解说〉》,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六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0] 冨谷至:《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注篇》,京都,朋友书店,2006。
[21] 冨谷至:《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竹简——特别是关于〈二年律令〉》,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2] 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载《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
[23][26] 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载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
[27] 张忠炜:《读〈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四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8][58][81] 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9][31] 林素英:《古代生命礼仪中的生死观——以〈礼记〉为主的现代诠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30] 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2] [38][77]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
[33] 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十三《礼论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
[34][70] 巫鸿:《“生器”的概念与实践》,载《文物》,2010(1)。
[35] 《仪礼》卷十三《既夕》,《十三经古注·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据《四部备要》影印)。
[36] 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载《史学集刊》,1990(3)。
[37] 巫鸿:《“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的观念化倾向》,载《文物》,2006(6)。
[39][42][49] 郑德坤、沈维钧:《中国明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据1933年版影印)。
[40] 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
[41][44] 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
[43] 罗振玉:《古明器图录·目录》,载《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
[46] 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第八十六《礼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
[47] 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
[48] 吴丽娱:《唐丧葬令复原研究》,载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
[50] 沈睿文:《唐镇墓天王俑与毗沙门信仰推论》,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5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52] [55] 黄人二:《简论先秦两汉书手抄写后之校勘大概》,载《出土文献论文集》,高雄,高文出版社,2005。
[53]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54]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载《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
[56] 李力:《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9。
[57] 张忠炜:《汉代律章句学探源》,载《史学月刊》,2010(4)。
[59]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载《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
[60] 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
[61]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2][64][66][73] 陈跃均、院文清:《“镇墓兽”略考》,载《江汉考古》,1983(3)。
[63] 黄莹:《楚式镇墓兽研究》,载《中原文物》,2011(4)。
[65] 松崤っ权子:《关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木俑与镇墓兽》,载《文博》,1995(1)。
[67] 高崇文:《楚“镇墓兽”为“祖重”解》,载《文物》,2008(9)。
[68] 张文瀚:《告地策研究评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1)。
[69] 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1][78] 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对非偶像表现》,载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72]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75]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76] Michael Nylan.“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Writing: Text,Ritual,and Culture of Public Classic Period(475B.C.E-220C.E)”.In Martin Kern (ed.).TextandRitualinEarlyChina.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
[79] 江村治树:《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的性质》,载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零一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0] 佐佐木研太:《出土秦律书写形态之异同》,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82] 徐世虹:《〈秦律十八种〉中对“有罪”蠡测》,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83] 游逸飞:《如何“阅读”秦汉随葬法律?——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例》,载《法制史研究》,2014(26)。
[84] 裘锡圭、曹峰:《“古史辩”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载《文史哲》,2007(4)。
[85] 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载《历史研究》,1998(5)。
[86] 邢义田:《从尹湾出土简牍看汉代的“种树”与“养老”》,载《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
[87] 李零:《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载《〈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88] 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辩”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载《文史哲》,2006(4)。
(责任编辑 张 静)
The Nature of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Excavated from Tombs in the Qin-Han Period
ZHANG Zhong-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value of excavated texts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scholar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Such a situation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tents of such texts can remedy the deficiency of received literature.However,scholars rarely consider the nature of excavated texts,namely,that they functioned as grave goods.For the Qin-Han period,the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excavated from tombs from Jiangling area of Hubei were common grave goods.As to whether such tex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mingqi (literally,“brilliant vessels,”or ritual burial goods),the designation is not ironcl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ds for“bright”and“actual.”Yet if we synthesiz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burial customs in the Chu area with numerou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ve goods,we can explore whether such texts were “used as vessels of cultural signifiers”,thus expanding on Tomiya’s hypothesis,namely,that the statute and ordinances functioned as grave goods that pacified the grave occupant and warded off evil influences.
statutes and ordinance;nature;ritual burial goods;space;function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XNQ012)
张忠炜: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2)
* 本文修改得到张春龙先生、沈睿文先生、凌文超先生的指教与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