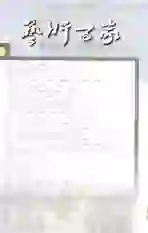对当代观念艺术的反思
2015-12-25李媛
李媛
摘 要: “观念艺术”自产生便在艺术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从索尔·勒维特到约瑟夫·柯索思都致力于对观念艺术做出理论上的论证,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尽管观念艺术家们竭力地追求标新立异,却无法割裂其与西方艺术哲学以及文化体制之间的关系,其思想仍然是西方传统思想中理性主义之上观念的再次嬗变而已。
关键词: 艺术学理论;观念艺术;艺术惯例;艺术作品;艺术规律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HK]
观念艺术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1917年法国艺术家杜尚就已开始倡导观念的重要性,他的代表性作品《泉》无疑是观念艺术的肇始。而以标榜某种思想或者传达某种信息的艺术被称之为“观念艺术”,这一概念最早因美国艺术家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于1967年所发表的《观念艺术短评》而得名。观念艺术从产生之日起就彻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对它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观念艺术的概念与内涵等方面,这也是笔者反思的出发点。
一、对观念艺术概念的思考 在观念主义艺术的第一篇宣言《观念艺术短评》中索尔·勒维特对观念艺术做出了详细的阐释,“在观念艺术中,关于理念或观念是作品最重要的方面,……理念成为了制造艺术的一架机器”[1](p.12-13)。首先,勒维特认为“理念或观念”是最重要的,然而在此他并没有区别“理念”与“观念”,且将idea置于艺术的首位,认为理念是创造艺术的机器。如果说“理念”是指人的思想情感的话,那么艺术的创造离不开艺术家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情感的积聚与爆发才是艺术创作的动机,这与创作之前的“计划”、“决定”没有关系,艺术思想观念的差异形成了不同艺术之间的区别。从这一方面分析,勒维特关于观念艺术的定义似乎并不适用于观念艺术,而是对艺术的定义。其次,勒维特认为理念是艺术创作的机器,即艺术品的生产离不开理念,理念才是艺术的根本所在,艺术的本质。如果理念是最重要的,与西方传统哲学中柏拉图认为理念是最根本存在的思想有何区别?再次,勒维特用到了理念与观念这两个术语,那么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在关于观念艺术的35句语句中勒维特对此作出了进一步地阐释。在第1句中他提出,“观念艺术家是神秘主义者而不是理性主义者”[1](p.103),他们在艺术中的结论是理论逻辑无法表达的,理念是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而艺术家的创作具有神秘主义倾向,是无法清楚阐释的。正如我们所知,柏拉图将文学艺术的创作归为神力驱使下无知无觉的“灵感”的作用,可见勒维特的观点与柏拉图的文艺创作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第9句、第10句中勒维特区别了理念与观念,指出理念是局部的,观念是全面的,理念是观念的构成要素,观念通过理念而实现。在区分两者之后,他又提出“理念本身就是艺术”[1](p.103),并在第17句中对其详细论述:“只要理念与艺术有关,并进入到艺术惯例当中。所有的理念都是艺术。”[1]( p.103)他认为艺术是理念的,并且理念需要在艺术惯例中得到肯定。第28句则指出艺术创作是艺术家根据理念所决定的形式进行创作。总之,艺术本质是理念,理念决定了艺术的形式,而艺术家在创作中无法阐释清楚自己思想。勒维特没能明确阐释观念艺术的特点,实质上仍然延续了西方传统哲学对艺术思考,勒维特不过是柏拉图唯心主义艺术哲学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二、对于艺术惯例的思考
从第17到第20句,勒维特着重谈了艺术惯例,认为艺术惯例是确认观念艺术的重要因素,隐含着言说的权力。对艺术惯例的探讨实质是要突破传统从艺术外部特征定义艺术的模式,转向挖掘艺术内在的不可诉诸于感官的特征。勒维特指出,只有当艺术的理念被艺术界的惯例所接受时,理念就成为了艺术。惯例成为判定艺术之为艺术的标准,那么为什么艺术惯例拥有这一决定权?勒维特在第20句中又谈到“成功的艺术通过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理解的惯例”[1]( p.103)。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引导与培养公众的艺术欣赏习惯和鉴赏力,达到对艺术惯例的影响,而艺术惯例又成为确认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据。他的阐释揭示了艺术、艺术家、艺术惯例之间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关系,但也使我们质疑其关于三者关系的阐释具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从艺术惯例探讨艺术本质,这是20世纪艺术界的热点,这些观点包括了亚瑟·丹托的“艺术界”,即强调艺术识别离不开艺术理论的氛围,勒维特的艺术惯例以及者乔治·迪基的艺术体制等。迪基提出从论证某物要成为艺术品需要经过的程序来定义艺术,他认为,“艺术家是有理解地参与制作艺术作品的人”[2]( p.80),即艺术作品为定义艺术家的条件,而艺术界是由艺术家所组成的,那么定义艺术界离不开艺术家,而艺术作品又是“创造出来展现给艺术界公众的人工制品”[2](p.80),艺术界的公众需要由艺术家与艺术作品去培养形成,这也构建了一个阐释的循环,其逻辑缺陷明显。迪基与勒维特的阐释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的阐释实质上也揭示了艺术身份的确立与艺术界之间的尴尬关系。20世纪艺术家在实践上的大胆尝试,挑战评论家与观众长久以来在何为艺术问题认知上的共识。革命性的艺术实践超越了理论阐释的范围使理论家们显得捉襟见肘,无法为新的艺术提供解释。当艺术与艺术批评的界限坍塌,对观念艺术的思考也就牵连出了“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
三、对观念艺术本质的思考
1969年观念艺术家团体“语言学观念艺术”成立,强调语言对观念艺术的重要性,约瑟夫·柯索斯作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之一,他的《哲学之后的艺术》成为了观念艺术理论的代表作。柯索斯的理论可以总结出三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一)语言的形式与现成品
柯索斯的《哲学之后的艺术》一文从论述观念艺术“不是什么”到观念艺术的功能来阐明观念艺术的本质,“杜尚之后的所有艺术(从本质上说)都是观念的,因为艺术只能以观念的方式存在。”[3]( p.164)柯索斯将观念艺术之前的艺术称之为“形式主义艺术”,在此基础上他明确了艺术的语言在观念艺术这里是现成品,而杜尚是首先关注这一问题的人。形式主义艺术关注的是“语言的形式”,而观念艺术关注的是“所说的内容”,也就是现成品。这一观念受到了语言哲学的影响,语言学哲学将语言看成是世界的根本,人类文明的一切都是语言的呈现与表达。语言学家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基本构成,能指和所指:能指即用声音或形象来表达某一事物;所指则是声音与形象代表的事物自身。艺术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语言体系之一,柯索斯所要做的是剥离出艺术的符号、形式、视觉等能指的特性,而直接关注艺术所指内容,以此反对他所谓的形式主义艺术的语言体系,进而打破这一话语体系,获得给艺术立法的权力。在柯索斯看来,形式主义艺术是将美的理念作为艺术的主导者,认为艺术与美学具有“概念的关联”,在这种艺术中“形式”与“审美”形成了封闭的循环,艺术与美学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艺术的本质”却没有得到真正地认识,被遮蔽了。关于艺术的本质,他认为是“观念”,即所说的内容,而不是“形式”。杜尚用现成品使人们认识艺术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现仍然具有艺术的意义,也使人们认识到艺术的功能,而艺术的功能正是艺术自身的身份。柯索斯所做的是对杜尚的艺术实践进行理论上的论证,进而颠覆形式主义艺术的言说体系,赋予观念,即现成品以根本的地位。当艺术家给予现成品以“艺术”观念时,它就是艺术。如我们所知,现代派艺术家们反对传统精英艺术观,认为这种艺术观主张艺术是天才之作,天才通过“形式”创造使其具有吸引力,成为审美对象。传统艺术在观念艺术家们看来不过是“一种美学上的纯粹演练”[3](p.162),根本不是艺术,绘画和雕塑成为纯粹审美对象,强调其作为装饰物的功能而导致了形式主义艺术与批评。只有恢复艺术“物之为物”的自身身份,才能割裂形式主义艺术对艺术与美学的捆绑。以杜尚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家采用激烈的对抗手段直接建立艺术与生活的联系,将现成品纳入艺术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变得模糊与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观念”,柯索斯关于艺术只能以观念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结论更促使了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相分离。观念艺术家往往以“观念”为旗号进行标新立异的创作,自说自话,甚至被认为是疯子,而这也更促使了他们的实践只能在激进与前卫的道路上前行。(二)权力与反权力观念艺术评论家罗伯塔·史密斯指出:“作为六十年代特征的政治上无休止的动乱和社会意识的增长也助长回避艺术和艺术家特权地位的趋向。”[4]( p.60)这一分析指出观念艺术的兴起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人们认识到传统艺术已然成为特权与精英的标志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其的全面抵制与排斥,社会开始涌动着改革和创新的思潮。20世纪的现代派的艺术家们开始了对美术馆、博物馆的反抗,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是少数精英分子所垄断的殿堂,作为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是具有强烈排他性和限制性的环境,它们使艺术脱离了生活与大众。以柯索斯为代表的观念艺术家们认为艺术应该渗透到生活和大众中去,生活是绝对的艺术。对于权力的反抗,最具有代表性是柯索斯提出关于艺术定义的结论“艺术作品就是分析性命题。……一件具体的艺术品是艺术,意味着它就是艺术的定义。因此艺术真的是先验的(这就是贾德所说的“如果有人说它是艺术,它就是艺术”的意思)。”[3]( p.165)柯索斯关于“艺术是作为艺术的艺术”[3]( p.165)的观点不再依赖于形式主义艺术的先验假定,艺术只是指向自身观念的存在。通过研究观念艺术的发展,可以看出观念艺术家的这种反抗是矫情的,无非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的表现。当艺术家们驳斥美术馆、博物馆、画廊以及艺术的商品化现象时,采用反叛对抗艺术体制时,却又不得不在商业性的画坛体制、美术馆的庇护下获得确认与发展。观念艺术鼻祖杜尚的“泉”如果离开了博物馆,只是一个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具而已。据此可以看出观念艺术家们所谓的反抗必然失败,这种反抗不过是作为精英们的艺术家在自身范围内对艺术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无法脱离或超越其赖以生存的艺术市场。
(三)形态学与功能学 柯索斯认为观念艺术是从形态学到功能学的转换,是从外观到观念的转换,这一转换的目的是在于切断形式与美在形式主义艺术中的联系。形式主义艺术中“形式”为言说的表现,艺术的性质是以形式为特征的形态学表现,形式具有话语的权力。对于话语权,福柯曾尖锐地指出知识从来都不是中立与客观的,权力总是利用知识来扩张它对社会的控制,在艺术的领域也不例外。在柯索斯眼里“形式”俨然成为形式主义艺术的重要标准,是艺术语言主要表现的内容。而他认为只有抛弃这种形态学的追求,才能使艺术避免沦为美学的演练,[JP2]将艺术的功能作为一个问题,从而恢复艺术的本质,使人们认识到艺术自身的身份。强调艺术的关键在于作为物的“观念”,而不在于“形式”,把现成物纳入艺术领域就是赋予某物“这就艺术”的观念。在柯索斯看来,艺术不应该是以往在形式与审美之间的形态学追寻,而是对艺术“物之为物”的追求,他认为具有“作为艺术的观念上的意义”[3](p.165)才是艺术。并且他认为即在他看来艺术命题的有效性不依赖于形态学的界定,以及审美的假说,而是以现存之物的物性展现艺术的观念,而艺术家应是分析家,所关注的正是如何增长艺术的观念,而不是事物的物理特性。认为艺术观念增加与丰富,其价值越高;认为艺术只是一种指向自身观念的“自我指涉”。所以柯索斯用“如果有人说它是艺术,它就是艺术” [3](p.165),即艺术是作为艺术的表达对于艺术本质的阐释与理解。 通过对柯索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艺术是作为艺术就已摆脱了艺术批评,彻底消解了艺术批评的存在,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说是艺术,艺术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线消失,艺术理论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柯索斯试图在西方哲学二元模式的取舍和徘徊中寻求艺术的本质,忽略了作为二元构成的现象与本质、能指与所指、语言与现成品、权力与反权力,以及形态与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没能从整体和全面的角度思考艺术本质。综上所述,无论是勒维特还是柯索斯都没能跳出西方传统哲学的逻辑思路。当观念艺术试图摆脱艺术史传统时,却又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的依据,将艺术的界定置于艺术惯例之中,却又无法回避逻辑的矛盾,让观念艺术用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发挥效力,其存在的合理性必然遭受到质疑。观念艺术的这一困境正是西方二元论哲学思维模式根本缺陷的折射。 (责任编辑:陈娟娟)
参考文献:
[1][ZK(#]Sol LeWitt.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A].Conceptual Art:a Critical Anthology[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2] George Dickie.The Art Circle [M].New York: Haven, 1984.
[3] Joseph Kosuth. Art after Philosophy[A].Conceptual Art:a Critical Anthology[C].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1999.
[4]罗伯塔·史密斯著,侯翰如译.观念艺术[J].世界美术,198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