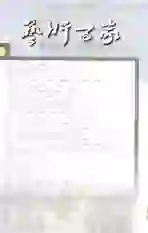关于濒危戏曲剧种的地方保护法规构建问题
2015-12-25邹元江��
邹元江��
摘 要: 面对极其脆弱濒危的戏曲剧种,我们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仅仅限于国家政府形态的一般政策措施,还应当采取地方法律法规等更有效的强制保护措施,这原本就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明确要求的。要在对戏曲剧种这类“濒危的文化形式”加以最为精细考察的基础上,确定戏曲剧种“濒危”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切实有效的、有威慑和约束力的地方法规。
关键词: 戏曲艺术;戏曲剧种;濒危剧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法规;构建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正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遗产的高度集中”[1](P.415)的表演艺术,它以其韵味儿独具的方言念白和纯粹质朴的民间声腔,以及极其丰富、俚趣的调笑、绝艺而凸显出精彩绝艳的地域风情。“地域风情”正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所强调的“文化空间”[1](P.419),即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文化场所”[1](P.412)而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强调“活的文化”[1](P.415)、活的整体的呈现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核心。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中国地方戏曲的地域性特征正在逐步丧失。
比如名不见经传的鄂西大山深处的小剧种“山二黄”在2008年举行的“首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汇演”中一亮相就让戏曲界大为惊喜,但是这个“天下第一团”的艰难处境却让人捏着一把汗。毫无疑问,无论是从剧种多样性保护的视角还是从声腔源流研究的维度,像“山二黄”这样的濒危剧种都是应当特别关注的。但要真正落实这种“关注”和“保护”又谈何容易。“山二黄”又称“汉调二黄”,系湖北十堰地方戏曲剧种。据查清乾隆年间,黄州府一带有众多移民迁徙至鄂西北及陕南等地落户。随着荆、襄移民带进山的楚调与鄂西北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长期流变结合,而形成了独特的山二黄地方剧种,距今已有250余年的历史。一般认为山二黄属皮黄腔系,以唱工见长。始以“坐万字”(即坐堂清唱)而闻名,学唱者众多。清道光年间,开办科班,组班立社,挂衣登台。主要活动区域在郧阳地区(十堰市)及鄂、陕两省毗邻地区的十多个县市,长年盛演不衰。新中国成立后,郧阳地区各县相继建立了山二黄剧团,可在“文革”期间又被全部撤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恢复了剧团建制,但各县剧团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纷纷改演其他剧种或歌舞节目,唯有竹溪剧团经批准恢复山二黄剧种,并先后招回了一批山二黄老艺人,排练演出山二黄传统剧目。山二黄剧种虽被载于《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北卷,并被录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存目,也被列入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作为湖北省地域性的稀有剧种之一其状况却岌岌可危,作为生存最起码的“文化空间”十分狭窄。又如在湖北省秭归县建都村有一个濒临失传的建都花鼓戏(花鼓调),而这是历次文化普查时都未发现和记录的戏剧文化遗产。2008年奥运会主场馆鸟巢落成演出,全国选出的原生态艺术表演的节目就是建都花鼓戏,但因建都这个地名没有什么名气,就改称为秭归花鼓戏。①还有一种濒危剧种的情况很特殊,即由于剧种自身的生存危机,该剧种就向生存状况相对好一些的大剧种的腔调上靠,如湖北的“麻城东路花鼓”和湖北的武穴“文曲戏”。东路花鼓戏起源于鄂东的麻城,已被列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唱腔有东腔、二高腔、二行、对腔和小调等,在鄂东广泛流传。文曲戏流行于鄂东的黄梅、广济、蕲春等县及与之邻近的江西、安徽两省部分地区,始称调儿戏,1956年黄冈专区戏曲汇演时改为今称。现武穴市文曲戏剧团系20世纪60年代初国营广济县文曲戏剧团之沿革。文曲戏系由湖北艺人在当地久已流行的坐唱艺术表演形式的基础上,学习汉剧的行当与表演、音乐并配上锣鼓而逐渐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剧种。20世纪20年代,调儿老艺人挂衣登台,演出了由调儿曲目脱胎的《金莲调叔》《苏文表借衣》《宋江杀惜》《点药》和由汉剧移植的《游龙戏凤》等小戏,受到群众的欢迎。从而标志着剧种舞台艺术形式的确立。文曲戏的主要声腔有【文词]、【南词】、【四板】、【秋江】、【平板】。另有多种小调。传统唱腔兼有板式变化体与曲牌连缀体两种结构形态。曲调总体风格清雅简洁、清新婉转而引人入胜,音乐的抒情性较为突出。其剧种主奏形式,从初期的一把调儿胡(土制的中音胡琴),到之后加入二胡伴奏,使单一的主奏形式发展到复合的主奏形式,剧种的音乐色彩和表现功能大大提高,起到了很好的“舞台烘托,托腔保调”等艺术作用,具有较强的鄂东地域特色。再如江西的“广昌孟戏”,又称“盱河戏”,是一种已传承了五百余年的专门演唱孟姜女故事的戏曲。它用高腔演唱,经考证,留有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海盐腔的遗音。“广昌孟戏”戏班在广昌县有三路,即广昌县甘竹镇的赤溪、大路背和捨溪三村,这三个村每年正月春节酬神祭祖活动时都要在甘竹家族祠堂或当地传习戏台演出一次本村特有的土戏“孟戏”。“孟戏”的剧情和唱腔有两种,赤溪村和捨溪村演唱的属两夜连台本,共64出,需9个小时演完。而大路背村演唱的属三夜连台本,共74出,需11个小时演完。经考证,赤溪村和捨溪村的孟戏演出活动起源于明正统年间,至今已连演了五百余年。大路背村孟戏戏班形成于明万历年间,至今也有四百余年的演出史。赤溪村和捨溪村的孟戏剧本是元代的《孟姜女千里送寒衣》,来自古南戏中的永嘉杂剧。大路背村孟戏的剧本是明代的传奇本,源于古弋阳腔的《长城记》。这个1980年秋才被江西省戏剧研究所流沙所长首次披露的“广昌孟戏”,就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特定地域的“文化空间”,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文化空间”奠基于赤溪村、捨溪村和大路背村这些几百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场所”而呈现出绵延不绝的“活的文化”气息。而强调对这种“文化场所”所延续的“文化空间”保持其“活的文化”、活的整体的呈现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核心。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中国地方戏曲剧种的地域性特征正在逐步丧失。此外,也有一种濒危状况,但却很难说这是一个剧种的濒危,而是一种遗存了很久远的、一种古老戏曲的民间演唱形式的岌岌可危,如浙江遂昌石练镇坑口村的“十番”演唱。遂昌是浙江西部一个贫瘠落后的22万多人的小县,汤显祖在那里当了5年县太爷,留下了美名,直到现在,遂昌人士还非常怀念他,有很多遗留物。距遂昌县城几十里远的石练镇坑口村的一群“泥巴腿子”却能演唱“十番”《牡丹亭》等“四梦”曲目。2001年当全国的汤显祖专家见到这些乡土艺人时,他们中的赖氏兄弟,哥哥的年龄是最大的,76岁,最小的艺人才十二三岁。他们中的一些年长者大多不识字,但他们演唱昆曲《牡丹亭》时却是那么的投入,情调是那么的优雅、古朴。他们唱的是什么呢?就是“十番”曲。“十番”形成于明代末期,流行于江南民间。也就是在各种迎神祭祀庙会的场合,在举行各种年节喜庆堂会的时候,有那么十一二个人,吹着笙(两人)、箫(两人)、梅管(一人),弹着三弦(一人),拉着提琴(一人),打着扁鼓(一人),敲着双清(一人)、九云锣(一人)等,根据不同情境轮番演奏不同的曲牌。但遂昌“石练十番”曲牌均是昆曲曲牌,其中80%是“临川四梦”的曲牌,如《牡丹亭·游园》中的【步步娇】【醉扶归】【皂罗袍】【好姐姐】,《拾画》中的【锦缠道】【石榴花】(千秋岁),《冥判》中的【油葫芦】,《紫钗记·折柳》中的【寄生草】【么篇】【解三醒】,《邯郸记·扫花》中的【赏花时】【么篇】,《南柯记·瑶台》中的【脱布衫】【小梁州】【乌夜啼】等。这些老艺人手里拿着的直排工尺谱是保存至今的1949年的手抄本《十番曲谱》。在遂昌还发现过民国初年署名有文氏的《响遏行云》抄本,录有93支曲牌,其中“临川四梦”的曲牌就有38支,约占40%。如《牡丹亭》有22支,《紫钗记》有4支,《邯郸记》有4支,《南柯记》有5支。由此可以看出,遂昌“石练十番”之所以演奏、演唱多以“临川四梦”的曲牌和曲文为主,这与遂昌县历代老百姓都深深怀念曾在此主政5年的汤显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当这些“泥巴腿子”把非常典雅的《牡丹亭》演唱、演奏得那么美妙动听时,“汤学”专家当时都非常激动,因为《牡丹亭》虽然典雅辞美但也艰涩古奥,按说很难被老百姓接受,也不明白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们大多连字也不认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有这么多专家如此钟爱很土气的“十番”演唱,当地的官员看到了没有什么资源的小县,可以鼓励农民演唱“十番”来作为偏远小县的文化名片。所以,当2006年“汤学”专家再次看到坑口的“十番”演唱时,当年土气的演出场所已经“焕然一新”,“十番”的乐器也多有更新,演唱者的服饰也开始讲究,并且仿佛一夜间遍地开花似的,当地不止有了一支“农民十番队”(据称过去就有四五支“农民十番队”),还出现了多支“十番”队,甚至有了“文十番”、“武十番”、“粗十番”、“细十番”之分,据说还有“女子十番队”、中小学生“十番”队,“十番”曲目也进了中小学的音乐课堂……如此惊人的“变化”,这实在是让专家们既特别感叹,又非常不安。近年在福建中部三明市(旧属延平府)的大田县朱坂村和永安市槐南村发现的宗族“作场戏”遗存,被某些专家认为有大量“宋杂剧”的信息。在朱坂村,十年一次(近年改为五年一次)在除夕前有余、廖二姓宗族祭祀戏剧“丰场戏”“大试”(正式彩排),正月初一“开场”,正月初四演出。在槐南村,有两年一轮的(现改为一年一次)的黄姓宗族的祭祀戏“人场戏”。②[2](P.42-56)可为什么要将十年一次、两年一轮的演出改为五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呢?最令人担忧的是,是当地政府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做出的改变,还是民间艺人基于某种压力而被迫所作的非传统“革新”呢?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目前濒危戏曲剧种生态保护是不近如人意的,也是令人担忧的。
早在1889年国际社会就曾在巴黎召开过“艺术品和文物古迹保护国际大会”,并做出了如下决议:“艺术品和文物古迹属于全人类。因此每个政府都必须指定专门人员,对每个国家所拥有的文物古迹进行研究,鉴定出有哪些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国际公约得到保护。”[3](P.28-29)“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被提出了,但2003年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32届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③仍是一件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在这这个“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1](P.445)④基于这个定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所谓“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1](P.445-446)。《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分“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一级”保护层面,该“公约”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并提出“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通过为这种遗产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这种遗产的承传”,“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1](P.450)。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群体、团体和个人遗留给后代群体、团体和个人的活态精神财富。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无形性。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物质财富,其意义和价值通过具体的“物”来体现,“物”与“文化”合二为一,实质是“物”,物是有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精神财富,在其表现和传承过程中固然也有“物”,但核心是“非物”即精神,精神是无形的。二是活态性。物质文化遗产的“物”是静态,不可变化的,因而是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因时因地因人而变,是不断变化的,因而是“活”的。三是实践性。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结果,是实践的凝聚物,文化凝聚在“物”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实践本身,文化体现在实践之中。[4](P.717-718)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这个概念“是直接为了全面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才明确提出的一个保护对象和范围的概念”[5]。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联合国教育科学暨文化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两个关键词,即oral和intangible。oral即“口传”之意,这比较容易理解;而intangible中文翻译成“非物质”(non-material)就比较难以理解,因为intangible这个词除了“非物质”这个解释之外,还有无形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难以理解、难以捕捉等意思。也就是说,所有的表演文化其实都是intangible:它们的存在只在发生时的那一霎那,稍纵即逝,观众的欣赏与心灵体会也就是在那一霎那,传统与现代、霎那与永恒的结合也就是在那一瞬间。由此看来,无论是出版的剧本,还是像片录影录音,所有这些“物质”都只能算是附产品,或是遗留下来的残骸,而不是表演文化本身。[4](P.665)这就特别提醒我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戏曲剧种更应该关注的是稍纵即逝的活态的表演和传承活动,这应该是我们真正从无形的、不确定的视角领会濒危戏曲剧种神髓的不二法门。
三 显然,面对这种极其脆弱濒危的戏曲剧种,我们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仅仅限于国家政府形态的一般政策措施,还应当采取地方法律法规等更有效的强制保护措施,这原本就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明确要求的。即在对戏曲剧种这类“濒危的文化形式”加以最为精细的的考察的基础上,确定戏曲剧种“濒危”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地方法律法规不同层级的保护条文。在此,首先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必须澄清,那就是简单的用现代的戏剧生产的模式对濒危戏曲剧种的套用。比如有一种说法是,今天观众还在享受,而且也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的剧种就要传承。反之,就应该做减法,加以淘汰。[6]显然,这个淘汰的标准是成问题的。上文提及的江西“广昌孟戏”,几百年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观众”也从未卖过票。也就是说,这个每年正月春节酬神祭祖活动时都要在广昌县甘竹镇的赤溪、大路背和捨溪三个村家族祠堂或当地传习戏台演出一次的土戏“孟戏”,这个五百多年来永远不出村(面对当代各种商业利益的诱惑和出国参加民间文化艺术节的邀请,几个村还爆发过究竟是恪守古训永不出村,还是顺应时代出去见见世面的大讨论)的“孟戏”完全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戏剧演出活动,而更多表现为一种古代宗教祭祀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因而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观众”,即便有少数本村的村民观众,他们看或不看都无关紧要,无论如何这个戏到了这个特定的时节都是要表演的。上文提及的湖北省秭归县建都村濒临失传的建都花鼓戏(花鼓调)以及福建永安、大田的“作场戏”等,如果也按照按照简单“淘汰”的看法,这些没有多少观众,也没有以卖票为生的戏剧演出活动都属于应被“淘汰”之列。显然,这也未免太武断了。毫无疑问,“濒危戏曲剧种”作为特定的“文化空间”其“濒危”的标准并不是以现代戏剧是否有观众欣赏、是否能卖票养活艺人等表象为尺度的,而是以传承人能否有效地激活剧种的文化积淀并加以活态传承为出发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德国模式”,即由地方政府制定严格的本土化、地域化的保护措施,并履行监督、维护和执法之责。[7](P.15-22)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即任何政治与法制方面的重大决定都必须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商议后才能得到确立。各州都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议会,州机关之下的行政单位是区县和乡镇,但二者是并列的,没有从属关系。这些下属机构只负责法律的执行,但可以出台相应的执法细则。就文化保护而言,它们是直接的监管机构,必要时也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借助公安机关),以确保法律制度得以执行。在是否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问题上,德国一直持审慎的态度。德国自民党曾向联邦政府提交的一份书面咨询函中问及“在德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进行一种国家的、以国际法来规范的努力是否必要”的问题时,联邦政府的回答是“并非如此”,并强调即便国家有必要介入,其权责主要也归于州一级政府。可见德国的国家意志,实际上是由州政府的立法和监督才能有效实行的。这一点特别值得中国借鉴,尤其是在“非遗”立法和监督的问题上,地方性法规的构建和监督实施是最有效的非遗保护途径。这是缘于濒危文化遗产大多都是地域性的,甚至是偏远、落后区域的尚存的文化空间的遗留,其生态极其脆弱,急需要熟悉地域本土文化状况的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司法部门根据本地域的文化遗产的特性加以区分的制定保护法规,而不能简单套用中央制定的法规。事实上德国自民党所特别担心的问题已在中国大力宣传“非遗”的这几年间出现:“国家行政管理的强化,活态的文化生活变得僵化,‘非遗名录遭滥用,商业性的或者偏离正确的政治轨道的活动被选入‘非遗名录等。”还不仅仅如此,在中国近十三年“非遗”保护的实践中还出现了包括德国一百多位各学科的专家讨论咨询报告所担心的保护非遗“由此发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重置、美化和‘事件化(eventisierung)”[7](P.22、20)问题。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非遗保护的误区问题。
四 综上所述,面对这种极其脆弱濒危的戏曲剧种,我们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仅仅限于国家政府形态的一般政策措施,还应当采取地方法律法规等更有效的强制保护措施,这原本就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明确要求的。要在对戏曲剧种这类“濒危的文化形式”加以最为精细的考察的基础上,确定戏曲剧种“濒危”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地方法律法规不同层级的保护条文。“濒危戏曲剧种”作为特定的“文化空间”,其“濒危”的标准并不是以现代戏剧是否有观众欣赏、是否能卖票养活艺人自己等表象为尺度的,而是以传承人即将难以有效激活剧种的文化积淀并加以活态传承的困境为出发点的。
面对现代传媒和文化观念对传统戏曲艺术,尤其是濒危戏曲剧种的巨大挤压,濒危剧种传承人的不断凋零逝去,濒危剧种的文化空间遭到或实质的危害、或文化关系的破坏、或文化价值的削弱亦或破坏等不同境况,我们必须尽快为濒危戏曲剧种的保护构建切实有效的、有威慑和约束力的地方法规,包括:地方政府不能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各种名义过度包装、加工、改变濒危戏曲剧种的名称、表演方式;任何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不能以国际文化交流等各种名义让濒危戏曲剧种脱离特定的文化空间去海外、域外展演,以维护尊重享用濒危戏曲剧种的特殊的表演习俗;地方政府必须制定为保护濒危戏曲剧种遗产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的具体措施,并加以严格限制、处罚对这些特定场所和空间的挪用、侵占和破坏;地方政府必须确保民间濒危戏曲剧种传承的经费投入,但不干预、不任意改变传承的民间方式,以保证所传承的濒危戏曲剧种的乡土气息的浓郁、地域特征的突出等,以维护中国戏曲剧种的生态多样性和戏曲文化的生命绵延性。 (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这是原湖北省文联主席、文化厅副厅长沈虹光女士于2008年11月28日在由湖北省文联和长江大学主办的“荆楚文化研究高峰论坛”的致辞时披露的。
② 两村的戏虽一曰“丰场戏”,一曰“人场戏”,但两村都称其戏为“作场戏”。
③ 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04年批准政府加入该公约,到2006年已有107个国家同意签署该公约,但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迟迟没有加盟。
④ 这段话另一种译文是:“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叶明生.福建宋杂剧的发现及其艺术形态初考[J].福建艺术,2012,(03).
[3] Kerstin Odendahl,Kulturgueterschutz.Entwicklung Struktur und Dogmatik eines ebenenubergreifenden Normensystems,Tuebingen:Mohr & Siebeck,2005.
[4]宋俊华.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生态与衍生态[A].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传统戏剧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2008,(10).
[5]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余秋雨.淘汰腾出创新空间[N].人民日报,2011-02-11.
[7]白瑞斯、王霄冰.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理念与法规[J].文化遗产,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