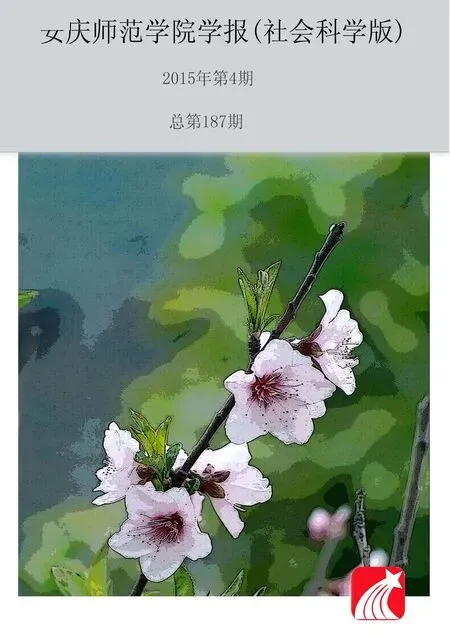局限刑法观与抽象危险犯控制
2015-12-17张伦伦
张 伦 伦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 天津 300134)
局限刑法观与抽象危险犯控制
张 伦 伦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天津300134)
摘要:作为刑法应对社会风险的主动措施,抽象危险犯的扩张适用为刑法充分发挥社会保护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刑法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不应该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直接手段。为了避免风险控制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失调,要建构社会整体的调控措施,明确抽象危险犯的规制方向,为刑法的体系调整提供依据。
关键词:抽象危险犯;刑法价值;谦抑性
随着人类实践的范围不断扩大,风险的全景渗透逐渐成为社会常态。为了减少风险扩张对社会发展的阻滞,必须升阶整体的社会调控措施,将社会防卫功能的发挥深入到社会风险转化之前。见之于刑事法律,即是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展开。因为“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为根据或者说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1],故而可以绕开复杂的因素影响,直接针对社会风险采取措施。只是,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刑法规制的扩张,相应的,也就会压缩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的适用范围,这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如何调整刑法的规范体系,平衡其社会保护与自由保障的双向价值,不仅需要在刑法的视野内寻找答案,还必须运用局限刑法理论,从刑法外围对刑法的变动进行审视。
一、抽象危险犯的刑法控制基础
抽象危险犯刑法适用的展开是基于利益衡量的结果,考虑到潜在的社会风险蕴含有严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如果放任其发展,损害状态的发生必将引起社会秩序的强烈不适应。刑法对抽象危险犯的控制必须立足于其属于底线防卫手段的地位,针对危险发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以保证刑法价值的倾斜不会盲目扩大。
(一)危险产生与刑法警惕
区别于自然风险的永续性,社会风险作为人类存在的衍生品,其大规模扩张必然与社会发展格局的变动密切相关。当前,随着社会结构的整体升级,社会全景转型已成必然之势,长期以来被社会调控措施所中和的社会风险,正逐渐利用转型时期社会调控措施表现出的僵化性和滞后性,由松散状态向凝聚状态过渡,并不时突破社会防卫体系的布控,从社会的多个方面威胁社会的安全。可以说,刑法视野中的危险其实是社会风险升级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源起于社会风险却更加现实和迫切,是具有法益威胁的社会风险。但是,对危险的关注并不是刑法直接介入风险调控的原因,在风险的累聚阶段,刑法也很难在保持自身价值稳定的同时进行有效的规范调整。
事实上,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所具有的社会风险的一般特征正是刑法要给予其特殊关注的原因。由于具有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传统意义上用以进行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法规制很难发挥有效作用。因为“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基于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而设定的类型性的危险”[2],其发生具有随意性,并且在已然的危险中,行为表现也并不完全相同,这就导致刑法既无法实现对特殊主体的威吓作用,也无法实现对一般主体的教育作用。刑法对抽象危险犯的处置,主要是给予社会高度的警示,使社会主体在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中注意自己的行为,努力规避风险的扩大和转化。刑法所发挥的是一种代表作用,表明“风险社会中的国家相对个人而言是后者对风险负荷时的政治同盟”[3],刑法对于抽象危险犯的扩张适用,是应对风险的社会整体防卫措施的一环,处于后发的位置,在对风险的控制上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并且,由于风险社会视野中的抽象危险是社会风险累聚的结果,以约束危险转化为目的的刑法就没有追本溯源的规制能力,只能寄希望于前置的社会调控措施能够有效控制社会风险的演进方向,尽量稀释风险的紧迫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刑法对抽象危险的评价是立足于危险行为本身,但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原因却更多的是出于其在社会调控过程中的不配合,易言之,“在该种场合,即便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永远都不能达到侵害法益的结果,行为人也应对其行为侵害‘不得实施某种危害行为’的规范而承担罪责”[4],这也是为什么要在追究抽象危险犯的刑事责任之前,必须了解社会调控措施进行了何种协调,以及是否还有继续运作余地的原因。
不过,刑法的警示只是表明了刑法对于危险的不容忍,任何试图促进或者放任风险转化的行为都将遭受刑法的谴责。但是危险是风险转化的结果,在此之前的较长阶段刑法无力介入,即使高强度的警示,也只是给予前置的社会调控措施以压力,促使社会调控措施在刑法的关注下进行升级。在抽象危险的产生上,刑法不针对将要规制的内容而针对前置的规制措施是刑法协调整体社会防卫手段的直观表现,随着抽象危险的继续转化,刑法的功能发挥必将变得积极和直接。
(二)危险截断与刑法预防
社会风险一旦凝聚成具有法益损害的力量,就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现实威胁,但要构成需要刑法规制的抽象危险,还必须考虑具体的行为动向。在风险向危险转化的节点上,刑法的警惕达到峰值,并做好了转变功能发挥形式的准备,即不再局限于对社会前端调控机制的警示,开始回归本身底线防卫能力的加强。可以说,刑法作为防卫手段对社会风险的干预是从社会前端调控机制失利的一瞬间开始的。警示到预防的角色转换是刑法价值维持的一种冒险,标志着刑法逐渐摆脱了其他社会调控措施的掣肘,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发挥社会防卫功能,刑法在风险社会中的存在具有了独立的意义。但是,如果其他的社会调控措施在此时尚足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刑法的干预就是失败的。一旦对危险行为的动向把握错误,刑法非但不会截断危险的发生,反而会将自身所具有的风险也附加其中。
为了避免刑法的价值失衡,在截断危险向实害转化的同时,必须评价刑法前端的社会防卫措施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抽象危险而言,由于其来自于风险的社会转化,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那么就可以在抽象危险成就的前后进行刑法的双向判断,以决定是否具有不顾虑其它因素影响而直接对危险行为加以谴责的必要。但是,刑法的内外审视必须具有连续性,在考虑到其他社会调控措施已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危险的类型及向实害发展的方向,并前瞻性地对可能的相似行为做出预测,以建构刑法的规制范围和模式。当然,刑法针对抽象危险犯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应该是预防,其条文设置不应包含解决风险的内容,否则刑法的规制就会脱离危险本身而对行为构成干涉,这不符合抽象危险犯的设定意图,即刑法将抽象危险犯作为自身控制力向社会风险施压的介质。其实“抽象危险是一种拟制的危险,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对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性做出判断就可以依据形式上的典型行为以肯定抽象危险的存在而因此具有实质的不法性”[5]。也就是说,抽象危险犯在刑法中的地位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
由此,刑法对于抽象危险的预防是在风险转化之后而实害造成之前的一种法益协调状态,一方面刑法要通过疏导危险的去向来缓解风险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避免风险向更多方向转化;另一方面刑法又要控制危险对法益的侵害力度,防止实害结果的发生。刑法从危险的角度不断审视危险之前和之后的状态,用以评述抽象危险本身的刑法意义,并综合纳入自己的调控体系之中。
(三)危险稀释与刑法处断
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危险行为因为具有促成风险实害化的趋向,故而为刑法所直接否定。但是刑法规范对危险行为的处断不完全是基于其本质恶,还因为其所带来的风险冲击难以控制。多数情况下,由抽象危险造成的既定结果仍然存在继续转化和升级的可能,并且可能会因为一个实害而造成全领域的危险蔓延。因此,在抽象危险发生的情况下,截断危险的转化只是刑法的前端任务,刑法最终的责任是稀释危险的强度,将其推出自己的视野。刑法对抽象危险的稀释是从危险成就的时候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实害结果的影响消弭,使抽象危险的发生成为自己周密防控的引源,促成刑法规范的升阶。
原初的社会风险是随着人类发展而伴生出的社会肌体的某种不适应,在社会过渡平稳的时期,社会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可以将风险的社会蔓延控制在较低级的层次。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以经验总结为构成基础的社会调控措施就会滞后于社会的转型,从而导致社会管理与风险控制的脱节,使社会风险的规模化具有了得以凝聚的时机。不过,单纯的风险凝聚即使走向了法益危险的道路,也只是法秩序内的威胁,尚不足以使刑事法律通过牺牲自己的价值稳定来做出预防性的规定。问题在于,“刑法因具有补充性,而必然具有不完整性,”[6]当刑法未能稀释社会风险转型后的法益危险时,就会造成社会风险的升阶,使社会的原初风险成为危险凝聚的风险。
刑法对抽象危险犯的处断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首先刑法要顾及社会风险的复合性,在其规范设置里必须考虑到如何分解风险的凝聚,使其复归于弥散的状态,以达到稀释其强度的目的,减缓危险的成就对法益的冲击;另一方面,刑法必须清楚自己在抽象危险犯的适用上不仅仅是为了惩处现实的损害而存在的,而是为了避免更大危害的造成,其规制具有超前性,行为人承担的是结果发生与否难以判定的责任,以此表明刑法的风险应对态度,即“在不能各得其所的条件下,一概禁止只能是唯一的选择”[7]。刑法的规制特点决定了刑法在抽象危险犯的适用上要具有双向性,不仅要主动的介入危险的调控,以检验自己的体系建构,促成自身的转型,而且要控制处罚的力度,避免刑法自身的风险因控制危险的需要而被放大。这种操作分别从刑法的罪和刑两个方面展开,在保证刑法灵活性的同时,不会损及刑法价值的稳定。
二、抽象危险犯的刑法控制体系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的刑法应对问题被逐渐提出。无论将风险置于刑法视野中的何种位置,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展开都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刑法的工具性应当受到刑法的目的性的制约,刑法的合法性应当受到刑法的合理性的拷问”[8]的观念转变,将刑法的存在价值由对“刑”的依赖转移到以“罪”为依赖的正确模式上来,刑法才能够在风险的动荡中顺利完成其“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结构转换。
(一)抽象危险犯的刑法规制背景
“迄今为止,我国刑法是建立在以‘道德—行政’为基础上的”[9]。这种建构过于强调刑法的工具意义,往往以牺牲行为的合理性为前提追求行为的合法性。由于扭曲了刑法的存在目的,刑法的功能发挥必定会陷入僵化,尤其是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刑法的固有模式直接导致了刑法的价值悬空,刑法操作逐渐丧失了风险适应性。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必须引入一种能够平衡刑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以实现刑法的阶层过渡。抽象危险犯的适用正是为了实现该种目的。
由于刑法的建构会牵涉到“罪”的模式与“刑”的模式,故而刑法的社会转型必定在这两个方面都会有所体现。传统意义上,刑法理论以“罪”为危害行为定性,强调刑法的损害识别功能;以“刑”对危害行为立威,强调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相互的结合之下,形成了完整的犯罪防卫体系。不过,因为这种建构过于强调刑法内部的规范配合,在针对具体的社会危害行为时,就难免要进行分别的评述,割裂了一体性的刑法防卫需要。其实“刑”作为“罪”确定后的自然顺承,从最开始的行为评价里就应该有所体现,并且“刑”的设置应该具有确证“罪”的效力的目的,即不仅仅是迎合“罪”的需要,而且要平衡“罪”的倾斜,在风险社会下,更应该如此。适应风险社会需要的刑法即是在强调“罪”的归纳功能的同时,注重“刑”的修正功能,通过降低刑罚的严厉程度来平衡刑法扩张导致的刑法价值的倾斜。如此,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就有了适用的余地。因为要对未知的社会风险进行提前预防,刑法在处置抽象的危险时,就难免要有所扩张,以尽可能地容纳可能出现的相似情况,相应地,为了避免对可能没有损害结果的行为连累过多,出于价值平衡的需要,刑法就要降低刑罚的严厉程度。于是,刑法的功能发挥实现了质的转变,明晰了危险行为所具有的“可谴责性这一概念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而仅仅在于指明它想要描述的东西”[10]136。
(二)抽象危险犯的刑法规制内容
作为理论概念,抽象危险犯没有必要在刑法条文中被系统提出,但是根据其所具有的特点,可以将相关内容逐步引入对社会秩序冲击较大的犯罪的刑法处遇中。为了实现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转型,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做出刑法的价值调整,在风险这一因素的催化下,刑法在理论建设上的某种让步是为了扭转其在社会防卫体系中的不利局面。事实上,如果不在刑法建构中介入抽象危险犯的内容,刑法就会因为社会防卫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而谋求刑罚手段的强化,刑法的自由价值将遭受更大的损害。
虽然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在理论上具有统一性,并且以此为基础为刑法的风险扩张提供了支持,但是“必然性之下有许多的偶然性,包括犯罪,有时候一个偶然性因素完全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11],因此,抽象危险犯的刑法实践必须灵活,应当考虑到每一个具体罪名在成立时就已经包含了司法实践的反馈和立法者深远的考虑,为了保证具体罪名的成立具有理论说服力,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必须要具有个别化的倾向,这也是抽象危险犯的刑法工具性价值所在。目前,我国刑法在吸收抽象危险犯理论时,在不同的罪名上设置了不同的惩罚趋向,表明刑法对于不同领域的风险持有不同的态度。
抽象危险犯的展开不但在“刑”上体现出刑法转型时期的特点,在“罪”的结构上也有所注意。 除了有些风险代价并不十分明确的犯罪,如危险驾驶罪,刑法的设置比较谨慎外,其他类型的犯罪在引入抽象危险犯理论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内容扩张,将属于传统意义上某些犯罪的边缘问题也纳入到犯罪体系当中去,通过扩大规制范围来减缓犯罪构成后危险的强度。抽象危险犯的刑法规制是围绕“罪”和“刑”双中心展开的,在“罪”的设置上发挥抽象危险犯的特点,以促进刑法结构的转型,同时利用“刑”的解构平衡刑法的价值需要,保持了刑法体系在风险转型时期的稳定。
(三)抽象危险犯的刑法规制目的
抽象危险犯在刑法中的扩张适用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改革的必然,即使在现实的条件下刑法的结构调整还面临许多的问题,但是抽象危险犯的理论方向毫无疑问已经为刑法的价值取舍做出了正确的定位。根据刑法当前的实践适应性,一般认为,刑法的结构转变必须具有引导刑法观念转变的作用,包括刑法自身的观念转变以及刑法视野之外相关因素对刑法态度的转变。
事实上,“对法律的畏惧是健康的,然而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是滋生犯罪的。”[12]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刑法建构立足于对犯罪人的惩罚,试图通过严厉的制裁实现对犯罪的预防效果,于是刑法的适用就会追求判决结果的震慑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运行是有违法治的,如果刑法以民众的畏惧为出发点,刑法的裁判就会受到国民情感的影响,刑罚的适用将演化为集体的暴力。事实上,司法实践中有相当部分的罪责承担不是基于法律的理性,而是舆论的推波助澜。这就导致了国民遵守法律不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而是对全民暴力的畏惧,这是不正常的。抽象危险犯的适用扭转了这种局面,因为抽象危险犯理论是作为刑法的风险预防工具出现的,其出发点不在于对“人”的关心,而在于对“行为”的关心,当刑法的焦点立足于“行为”时,只有客观的判断才能够令结果具有普遍性,从而保证了刑法的公正,这正是刑法转型所追求的目的。
另外,刑法不能一味迎合公民的情感需求,还必须具有引导公民进行理性思考的责任。由于我国重刑主义传统的影响,国民常以刑法作为集体报复的工具,这就导致了我国刑法中的刑罚变成了国民情感宣泄的出口,这对犯罪预防当然是无益的。在刑法所进行的转型中,抽象危险犯的适用为改变这种影响奠定了基础,因为抽象危险犯的适用是不以结果的造成为条件的,其主要目的在于风险预防,在对行为人的处罚上就会更注重教育的作用,这就导致了刑法的适用高于国民感情的变动,其实施使社会舆论处于被动的局面,向社会证实了教育对于犯罪预防的意义远大于单纯的惩罚。
三、抽象危险犯的刑法控制方向
抽象危险犯在刑法体系中的扩张是风险适应的结果,其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刑法的结构转型,以应对突发的大规模社会不利事件。由此,刑法运用抽象危险犯理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风险的社会过渡,简言之,对于其他社会调控措施无能为力的社会风险,要依靠刑法功能的发挥进行有效稀释,待凝聚的社会风险被分解后,再由刑法将其过渡到其他社会调控措施中去。因为“刑法是处理犯罪的有力手段,但不是决定手段,为了消灭犯罪,必须除去犯罪原因,而除去社会原因是社会政策的任务”[13],刑法不能只是在自己的体系之内进行社会的风险消化,刑法的作用发挥必须配合整体的社会防卫需要,尤其是在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发挥上,刑法必须注意到其展开会对刑法之前以及之后的社会调控措施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以此为基础,刑法体系内的抽象危险犯适用才会具有社会协调性。
(一)抽象危险犯适用的刑法结构倾斜
抽象危险犯在刑法体系中的扩张适用代表了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犯罪控制倾向,因为“每一种犯罪都有特定的多种原因”[14],刑法没有办法在体系建设上照顾到所有犯罪的个性,只能够根据不同犯罪的共性做出一般性的规定,所以刑法的理论设计就必须考虑处置犯罪的普遍性基础,以免刑法的功能发挥太过片面。但是,我国传统的刑法结构以追求对犯罪的惩罚作为实现犯罪预防的手段,导致刑法在体系设计上过于强调针对每一次犯罪的具体情况,落脚于“刑”的作用发挥,刻意忽视了“罪”的作用,造成了我国刑法“厉而不严”的结构模式。
由于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主要任务是风险预防,所以其制度设计必须针对社会风险隐蔽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对于风险的全景渗透,能够有所作为的刑法操作方式无非两种,一是在规制上前移,在风险凝聚成大规模的社会威胁时将其在刑法的调控下进行解分,通过稀释其危险强度,减缓法益的紧张程度;二是在适用范围上展开,以刑法的规制向社会的全领域进行布防,严密控制不同领域的社会风险融合,为其他社会调控措施的功能发挥提供后盾保障。但是,如果刑法只是按照这种操作进行结构调整,就会违反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最终损害刑法的价值稳定,所以刑法在风险展开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惩罚措施的调整,以实现刑法的利益协调。
实践中,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已经证明了其可以成为最佳的选择。因为抽象危险犯只对危险行为本身进行评价,不过分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其规制比刑法的传统手段要提前,以实现遏制危险向实害转化的效果。另外,抽象危险犯的相关理论是按照相似行为进行的犯罪归类,所以其所包含内容的范围就比较广,如危险驾驶罪,包含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关联不大的行为,并且还有可能扩张至吸毒驾驶等行为中,充分说明了抽象危险犯的犯罪行为包容性。因此,抽象危险犯刑法规制的内部方向之一在于适用范围的扩张,包括在规制上的扩张和范围上的扩张。
总而言之,刑法因为抽象危险犯理论的适用,所表现出的典型的体系内调整就是在范围展开的同时进行手段的紧缩,相互协作之下,刑法将实现由“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结构转换,从而达到“在法治国的自由状态里,教育受刑人并使之融入合法生活中,可能并不需要对普遍的自由进行限制”[15]的效果。
(二)抽象危险犯适用的刑法制度衔接
刑法以抽象危险犯的扩大适用为方向,通过自身的结构转型,完成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犯罪预防任务。但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应该考虑最有力的,最有效率的东西”[10]126,而“刑罚的本质是恶,是痛苦”[10]126,故而刑法作用的发挥只能定格于风险的高度凝聚状态,即危险。
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理论不是作为直接的犯罪处置内容存在的,其在刑法中的展开只是为了适应对社会风险的提前预防。在制度建设上,相比于对犯罪现象本身的关注,刑法更加注重对其他社会调控措施的警示意义。有鉴于此,抽象危险犯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会针对性地审视每一次危险行为的实施,通过鉴别其风险组成,强调对促成风险转化行为的特殊预防。由于对抽象危险犯进行惩罚是要其承担结果不明的责任,所以刑罚的适用不会严苛,只是为了在对具体犯罪人进行教育的同时,提高潜在行为人的警惕性。配合刑法风险转型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就是在刑法中增设甚至扩大保安处分制度的适用,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的凝聚,又能够实现刑法的价值维持,是比较理想的刑法演进方向。
司法实践中,与刑法的作用衔接比较密切的有关规范,比如在民事法律中强化严格责任的适用即可以实现这种作用。因为在风险凝聚成刑法视野中的抽象危险之前,其势必会在社会多个领域有所体现,对于这种潜在的威胁,直接的关系人要先进行内部的分析和控制,在风险蔓延后还有监管部门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甚至在监管部门无能为力后,还有民事法律规制或者私力救济的余地。以危险驾驶罪为例,具体的行为人出于对自己负责的目的,首先要进行自我的约束,其次要依靠舆论的压力和行政处罚的手段,在前端调控措施均无力对这种危险进行充分的警示之后,刑法的适用才是必要的。抽象危险犯协调刑法体系内的保安处分制度与其他的社会调控措施进行配合,能够实现风险预防和刑法价值维持的平衡。
由此,抽象危险犯的刑法控制方向其实就是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建设方向。刑法的风险转型不仅要立足于刑法体系内的结构转换,而且要配合其他社会调控措施,刑法不能改变其作为后盾法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3.
[2]黎宏.论抽象危险犯危险判断的经验法则之构建与使用—以抽象危险犯立法模式与传统法益侵害说的平衡和协调为目标[J].政治与法律,2013(8).
[3]焦旭鹏.风险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9.
[4]张红艳.欧陆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及其启示[J].河北法学,2009(9).
[5]高巍.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及正当性基础[J].法律科学,2007(1).
[6]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12.
[7]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23.
[8]梁根林.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9]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冯军.比较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刘仁文.死刑的温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5.
[12](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3.
[13]赵秉志.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
[14]赵秉志.英美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1.
[15](德)克劳斯·罗克辛.形势政策与刑法体系[M].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16.
责任编校:汪沛
The Limited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Control of the Abstract Potential Damage
ZHANG Lun-lun
(Law School,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As an active measure of the criminal law to deal with social risks, the abstract potential damage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riminal la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ocial protection function by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However, the criminal law is determined by the limitation that it should not be a direct way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 of the control mechanism losing its balance in operation, we must construct social regulations and control measures, determine which position that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be played as a bottom line, and provide bases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potential damage; criminal law value; cautious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4-0050-06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12
作者简介:张伦伦,男,山东德州人,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4-03
网络出版时间:2015-08-20 12:5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