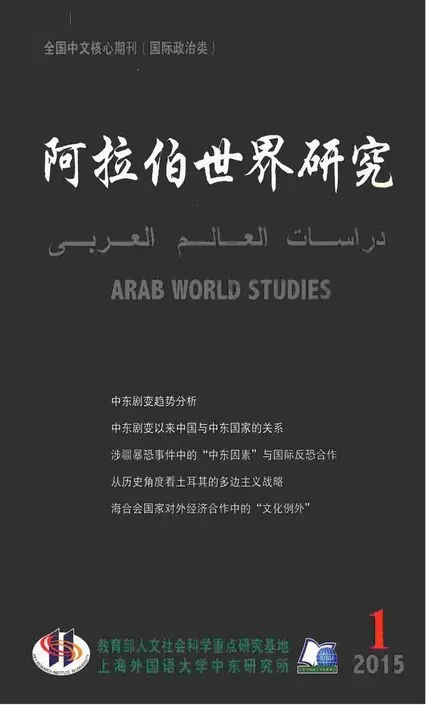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
2015-12-17慈志刚
慈 志 刚
柏柏尔人是北非地区的土著居民,早在阿拉伯征服之前他们就在马格里布地区生活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柏柏尔”一词系外族入侵时对原土著居民的称谓,意为“野蛮人”、“未开化人”,由于历史的变迁,其中蔑视之意逐渐淡化而成为指代这些北非土著居民的专有词汇。在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更多地被称为“卡比尔人”和“查乌亚人”,①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卡比利亚山区和西部的奥雷斯山区是柏柏尔人的主要聚居区,其中奥雷斯山区的查乌亚人基本上已经实现阿拉伯化。此外,在阿南部山区游牧的图阿雷格人也属于柏柏尔人的一支。而在摩洛哥,柏柏尔人更喜欢称自己为“塔玛齐格人”(意为自由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格里布各国的历史发展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各异,所以柏柏尔人问题在各国的表现程度也各不相同。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自独立起,就在为平等的民族权利而斗争,并显现出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趋向,构成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挑战。
一、“卡比利亚神话”——柏柏尔民族是原生的还是建构的?
“民族是原生的还是构建的”这一话题在近代以前阿尔及利亚历史上未曾有过相关的讨论,与其他和现代性有关的事物一样,民族及民族主义的传播是欧洲人入侵完成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结果。对于柏柏尔人问题,法国殖民者、阿拉伯民族精英有着不同的认知,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使柏柏尔人问题从文化历史层面不断转向政治层面,最终具体化为各种困扰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动和事件,可以说,柏柏尔人问题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最重要的民族难题。
1、殖民体系下的柏柏尔民族构建
现代意义的柏柏尔人问题要追溯到法国殖民当局制造的“卡比利亚神话”。所谓“卡比利亚神话”是法国殖民者为实现对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和柏柏尔人“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虚构出来的概念,它认为柏柏尔民族具备许多“原生的”民族属性,这种民族性使其与阿拉伯人分别开来,在文化上,柏柏尔人倾向世俗主义,他们天生就与“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联系在一起,他们接受了《古兰经》但从来不是虔诚的信徒①Paul Silverstein,“Realizing Myth: Berbers in France and Algeria”,Middle East Report,July-September 1996.;在经济上,柏柏尔人厉行节俭,拥有一种有别于阿拉伯人的“商业天赋”;在政治上,柏柏尔人与生俱来的无政府状态被视为表达了一种潜在的民主特质,柏柏尔人的村落议会更是平等主义的主要标志。总的说来,法国殖民当局意在构建一个具有欧洲品质的柏柏尔民族,要让它能够在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中代表和体现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法国的殖民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殖民体系的教育和雇员方面,殖民者有意识地偏向于卡比尔人。②World Infopaedia,Pragun Publicaion,2007,p.117.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很多柏柏尔人接受了殖民体系下的法语教育,成为殖民者执行其“文明使命”的主要对象,除了母语以外,法语成为柏柏尔人更为常用的语言。法国殖民者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重构了一个与过去的历史迥异的柏柏尔民族,人为制造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对立,以推行使阿尔及利亚完全法国化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这种殖民政策给阿尔及利亚留下了双重遗产:一方面,阿拉伯精英将卡比利亚神话与法国的殖民统治相联系,认为柏柏尔人问题完全是服务于分而治之政策而虚构出来的;另一方面,该政策也确实培育了大批接受法语教育的柏柏尔精英,能够为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识字率较低的阿拉伯人相比,他们更胜任独立后的国家建设。事实上,柏柏尔人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迅速进入了经济、行政各领域,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法语特权阶层”的集团,柏柏尔人的特殊地位招致阿拉伯人的不满。
2、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柏柏尔人
尽管柏柏尔人在法国的殖民体系中享有特殊的“礼遇”,但是柏柏尔人反抗法国殖民侵略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柏柏尔人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划分“我者”与“他者”,构建同质化的反抗共同体,但在实践中这种同质化的共同体是很难形成的,这要求对诸如领土、语言、宗教、历史等资源重新建构,以形成共同的民族主义话语。伊斯兰贤哲会提出的“伊斯兰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的口号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斗争的旗帜以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成为民族主义认同的基础,柏柏尔人出于团结斗争的需要,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954年在柏柏尔人聚居的奥雷斯山区,民族主义者打响了武装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柏柏尔人为民族独立革命的最终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涌现出多位杰出的民族解放斗争领袖。但是在革命后期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柏柏尔人地区逐渐边缘化,而阿拉伯人占主导的地区逐渐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特别是1962年以本·贝拉为首的“特雷姆森集团”与以卡比利亚地区为基础的“提济欧祖集团”在争夺领导权问题上发生分裂,最终本·贝拉在布迈丁的支持下成为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任政府首脑,柏柏尔人也因此失去了在政治核心领域里的话语权。
3、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各种民族主义力量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团结起来,民族主义成为各种思想、意识的集合体并彼此竞争。在阿尔及利亚获取独立以后,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成为其首要的任务,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将从对抗性的反殖民斗争向建设性的国家建设转变。但民族主义的惯性使独立后的国家过度强调同质性,而忽视或否认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多元性。本·贝拉政府将阿拉伯—伊斯兰化作为恢复民族性的必要手段,特别是要恢复阿拉伯语作为“文明的语言的尊严和有效性”,①《阿尔及尔宪章》,载《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66页。为实现这样的目的,阿尔及利亚第一个学年就要求实现阿拉伯化。②本·贝拉:《在新学年开始前的电视演说》,载《本·贝拉言论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9页。在突出阿拉伯语地位的同时,柏柏尔文化遭到了极大的贬低,在阿尔及利亚的文献中,柏柏尔人关于文化差异性的主张被讥讽为“封建残余”和“民族统一的障碍”。作为对此政策的回应,1963年9月卡比利亚革命领袖侯赛因·埃特·阿赫迈德领导了一场持续10个月之久的反抗斗争,以示对一党制的民族解放阵线政府推行“种族法西斯主义”的抗议。③Paul Silverstein,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Middle East Report,Winter 2005这场斗争遭到政府的镇压,侯赛因·埃特·阿赫迈德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阵线(Socialist Force Front)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并流亡欧洲。布迈丁执政以后,更为坚定地推行阿拉伯化,将柏柏尔人妖魔化,视为落后的标志和殖民者虚构的“神话”,为此,大学里柏柏尔语的课程被取消,公共场合及文学作品中使用柏柏尔语被认定为违法,并在柏柏尔语区设立了大量伊斯兰研究机构。在布迈丁时期,由于国家的主要焦点是工业化建设,民众对政治参与异常冷漠,所以柏柏尔人问题没有再产生重大的影响。1976年的《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称:阿拉伯语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文化共同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对民族语言选择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关于阿拉伯化的辩论只能是关于内容、手段、方法和步骤等方面的内容。④《阿尔及利亚宪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局,1984年版,第70页。
柏柏尔人问题的产生最初是源自于法国殖民者和阿尔及利亚国家对柏柏尔人民族属性的双重描述:殖民者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美化柏柏尔人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虽然没有造成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事实上的分裂,但给这一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出于构建民族国家的需要,抹煞柏柏尔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平等的权利,否认柏柏尔人的民族属性。由此可见,柏柏尔人问题从产生起就从属于行政当局,因而无法掌握本民族的命运,柏柏尔人问题因而也被纳入到了阿尔及利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之中,寻求独立和平等的民族地位对柏柏尔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神话”。
二、柏柏尔人的文化复兴运动
1979年沙德利成为国家总统,阿尔及利亚进入了一个改革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柏尔人复兴运动开始兴起。由于国家的限制,柏柏尔人的复兴运动最初出现在法国的柏柏尔移民社区中,他们反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柏柏尔语言和文字的压制政策,在法国出版柏柏尔语书刊,翻译诗歌和刻录唱片等,并将这些出版物随同人口和商品的流通散播到卡比利亚地区,很多年轻的柏柏尔人就是通过这些出版物学会了对本民族语言的读写。①Paul Silverstein,“Realizing Myth: Berbers in France and Algeria”,Middle East Report,July-September 1996.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在阿尔及利亚兴起,政府为了能够将运动限制在体制内而采取了对伊斯兰运动妥协的办法,推行阿拉伯化的态度更为坚决。国家的这种政策引起了柏柏尔人的严重不满,1980年3月10日柏柏尔语言学家、作家马默里准备在提济欧祖大学给学生作一场关于“古代柏柏尔诗歌”的讲座,这一行为遭到了政府的禁止,于是在学生中引发了一场骚乱,提济欧祖的学生被逐出校园,不久骚乱便波及整个阿尔及利亚。激进的柏柏尔人控诉政府的“文化帝国主义”和阿拉伯语多数群体的“独裁”,反对教育体系和行政机构的阿拉伯化。他们要求政府承认柏柏尔语是一种主要的民族语言,尊重柏柏尔文化并对卡比利亚和其他柏柏尔人聚居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更大的关注。②World Infopaedia,Pragun Publicaion,2007,p.118.这一运动遭到了政府的镇压,柏柏尔人借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以讽刺政府对自由的压制,称这场运动为“柏柏尔之春”(Berber Spring)。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柏柏尔人的抗议活动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演化为暴力冲突。
柏柏尔之春开始了柏柏尔人的文化复兴运动,导致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泛柏柏尔主义”现象,一些柏柏尔人致力于创造规范的语言标准(塔玛齐格语,意为自由人的语言),并通过文化组织、报纸和政治歌曲等传播泛柏柏尔认同的概念③Paul Silverstein,“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Middle East Report,Winter 2005.,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文化运动(Berber Cultural Movement)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组织。由于沙德利政府采取坚决镇压的立场,柏柏尔人问题没有演变为政治上的危机,但让柏柏尔人意识到捍卫民族权利的重要性。政治上的高压使得柏柏尔人问题缺乏合法的宣泄途径,教育体系问题更多时候成为双方的战场。在阿尔及利亚,教育体系显然是同化少数民族以实现阿拉伯化的最好工具,但是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法语在高等教育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卡比利亚地区,法语不仅是柏柏尔人求生的手段之一,而且还深刻影响到他们日常的经济文化生活,阿拉伯语只能算是第三种语言。1987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承认公民有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组成非政治组织的权力,因此柏柏尔人的文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89年夏154个由年轻人占主导的组织得到官方认可,其中部分在城市,多数分布在山区村落。这些组织的基本目标就是推广柏柏尔语言和文化:他们开办语言课堂;油印时事通讯和语言小册子;搜集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资源,如谚语、民间传说、传统药方、动植物的土语名称和已经废弃的手工艺等。①Jane Goodman,“Berber Associa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lgeria”,Middle East Report,July-September 1996.他们这些恢复民族传统文化的努力帮助柏柏尔民众重新寻获了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感,推动了柏柏尔文化复兴的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柏柏尔人问题开始出现转折并走向政治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柏柏尔人争取平等民族权利的文化运动遭到了政府的强力镇压,使运动朝向政治暴力化方向发展;第二,随着阿尔及利亚经济改革的失败,政治改革提上日程,这就为柏柏尔人的政治表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第三,1989年宪法修订以后,多党制成为国家政治的选择,两个主要的柏柏尔人政党——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②该党强调阿尔及利亚是五种认同的统一,即:阿拉伯、柏柏尔、穆斯林、非洲和地中海。(Rally for Culture and Democracy)——得到了政府承认,成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最后,伊斯兰运动在选举中的胜利促使柏柏尔人意识到了维护民族权利的紧迫性。在1990年的市镇选举中,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获得了卡比利亚地区的大部分选票,在随后的地区选举中获得一个选区的胜利。由此可见,柏柏尔人即使参与到政治进程之中,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微弱的,但是这意味着一个孕育希望的春天毕竟到来了。
三、柏柏尔人问题的政治化
1992年阿尔及利亚即将举行的议会第二轮选举因军队发动政变而取消,在选举中稳操胜券的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对这样的结果表示抗议,一部分激进分子拿起武器将国家拖入内战的深渊。在政府与伊斯兰运动对抗的过程中,柏柏尔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它一方面反对伊斯兰运动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主张,同时对国家的民族政策不满。其中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与军方立场基本一致,明确反对政府与伊斯兰武装的对话,其领袖萨迪博士认为伊斯兰武装抵抗运动将国家带入内战,这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温和的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的秘书长赛义德·赫利尔也表示,如果军队与伊斯兰拯救阵线之间的交易以损害柏柏尔人的利益及其愿望为代价的话,这样的交易将很难实现。③Susan Morgan,“Berbers in Distress”,The Middle East,July 1994.由于柏柏尔人的斗争和政府平息国内叛乱的需要,国家在加强对柏柏尔地区控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柏柏尔人的要求做出了妥协,允许在全国媒体和教育体系中使用塔玛齐格语,设立柏柏尔语最高委员会,并在1996年宪法中承认塔玛齐格语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一。
随着伊斯兰武装反政府暴力行为的升级,军队采取了更为坚决的打击措施,但是持续多年的内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状况,这就使得柏柏尔人问题由文化层面演变为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失业、住房短缺以及缺乏教育机会等,使得柏柏尔主义和文化认同感成为年轻人发泄不满的主要途径。1998年6月著名柏柏尔歌手鲁那斯·马特布(Lounès Matoub)遭到暗杀,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周的政治骚乱。马特布的音乐和诗歌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但反对阿拉伯化,而且认为阿拉伯语是一种无聊的、不利于知识和科学传播的语言,因而他也被视为柏柏尔人为争取柏柏尔语平等地位而斗争的象征。政府宣布这起暗杀事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所为,但是柏柏尔人认为是政府当局杀害了马特布,至少当局没有能担负起保护公民的责任,并认为这起暗杀事件是对柏柏尔文化的挑衅。一个名为柏柏尔武装运动(Armed Berber Movement)的组织甚至威胁要对马特布的死进行报复,并杀死任何执行阿拉伯化法的人。①Adel Darwish,“Divisions with Divisions”,The Middle East,August 1998.2001年4月,柏柏尔高中生马西尼萨·古尔马赫被警察枪杀,由此引发了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持续时间最久的柏柏尔人暴乱事件,5月初卡比利亚发生了一次40万到50万人有组织的抗议示威,16个地区发生骚乱。示威者认为政府应该对警察枪击事件负责,高呼“政府是杀人犯”的口号,袭击政府机关并与安全部队进行对抗。政府再次以铁腕手段予以回应,在不到一年时间内100多卡比尔人被杀,5,000多人受伤,这次事件因此被称为“黑色的春天”(Black Spring)以纪念20年前的“柏柏尔之春”。
“黑色的春天”事件进一步加剧了阿尔及利亚政治的碎片化和离心倾向,此后在柏柏尔人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迫使柏柏尔人政党与执政者决裂,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第一时间退出联合政府,并与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共同致力于此事件的和平解决;第二,由于上述2个政党在维护柏柏尔人权利方面的无能,新成立的“家族、州和社区”协调组织(Coordination of“Aarouch,Daïras and Communes”)逐渐超越了两者在柏柏尔人中的权威地位,它联合了众多非政府的、以村落为基础的决策机构,并成为政府唯一的谈判伙伴,②Paul Silverstein,“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Middle East Report,Winter 2005.其政治要求主要是要求警察撤出卡比利亚地区、惩罚对示威人群开枪者、进行地区的经济改革和承认塔玛齐格语的官方语言地位;①Heba Saleh,“Algerian Insurrection”,Middle East Report,Fall 2001.第三,除上述组织外,卡比利亚自治运动(Movement for the Autonony of Kabylia)的主张在柏柏尔人中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它鼓吹建立独立的自治机构和武装力量,以取代阿尔及利亚的地方议会和警察,在其《卡比利亚自治计划建议书》中将卡比利亚与阿尔及利亚视为两个平行的实体,本质上主张实行联邦制。第四,柏柏尔人争取合法平等权利的斗争出现了极端主义倾向。由卡比尔人哈桑·哈塔卜在1998年成立的萨拉夫宣教和战斗组织于2007年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卜基地组织,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政府和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特别是2010年7月的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据称是为“黑色的春天”中死去的柏柏尔人复仇。
迫于柏柏尔人的政治压力以及民众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的呼声,政府不得不对柏柏尔人的要求做出妥协,2002年阿尔及利亚议会确定柏柏尔语为官方语言之一,但是柏柏尔人问题早已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只是因为柏柏尔人内部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必要的力量整合,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清晰的政治主张,这导致柏柏尔人的斗争始终处于一种力量分散的状态。特别是9·11事件以后,阿尔及利亚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密切,因而使政府在处理柏柏尔人问题上仍能坚持强硬态度。当前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距离最终解决还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
四、影响柏柏尔人问题的主要因素
柏柏尔人问题是阿尔及利亚近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它又与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等问题相交织,因而造成了该问题的复杂化。正因为如此,柏柏尔人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历史的视野和综合分析的头脑。当前阿尔及利亚已走出内战的困境,国家的各项生活也步入正常的轨道,这些良好的趋势为柏柏尔人问题的走向创造了历史的契机,然而正如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当机遇到来的时候挑战也相伴而生了。
1、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迟滞
民族国家建构是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同时也完成由传统的民族认同向现代国家认同转变,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是一个共时、互补的过程。阿尔及利亚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是从反抗法国 132年殖民统治开始的,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发展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的建国方案,所有的民族主义最终在武装反抗殖民统治的旗帜下汇集在一起。独立以后,这种长期以来的分歧表面化,最终通过建立军政体制实现了一种集中式的稳定,国家垄断资源并指导一切建设问题。柏柏尔人的民族属性被纳入应该改造的范畴,阿拉伯——伊斯兰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但是强权能够维持短暂的稳定,却不能消除社会的碎片化,作为一个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柏柏尔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渐行渐远。随着20世纪80年代原有的政治体系被突破,阿尔及利亚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暴露出来,柏柏尔人开始公开追求平等的民族权利。经历了近10年的内战,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离心倾向更为明显,柏柏尔人问题再次复苏就是这一倾向的表现。布特弗利卡执政以后实现民族和解成为国家的主题,但是柏柏尔人认为国家正在利用特殊的历史时机强行推行其“民族”概念,柏柏尔人的民族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尊重。在2005年7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卡比利亚自治运动发言人法哈特·梅赫尼表示,卡比尔人不会轻易忘记他们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无论他们是在1963年的起义中被杀害的,还是在黑色的春天,或在两者之间。①Paul Silverstein,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Middle East Report,Winter 2005.
2、阿尔及利亚政治民主化的顿挫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经过内部的斗争,最终选择了集权式的军政体制,侯赛因·埃特·阿赫迈德以要求实现国家政治多元化为由在卡比利亚发动游击战,挑战本·贝拉的“文化法西斯主义”。这次斗争遭到政府镇压以后,柏柏尔人对民族权利的呼声暂时被压制下来,特别是在布迈丁时期,政府利用复兴伊斯兰文化来压制柏柏尔人运动,却导致沙德利执政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对国家政权发起了挑战。此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政治体系进行调整,实行多党制,从而给柏柏尔人提供了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但是随后军队发动的政变表明,所谓的调整不过是延续以往军政体系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变革。在随后军队与伊斯兰武装的长期对抗中,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国家不断将各级权力进行集中,因而在阿尔及利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首都阿尔及尔,柏柏尔人与伊斯兰拯救阵线站在一起以示对军政体制的不满;在卡比利亚地区,柏柏尔人武装与政府一道对抗伊斯兰主义者。当然,柏柏尔人在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往往占据很多重要的职位,②Isabelle Werenfels, Managing Instablility in Algeria: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since 1995,London and New York,2007,p.51.但是民主的政治并不是这种个人代表的算术叠加,而是要反映出其所代表民众的政治参与内涵,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柏尔人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3、阿尔及利亚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曲折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社会经济资源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和分配,特别是在实现石油国有化以及国际油气价格升高以后,阿尔及利亚开始大力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在阿尔及利亚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斗争的同时,柏柏尔人也在为国内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合理进行着斗争,他们认为政府推行的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并坚信这至少在表面上与事实不符。①James Ciment,Algeria: The Fundamentalist Challenge,Facts On File,Inc.1997,p.120.20世纪80年代初沙德利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后,大量国有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国家对日用品价格的开放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大规模削减使人们怨声载道,特别是经历了近 10年的内战破坏以后,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引起民众普遍的不满。1998年和2001年柏柏尔人的两次抗议行动除了争取平等的民族权利以外,都有深刻社会经济根源,正是由于社会经济上的困苦才导致扩散到全国范围的社会不稳定,在2001年走上街头示威的除了柏柏尔人以外,阿拉伯人也在表达他们的不满,在一些阿拉伯城镇中可以听到诸如“我们都是卡比尔人”的口号。②Heba Saleh,“Algerian Insurrection”,Middle East Report,Fall 2001.当前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或许可以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好的基础。
4、阿尔及利亚文化多元化的艰难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族国家,柏柏尔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这就意味着独立战争时期所付出的牺牲换来的只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否定以及强制性的阿拉伯化,这种建立在单一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遭到了柏柏尔人的反对。随着学校教育的阿拉伯化,柏柏尔人也开始了其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并最终演变为争取平等民族权利的政治斗争:一些激进分子将学校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与歧视,视为导致柏柏尔民族意识政治化的重要因素。③David Crawford,“How ‘Berber’ Matter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Middle East Report,Summer 2001.1996年宪法把柏柏尔语视为民族认同的因素之一,但这也只是在形式上做出改变,阿尔及利亚距离建构多元民族文化还有很长的距离。在一些激烈的政治经济斗争之后,不平等的民族文化问题仍是难以消释的悲剧情结,每当遇到剧烈的社会转折,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都会通过新的斗争得以释放。正如一位柏柏尔诗人所言:“我不是阿拉伯人,但我是阿尔及利亚人,当摆脱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指法国殖民者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以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屈从于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呢?”①James Ciment,Algeria: The Fundamentalist Challenge,Facts On File,Inc.1997,p.121.因此能否建构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性格,将继续成为左右柏柏尔人问题发展的限制性变量。
五、结语
作为一个占阿尔及利亚人口约20%的少数民族,从反抗殖民入侵到民族独立运动,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国家的痛苦转型,柏柏尔人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民族的平等权利遭到了压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柏柏人选择了从文化复兴到要求政治自治的斗争道路,并开始挑战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民族定义。纵观其争取平等民族权利的斗争历程,柏柏尔人问题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维护平等的民族文化是其斗争的主要目标,柏柏尔人从独立初期要求文化的多元化到反对阿拉伯化,再到文化问题的政治化,文化诉求始终在其斗争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政治斗争在柏柏尔人问题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它更成为柏柏尔人斗争的主要手段,除了独立初期的武装斗争以外,柏柏尔人问题经历了逐渐政治化的过程,未来民族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政治方面制度化的保证;第三,柏柏尔人问题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交织是发展中国家通常要面对的问题,民族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只有阿尔及利亚社会经济完成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变,柏柏尔人问题才可能追寻到圆满的答案;第四,柏柏尔人问题往往与其他政治问题同时发生,它是阿尔及利亚政治变革临界点被突破以后,社会政治力量总迸发的一部分,比如在多种政治力量,甚至在伊斯兰拯救阵线中,都可以发现柏柏尔人的身影。第五,柏柏尔人问题不是民族分裂问题,它也没有演变为跨地域的民族独立运动,柏柏尔人分布在马格里布多个国家,由于聚居地区的分散性以及柏柏尔民族的适应能力,各国的柏柏尔人基本都是在体制内寻求解决民族权利问题的途径,虽然存在柏柏尔文化的跨国交流,但是在柏柏尔人中并不存在分离主义运动。②William Quant,Between Ballots and Bullets: Algeria’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p.95.
由于柏柏尔人问题表现出来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这一问题将继续影响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发展:在政治上它关系到阿尔及利亚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在经济上它将影响到国家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延续性;在文化上它将影响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以防止统一国家内部张力的扩大。因此,柏柏尔人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社会的整体变迁必然会影响到这一问题的走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柏柏尔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程度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一个有独立文化特点的民族,柏柏尔人在国家中的地位终将得到承认,民族国家认同、必要的制度安排以及决策者的智慧是这一曲折过程中的关键词,唯有如此,柏柏尔人的春天才会真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