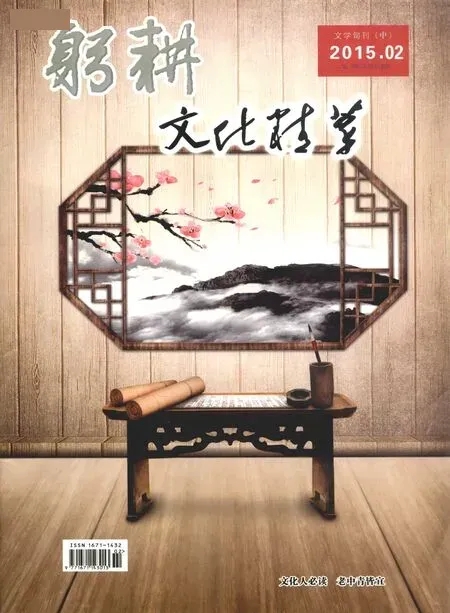西行漫记(外二章)
2015-12-17◆马蕾
◆ 马 蕾
一个人,要不停行走。朝着前方未知或已知的路。
时间在慢慢地悄逝。可是,你能说它很慢吗?——题记
1
晨起,有雨。新闻播着舟曲泥石流的消息。堰塞湖,曾走过不久的地方已变成电视屏上显示的浑浊黄泥汤。这已不是开口说话的时刻,天灾、人祸,我们无法把责任推向自然界。
指着图册,讲玉门关、阳关、莫高窟的一些知识给丫头听。讲着讲着,荒凉感自我心底长出。
我一直在想着敦煌会不会消失,或已经消失。敦煌,始终堆积在心里,渐渐地比梦厚实。可我很少去碰动它,甚至会被暂时遗忘。有一天,亲手揭开蒙住的幕布,走进它,悔恨瞬间遍布,经久不退——
我,来迟了!
戴草帽的人,独自伫立。脚下,山坡的断层。他支着手杖,身后大片绿色田地;跳过土地断层,出现他眼前的,是一小片金黄色向日葵。
山体绵延,他如此静默地在山之外。我仿佛看见一张面孔,写着不安、焦灼的凡高的面孔,被这列山脊铺陈出的格外孤独。有时候,读懂一个人,走进他内心,就是这样地简单。
车过定西,拿出所携书本,却没读,用手臂压着,望窗外。和陌生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听童年的火车开过中年的轨道。
叶子在秋天里变黄,春天里重焕生机。土胚圈住的院内有尖起的屋顶,铺着灰瓦,缓慢的岁月积满尘屑。风晃动了铁马,琉璃脊背上站一排乖乖的走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山和水的间距塞进各种铲车、挖掘机,忽地有种冲动,在林间替他们,放把火。
2
2010.8.14.
比我的背包大些,侧袋插根手杖,他动作麻利地把登山包放进行李架,脱掉鞋爬上床铺休息去了。似乎只看见他下来泡过一次碗面,余下时间都在自己的铺位上,没听过他和旁人搭话。
孤独地行走,沉默寡言人,不多的人生态度和勇气。
景色渐渐单一,沙子,低矮灌木,偶尔扬起的尘土。车厢里飘着淡而轻脆的钢琴曲,内心充满凉凉的忧伤。
戈壁滩上,“兰州铁路局祝您平安”的蓝色标牌比宣传计生、其他国策富有温情,更易彻入人心。阳光下,这趟车的影子沉静地移动,在人烟稀少的沙漠。我也安静地临窗而坐,眼底只有无限虚空。
除那位孤独旅人外,遇到一位游学僧人,峨眉来,敦煌雷音寺去,脸庞清瘦,戴副眼镜。餐车上,听他和列车员聊几句。临近瓜州,他斜挂背袋从我身边走过。
这些人,总让我心生亲切。与他同行。与孤单游走者同行。
(07:35,近瓜州)
远远观望,鸣沙山前一队队骆驼。人,显得异常渺远。这画面并没使我激动,读图时代的缘故吧。
行前,有人对我说:月牙泉,已经消失了。
哦,消失就消失吧,至少我亲眼看过,便无遗憾。
这里竟修了一泊人工湖,我头也不肯扭地从它旁边走掉,连这人工湖泊的名字都无须知晓。向右一转,月牙泉就那样静然地被沙漠环抱——谁,说它已消失?哪怕它愈加瘦弱,那汪寂静始终会在。除非,陪伴它的沙漠消失,蓝天和白云也消失。
泉水被栏杆围起来,虽不能贴近,心里仍欢喜:如莲,远观已如此之好,就不必亵玩。朴拙的古建筑,木已斑驳,我就在廊上踱过去,又踱回来,落日渐渐笼然上身,“听雷轩”三个字也模糊下去。
一弯月,细瘦,清凉,鸣沙山黑色的剪影在这月光中静止。还有这泊细瘦如月的泉。
2010.8.15.
[莫高窟] 打票时,问售票员可以在这里呆到几点钟?他笑:下午四、五点,只要你喜欢。
我们这拨人是今天莫高窟的第一批游客,“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来的游人方可享用清静。来时乘坐的中巴车内,两位老外,一对母子,一位六旬老人,一位八旬开外——满车不多言的有缘人。
看完洞窟,坐在窟前石阶上,目光贴近山体、蓝天,一朵朵白云。宋代建造的木楼沧桑地固定在沙岩间,层次明显的沙体、岩块崚嶒着,盯久了才会明白为何画笔难以描摹出大自然深处的美,这美里隐着的睿智、内涵是无法诉诸任何一种表现形式的,只有选择最近距离地陪在它身边,默默地走进它。
那三层楼阁映衬在不能比拟的天空下,当蓝色里划过一道经久不散的云时,我心匐然,又无上寂静。
敦煌这座城,果然极小。莫高窟内,我再次与行脚的僧人、背包的旅者相遇。从早上,到下午,和女儿泡在这里,舍不得归去。
2010.8.16.
[雅丹] 景区尽处,向前8公里已无通路。自那里进入真正的罗布泊。
脚下纷沓,可视作路的另一种生成方式,须掏出生命全部勇气。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雅丹地貌,昔日疏勒河之干涸、河床上升所造就。阳光,风沙,一切过后,身陷其内的人会迷失方向。魔鬼城,恐惧悄然腾起的疆域,面对自然界,膜拜、敬畏是我们的惟一抉择。
罗布泊,容易激起雄心壮志的地方,孤胆英雄死亦无憾的地方。
中巴车晃晃悠悠地驶过被晒压坏的路面,一粒粒石子颠簸着我们这群来自不同方向的过客,而步下车子,我们又隐没于各自的行程。茫茫戈壁,像是走不到尽头,和上个月怎么也走不出草原、沼泽的感觉近似。
电线杆傻头傻脑地站着,草原、沙漠都被它们穿透,生命力比植被顽强和旺盛。看到它们,我再次想起劈开草原的公路、利益驱使下的所谓建设项目,内心寒冷如破不开的冰封。我也想起那个美国诗人斯奈德拥有梭罗的勇气索居山林,抗拒一切与工业有关的。
而我与我们,一边批判一边享用,把最先布满自己人生的悖论忽略不计。我生活在一个多么可怕、值得悲悯的世界!
[玉门关] 来敦煌,除了莫高窟、月牙泉,使我念念不舍的,就是阳关和玉门关了。
渭城曲。阳关三叠。它和那支二泉同样地不忍听闻。列车出嘉峪关后,“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凉曲调即阴沉沉地压在心喉。那时,车窗外阒无人烟的戈壁滩,骆驼刺、红柳也染着沉暗。琴曲在耳,“遄行,遄行”,一低一高,遏止云霄。见不得折柳之悲的我,庆幸通往阳关的道路正在维修,为我遮掩此份悲凉。只是,不能亲赴渥洼池,走一走传说中天马的故乡,实属遗憾。天马行空,留待下回。
一段关口,肃立烈日下,当年金戈铁马、粮草将士已难寻觅。沼泽地仍在,玉门关前,良久站立之后,那首羌笛无须怨杨柳赋我以另种深意。
醉卧沙场,君莫笑啊!古来征战几人回?大漠,落日,烽火台上狼烟四起;我举杯盏,只和玉门对饮。旁人莫多言;营帐外,千军、万马。
2010.8.17.
[雷音寺] 扩建中的寺庙,后院堆积着大量木料,殿堂已修出大概模样。坐在甬道,正、偏两殿泛出原木的光泽和清香;此刻,午后三点的阳光正艳。风吹过杨树叶子,哗然的涛声。木香里听这过耳林风,偶然掠响林梢的雀鸣,身后屋舍内僧人的轻咳与步履声——这心也就不易觉察地没入头顶缓缓消散的云内。
重重彩绘,翘起的檐角,风动的铁马,枯黄的瓦松,这些始终是我所至爱。尤其那些漆色斑驳的木制阁楼,在雷音寺每个角落穿行,遮挡、重叠的视角可见古朴的美。道光年间的匾额尚未修整,能见到脱落掉重彩露出木色的沧海桑田。仰头可见赵朴初先生、启功先生的题字,亦是心之欢喜。
来此游学的僧人坐在廊下长椅上,和同学辩论佛义。我上前与他招呼后,躬身告别。后来想想,未曾问其法名。再想想,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遇见即缘,余者并不重要。
[离] 干裂的地表上,我再一次行走。不是进入,是离去。
大漠中,太阳落得迟缓,月亮升起的倒不晚。此时的戈壁滩上空挂着弦月,陪伴的,还有湛蓝天空,灰白云朵。明早我一睁眼,这些灌木这些场景都将遗失梦界。
由此,心中漾起淡淡忧伤。我很固执,总是认定走进敦煌、石窟、山和泉,须有美的慧眼、悲广之心。不能或缺的,还须冥冥注定的,我和敦煌的缘分。
2010.8.18.
[白塔山] 抄录古诗一首:
隔水红尘断,凌空宝刹幽。龙归山月晓,鹤唳海天秋。
白塔连云起,黄河带雨凉。倚栏凝望乡,烟树晚悠悠。
念到“黄河带雨凉”,不免记起“春潮带雨晚来急”。
[幽窗] 兰州的街上,茶座很多;三泡台,八宝茶,一柄阳伞,散落座椅,很容易让人想到欧洲那些临街咖啡座,成都的小茶馆,懂生活的城市与人。白河岸边儿,似乎永远是脏兮兮的砂锅摊,若我在河边开个这种茶座,不知生意如何?
白塔附近的长廊内,我和女儿点了蜜瓜,舒服地缩进躺椅内。山的清凉气息从右手边渗过来,每个隔断都仿佛手指能穿破的“窗”,窗外一色青幽。懒懒地,我们伴着碧凉睡上一小觉,睁开眼,仿佛已沾过几分仙灵之气。
岁月,静好。
2010.8.19.
[桑科草原] 女儿说:在这里写诗,多美呀!
可怜她老妈正在喝茶,闻听此言,一口茶硬没咽下去,差点被噎倒,也差点被雷倒。
草原的夜晚,和住在当巴家的几个遇见者同看星空。最先浮出来的,是月。星星慢慢地从云底走出,像是帘栊极深,它们打开得极费力气般。哦,只有看过草原上的星星,你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群星如钻。
独自旅行的柠檬酸听后,说:要记下你这句话。
这样的夜,有寒凉从草尖儿上游荡过来。和柠檬酸聊了聊天葬,他明天一早赶往郎木寺。
深圳来的大姐一个人坐在当巴家的帐篷内,看天空看星星,看月亮。她定好了22号去敦煌的车票。
2010.8.20.
[拉卜楞] 逢一场雨,在这里;能否称为我的夏河?
气温比上次来时有所下降,九月底这里将落雪。卓玛旅社旁的饭馆兼茶室,和丫头临窗坐着,拉卜楞寺和一片黄绿相间的青稞浸在雨里。除了我们,寺庙的喇嘛们也在这里喝茶、交谈,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藏语。
看他们的笑脸,听他们的声音,会想起释迦的中道之修。嗯,对普通人来说,心中有佛,有点宗教情结,或然好事。得道者,终归小众;赵州八十犹行脚:若修不若顿悟。个中奥秘,尽在“机缘”。
夏河县城很小,主干道仅是一条窄小街道。走来走去,常看见藏胞和善的面孔,和我们打招呼,桥边一位藏族男子教我用藏语说“你好”——丘得姆。卖饼子的老阿玛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心被欢喜饱涨着。
当然,偶有不甚友好的,心知肚明,并深深理解。
[补记] 驶离敦煌的列车上,一对年轻情侣说:喜欢的地方,宁愿一次次地来;不喜欢的地方,一次也不肯去。
当我再一次坐上开往拉卜楞的汽车,走过的长长隧道,一晃而过的熟悉地名,此行所遇的背包客,他们都像眼前白云、阳光那样亲切。
望向车窗外面,我一遍遍念叨“不要修高铁,不要建机场”,已有的,就足够。劈开草原、沙漠,不亚于以锋刃割裂我们的心脏。没有人愿意看见,大自然以平静和睿智的眼光注视人类的自戗。
云梢下,闪过许多美得泛出光泽的名字。
拉则塘。格日多。格尔迪寺。
孜孜合。果则塘。德尔隆寺。
乎尔卡加。达尔宗湖。
[在夏河] 离家,几千公里。这异乡里孤独地走久了,心头慢慢滋生出一些描画不出的阴云,像此刻压紧山顶的乌云一样粘滞在眼底、喉间。
夏河,拉卜楞寺,桑科草原。我来了又来,仍将再来的地方。只是这一回,我与夏河的雨不期而遇,它给了我凝重的阴翳。我打着伞从泥泞中踱过去的时候,在想下次相遇,会不会白雪皑皑?
明天一早,我离去后,留下满纸思念。
丘得姆。你好。
2010.8.22.
一宿没睡。翻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歙砚。云南哈尼村落。北上农民工的剧情。频道错落得像断裂的语句。
西安站旁的旅馆内,我也听了一夜的火车鸣叫,这小时候怎么也听不够的声音。
凌晨四点钟,暂无火车进进出出。两点多的时候,站在窗前注视着原定乘坐的那趟车换车头,驶出站。然后,又一列车开走。
不知怎的,想起当巴,想起女儿和她乘坐一匹马“咯咯”大笑着走在草原上,后来当巴干脆让女儿和她一起骑马赶牦牛,还让女儿挑只喜爱的牲口送给她。临走时,当巴说下次直接到她家来,我请柠檬酸给我和当巴拍了合影。一个能干的、单纯的好女人。她做酥油的清晨,我蹲在她身边和她聊天。聊着聊着,她拿出手机让我帮她重新设置,满屏的汉字当巴一个也不认识。锅内牛奶残留底部时,当巴示意我将它们倒进器具内,那表情那语气的毫不见外仿佛我是她的亲姐姐。看着她,我心中还能装下什么?
卓玛旅馆吃晚饭时,结识一位武汉来的阿姨,年近六十岁。她独自背着相机从成都一路走来,已走了六十多天;她计划十月底由西藏回家。若不是女儿即将开学,我真想和她结伴而行。
每个人,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走下去,朝着各自内心向往的净地。这是生命里难得的勇气和态度。
武汉的阿姨对女儿说:你有一位好妈妈,你的童年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那晚,我们从她房内出来,她紧紧拥抱了女儿。我回头时,她正躬身向我们道别:明早,我不能送你们了。那一瞬,我眼中有泪。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乘车去兰州赶火车。她和碌曲赶到夏河的朋友去青海,她朋友一家人准备朝圣。
女儿五岁起,我几乎每年都带她行走,尽力向着有内涵的方向奔去。她的妈妈愿意她长大后富有人文情怀、永怀悲悯,愿意她长大后清醒地活着,哪怕清醒里长满隐痛。而有一天,她将明白那痛里盛开着甜蜜的花朵,蘸满了幸福。
听,一些很江南的音乐
范宗沛,享有台湾“配乐鬼才”之称的音乐人。
水色漫无边际,我走过青石的街道向晚,小小码头上,摆渡之人以吴侬软语唱我听不懂的歌谣,杨柳依依,静水深流……而实际上,这些统统是喜欢人家叫他“胖子”的范宗沛的曲子,充满绮丽江南情调的音乐,西方与东方诡异结合的产物,很好听。
水色
一段时日以来,我心头总纠结着《水色》的音调,以钢琴低缓的流畅、叠叹拉开序幕,柔美得让我的心在琴键上跳舞。
江南女子清扬的嗓音这时如约而至,清扬里沾着湿润。脆脆的琴音逐渐低迷,反复回旋着。弦子偶尔弹响时,钢琴便回归自己的清脆本色,黑白色的琴键跳动着那名女子的弹唱,这时琴声强而人声弱,琴声和人声都有些着急的味道,却猜想不出它们在追赶什么。
停止的吴音在近四分钟的时刻再次响起,进行着序幕的重复,弦子、钢琴、人声,相交,尔后分离,只有钢琴独自唱着小调,带来水的滴落与微漾。
每回听这支曲子,我便以为自己在雨中,然后看见流过古镇的小河、河面上雨点击起的水泡,摇桨的阿姐唱着潮湿的民间歌谣,雨一直下,一直地下。
最爱的,反而最遥远。
摆渡人之歌
《水色》一辑中,我第二喜欢的曲子即为:摆渡人之歌。至少,“摆渡人”这三个字一眼就让我迷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需归。
如果,这摆渡人再于危难之中载那痴情的人一程,岂非更加妙绝?
一个男人的吴声道白,船桨拨动水的声音,钢琴重重叠叠,将人的心事压到低处、最低处。弦子声在最低处弹起,男人开始唱起《珍珠塔》。我喜爱的那些水的声音慢慢远去,小船摇摇晃晃地跟着水声离去,它被划到哪里去了呢?摆渡人始终都在。
也许,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摇桨,一边倾听“想你千里迢迢真是难得到,我把那一杯水酒表慰
情……”
也许,他一边望着失魂落魄的穷书生,一边怀想自己的年少时。
最后一句唱词被压低了的嗓音消褪在船桨拨动的水声里面,天地间倏然静止。
杨柳
杨柳,很容易让人想到《诗经》里那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自古杨柳唯离别。尤其是当我知道这支《杨柳》是范宗沛为白先勇那部《孽子》而配的乐曲之一时,更加重了我心里的伤悲。因为这本《孽子》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它曾深刻地触及我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隐痛与悲哀。长大后的我,甚至缺乏重读它的勇气。
因为懂得,所以爱;因为爱,所以痛。这样我就明白为什么《杨柳》会以低沉的大提琴为主旋律,无限的忧伤深藏其中,大提琴往往会震落一个人滴血的眼泪,清脆的钢琴永远都不能替代的角色。
音乐初始的钢琴声压抑、低调,带着浓浓的无奈,生命的无奈、成长的无奈、青春的无奈;大提琴拉响时,眼泪慢慢沁出来,从心底沁出来,生命更加深重的无奈与痛,虽不是撕心裂肺,也是一个少年终身不能泯灭的痛楚。中央公园,莲花池,这些从不曾消失过的地名再次冲击我的眼眶。
那些对人间的渴望与向往,被大提琴的哭泣演绎着,却无人倾听。所有的一切,都是少年人的心事:我们愿意爱这样的世界,无论它黑暗还是光明,所以请不要,剥夺我们爱的权力。
《杨柳》,一支让人心酸、落泪的曲子。
其他
我还喜欢《青石的街道向晚》、《烟波弄》及其他一些乐曲。有人说,范的《水色》专辑是“一场不可能的奇遇,发现Lounge、钢琴、交响乐与苏州评弹的完美交融。”
可能与不可能,它们没有明显的界定,如果愿意,可能与不可能能够合适地转换。
江南,一个除了美,更充满奇思异想的地方。
夜闻女子十二乐坊
总感觉女子十二乐坊带着浓郁的商业气息,所以她们的CD买回家之后,听的次数屈指可数。可是,音乐没有界限的区分,不同的心境之下需要不同的音乐。正如此夜,我突然想到她们,便将CD放进机子里,任由这些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乐声忽而平和、忽而急促的流淌在春风吹起的夜……
刘三姐
遥远的山歌声掠过,稍纵即逝;渐渐地,水声潺沅,滴嗒作响,溪流清脆,欢快的淌进我心灵的原野,滋润着我近乎荒芜、干涸的心田;那一刻,我突然想掬水在手,让山涧甘泉流入我的喉间。
倏地,鸟声过耳,鸣啾着大自然空灵的奥妙。一小段葫芦丝飘过,悠扬、婉转;琴音弹奏,带着壮族民歌的风情。
旋即,依然是一阵葫芦丝夹杂着琴声拂过耳畔,仿若一叶轻舟划过秀丽的漓江,如镜的江面上顿起一道深深的水痕,波纹过处,刘三姐甜美的嗓音在水面上方久久环绕着:唱山歌哎,这边唱来,那边和……
自由
急剧的小提琴、雨点般密集快速的节奏,奔放的音乐让我的思绪在这个春天的夜空下,信马由缰。
我醺然欲醉,几乎乘风而去,羽化为仙。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是一个永恒不破的梦,是人类美好理想的归宿。
有人说:大千世界里面,每个人都应该寻找自己内心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是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甸、湖泊等种种自然景观所能够给人们带去的内心的宁静:美丽、安然、闲逸以及和谐。
音乐游走在我的梦境,洁白的冰雪悄然融化着,河流淙淙,弯弯曲曲地流过无际的草地,最终汇成一泊宁静悠远的湖,沉淀着我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渴望与爱恋。
无词
忧伤的二胡声声碎,轻慢的琵琶欲语迟,清扬的竹笛穿插而过,挽着行云流水般的筝。穿透时空,我仿若看到身着古装的仕女,衣袂蹁跹,流苏摇曳。伊人无言地伫立于梧桐院落,只凝住西楼之上,那弯明月。
当琵琶、竹笛、二胡与筝交错着奏出同样伤感的旋律时,我触摸得到伊人眉宇间的轻愁,淡淡如烟——
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漠漠烟如织。
感谢年华
这是女子十二乐坊用多曲民族器乐拼合而成,并在电子音乐烘托下带来的感谢年华。
二胡在电子节奏中拉响,充满维族情调的乐音明快地撞击着我的耳膜。
悠扬的葫芦丝缓缓吹起,傣家少女在皎洁的月光下轻柔而舞蹈着,凤尾竹的清影婆娑,与少女的舞姿共同晃动着星空下的一片皎月。
琵琶声急,弹拨着杀机四起的十面埋伏,军营如林,旌旗蔽空,战鼓隆隆,铁骑驰骋,呼号震天,如雷如霆般壮阔。
这支感谢年华只选取了多曲民乐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它并不能彻底表现出这些民乐的景致。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年华,感谢似水般流逝的年华中,曾有女子十二乐坊给我带来春夜中乐音的美妙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