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壁画中的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2015-12-13杨文豪王兴怀
杨文豪,王兴怀,薛 强
(西藏民族学院体育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布达拉宫壁画中的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杨文豪,王兴怀,薛 强
(西藏民族学院体育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分析西藏布达拉宫壁画中的体育图像。布达拉宫的壁画是西藏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古代西藏藏民族开展的体育运动,有其独特的体育特征,为研究古代西藏体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今后西藏藏民族传统体育的恢复与传承西藏体育事业与文化事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布达拉宫;壁画;藏民族;传统体育
布达拉宫是西藏的标志性建筑,它是一个包含了西藏藏民族建筑、宗教、历史、文化、美术、经济的宝库,它的壁画反映了西藏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宗教、社会生活、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方面,本文就布达拉宫壁画中涉及的藏民族传统体育作一研究探讨,为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
一、布达拉宫及壁画
布达拉宫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区西北海拔3700多米的红山(藏语称“芒波日山”)之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寺院于一体的建筑。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起初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兴建。因为松赞干布把观世音菩萨作为自己的本尊佛,所以用佛经中菩萨的住地“布达拉”来给宫殿命名,称为“布达拉宫”。布达拉源自梵文“普陀洛迦”意为光明山、海岛山、舟岛。[1]后来在吐蕃王朝灭亡时,布达拉宫未能免于战火,几乎全部被毁。直到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建立甘丹颇章政权才开始重新修建布达拉宫。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入住宫中,从此历辈达赖喇嘛都居住在这里,重大的宗教和政治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布达拉宫由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布达拉宫后来经历多次扩建,才形成今天的规模。
布达拉宫是西藏佛教建筑的杰出代表,它巧妙利用地形,就地取材,是西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布达拉宫中保存着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各种封敇、诰命,皇帝册封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玉册还有皇帝御赐的金瓶、堂床、亲政大典使用的幔帐,历代唐卡,明清时期的锦缎、瓷
器、玉法琅器等器物,价值连城。
布达拉宫内的宫殿、回廊、门厅内的壁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壁画工笔细腻、绚丽多彩、线条流畅、保存完好。壁画总面积达到2500多平方米,壁画体裁广泛,有佛陀本生传、观世音本生传、藏民族起源传记、宗教活动、节庆典礼、民风民俗、歌舞体育等。壁画全部用天然颜料绘制,其中金黄色的是用黄金研磨而成的金墨所绘,红色是用红珊瑚作为颜料,蓝色是松耳石研磨而成。这些天然颜料具有超强的经久不褪色的特点,因而布达拉宫中的壁画历经数百年依然鲜艳。全部壁画都出自各画派名家之手,是西藏最著名的画派钦孜派与门唐派的高徒传世之作和代表作。这些壁画堪称是壁画艺术的宝库,是研究西藏历史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2]
二、布达拉宫壁画中的藏民族传统体育
(一)朵加(抱举石头)

图1:朵加(抱举石头)
图1描绘了抱举石头的参赛者身着藏袍,进行竞技的情景,画中有人正从地上抱起石头,有人抱至胸前,有人已将石头扛举到肩膀。四周观众正为参赛者加油、鼓掌。这幅图重现了古代武士举重物的景象,具有现代体育中力量素质的特征。
抱举石头(藏语“朵加”),起源于藏族先民的生产劳动,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逐步演变发展起来的。由于古代兵器尚不锐利,且十分笨重,因此要求持兵器者必须有一定的举重技能,持兵器者的力量大小几乎就决定了战斗力的强弱。所以,练习力量也是古代军事练习的必要手段之一。抱举石头有利于发展人的力量,无论在军中、民间或宫廷贵族多以此来作为健身的手段。同时,西藏古代部落之间战争频繁,而战争需要力量、勇敢和智慧,力量作为表现最为表象的重要元素受到社会全体的崇拜与向往,成为衡量社会个人(尤其男性)价值的标志。西藏古人发明创造了很多力量练习的方法和手段,大多以抱石头、举重物、搬运器具来显示力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石头在西藏非常普遍,便于就地取材,所以抱举石头自然成为重要的竞技体育活动。
赞普赤都松执政时期,把体育视为民族兴衰的重要标志,甚至把体育列入极其重要的议事日程。除了考虑训练士兵和军事作战外,还把朵加作为选拔精兵强将与邻邦进行体育比赛和表演的项目。这一时期不仅是王室和贵族重视体育的时代,也是西藏体育呈现出朝气蓬勃、繁荣昌盛、能人辈出的时代。
进入现代社会,朵加成为各种喜庆节日中表演或比赛项目。1994年8月在拉萨市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朵加首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99年,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朵加被列为表演项目。
(二)北嘎(藏式摔跤)

图2:北嘎(藏式摔跤)
图2描绘了6对壮汉在摔跤,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西藏先民“相扑之戏”的情景,摔跤者身材魁梧,体形健壮,头发盘顶,赤膊上阵,或扑、或摔、或跌的技巧描绘刻画仔细而生动。周围围观者甚众,表明了北嘎运动在当时社会中的广泛开展。
藏式摔跤(藏语“北嘎”)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徒手战争,那时的冷兵器笨重而且不锐利,藏族先民在与自然界,与敌对部落的战争中,人们只能靠徒手与对手进行搏斗,两两较力,进行徒手的搏斗与扭摔。这种贴身的肉搏战就是摔跤的雏形,由于部落战争的频繁,徒手搏斗也是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在松赞干布时期,摔跤等体育活动被列为军队的训练和作战主要方式之一,更是男子必备的竞技能力。它是锻炼士兵的力量、意志和提高对战技巧
的重要手段,士兵之间也会经常进行比试。如果说战斗中的摔跤是以生死为代价,那么,吐蕃士兵中进行的比试切磋应该是最早的接近竞技体育的摔跤比赛。
藏式摔跤是西藏古代开展较为普遍的体育项目之一,从摔跤形式上分为固定式、自由式和背抵式,在西藏古代一般以固定式为主。固定式摔跤为双方互相交叉抓住对方的腰带或搂住对方腰部以上的部位,用摔、拉、提、掀等方法把对手摔倒,对方背部着地就算赢一回,连续三次摔倒对方者为胜。在摔跤的过程中讲究“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守中有攻,就势借力”,四两拨千斤,反映了藏民族以智斗勇,追求技巧的审美心理。
在古代西藏,摔跤不仅在男子中进行,在女性中也有开展,尤其在牧区更为突出。牧区妇女因历来承担着比男人更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其力量不亚于男性。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记载摔跤成为康地藏族的婚俗:“当婚礼完成后,新郎角胜,始得同宿。否则,新娘逃去,更须另下聘礼。”这不但说明藏族女子的强壮与摔跤运动的普及,同时也表明藏族人民对身强体壮者的力量崇拜。
在现代社会,北嘎也有了更新的发展。1982年,在西藏自治区第四届运动会上,北嘎被列为表演项目。1985年,西藏摔跤队正式成立。1987年,西藏男子摔跤队首次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古典式摔跤比赛。近年来,西藏摔跤队在全国夺得各种荣誉上百项。西洛卓玛在2011年世界摔跤锦标赛中夺取女子自由式摔跤67公斤级冠军,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来诞生的第一个竞技体育世界冠军。
(三)达喷(射箭)
图3描绘了10位身材健壮的藏族先民弯弓射箭的场景,画面中的人物动作一致,面朝一个方向侧身站立,左手持弓,右手拉弦,弓与弦成近圆,可见射手力量之大,箭身成水平,说明他们是在进行射箭活动。
射箭(藏语“达喷”),距今4000-5000年前远古藏族先民就已发明了弓箭。在昌都地区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石镞,就是现代弓箭的箭头样式。人类社会早期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依靠群体力量进行狩猎,为了不受野兽伤害,而且能有效的捕获猎物,人们发明了弓箭这一远距离杀伤武器。弓箭出现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成为武器中的领头者,使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跨越了一大步。

图3:达喷(射箭)
弓箭最初仅使用于原始狩猎的生产活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武器并用于战争。射箭产生于远古,应用于狩猎和军事战争,最终成为体育项目。弓箭所使用的材料大多是野牛、野羊的犄角,其特点是软而刁,脆而韧,硬而不僵有强劲。
早在第7代赞普时期,西藏就开始有了射箭比试的活动。吐蕃时期的射箭比试通常是站立射箭,分射远和打靶两项。射远比试主要是比拼臂力,以射程远近定胜负。打靶分为击碎山石或射叶(固定靶),疾驰的野牛(移动靶)。这一时期,射箭成为民间和宫廷贵族都广泛开展的竞技比赛项目,尤其是藏族男子必备的技艺。后来射箭比试成为民间庆典活动的竞技项目之一,而且形式更为多样,在原有的射远和打靶基础上,增加了对空射箭,一比高低的项目。
进入现代社会,射箭已经成为西藏各地节日庆典的必备活动,西藏的藏历年、工布节、达玛节等众多民族节日里都会举行射箭比赛。1964年,西藏射箭队成立,先后培养出多吉秋云等多名国家级运动健将,并在国内外大型比赛中取得不俗成绩。
(四)达久(赛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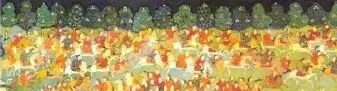
图4:达久(赛马)
图4描绘了在西藏进行赛马的盛况,赛道两边人潮涌动,全神贯注关注着赛马景象,画面中马匹
膘肥体壮,精神饱满,四蹄有力,奋力奔跑,众多骏马争先恐后,整个画面栩栩如生,把人带入到万马奔腾的情景中。
赛马(藏语“达久”)运动在古代不仅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而且是古代军队习武强体的重要手段。藏族先民过着游牧的生活,因而马成为人们交往、生产、战争中的重要工具。生活和环境要求人们必须精于马术,从小就受到训练,随之赛马运动就产生了。
吐蕃时期,战事频繁,需要精于高超马术的将士,赛马成为选拔将领的重要考核项目。在长期的养马、驯马过程中,藏族先民不仅培育了优良的马种,而且掌握了高超的骑术,敦煌出土的《训马术》、《医马术》就足见当时人们对马的重视。藏民族在长期的骑马生涯中,造就了许多精于马术的英雄。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描绘了一位名字叫岭·格萨尔的英雄。他出身贫寒,但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马术本领,在一次赛马胜利后成为岭国国王。自古以来,格萨尔便成为藏族古代骑马称王而有代表性的英雄形象。赛马是古代西藏藏族游牧部落人民经常开展且十分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常以赛马的方式选拔领袖。在征战频繁的年代,领袖要亲自统帅大军南征北战,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藏语有谚语“赛马要在平坦的草原上,英雄要在烈马的脊背上。”[3]
吐蕃时期,马是交通、军事、祭祀等活动中常用到的牲畜,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尊为六畜(即马、牛、羊、猪、狗、鸡)之首。藏文史籍《五部遗教》说,唐代时期吐蕃全境分为4个茹:藏茹、约(左)茹、叶(右)茹和卫茹。每茹又分上、下两个支茹。每个支茹的马匹呈不同毛色。按照马匹毛色进行编队,4个茹兵力共计四十余万。吐蕃精选优良马匹武装士兵,可见,唐时吐蕃确实实力雄厚,兵强马壮。公元756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达扎路恭趁机率骑兵击败唐朝军队,进一步说明当时吐蕃的骑射战斗力不逊于唐朝军队。
吐蕃时期,会骑马是当时游牧为主的藏族基本技能,在马背上开展各种技巧的马上运动,成为人们的娱乐方式。《艺海》记载:吐蕃初期,赛马极为普遍。当时赛马有两种方式:一种以长距离跑,以快慢决胜负;一种是在中心点一骑士驻马而立,另有两个骑士自等距离同向飞驰,先到达中心点为胜。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时,除举行盛大婚礼庆典,还举行赛马大会,藏王松赞干布亲自参加,名列第13,文成公主喜悦之余特献上哈达以表祝贺,按照这一习俗,如今举行的赛马,对第13名获胜者也要多奖励一条哈达。
藏族人民在长期的骑马活动中,马上骑术不断精湛,技艺不断提高,现代赛马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在民间开展的活动形式有:马上射箭(骑射)、马上拾哈达、马上献青稞酒、一人骑两马、多人骑多马、马上叠罗汉、马上形体表演等。如今在西藏有影响力的赛马大会有:羌塘恰青赛马会、当雄赛马会、江孜达玛节、定日赛马节、松宗赛马节等,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此参观,是西藏旅游产业中重要的支柱。
(五)跑马射箭

图5:跑马射箭
图5的壁画中生动描绘了骑马射箭的比赛场景,图中有多名骑手身跨骏马参加比赛,骑手身穿藏袍,头戴胡帽,脚踩金蹬,手持弓箭,精神抖擞,强悍骁勇。第一位骑手手中弓箭已经蓄势待发,弓呈满弓,箭指标靶。其身后第二位骑手紧随其后,准备弯弓搭箭,似乎急不可耐。第三位骑手左手把弓高举,右手持箭,对比赛的渴望似乎更甚。这幅画面给人带来强烈的比赛紧张气氛,周围观众席地而坐,秩序井然,全神贯注地关注比赛,偶与身边观众进行交流。
跑马射箭就是人骑着飞驰的骏马,同时用弓箭射靶。在古代,骑马和射箭往往是不分家的。西藏历史上长盛不衰的体育活动中,跑马射箭是其中之一,它作为西藏古代军事作战的基本手段和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历来都深受重视。藏族的跑马射箭源远流长,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射猎,畜牧为生”。真正的骑射形成应该在吐蕃奴
隶社会初期,发展于吐蕃王朝以武力扩张领土的一系列战争中。吐蕃王朝为了开拓疆土,征战频繁,战争需要在草原战场上驰骋纵横,而跑马射箭成为军队的必备技能。在古代,一支精锐的骑兵队伍往往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利。这不仅要求士兵有高超精湛的骑术,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射术。由于骑兵快速、弓箭锐利,因此他们是当时战场的“快速反应”的特种部队。
作为军事技术的骑射转化为具有娱乐、健身、竞技功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作为过渡的。随着吐蕃王朝公元9世纪40年代的崩溃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爆发,骑射这一军事活动很快传入民间,逐渐扩展到青藏高原各地区,成为藏族在喜庆节日期间举行的跑马射箭表演或比赛活动。
跑马射箭在青藏高原各个地区,尤其是辽阔的牧区经久不衰,深受喜爱。无论欢度佳节,或是集会祭奠,跑马射箭都是最受欢迎、最有魅力、最为精彩的表演项目。跑马射箭在青藏高原之所以能够持久、深入、广泛开展,不仅依赖藏区的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传统,根植于这片土地,自然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4]
(六)游泳

图6:游泳
图6的壁画中描绘了数十名身强体壮的男子上身赤裸,下着短衣在河中泅渡竞赛的场景。在壁画中展示了仰泳、自由泳等诸多泳姿,与现代泳姿无异。还有跳水、踏浪等动作,图画中间的男子甚至是瑜伽静坐的姿势,与现代花样游泳似乎有几分相通。
西藏高原江河湖泊众多,有丰富的水资源,西藏境内的河流有拉萨河、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年楚河、怒江等大江大河,它们组成了西藏的江河网络,在这样的水网地带的居民,临水而居,必须适应水性。人的技能来源于实践,实践由环境来提供,居住在水边的藏族先民自然学会了游泳,也锻炼出了高超的泳技。《格萨尔王传》就将格萨尔王的泳技描绘成“蛟龙戏水”。
西藏古代体育的许多项目都是在战争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游泳虽然是生产、生活的技能,是人与自然斗争的手段,但是战争则赋予了这种本领特殊的意义,游泳技能关系到生死存亡,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所以能够泅渡江河的游泳本领是军队中的主要技能。在拉萨一带,游泳主要集中在沐浴节举行,地点主要设在拉萨河,规模很大,受到民众的喜爱。由此可见西藏古代就对游泳有了掌握和发展。人们认识到游泳在健身、生产、生活、军事等方面的功能,并经常开展游泳比赛,提高游泳技能。
但是,由于藏民族所居住的较为严酷的自然环境,常年低温,气候寒冷,所以大部分地区不宜开展游泳运动。
(七)划牛皮船竞速

图7:划牛皮船竞渡
操舟是古代“越深水渡江河”的技能。在古代西藏,无论是生活还是军事需要,除了掌握游泳技能,驾船也是可不缺少的水上技能,尤其是在河流纵横,湖泊众多的自然环境下。吐蕃时期西藏民间开始用牛皮绷制牛皮船,它是西藏独有的渡河工具,以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牛皮船制作工艺精良。牛皮船造型结构简单,用比较坚硬且有弹性的树木来做骨架,牦牛皮泡水后将毛去掉,四张牛皮并对缝起来,在牛皮泡软时包在骨架上,同时用牛皮绳捆扎,做好密封,防止漏水。然后晒干、擦油定型,制作一副桨就可以下水试船了。牛皮船单人即可操作。牛皮船下水后比较湿软,不怕礁石
撞击,自身重量小,河道深浅均可划行。
由于战争的需要,牛皮船常被用来摆渡和运送物资,必然以牛皮船竞渡形式来训练士兵,对其驾船技术提出更高要求。《隋书·附国传》中记载:“嘉良有水……用皮舟而济”,“用牛皮为船以渡”。
牛皮船不仅用于摆渡和物资运输,也成为民间的一种竞渡民俗和带有娱乐与竞技功能的运动项目。直到现代,这一古老工艺在藏族群众中仍在传承,在拉萨市曲水县俊巴村,村民们用有远古遗风的牛皮船摆渡、捕鱼和牛皮船的制作与修复。
三、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分析
所谓体育文化,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以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机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体育文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民族传统体育和其他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藏民族虽然处在边远地区,经济、文化、卫生落后,生活条件差。但其所创造发明并被后世传承发扬的民族传统体育为其民族生存繁衍,发展壮大提供了合理科学的锻炼方式,且经过代代相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逐渐形成并发展成现代灿烂夺目的独特体育文化。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从藏民族文化中突显出来的一种体育文化形式,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特征外,还具有如下独特内涵的民族文化特征。[5]
(一)强烈的民族性
所谓的民族特性是指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群体所共有的并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性。它成为一种精神,一种行为制度,一种习惯和规范。例如藏民族传统体育当中的“北嘎”,藏式摔跤对其参与者不仅要求具有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技巧,并且要有勇猛顽强的精神。由于其对抗性强,所以人们在进行摔跤时难免有受伤的事故发生,于是形成了人们共同遵守的规矩,就是因为“北嘎”过程中造成的伤害不得怨恨对手,更不得因此结仇。比赛中不允许使用故意伤害对方的动作,否则要受到大家的谴责。
正是由于藏民族所特有的奔放、豪爽的民族性格成就了丰富的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使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传承和发展,并在数千年来形成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体育文化。[6]
(二)经久不衰的传承性
传承性是民族体育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是历史的纵向延续。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藏民族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联系纽带,是在原始生产、生活以及宗教祭祀中保留下来并在长期社会发展中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发扬的。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藏民族的风俗文化的“活化石”,它反映了藏民族的民族性格、崇尚喜好和审美情趣,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西藏古代体育是中华民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经历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经久而不衰竭,繁盛而不泯灭,始终与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信仰和政治经济之间相互联系,世代相传具有明显的传承性。众多藏民族传统项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锤炼、优化而升化、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三)文化内涵的鲜明差异性
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藏民族文化风尚典型的体现,其文化内涵不仅与藏民族思维方式有关,又和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相联系。如“达久”赛马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使得赛马的形式和内容都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色彩。在古代,由于战争和生活的需要,马成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驮运、迁徙和放牧都需要马的参与。长期与马的共同生活,使藏民族从小就练成了高超的马术,赛马、骑射和各种马上技术成了藏民族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赛马自然而然成为藏民族极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和最普及的体育活动。
藏民族传统体育与其他民族传统体育的差异性尤为突出。其中著名的马球运动就是典型代表,它为吐蕃与唐朝的交流搭建了桥梁和渠道。西藏特有的动物牦牛在承担了藏族人民的生产、运输任务之外,也被藏族先民创造了在西藏深受喜爱的赛牦牛运动。这些都是在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所
见不到的西藏藏族所独有的。充分体现了藏民族体育文化与其他民族的差异。
(四)竞技和谐性与审美健康性的结合
藏民族传统体育深得藏族人民喜爱,反映出藏族社会经济及其特殊的生活习俗,且具有很强的审美意义。以藏式摔跤“北嘎”为例,前文中就提到牧区妇女也广泛参与摔跤运动,在生活中男子如果在摔跤上输给了女子是很丢脸面的事情,甚至连婚事都可能不保。这反映出藏民族传统体育中威武有力,粗狂野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藏民族传统体育又精致细腻、平静文明,需要从容镇定的斗智,如“密芒”藏式围棋,又称为“多目棋”就是要眼观多路的意思。藏民族传统体育的竞赛因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对获胜的奖励在现代看来毫无吸引力,对获胜者往往是一碗青稞酒或一条象征吉祥如意祝福的哈达,前文中提到赛马对参赛的第13名运动员也会献上哈达以表祝福,说明藏民族传统体育不鼓励受物质诱惑目的功利的竞赛,反映了其竞技的同时追求和谐的特性。
竞技性与审美性的结合又可以在现代西藏地区各种节庆节日中常见的赛马项目中找到印证。在赛马开始前,各参赛村镇挑选代表选手时都要求男子要选身材魁梧,五官端正,肌肉发达,威武有力,技艺高强,威风凛凛的青壮年男子。女子选手则要选拔那些身体健壮,宁娴雅致,穿着讲究,首饰齐全的年轻女子。这一现象反映了藏民族传统体育对健康的追求与向往,是其审美健康的典型代表。
(五)鲜明的生态文化性
藏民族自古生活在高原环境中,西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草原、湖泊、森林等独特的生态自然环境,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藏民族文化,孕育了剽悍的藏民族性格。藏民族传统体育中不少项目都表现出藏民族的好“动”善“武”、与高原生态环境相适应,同时也是与马为伴的民族文化特征。藏民族在特殊的高原生态环境中创造出的西藏古代体育是人类体育文化的财富,它不仅反映了藏民族对自然环境的眷恋又保留着不同历史时期高原环境下藏民族生活的遗迹。
西藏古代体育积淀着藏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且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藏民族的体育文化中有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共同构成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从史前时期到吐蕃王朝再到近代,藏民族虽然经历着战事连绵,朝代更替。但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却一直未曾中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现代竞技体育成为城镇居民的主流,但藏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些形式和内容仍然在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四、结 语
在布达拉宫的壁画中的体育运动图案上,我们都能找到现代体育的影子和源头,奥运会比赛项目的举重、摔跤、射箭、马术、游泳等都可以在此找到相似的内容。这充分体现了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的聪明与才智,体现了藏民族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内涵。这些壁画将为西藏体育史以及藏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有深远的意义。
[1]王清华.布达拉宫名称溯源[J].传承,2012(6).
[2]李最雄.布达拉宫壁画的保护研究[J].文博,2009(6).
[3]丁玲辉.藏族传统节日与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探讨[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3).
[4]杨海航.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在构建和谐西藏社会中的作用探讨[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9).
[5]耿献伟,丁玲辉.西藏节庆中的藏族传统体育调查[J].体育文化导刊,2013(6).
[6]丁玲辉.试论藏族的体育文化起源与发展[J].西藏研究.1996(2).
[责任编辑 杨海航]
[校 对 赵海静]
G812.47
A
1003-8388(2015)01-0048-07
2014-10-26
杨文豪(1983-)男,河南周口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体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本文系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和谐西藏视野下的西藏体育发展研究”(项目号:13BTY00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