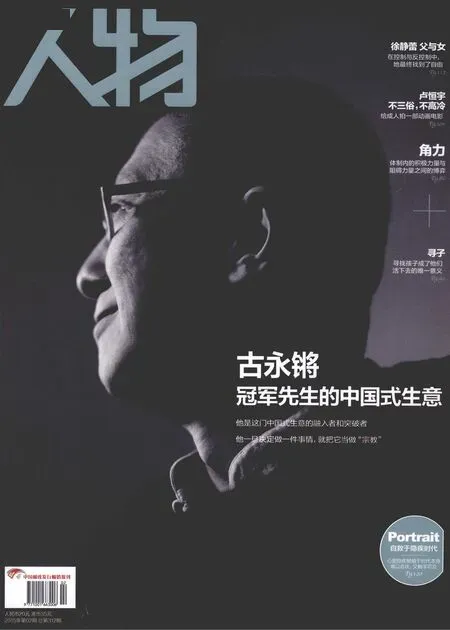统治史:四个转喻和两个不幸的发明
2015-12-08思郁编辑赵立
文|思郁 编辑|赵立
统治史:四个转喻和两个不幸的发明
文|思郁 编辑|赵立
芬纳以笔驱使六合的雄心太大,以致《统治史》就像昔年日本棋手武宫正树在围棋开局所用的“大模样”,气势恢宏,仔细推敲却不免有空疏之感。
《统治史: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
作者:塞缪尔·E.芬纳
译者:王震 马百亮
类别:政治史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塞缪尔·E.芬纳是我所见最有雄心的历史学家之一。这个英国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果壳中的宇宙之王”,仅凭一人的血肉之躯,就要完成浩淼无疆的世界各国统治史的大模样建构。
芬纳于1982年开始撰写篇幅宏伟的《统治史》,搁笔于1993年。死亡是使他搁笔的唯一原因。在去世前,他已完成该书34章的写作(原计划36章)。芬纳的意外去世,使此书所论截止到20世纪初,而没有涉及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史,也未能为全书提供一个有着巨人目光的总结。即使如此,此书仍被学界视作超凡之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如果政治科学领域存在诺贝尔奖的话,芬纳一定会因为这部超乎寻常的三卷本《统治史》而获此殊荣。”
《统治史》主要聚焦于世界各国政权的演变历史,从最古老的苏美尔城邦,直到工业革命后的近代民族国家。在导论中,芬纳说明了他选择研究对象的4个标准,主要是政府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该政府在组织技术和统治理念上对后世所产生影响的大小。根据上述标准,芬纳在世界史范围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十数个政权进行分析,所用方法犹如复调音乐,兼有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
学者赵鼎新在中文译序中指出,《统治史》分析框架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分类系统。芬纳认为一个国家的性质—如组织形式、执政能力、合法性基础、所受制约等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4种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宫廷、教会、贵族和论坛。这4个词都是转喻。宫廷指专制政治,教会指神权政治,贵族指精英政治,论坛则指大众政治。在当代,宫廷与论坛组合就形成极权国家,而贵族与论坛结合则形成代议制政府。在人类历史上,这4种力量的任何一个都很难完全排斥其他力量而对国家进行全面控制,因此,大多数政府是混合型的。
在前述分析框架之上,芬纳概括了4个基本变量:疆域,政权类型,是否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对政治权力的限制。紧接着,他又列出了评价标准的清单:防御、内部法律与秩序、税收与勒索、公共建设与福利、权利与公民身份等。在芬纳看来,决定一个政治建构成功的条件随着时间推移会不复存在,历史上的任何政治建构,即使是一度被视作很完美的建构,通常都会走向衰败。
大致依照历史时间顺序,作者将我们带入苏美尔城邦、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里发、中世纪欧洲、近世日本、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史……他精力充沛地为读者一一辨析:亚述这个遭人讨厌的国家发明了帝国的概念,而这个帝国是宗教帝国;波斯创造了第一个有世俗思想的帝国;通过宗教情感的作用,犹太王国创建了有限君主模式;中华帝国贡献了按照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官僚阶层与常备军,以及科举制;希腊城邦发明了公民概念和民主制:作为公民的个体是独立之人,而非统治者附庸,民主的必然结果则是统治者要对被统治者负责;罗马共和国发明了权力制衡机制,还创造了纳税人选举制;罗马帝国最持久的发明是法治的概念,也即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约束,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中世纪欧洲产生了与世俗权力对抗又共存的教会,对统治者的实质性约束由此达到空前的体制化,中世纪欧洲还创造了代议制,这是现代民主国家模型中最本质的东西之一;英国创造了君主立宪制,并逐步形成了代议制民主不可缺少的工具—竞争性政党;法国发明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美国则贡献了成文宪法、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司法审查以及联邦制。
芬纳还特别强调了现代统治史上的两个全新发明,并将之称作“不幸的”。一个是垄断性官方政党,被政府用作“通向群众的传送带”;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它逐渐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但保留甚至夸大了其武断和对迫害的热情。这两个不幸的发明,加上工业革命后急剧提升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力量,就导致了一种新式的宫殿/论坛政体,即极权主义国家。
在芬纳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各国政权的叙述与分析中,我最注意他对中华帝国的评议。
从提笔描述中华帝国统治史的起始,芬纳就毫不犹豫地揭示了他所看到的帝国秘密: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完全不同。事实上,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主流的社会价值体系相辅相成,这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政府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西方更是不曾出现过。中国稳定、持久的社会政治体系与躁动不安的西方相比,后者更依赖于自由行动与个人责任,而前者则依赖于集体,每一个人都要为其他人的错误承担责任。后者孕育出了公民,前者却只有臣民。西方传统体现了人类在法律和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而中国则与之相反,它一开始就强调年轻人要遵从年长者,女人遵从男人,男人遵从父亲,父亲遵从祖先,然后一切都要遵从皇帝”。
芬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不平等的秩序,并通过规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日常礼仪,将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导入一个总体和谐的有机社会。儒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证明并规定了社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
芬纳进而分析说,2000多年的中华帝国史中有一个跷跷板游戏:“皇权通过自身人事安排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与外戚、宫廷官员及中央大员利用手中权力追求自身利益之间的长期拉锯战”。在拉锯战之外,则是只有服从义务的庶民。换言之,中华帝国的庶民几乎从未有过政治参与的机会,因此形成了一个二元社会:行使权力的统治者(包括皇帝、皇亲与宫廷人员、中央及地方官员)与服从权力的庶民。
汉代衰亡之后,中国进入400多年的分裂时期,这一状况仍未有根本性改变,于是出现了3个后果:“首先,官僚化的中央集权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出现向封建分封制的逆转;其次,在接受官僚机构的过程中,新的统治者们接受了儒家传统,所有的仪礼都需要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的诗赋、历史以及中国的宇宙论和政治科学,‘五经’成为与西方《圣经》一样的经典;最后,一切以上天为中心的概念被保留了下来,‘天下一统’成为帝国的理想。”
接下来,芬纳描述了唐代政治的3个创新—世俗理性的官僚机构、打破世袭的科举选人制、通过御史台与谏官等形成的政府自我批评机制。跟着又分析了明清的士绅政治,地方精英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最后讨论了满清是否够得上“专制主义”的称号等等。这些篇章虽不足以令人耳目一新,但也颇有中的之语。
通观全书,芬纳以笔驱使六合的雄心太大,以致《统治史》就像昔年日本棋手武宫正树在围棋开局所用的“大模样”,气势恢宏,仔细推敲却不免有空疏之感。以该书关于中华帝国的篇章为例,作者在写明清以前的帝国时,主要依赖法国汉学家白乐日的《中国古代历史制度》与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或许因为这个系列未出宋代史,芬纳干脆对宋代只字不提——当然也可能他认为宋代与唐代在统治结构上并无大异,无需单列。而他在写唐代统治史时不断引用《水浒》作为史料证据,就很难说是得体的了。至于将明代的言官制度视为“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更近乎于梦话。不懂汉语,只能依赖间接材料来写中国统治史,难免有点捉襟见肘。
此外,《统治史》的中文译笔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将孔子的“为政在人”,译成“人,而非措施”,又将洛阳称作西周时代的西京等,都是比较离谱的常识性错误。
相较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因充满情感而额外动人的作品,芬纳的《统治史》更加现代,更加技术化,却缺少了古典史家所具备的情感力量。芬纳就像《浮士德》描写的斯芬克斯,“坐在金字塔前,阅尽诸民族的兴亡:战争、和平、洪水泛滥—都像若无其事一般”。也许正因如此,我读《统治史》,能够得到启发,却很少遭遇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