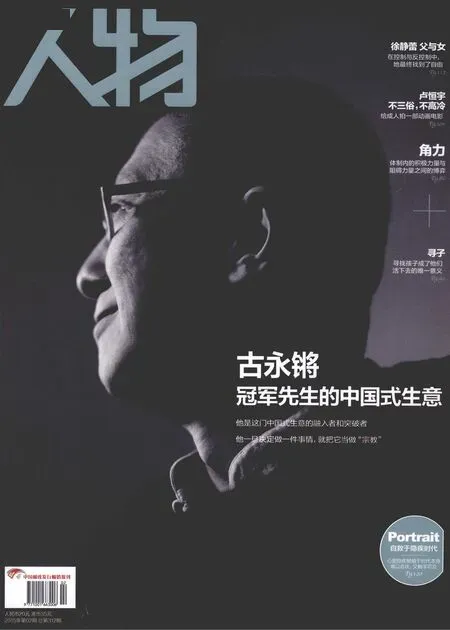来函
2015-11-07
来函


谢谢你用8个小时与《人物》记者钱杨谈论了自己挂职死刑复核法官时的境遇和灵魂折磨。可能我们的读者中有提倡“废死”者,亦有支持“血债血偿”者,无论他们持有怎样的立场,这篇文章都可能为他们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很高兴得知此文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种“灵魂之苦”值得被继续讨论。
同时,有关文章中出现的事实错误,正式的勘误已刊发于卷首处。错误没有任何借口,即便它被认为是可修正的。向相关当事人、读者和受访对象道歉。
都是“人”而不是“物”
谢谢小钱的采访,特别是如此精彩的文章,广泛的社会反响超出了我的意料,但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今天上午新华社记者给我电话说正在翻译本文的英文版,看来影响还在扩大。文章虽然是以我第一人称来叙述的,但谋篇布局的功夫在小钱,她是一个好记者,不仅有很好的文笔,更有独特的文思。
我最喜欢的还是文章的结尾,一个法国老清洁工倚在门框上,而我正在准备回国的行囊,两个人之间有着国籍、种族、文化甚至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等等太多的差异,然而同属人类一家、我们是近亲(Nous sommes proches)的理念使画面充满了浓浓的人间关怀。
关于proches的译法,词典里作形容词是接近、靠近的意思,而作为名词就是近亲,也可以译为同类。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亲近感,这种跨越种族、国籍、民族、文化距离和贫富差距的可感知、可触摸的人间温情与关怀。
谢谢小钱的选题和采访,她拉近了人们和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法官的距离。制度的“最高”掩饰不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法官的身份也不妨碍他们有我们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在面临生死抉择时他们也会犹豫也会苦恼,面对可能出现的错误,他们有着比谁都大的恐惧和害怕。而死刑复核法官们之所以如此纠结、灵魂折磨,也正在于他们将要决定生死的罪大恶极的罪犯们既不是外来星球的怪物,也不是人见人弃的所谓“社会垃圾”或“人间恶魔”。犯罪学历史上天生犯罪人的那一页早就翻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因素、个体因素与自然因素交互作用的综合原因论。死刑犯们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命同样也是命,他们也是我们的同类啊!
套用一下贵刊的刊名,死刑犯和死刑复核法官或者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物”,所以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一样值得关注。
如果再狠心去提一下关于李某案件最终结果的文字错误,我想说的是,即便记者非常认真想方设法地避免犯错,但错误总会发生,不可避免,于是需要制度,例如编辑审稿、核对、校对,或者和作者、采访对象核实情况,然而世上也没有绝对保险的制度,保你万无一失,因此对于制度也要有监督有审视,不能绝对依赖绝对信任。文字错误尚且可以修正,就像韭菜割了可以再长,而对于一旦落地无法再生的人头,我们又该如何补救?这也就是我和我的法官同事们面对生死纠结不已的缘由了。
谢谢!预祝新春吉祥如意!
卢建平
一些读者认为《死刑复核 灵魂折磨》是最近读到的最好的特稿之一—我们认为这并非溢美之词,功劳在于记者,也在于卢建平先生,
缺了点悲天悯人?
我的两个观点,记者过于冷静而显得刻薄,对一个用力过猛的人缺了点悲天悯人的情怀。二是社会阶层的口子撕得太开了,庞就像一支灰头土脸的老鼠,不知怎么钻进了建外SOHO,大家看了新鲜,有玩的,有打的,有想拿他发财的。可问题是,阶层之间的差距怎么会差得这么远了?
衔枚浅唱
《惊惶庞麦郎》是一篇引起极大讨论的报道。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重申《人物》报道的三条原则:新闻真实客观原则,无利益交换原则,为读者提供优质产品原则。也许会有读者对于此文是否符合第三条原则表示怀疑—尽管也有媒体同行认为“文章好得令我嫉妒”—但在编辑部内部,我们认为这是一篇好特稿。引用《人物》执行主编张捷所写的一篇业务讨论,“悲悯这个词不应该是衡量报道的标准,这个词天生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记者没权力悲悯。但是悲悯可以成为读者的感受,读者看完一个人物故事,可能为人物的处境而心生悲悯。”所以当你谈到“缺了点悲天悯人的情怀”时,我们其实不能认同记者被赋予了这种权力。当然,在庞麦郎令人困惑的表象背后,如果能够继续探索追问内心逻辑,可以让报道更完整。这是一篇好特稿,但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好。
(本期回复:编辑总监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