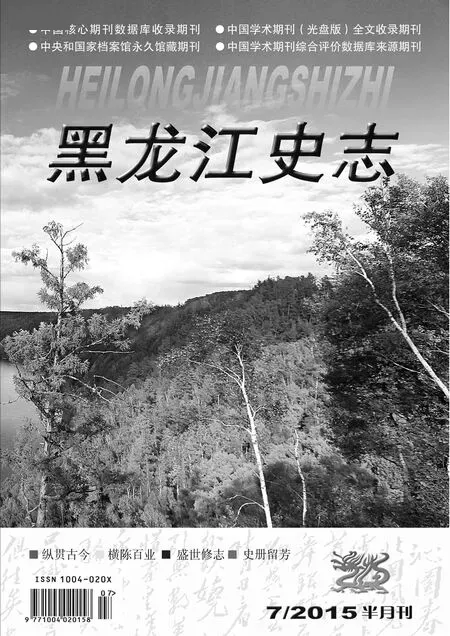道安佛教教育思想探微
2015-12-06罗文
罗 文
(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道安(312-385),俗姓卫,晋长安扶柳(今河北冀县)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领袖之一。佛教初传中国时,一方面遭遇了传统文化的阻力,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也面临典籍缺乏、译经良莠不齐、教理不明、戒律不清等各种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道安致力于佛教教育,成为一名伟大的佛教教育家。道安的佛教教育思想主要有:
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道安生于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从道安的生卒年可知,其进行佛教主要活动的年代正是历史上混战不息的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佛教如果能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和庇佑,不亦为佛教教育的推广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安稳的政治环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正是道安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佛教教育政治方针。
公元349年,后赵石虎死,石氏政权陷入内乱。继而冉闵之乱、慕容氏入主中原、氐人苻健入据长安、桓温北伐等战事纷起,中原重新陷入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道安不得不带领自己的僧团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据《高僧传》所记,道安僧团先居濩泽(今山西阳城西),后又北往飞龙山(今河北石家庄西南)。晋穆帝永和十年(354),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部)立寺,后应武邑(今河北武邑县)太守庐歆的邀请来到武邑。晋穆帝升平元年(357),道安还冀部(指邺都),住受都寺。此后道安又与他的僧团先往西到达牵口山(在邺都西北),后又到王屋女林山(今山西阳城西南),并再次渡河到达陆浑(今河南西南)。直到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慕容氏攻进河南,于是道安和他的僧团准备往南前往襄阳(今湖北襄樊)。《高僧传·道安传》载,“俄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咸曰:‘随法师教。’”在十多年的漂泊生活中,道安僧团深深感到“今遭凶年”所带来的困厄。于是在前往襄阳的途中,道安在新野(今河南西南)对其僧众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实则保障了在战火狼烟下僧人的生存和安全,也为弘法活动的顺利展开提供了稍微宽松的环境。
“不依国主”的“国主”指的是社会上层统治阶层,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领导者、政治强权、军事独裁者,以及南方的王室成员和豪强士族阶层。道安凭借个人魅力,在当时社会各阶层影响深远,得到诸“国主”的尊重和厚待。《高僧传》分别记载了当时武邑太守庐歆、彭城王石遵、凉州刺史杨弘忠、襄阳习凿齿等名士对道安的赏识和重视。东晋孝武帝对道安十分敬仰,曾给予其同王公贵族一样的待遇。其曾下诏,使道安“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前秦皇帝苻坚对道安也器重有加,认为道安“是神器”,给予道安“升輦同载”之荣。《高僧传》就清清楚楚记载了这件事。“会坚出东苑,命安升輦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輦之荣,未称其德。’即敕仆射扶安登輦。”正是这些“国主”的鼎立扶持,使佛教在当时动乱的社会中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
取得这些“国主”的保障和支持,在当时社会是一种顺应时事的明智之举,成为弘扬佛法,传承佛教教育的重要策略。不过,需要明确的是道安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思想,并不是对“国主”的完全妥协和依赖,而是一种相对独立,有原则的依附,这一点在后来道安的学生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有所体现。
二、“教化之体,宜令广布”
如果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是道安为顺应时势而提出的权宜之策,那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则是道安为使佛教弘扬中土所提的百年大计。“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将僧众分开,在不同的地域传道弘法,使教化广布。道安有过两次分张徒众。一次在新野,另一次在襄阳。
如上所述,为避战乱,道安带领自己的弟子南投襄阳。经过新野的时候,道安对自己的徒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大家都表示愿意听从道安的安排。于是在新野,道安开始了其第一次部署。这次分张徒众,被派遣去其他地方进行佛教教育比较杰出的两位僧人是竺法汰和释法和。他们本都是道安的同学,道安根据两人的特点,竺法汰被派往扬州,释法和则前往四川。《高僧传·释道安传》载“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尙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休闲。”《高僧传·竺法汰传》竺法汰“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乃与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遇疾停阳口。时桓温镇荆州,遣使要过,供事汤药,安公又遣弟子慧远下荆问疾。”竺法汰“好尙风流”,他的弟子昙一、昙二“善老易,风流趣好”,他们的“风流”正符合了当时江东名士好清谈的风气。如此,竺法汰及其弟子在扬州的弘教事业顺利展开。“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汰形解过人,流名四远,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及咨禀门徒,以次骈席,三吴负裘至者千数。”可见他们在建康的影响。《高僧传·释法和传》载释法和“以恭让知名。善能标明论纲,解悟疑滞。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四川相比建康,地处偏僻,佛教教育在四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释法和性格恭让有力,又能研究佛教理论,擅长提纲挈领,释疑解难,因此很适合在四川弘教。“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则说明释法和在四川、汉中的传教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第二次分张徒众是公元379年。从公元365年,道安和慧远等弟子渡河南下襄阳后,便安心发展佛教教育,然遇苻丕围攻襄阳,危急之下,道安又进行了第二次分张徒众。《高僧传·释慧远传》载,“伪秦建元九年(实为建元十四年),秦将苻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皆被诲约,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汝者,岂复相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往上明寺。”相对于第一次以道安同学为主体的分派,这一次被分派的主体则是道安的弟子,如慧远、慧持、法遇、昙翼、昙徽等。释昙翼“杖锡南征,缔构寺宇,即长沙寺是也。”释法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释昙徽“乃东下荆州,止上明寺。每法轮一转,则黑白奔波。”慧远和弟慧持及其弟子听从道安安排住荆州上明寺,后在路过庐山的时候,觉得庐山清净,便创立东林寺。此后慧远一直在东林寺居住,钻研佛典,结社念佛,成为东晋著名的佛教领袖,为佛教教育做出杰出的贡献。
对于道安“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的佛教教育思想,汤用彤先生曾称赞道安,“比之遭逢世乱,嘉遁山泽,其在佛教推行上之影响,实不啻天壤。”
三、“弘赞教理,宜令允惬”
自佛教传入中国,译经便是佛教教育一项重要的任务。然而译经质量参差不齐,时人因循守旧,坚持竺法雅的“格义”之说。然而道安认为这样并不妥当,提出“弘赞教理,宜令允惬”。
《高僧传·释僧先传》载“晋飞龙山释僧先与道安重逢于飞龙山,共批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与理多违。’先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竟鸣,何先何后。’”
“格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讲经的一种重要方法,即用中国文化的概念来解释佛教文化的范畴,使国人能够更容易理解佛经的内涵。佛教传入中国初期,采用中国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理论是有益于佛教在当时社会的传播的。然而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毕竟有很多的差异和冲突,而且随着人们对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完全片面的实行“格义”之法已经不能使人更好地把握佛教理论的内涵,只会造成道安所说的“先旧格义,与理多违”的局面。“弘赞教理,宜令允惬”,便是道安争对“格义”而提出的传播佛教理论所应有的一种态度和原则。
为“弘赞教理、宜令允惬”,道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佛典的翻译和整理。“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他还主持翻译了《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受大戒法》《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比丘尼大戒》《鼻奈耶》等。为了能更接近佛教理论的实质,道安就翻译佛经还提出过“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对后世翻译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道安对于“格义”并不是一刀切,认为全无用处。有这样一个例子,《高僧传·释慧远传》载,“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慧远用《庄子》中的道理来解释佛经中的实相义,使听者终于释疑解惑。道安因此“不废俗书”,表明安公在佛教教育的时候还是注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
四、制定僧尼轨范,统一僧尼姓氏
作为佛教教育的主要对象,僧尼是一个大集体,需要一定的集体轨范约束。在襄阳期间,道安率领的教团已相当庞大。由于生活比较安定,除了钻研经纶,编纂经录,传播佛教义理外,道安还在严肃教团戒规,确定佛教仪式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高僧传》载道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道安制定的这一系列僧尼轨范是卓有成效的,从习凿齿给谢安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习凿齿称赞道安僧团“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在戒律方面,道安对弟子的要求很严格。《高僧传·释法遇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
道安还统一了僧尼姓氏。佛教初传,僧人从师姓,师来自康居则姓康,师来自天竺则姓“竺”,师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这对佛教的一体化极为不利。《高僧传》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1]道安统一佛门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古佛教的一大特色。
道安用其一生的时间传教译经、发明教理、厘定佛规、保存经典,为两晋之际的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释:
(1)(南朝梁)释慧皎著《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2)(南朝梁)释僧祐著《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3)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5)方广锠著《道安评传》,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出版。
[1]《高僧传·释道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