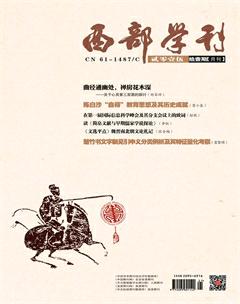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内涵与特色
2015-12-02卢絮
摘要:新历史主义具备关照历史与文化、文本与现实的独特视角,把文化视为完整而自足的网络系统,主体的建构与塑造既是文化网络制约的结果,同时,主体也拥有对文化的阐释权力。轶闻主义力图引起人们对宏大历史叙述的怀疑,同时也以触摸真实的方式对某个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进行精炼而准确的描述。新历史主义对奇闻轶事的重视,其实质是要强调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模糊性和互动性,强调文学和非文学彼此进行“厚描”。同时,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在诗学层面获得沟通,这样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得到修正,历史话语的诗性空间得以拓展。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化网络;轶闻主义;历史话语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新历史主义作为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本土文学批评界出产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和流派,具有强烈的美国特色。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它以美国为中心思考问题,处处体现出民族优越感,是一种偏狭的理论。[1]103但是,毫无疑问,新历史主义具备关照历史与文化、文本与现实的独特视角和基本立场,刷新了传统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念,适应了当代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发展潮流,拥有自己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可实际操作的方法论特色。
一、文化作为符号网络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是由符号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网络。[2]3 这种文化观念主要受到克利福德·格尔茨人类文化学研究的影响。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地方性知识》等作品中强调:“‘文化这个词语指出了一种以符号表示的通过历史传播的意义方式,是一个以符号形式表达的继承性的观念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们得以交流、维持和发展他们的知识以及对生活的态度。”[3]398可见,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符号媒介,具有管理和控制文化系统内人们的行为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作用,文化也是意义的交织网络,人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这些文化网络中形成和指导自己的行为。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通常有两个相反的特征,一是约束性(constraint),一是流动性(mobility)。[4]11组成文化的一整套规则和实践成为了无处不在的控制系统和限制机制,人们的行为必须接受其监督和制约。同时,也充当着文化流动的调节者和保证者,实际上,没有流动,没有即兴发挥、试验和交流就没有文化边界的建立。[4]14可见,新历史主义者心目中的文化充满了流动性、可塑性,具备足够的弹性和张力。不仅如此,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文化的限制性和流动性,文学还通过自身的优势帮助塑造、表达和重建这些特征。对于文学与文化的这种互动的双重阐释和双重建构的关系后文还将提及,实际上,这也涉及到文本与世界、想象与现实、社会与审美、物质与话语等的相互指涉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对话或称“振摆”式的理论视角正是新历史主义始终坚持的一条原则,就如格林布拉特所说:“当代理论必须有自身的定位:不在阐释之外,而在谈判与交流的隐匿处。”[5]28
格尔茨对文化的阐释性内涵是这样理解的:“我把文化看作是网络,文化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科学实验,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行为。我追求的是阐释,以及阐释表面上神秘的社会表达方式。”[6]10强调文化是一个象征性符号网络系统,主体的建构与塑造既是文化网络制约的结果,同时,主体也具备对文化的阐释权力。格尔茨提倡一种文化阐释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厚描”是相对于“薄描”(thin description)而言的阐释概念,源自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薄描”只是对无声的行为的描述,而“厚描”是要把这行为放入一个充满话语意图和文化意味的网络中进行分析。赖尔说:“‘厚描需要对赋予行为以意义的意图、期待、环境、背景和目的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厚描”不是关注产生某种行为的一系列机械的物理动作,而是围绕参与这一活动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展开。“厚度也不是指事物和行为本身,而是指叙述的厚度,是附加在行为上的,如一个嵌套式框架的叙述结构的厚度。”[7]32“厚描”被格尔茨广泛应用于他的人类文化学田野调查中,即抓住一个事件、某个行为或者别的实践,通过询问最细微的繁枝末节,来发现和揭示某种文化的精神气质。格尔茨聚焦于地方性土著文化的意义,而不是普遍的社会原则;聚焦于文化的连贯性而不是社会斗争;聚焦于个体体验式事件而不是人造加工的信息。他会记录下偶然得来的原始材料或证据,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是内嵌在文化中的,它们从文化中来并表达着某种文化意图。“从这件简单的小事情”格尔茨曾经谈到一件偷羊的奇闻轶事,“我们能够拓宽视界,体验到社会经验的极其复杂性。”[6]19 新历史主义者几乎是自觉运用了格尔茨的“厚描”模式,并进一步发展了与“厚描”并行不悖的“轶闻主义”(anecdotes)方法。
二、历史以轶闻方式出场
轶闻概念在历史学中一直有一席之地,不过它往往作为道听途说的野史、秘史、稗史,充当着正史的补充或反叛的配角。克罗齐认为“轶闻和历史同样发展,即使最哲学化、最严肃的历史学的巨大进步,也未去除回忆录、生平传记和所有其他轶闻占据的位置。”[8]93同样,波普尔认为历史的“兴趣应该在于具体的个别的事件和个别的人,而不在于抽象的普遍规律。……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方面的历史。” [9]64福柯提出建立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历史概念,其实质也是对线性、权威历史的解构,提倡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揭示局部话语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网络,将某些事情带入真理和谬误的嬉戏过程,强调历史的断裂性、偶然性和话语性。福柯虽然不是典型的轶闻主义者,但是他的断裂历史观和对历史文化问题的症候式阅读方式无疑和新历史主义有理论契合处。叙述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倡对历史进行诗学的研究,他在评价新历史主义时,指出:“新历史主义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10]106海登·怀特无疑对这些逸闻趣事是抱有相当诚意的,甚至认为其可构成历史诗学的一部分,也十分中肯而客观地评价了新历史主义的这一特点。
一个典型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文本往往以一则令人震惊的事件(event)或奇闻轶事(anecdote)开篇,其效果足够引起对宏大历史叙述的怀疑,同时也力求对某个历史时期,如文艺复兴,进行一针见血、精炼而准确的描述。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这能让我们“触摸真实”。(the touch of the real)[11]3对奇闻轶事的关注,从理论的高度来审视,就是对遗落的历史片段的关注,对边缘历史和边缘人物的关注,对鲜活的生命个体的关注。它的功能就在于推翻某种纲领性的分析模式和约定俗成的系统化方法论,也有助于人们对某种单一的、绝对的历史和文化叙述产生质疑。这类逸闻趣事不是被随意捏造出来证明一个抽象观点,而是一种原始素材,就如格尔茨所言的“漂流瓶中的一张纸条”(a note in a bottle)。它不仅是被人们偶然间发现的,而且是完全“原生态的”( raw),因而其真实性和说服力不容怀疑。格林布拉特认为:“轶闻主义运用到文学研究就是要找寻不被人所熟悉的文化文本,这些通常是边缘的、奇异的、零碎的,意外之中且原汁原味的文本,让它们和人们感觉熟悉而亲切的文学经典文本形成有趣的互动。”[7]36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用词是“互动”(interact),而不是所谓有益的补充或给文学正典添加些边角余料。格林布拉特继续说:“我们要利用这些奇闻轶事,以一种精炼压缩的形式,来展示活生生的经验元素如何进入文学,平凡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如何被记录。”“我们想要发现过去真实存在的身体和声音,如果这些身体早已腐朽,声音早已沉寂,从而无从发现,那么我们至少要抓住那些与真实经验息息相关的蛛丝马迹。”[7]37 实质上,新历史主义的轶闻主义想要恢复的就是文学批评中对于真实存在的确信无疑,而不是利用文学的力量来回避和逃离日常生活,或者放弃最基本的理解,即任何文本的成立都是建立在它所代表的身体和声音的消逝之上的。因而,对“真实的触摸”变得如此重要,它几乎成为文学和文学批评不可不承担的一个责任。
三、重新划定文学边界
传统文学观认为奇闻轶事是非文学的,属于非文学文本。但新历史主义对奇闻轶事的重视,其实质是要强调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模糊性和互动性,强调文学和非文学彼此进行“厚描”。对文化文本的厚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带领着我们不断靠近文学的种种因素往往潜藏在非文学中,这说明所谓文学性是不稳定的,不同叙述类型的差异,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必定要得到重新界定和修缮。这涉及到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格林布拉特曾说:“文学不是一劳永逸东西,它是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它是概念上的权利和对权利的约束不断较量的产物。不仅任何类型的经典文学作品都是在对文类边界的守护又同时受到侵犯下形成的,就连文学概念本身也是不断商讨的结果。”[12]5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文学观念与前文所说的整体文化观一脉相承, “如果将整个文化看做一个文本,那么,所有事情就在叙述层面和事件层面至少潜在地相互关联牵制,那就很难在叙述与事件之间划出明确界线。至少,这种划分本身就是一个事件。”[13]15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是文化的,它的文化属性不仅指向文本外的文化世界,其自身更是浸透在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这个世界充满了文本”,格林布拉特感叹到,“其中绝大多数文本如果离开了它们所处的语境将变得不可理解。为了恢复这些文本的价值,让它们至少变得有些意义,我们需要重建生产它们的文化语境。相比之下,艺术作品(文学文本)直接包含或暗示了这些语境,就是凭借这些持续不断地对文化语境的吸收,使得许多文学作品能够在其生产语境和社会条件崩溃后仍能存活下来。”可见,格林布拉特所说的文化分析不是一种外部分析,也不是文学内部的形式主义分析。其实,他反对的就是这种文本的内外两分的观点,“文本内外根本不存在明显的本质上的差异,新历史主义要重构的就是这种打通文本内外的文化的‘复杂整体(complex whole)。”[4]13这里涉及到的几个基本观点是,首先,文本不限于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有时比文学文本更能让我们触摸到生活的真实,两者之间可以不间断地流通往来。其次,文学的概念和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学概念自身是一个建构和不断重构的过程,这就自然地把文学放入一个历史视域来观察,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时段文学才具备具体意义。最后,文化也可以看做是一个文本,既然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相互交织和流动的网络系统,那么在文本与世界之间、想象与现实之间,或者说艺术与社会之间也是一个不断协商和流通的过程。
格林布拉特在他的代表性文章《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谈到,詹姆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文化文本和与之相反的文化文本之间,独立的审美领域和政治社会领域之间的功能性区别并不存在,并没有这些话语区域的分离,它们是完整的统一体,而资本主义打破了这种和谐统一的模式;利奥塔则认为资本主义力图消灭不同话语领域的区别,使之分崩离析,或抹杀,或断裂,从而建立统一的独白性话语霸权。格林布拉特则持不同意见:“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和谐共处,也不会产生一切话语都彻底孤立或断裂的社会制度,而只会产生趋于差异、分化和趋于单一、独白的推动力同时发生作用的社会制度,或至少两者急速振摆(oscillation),让人以为是同时发生作用。”[5]22 “从十六世纪直到现在,资本主义就已经在确立不同话语领域与消解这些话语领域之间成功而有效地振摆。正是这种一刻不停的振摆,而不是固定在某一位置,才形成了资本主义独有的力量。个体性元素——一系列间断性话语,或兼容所以话语的独白性话语——在其他经济和社会体系中都得到清晰的表述;惟有资本主义试图在这两者之间令人头晕目眩地、不知疲倦地流通(circulation)。”[5]24由上可以看出,格林布拉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审美与现实、真实与想象、政治社会文本与审美文本,抑或文本内外的关系理解非常清晰,即在一种不稳定状态的摆动、交流和往复循环中,两者的功能性区别在确立的同时消亡。
四、历史话语的诗性空间
上文提到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历史观念的变迁,从对历史普遍性和真理性的质疑到叙述历史主义的兴起,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在诗学层面获得沟通,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得到修正。新历史主义者眼中的历史“既是指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或一系列事件),也是对这些事件(故事)的讲述。历史真实来源于对讲述这些故事的充分性的批判和反思。历史首先是一种话语,但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事件的否定。”[2]3新历史主义对个人日记、档案记录、奇闻轶闻等的偏好其目的就在于触摸这种历史真实。这里让我们想起了卡尔·波普尔的话:“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 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 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虽然没有目的, 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 历史虽然没有意义, 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14]259 同样,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事实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不过是构思和讲述故事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表达和抒发历史学家自身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他在《元史学》的序言里说:“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① 这种对历史文本性的极力推从似乎就是要断言历史的虚妄,全然否定历史的真实,这和格林布拉特所提倡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是有一定差别的。
人们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段,所有的历史本身只能取决于建构历史的现在。新历史主义正是在“反历史”的形式化潮流中重新确立历史的维度,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新历史主义眼中的历史与现实并不完全是一种线性的先后序列关系,更是一种共时的历史与现实的文本对话关系,两者之间通过文本存在着相互协调的对话性特征。文学则不是孤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事物,而是历史、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参与到历史之中,并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形成相互角逐和交锋的场所。就如文学文本不再游离于它的作者和读者之外一样,历史也不是游离于它的文本建构之外的事物,历史更不是作为某个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可被拆分的背景或装饰性材料,“历史与文学是相互叠盖的”。[2]3
蒙特罗斯曾用“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来描述新历史主义对历史与文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句话非常流行,以至于被认为新历史主义的标志性主张。一方面,历史的文本化是指历史是通过文本来叙述和显现的,没有文本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也意味着我们无法接触到真实的过去,无法接触到没有经受当时社会历史制约的文本痕迹。而这些文本痕迹不是偶然性存活下来的,至少是一个选择性保存或删除的微妙过程。之后,在被人文学者拿来当做文献时,遗留下来的文本痕迹本身也会再次受到学者们为符合描述或阐释活动的需要而作出相应的选择和调节。另一方面,蒙特罗斯认为“文本的历史化是指历史具体性,即社会、物质内容,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们阅读的文本以及我们所阅读的批评家的文本,也就是说所有阅读形式中的社会和物质内容。”[3]409换句话说,文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植入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物质内涵,文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向前推进,带上不同时代赋予它的意义,留下时代的烙印,甚至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影响,成为了历史事实构成的一部分。新历史主义主张对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存在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对文学文本中的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展开双向调查,其本质就是体现了一种对话理念,表达了一种现在和过去、后人和前人的对话愿望。所以格林布拉特认为学者的工作就是要 “与死者对话”(Speak to the dead)以及“让死者说话”(make the dead speak)。[15]479人类通过文学为逝去的历史留下回味的空间,依靠文学寻找曾经鲜活的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足迹,让当代人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与之产生心灵的共鸣。这说明,文学是历史时空中最活跃的思想因子,它建构了历史,参与了历史进程,同时也是现实文化塑造和发展的最有力的推手。
新历史主义从关照历史与文学、文本与现实的视角出发,把文化视为完整而自足的网络系统,从中探讨主体的建构与塑造问题。而轶闻主义对宏大历史叙述保持怀疑态度,试图以触摸真实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重新描绘。轶闻主义其实质就是要强调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界的日渐模糊,同时主张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在诗学层面获得更多的阐释自由,这样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得到修正,历史话语的诗性空间得以拓展。
注释:
①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序言。
参考文献:
[1]Christopher Prendergast, Circulating Representations: New Historicism and the
Poetics of Culture. SubStance, Vol. 28, No. 1. Issue 88: Special Issue: Literary
History, 1999.
[2]Stephen Greenblatt, The Greenblatt Reader. Micheal Payne,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3]Louis Montrose, New Historicisms. Stephen Greenblatt.&Giles.Gunn, e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1992.
[4]Stephen Greenblatt, Culture. In The Greenblatt Reader. Micheal Payne,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5]Stephen Greenblatt, Toward a Poetic of Culture. In The Greenblatt Reader.
Micheal Payne,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6]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7]Stephen Greenblatt, The Touch of The Real. In The Greenblatt Reader. Micheal
Payne,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8](意)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华夏出版社,1987.
[10]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1]Stephen Greenblatt, Introduction in The Greenblatt Reader. Micheal Payne,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12]Stephen Greenblatt.&Giles.Gunn, Introduction.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1992.
[13]Catherine Gallagher & Stephen Greenblatt,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4]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Routledge. London, 1957.
[15]Stephen Greenblat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Critical Inquiry, Vol. 23,
No. 3, Spring, 1997.
作者简介:卢絮(1979-),女,文艺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14SK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