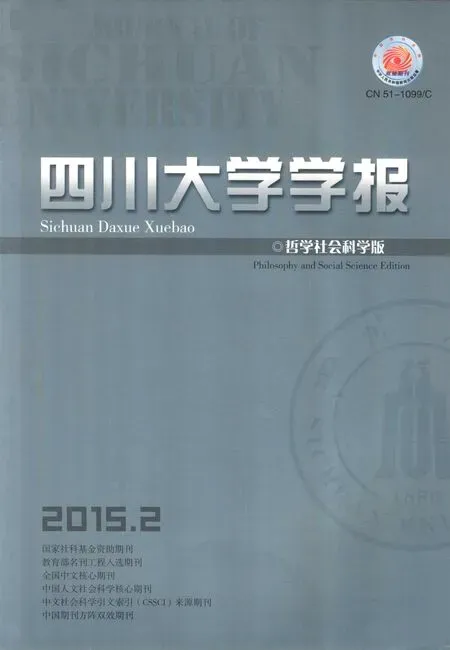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像教”社会——北魏兴佛与废佛的社会结构分析
2015-12-02陈昌文
徐 婷,陈昌文
北魏时期,佛教造像行为盛行。从最初的国家营建到后来民间大量效仿,除去短暂的废佛时期,制造佛教造像的行为贯穿了北魏建都平城到迁都洛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魏书·释老志》首次以“像教”指代当时这种鲜明的社会信仰特征。
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也是“像教”在北魏社会中地位较为稳固的时段,相应地,佛教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也相对稳定。如果用吉登斯结构主义的语言来表述这一状况的话,可以称之为一种“结构”,但此处的“结构”不是指凝固化的既定状态,而是指事物在“社会生活中较为持久的特性”。“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复使用的规则与资源”,①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对结构的解析,可以通过对社会的规则和资源的结合状况来分析,不同规则和资源的结合是社会状况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对“像教”的结构化分析可以明晰宗教社会的特殊社会结构特征。
一、“像教”社会结构化分析要素
关于社会结构,吉登斯提出了“一套相对正规且抽象的概念体系,用来分析社会世界”,②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齐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即“结构论”。结构论主张,进行社会研究应运用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和研究的有效工具。“结构”可以概念化为行动者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与资源。规则即是社会约定,是行动者“知识能力”的一部分,它包括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各种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各种表意性的规则。其中,正式规则主要是指行动者所遵从的法律、规范等正式制度,也叫合法化规则;非正式规则指对行动者行为产生影响的习俗、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也叫支配性规则。资源是行动者处理事务的工具,对资源的运用产生权力。资源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权威性资源,即行动者对所拥有的权威和社会资本的控制,它是强加于人的指挥能力;二是配置型资源,即行动者对所拥有的各种物质实体性资源的控制,它是强加于物或其他物质现象的能力。资源通过不同的形式被调动起来,能够与规则产生出不同的结合方式,使社会系统内的“各种关系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体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
对于宗教而言,其权威性资源是能动性的主体资源,不但包括上层统治权威对于宗教的扶持,还有下层民众对宗教的广泛支持,吉登斯将这两种不同层次的资源统一归入权威性资源。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群体组合方式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征。中国社会宗教群体的组合往往不能够完全依赖于精神秩序,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世俗秩序的维系,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地位、权力等世俗性要素也是维系宗教群体的关键因素,反之,它们也是破坏宗教群体的决定性因素。从云冈石窟反映的北魏佛教来看,北魏早期的佛教发展基本上是上层统治阶层的宗教行为,中后期才深入其他阶层。杨庆堃先生认为,汉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与政治共同体都处在“紧密的结构性关系”中,不可分割。汉代以后,随着道教和佛教的发展,才出现了纯粹出于信仰需求的“自愿宗教”,并且出现了宗教的自发组织,但是他们仍然与上层制度性宗教有着很大的区别。①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3-115页。因此,对于中国社会宗教主体性资源的认识,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根据其不同的形成机制进行划分。本文认为,北魏时期的宗教信仰主体可以划分为两类:统治权威型资源和信仰权威性资源,分别指代中国社会上层具有政治权力的权威主体和下层具有自发能动性的信仰主体。
由此,对中国北魏社会中宗教的研究我们可以在借鉴吉登斯结构论基础上作出如下改进:

图1 宗教社会的结构化分析要素
从图中所显示的宗教结构化分析要素出发,可以进一步根据北魏石窟造像符号的社会特征探究当时社会宗教规则与资源的不同结合方式,在分析宗教社会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对北魏“像教”社会状况获得系统性认识。
二、兴佛时期的稳定社会结构
(一)早期规则与资源的深度融合
云冈石窟造像是北魏兴佛时期的宗教产物,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性,尤其是在早期的昙曜五窟时期,石窟以皇家工程的方式建造,佛教信仰也以国教的形式被接纳和推广,这是在规则与资源的高度融合条件下的信仰行为,体现出两类结构要素在多方面的结合。
北魏是最早实行僧官制度的朝代。魏道武帝 (公元386—409年在位)喜好佛教,规定沙门须拜王者,建立“道人统”,设置了“监福曹”。除中央宗教管理机构外,地方还设置了维那、上座、寺主等,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法律和规范,包括带有强制性的宗教制度。北魏宗教制度在总体上而言很成熟,宗教管理比较成功,规范性规则与统治权威性资源的结合程度较高。
同时,北魏时期,佛教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内容,佛教中国化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儒释道三教合流也达到了一定程度。在北魏云冈造像中的具像中,随处可见源于儒家文化的造像元素,现国内唯一留存的三教合一寺院——悬空寺——正与云冈石窟位于同一地区,只是修建时间略晚于云冈石窟而已。此外,大量文学作品中也随处可见有关民众宗教文化生活的描述,佛教伦理思想对社会习惯和风俗的影响可见一斑,充分体现出支配性规则同信仰权威性资源的深度结合。
最后,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开窟造像所带动的经济行为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满足了部分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尤其是以僧侣阶层为中心的寺院经济的形成,适应了国家和民众经济的客观需求;围绕“像教”进行的福田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惠及下层民众的经济需要,显现出“像教”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表意性规则同配置型资源全面结合的集中体现。

图2 兴佛时期的社会规则与资源结合特征
(二)中晚期规则与资源结合方式的变迁
云冈石窟的存在表明北魏时期的佛教表意符号在社会符号体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造像运动的兴盛使得这一时期的表意性规则在宗教规则结构复合体当中①翟艳春:《宗教的结构化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处于主体部分。从社会结构上讲,一方面,造像符号是北魏社会中宗教表意规则与配置型资源深度结合的结构特征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它也是宗教表意性规则同权威资源相结合的产物。
当然,这种结合在不同时期具有差异性。如果我们沿着历史把这段时间划分为云冈早期、云冈中晚期两个时段,可以看到,云冈石窟早期作品中所具有的鲜明政治象征性是表意性规则同统治权威性资源和配置型资源的深度结合的反映,而中、晚期作品对不同社会阶级的象征性则反映出社会结构中表意性规则同信仰权威资源和配置型资源的结合状态。虽然前后两个时段结合方式不尽相同,但在总体特征上,规则与资源的结合始终保持了比较紧密和稳定的特性。

图3 早期、中晚期规则与资源结合的变迁
可见,在北魏建都平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像教”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始终维持在比较一致的水平上,北魏宗教社会的结构也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像教”通过与各种社会资源的互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并有效地在时空中延续了这样的关系,维系了自身的状态。当然这里并不是把宗教看做是一个具有能动作用的事物 (实际上唯一具有能动作用的主体只是实践当中的人而已),宗教只是实践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实际上维持这种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处于时空当中的人,维持着种种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实践主体是人自身。
(三)人作为宗教实践的能动因素
从吉登斯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规则与资源都是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和交织在一起的。当行动者在时空中对规则和资源加以运用时,能够在互动中再生产出社会关系,这是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二重性”。当然,这种“再生产”对原先的社会结构有维持的部分,也有转化的部分,这要视具体的情景而定。一般而言,如果社会规则和资源的结合较为稳定,那么由此而形成的符号秩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就相对稳定,社会结构也能够进一步在时空中延伸,反之,社会结构就会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那么,规则和资源的结合方式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并没有超出行动者的实践范围,理论的关键之处实际仍然聚焦在人的能动性上面。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生活的运作过程中,实践是通过或多或少松散地组织在一起的集合形式得以维续的”。①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80页。而这些进程的动力来源实际上都出自人类心理的需要,尤其是对于安全感的需要,这些具体的需要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它们依赖于行动者所在的社会制度模式。换句话说,对于当下情景的反思能力使人们具有延续或者改变未来环境的可能。
吉登斯所说的“或多或少松散地组织在一起”正像戈夫曼的“松散的耦合”,“耦合”的概念是戈夫曼在表述有关社会结构的观点时使用的。戈夫曼认为,对于社会研究,虽然不能仅仅用微观层面的解释 (例如个体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互动)来说明宏观事物 (例如社会结构的形成)的变化,但是微观层面的原因却可以作为宏观方面解释的补充出现,因为宏观的现象可以被转化为具体的个体投入互动的行为方式,例如实践行为。
对北魏“像教”社会而言,造像活动是社会中信众普遍的信仰实践行为。北魏时期的造像活动从国家层面开始,此后逐渐转化为民间的信仰方式。无论是从行为的规模还是从持续的时间上讲,这种宗教实践行为的影响都未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或较小范围内。仅从造像行为,我们虽然不能完整地判定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却可以从这种实践行为中判定行动者的某些特征。但是,对于不同的社会类型来讲,“行动者”所指称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对于北魏这样的阶级社会而言,在权力极端不均衡的客观情况下,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有很大差别,怎样理解他们被“或多或少松散地组织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在灭佛时期的社会结构中进一步寻求。
三、灭佛时期的社会结构调整
北魏平城时期佛教的繁荣发生在太武帝灭佛之后,从时间的序列上讲,灭先兴后。与兴佛时期的社会结构特征相对比,灭佛时期宗教社会规则与资源的结合关系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断裂:在统治阶层对“佛教”的态度转变下,统治权威性资源与规范性规则相分离,佛教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进而佛教寺庙、造像尽被拆毁,宗教表意性规则同配置型资源和统治权威性资源相分离。同时,佛教伦理在社会当中的影响虽不能瞬时消失殆尽,但也受到严重影响,因而支配性规则同信仰权威性资源的结合也受到破坏。
从这一系列规则与资源结合关系的断裂序列中,能够看出灭佛时期的关系断裂并不是同时性的,最先出现的关系断裂发生在统治权威性资源与规范性规则之间,也就是最具有强制性的部分。这样的社会结构特征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结果。
对于“社会结构再生产”,吉登斯认为“在大多数社会生活情景下发生的是有选择性的‘信息过滤过程’,借助这样的过程,具有战略性位置的行动者努力以反思的方式,调控系统再生产的总体条件,要么维持原状,要么改变他们”。①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92页。这一观点鲜明地强调了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很显然,阶级社会中“具有战略性位置的行动者”是统治阶层,他们在权力分配上的绝对优势使他们具有对于社会规则和资源的支配权,即使是在“像教”信仰最为盛行的北魏亦是如此,云冈石窟造像在各方面的特征都说明了统治阶层对宗教符号表意系统的巨大影响。同样,在灭佛的过程中,统治阶层的能动作用也就具有决定性。
可见,在北魏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无论是兴佛时期,还是灭佛时期,不同阶层行动者的能动性存在巨大差异,对社会结构造成本源性影响的仍然是上层的统治阶级,行动者行动能力的“组合”是以统治强力为先导的组合。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规则和资源的结合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特征是以行动者的有选择性的反思为前提的。那么北魏时期什么才是这种反思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呢?
对发生在公元445年的灭佛运动,学术界一般认为与两方面的原因直接相关。首先是来自宗教内部的争斗,即佛教和道教实力的此消彼长。《魏书》记载: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②《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3页。
其次,佛教自身的腐败成为灭佛的导火索。史书记载:
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 (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③《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3页。
这次灭佛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几乎造成佛教毁灭性的灾难。但这两方面的原因并不足以构成灭佛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这次灭佛之前,太武帝已经实施过一些对佛教进行抑制的措施:“太延中 (公元434年以后),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增。乃以沙门众多,召罢年五十以下者。”④《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后来这些被召罢的人,“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⑤《资治通鉴》卷123《宋纪》五,文帝元嘉十五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867页。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原为僧尼,可以逃赋税、免劳作,如今则回归到农业生产和兵役当中去。可见当时僧尼人数众多已对国家统治造成阻碍,太武帝已经有意识地对沙门规模进行限制,并力图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但这种抑制举措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僧尼人数继续增长,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而可以断定的是,太武帝灭佛的深层次原因是佛教具备的各方面实力已经大到让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地步。佛教有组织的聚会、活动对统治秩序造成威胁,被认为“视王者之法蔑如也”,将导致“礼仪大坏”、“使王法废而不行”,⑥《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同时佛教也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经济秩序。实际上,复法以后这个问题也还是存在。北魏孝文帝时,孙渊曾上表谏言:“关右之民,自比年以来,竞设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无上之心,莫此为甚。”⑦《魏书》卷47《卢玄传附卢渊传》,第1048页。这些都说明北魏时佛教发展规模使统治者在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上产生危机意识,因而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彻底转变对佛教的态度。
因此可以说决定北魏统治者“反思”的两方面关键性要素是政治和经济统治秩序。虽然有学者在一般情况下认为“信仰所导致的精神结构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原因,而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强化精神结构,进而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非信仰行为”,①陈昌文:《圣俗边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但从北魏佛教的兴衰看来,情况有所不同,信仰的精神结构并非决定社会结构的原因,统治者所执掌的经济秩序和由此决定的政治秩序才是决定社会结构的关键。
从北魏灭佛前的社会特征来看,北魏社会的权力分配特征与社会规则和资源的结合特点是不匹配的。太武帝灭佛前,民间佛教徒众多,造像活动轰轰烈烈。虽然统治者在社会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但此时的统治权威性资源与表意性规则的结合程度及其对宗教配置型资源的支配程度却非常有限,其程度甚至比不上信仰权威性资源与表意性规则的结合程度。由此,便导致了宗教的非制度性规范的有效性超过了制度性规范的有效性。北魏在经历了灭佛和复佛后,佛教再一次蓬勃发展,这一次的发展与前次的有所不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统治权与宗教的结合,表现在社会结构特征上,信仰权威性资源、宗教配置型资源与宗教表意性规则深度融合,统治者对宗教配置型资源的支配程度也很高,尤其在云冈早期尤其如此。从灭佛到复佛,社会规则与资源经历了不同的结合,社会结构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出,规则与资源的结合并非是任意的过程,它们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有着保持一致的趋势。
在这种一致中,只要权力的分配没有大的改变,规则与资源的结合就存在着相对平衡的状态。但这并不是说某一规则和某一资源的结合存在一个平衡点,背离了这个平衡点就会发生结构上的调整,而是意味着,在构成社会总体的各种规则和资源的相互结合中存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这些结合状态在构成总体的社会中是相互匹配的话,那么整体结构就相对稳定,这样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被复制的程度就大,反之就小。
从北魏“像教”的发展历程看,北魏社会中,决定这种匹配状态的是社会中权力的分配状况。北魏的统治阶层是享有至上权力的阶层,从统治阶层到士人阶层、僧尼阶层和普通民众,权力秩序处于有序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废佛之前,北魏僧尼泛滥,造像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逃避税赋、经济特权等现象层出不穷,位处社会中层的士人和僧尼阶层的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不断扩大,威胁到上层的统治权力,成为权力秩序金字塔中的不稳定因素,统治阶层于是采取了激烈的措施来维护先前的权力秩序,可以说,北魏时期发生的太武灭佛事件是激烈的社会冲突的一次体现。对于社会冲突,一般认为其激烈的程度与它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程度正相关,从废佛后的社会情况看的确如此。但是,后来的复佛则又表明,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与再组织的方式又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直到兴佛后的平城时期,规则与资源的结合重新与社会权力秩序相匹配,体现出新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征。
四、结 语
北魏“像教”的复兴,如果只从需求上看,体现了佛教自身的需求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交互作用,是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结果。若从社会结构的高度上来看,佛教适应的过程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宗教社会的规则和资源之间的结合方式逐步调整的过程。显然这种调整不是随机和任意的,它受到社会权力秩序的制约和引导。所以,从外在表现上来看,造像行为在北魏时期是以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样态呈现的。但是,它的行为效果却并非仅仅体现在造像的塑和拆之间,其社会意义是复杂和深远的。
从社会学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出发,北魏“像教”的兴与衰实际上反映了历时状态下社会规则与资源的不同结合方式。兴佛时,在“像教”的影响下,社会规则与资源高度结合,其中,社会规范性规则与统治权威性资源的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法律和规范;支配性规则同信仰权威资源的结合,形成了对社会习惯和风俗具有一定影响的宗教伦理思想;表意性规则同配置型资源结合,使得宗教经济制度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废佛时,统治权威性资源与规范性规则相分离;宗教表意规则同配置型资源和统治权威性资源相分离;支配性规则同信仰权威性资源的结合也受到破坏。在前后两种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对社会规则和资源形成调控的是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顶层的统治阶级,而调控的原因则是成为信仰识别符号的“像”在规模化和体系化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同权力结构的不匹配,这直接导致了“教”的衰落。这是“像”与“教”的互动关系在北魏社会中的特殊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