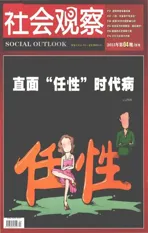卡夫卡的权力恐惧
2015-12-02姜书良
文/姜书良
卡夫卡号称“弱者天才”,他的小说,浸透着莫名的恐惧。对此他深有自知之明,他曾在致密伦娜的信中说:“我的本质是恐惧”;在日记里他也说:“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使自己感到可笑的羞耻的恐惧。”确实,当我们翻阅卡夫卡的书信、日记、随笔及小说时,不时会感受到其中的恐惧,如《城堡》中K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甚至在夏天也忧虑下雪。这种对恐惧情感的深刻描写,是卡夫卡贡献给世界文学的一道独特的精神风景。
权力魔网:无处不在
让卡夫卡恐惧的外在力量,都可概括为某种权力挤压。尼采有言:“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卡夫卡小说几乎是对尼采这一哲学命题的图解:权力无处不在——伦理血缘、经济优势、法律裁断、政治统治,以及由之而衍生出来的某种依附权力,都在发挥作用。人类文化进步的主要成果便是形成了无数的规矩、机制,人群由此划分开等级却又必须互相依存,权力得到落实,而弱者的自由空间总是被剥夺。
最为显著的恐惧表现是卡夫卡对父亲的矛盾态度,父亲在其创作中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某种程度上说,卡夫卡的写作生涯是与父亲这一形象息息相关的。他自己也说父亲就像“上帝”,而写作犹如“祈祷”。他在《致父亲的信》中甚至宣称:“我写的书都与您相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泻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卡夫卡说他的写作与父亲相关,不是如别的作家那样怀有对父亲深厚的眷顾,而是暗含着对父亲的那种既遵从又反感的矛盾感情,对父亲这一形象产生的恐惧心理。这在他《致父亲的信》中有直接表达:“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您的看法正确,别人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是偏执狂,是神经不正常。您是那样自以为是,以至于您可以不讲道理,总是您常有理。”
形象阐释对父权恐惧的是短篇小说《判决》。格奥尔格·本德曼的父亲高声叫:“我宣判你去淹死!”格奥尔格也就服从,跑下楼去跳河自尽,最后还喊:“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在家人的疏远、冷漠对待下默默死去。而父亲,不仅没有分担儿子遇到的灾难,还用苹果去砸他,正好击中格里高尔的背部,造成致命伤。格里高尔与《判决》中的格奥尔格一样,至死对伤害他们的父亲没有任何的怨言,理由很简单:父亲是代表握有权力的一方,可以随意处置他们。
除父亲之外,卡夫卡还不断寻找更具代表性的艺术载体对权力进行解读。他在《审判》中找到了父亲的替代品——“法”。《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而他自己竟也稀里糊涂进入了这一审判的怪圈,去做一系列无效的申辩,最终被荒唐地拖到郊外执行死刑。那设置在昏暗的阁楼上操着生杀大权的“法庭”似有似无,所谓的法官、律师均朦胧模糊,从而使得对约瑟夫·K的这场审判显得荒谬绝伦。但它让主人公无法逃避,更荒谬的是主人公最后心理上也屈服于这一法律权威。
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城堡”象征的权威更为强大。小说主人公K自称是土地测量员,要进入城堡。城堡就在目力所及之处,却永远不可能接近,而且谁也不知其真面目。K挖空心思,做了多方努力,但哪一条都没走通,甚至越是努力,离目标越远。K为进入城堡所做的努力与失败,显然是一个象征寓言,隐喻奥匈帝国官僚机器与人民的隔阂和对立,底层小民在专制体制掌控下的无奈及可悲,等等。从更深的层面上,它也象征某种笼罩一切的力量,一种让人感觉得到而捉摸不透、无处不在且阴森可怕的强大势力。福柯认为权力上的不平等永远无法消除:“权力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肯定的特征,这种观点产生出一种思想,即主体并不先于这些关系而存在,主体事实上是这些关系的结果。”卡夫卡在福柯之前已经用小说形象地阐释了这种权力理论。
权力运作模式:随意和荒诞
人类社会告别原始时代进入文明阶段,当然需要有管理和统治,也就必须有权力,但权力的运作模式,在卡夫卡笔下,并不像文明史中所写的那样井井有条,而是随意而荒诞的。

卡夫卡号称“弱者天才”,他的小说,浸透着莫名的恐惧。
权力运作的随意和荒诞性在《城堡》中得以集中体现。城堡代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密密层层的等级,数不尽的官员干的皆是一些无效和无聊的工作。卡夫卡的好友勃罗德说:“卡夫卡在《城堡》中展现一部伟大而悲剧性的图景。”城堡外表看组织严密,按部就班,实际空洞而不合理。在城堡的官员办公室里,“文件堆满了四面的墙壁”,“成捆的公文还陆续不断地送进来”,“官员们忙于处理事件,却只是站在桌边,在书桌上并排放着一本本翻开的大书,他们并不盯着一本书看,也没有交换书本,而是不停地交换站的地方”,“录事员坐在矮桌边等候口授记录,但官员从不明确地发布命令,也不会口授指示,只不过在看书时说着什么话……”而这极其荒诞的统治机构就代表着最高权威,使城堡的村民甘愿受其统治。
与此类似的寓言还有《法之门》,一个农民请求进入法之门。但是门卫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农民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门卫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直到他快要死了,门卫对他吼:“其实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关门走人。”法之门为他一人而开,他偏偏又不能进去,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悖论,所谓的“滑动佯谬”。如此认真地并游戏式地对待其所服务的对象(这门是为你开的),深刻揭示出权力运作的随意和荒诞特征。
对此,卡夫卡在随笔《我们的法律》中也有明确揭示:“我们的法律一般是没有人知道的。它们是一小群统治我们的贵族的秘密……这些一目了然的法律,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臆测出来的东西……如果存在着什么法律,其实质也只能是这样:贵族的言行就是法律。”《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劳师动众动员全国之力修的长城工程,貌似有一个抵御北方民族的神圣目的,其实人们根本就从没见过那些骑马的民族,分段修的长城留下了很多缺口,根本实现不了抵御的功能,而且修长城的命令也不知是哪年哪月由哪个皇帝发出的,“他们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着怀疑”,但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权力,照样驱使着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开家乡奔向遥远的北方,一代一代持续着那毫无意义的修长城工程。
不要以为权力运作随意和荒诞会使它成为纯粹可笑的游戏,而消减其伤害性,事实恰恰相反,非但不减轻,而且因为权力的滥用,随意伤害无辜便成了必然。《城堡》中城堡的一个普通官员索尔蒂尼,写信要阿玛丽亚去陪他,用语粗俗下流,阿玛丽亚愤怒拒绝了,结果全家陷入恐惧,甚至引发了全村的恐惧,惧怕城堡方面的报复。《审判》中约瑟夫·K想为自己辩护,有人告诉他:辩白肯定无效,法律一旦认定谁有罪,就不可能让你翻身。关于权力荒诞运作使人人自危,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捷克工程师去伦敦参加学术研讨会,回国后发现《红色权利报》说他叛逃到西方了。他对这一不攻自破的谣言非常恐惧,到处申诉,但已无济于事,最后只好真的跑到西方去了。米兰·昆德拉说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故事:“工程师面对的权力有着一个漫无边际的迷宫的特点。他永远也无法达到它那些无穷无尽的通道的尽头,永远也找不到是谁发布了那致命的宣判。所以他跟约瑟夫·K面对法庭,或者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们身处的世界都只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般的机构,他们无法逃出,他们也无法理解。”
权力赋予:侵夺的合理化和秩序化
卡夫卡经常对小说中的人物背景不作什么描述,主人公一出场便被设定在一个权力机制完全成熟的环境中。而那貌似神圣的权力,其实都是侵夺的结果,各种强盗式的侵夺,一旦成为事实,便顺理成章地变成合法合理,进而演化为某种秩序了。就像公共汽车上有人强行占座,本是无赖行径,但过了两站,那占座的无赖不但未受到谴责,反而把占的座位卖钱了,人们也就稀里糊涂地认可这种荒唐的权力秩序。
小说《审判》开头,两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冲进约瑟夫·K的房间,登堂入室,这明显是一种入侵,但入侵者没遇到反抗,还大大咧咧地坐下来。这一入侵的合法化过程,象征了卡夫卡对权力秩序的理解。入侵者反客为主,是卡夫卡小说中常见的情节模式。卡夫卡多次写到了关于入侵者的梦魇:《舵手》中的“我”作为舵手的合理合法的位置,被一个黑大汉无来由地抢去了,所有的船员无动于衷地接受了这种无理的占有和抢夺;《我的邻人》中突然降临到“我”隔壁的哈拉斯事务所,盗取“我”的商业机密,而“我”只能提心吊胆,从此“我生意上的决策变得毫无把握,我的声音会发抖”;《梦》中约瑟夫·K被推进墓穴;《桥》中第一人称的“桥”被行人刺痛翻身跌落;《乡村医生》中医生被病人家属按倒在床上而吓得要死……这类的入侵和暴力伤害,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但没有遇到任何的愤怒斥责,更不用说反抗。
在卡夫卡小说中,好像世界上任何一方突然冒出的力量,都可以随意地挤占平民的空间,进而伤害主人公。本来,按正常法理逻辑,这些暴力入侵者,是应该受到指控和受到遏止的,在卡夫卡小说中,却只是无奈甚至无法避免。主人公无法抗拒这些意外的强加,入侵者反而占据着道义的高地。如《地洞》写的是一只人化了的鼠类动物,为了保护自己,抵御外来动物的进攻,营造了一个既能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但这只动物又对自己营造的地洞是否安全可靠满腹狐疑,缺乏信心。“我安安静静地住在我家的最里层,与此同时,敌人从某个什么地方慢慢地,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垒,向我逼近。”它整天忧心忡忡于可能的强敌进攻,却从来没有质疑过那外来的动物有何种道义上的理由。
短篇小说《拒绝》最为典型地揭示了这一权力法则:权力来源不明,但一旦有人宣称其拥有权力,民众便服从。小说中那个掌管着全城的上校,其实他的权力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位上校掌管着这座小城。我想他从来拿不出一份委任他这个职位的文件;多半他并不具有这样一件东西。也许他真的是一员税务官,但那就是一切吗?那就给了他权力,也能来掌管政府中其他所有的部门吗?”小说最后,就是这个不知道其权力从何而来的上校,轻松地拒绝了人群发起的请愿。“请愿已被拒绝,”他宣布,“你们可以走了。”“市民们总预料会遭到拒绝。而今奇怪的事实是,没有这种拒绝,人们简直就不能过日子。”
“没有这种拒绝,人们简直就不能过日子”,这种荒唐深刻地揭示了民众盲从于强占式权力的普遍悲剧。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在卡夫卡那里,机构成了个遵循自身法则的机制,而这些法则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定下的,而且跟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
退缩:卡夫卡式的敏感
面对无处不在的权力挤压,作为弱者天才的卡夫卡没有书写抗争,甚至没有愤怒,只有退缩。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遇我皆亡’;在我的手杖上则写着:‘一切障碍皆摧毁我’。共同的是‘一切’。”卡夫卡说,他的小说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弱点”,就是退缩和服从。如短篇《兀鹰》写的恶梦式情节:一只兀鹰猛啄我的双脚,一位绅士从旁经过,观望了一会儿,于是问我为什么要容忍那只兀鹰,回答是“我无能为力”。再如《地洞》中的主人公:“作为地洞的主人,我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任何来犯吗?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我从来没有过占领欲或进攻心。”它只能设想着强者一旦进逼,“我就把我的贮藏品分些给他”。
但这种退缩并不是怯懦,并不是人格的病态软弱,而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敏感。对时代危机的敏锐性与预见性,是造成卡夫卡恐惧心理的最根本的原因。从卡夫卡独特的写作方式上也可以看出,他观察事物时,不肯止步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坚持凭眼力去洞察事物的真谛。于是,他会因为发现了常人感觉不到的真实而感到恐惧。试想权力运作不按理性法则,而荒诞得如同大街上疯狂飙车,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包括驾车的狂徒。不同的是,有人对这种不安全敏感意识到,有人则麻木不仁。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过:“任何没有领悟到恐惧的人,无疑终将不能成为信仰义士。”而所谓的信仰义士却不但要在荒诞世界中保持清醒,还力图以某种形式唤起麻木的人群。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卡夫卡无疑是最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的人了。所以,卡夫卡笔下异化的权力世界描写,其意义是引发思考。正如福柯指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