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燕小说女性解脱方式浅析
2015-11-28马敏
马敏
郭海燕小说女性解脱方式浅析
马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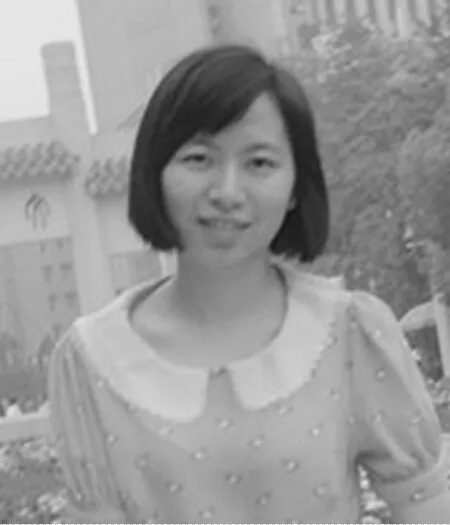
马敏,1991年11月生,湖北省十堰市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喜爱阅读、手工。
作为70后女作家,郭海燕擅长写男女情事,并以此为突破口展现其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理解。近些年来,《春嫂的谜语》及《理想国》等作品显示了其为寻求新天地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总体来说,她的小说始终致力于探索女性心理和关注女性命运,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时时刻刻处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中。因此,对其小说中女性解脱方式即如何摆脱各种矛盾的分析就有了意义。
一、从性中找寻出路——对现实的抗争与逃避
郭海燕早期作品以写滚滚红尘中各式各样的两性关系为主,侧重细致入微、生动形象的心理描写,因而故事的时空结构是错杂的、无序的。作为主体的男女两性关系也常常是畸形的。在这些关系中,女主人公的另一半总是在不断地背叛着她们,她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和对方决裂,并因此而感受到难言的失望和痛苦。内心的煎熬迫使她们在丑陋的现实中借助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来麻痹自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的报复和反击,但同时也是她们对现实妥协与退让的表现。
这些女主人公在脱离苦海之前,一般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对另一半的身体洁癖过程,这可以说是郭海燕小说中很有意思并带有普遍性的一个现象。
《殊途》中,泠渝发现丈夫张鲁和自己的姐姐在父亲的灵堂内乱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拒绝与张鲁发生关系。《如梦令》中,喻言虽然原谅了出轨的方理,但是她的身体不接受他,二人和好后第一次亲密接触就以失败告终。《秋分》中,柳卡更是将这种洁癖诠释到了极致。她不仅不让方杰触碰自己的身体,同时极度追求清洁。“地板擦得镜子样,还时不时哈气擦墙上逆光才看得见的可疑污迹。”[1]P124小说中,甚至还多次出现了她对洗手的病态渴望以及对气味敏锐捕捉的情节。
在笔者看来,身体洁癖是女主人公妥协现实之后的一种无声抗争,在某种层面上展示了其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在理智上,她们或多或少地原谅了丈夫或男朋友,但她们内心的不满和委曲却被身体诚实地挖掘出来,并加以展现。
尽管女主人公在与其他男性的性中得到了安慰,但这种安慰往往是脆弱的并被现实所左右的。这就使她们不能最终超越生命的苦难,而达到完满的境界。
《秋分》中,柳卡清楚地认识到,她与章成辉的亲密关系使她的生活多了一块茶色玻璃。“那些狂暴的烈日、风雨,从此与她有了1厘米的距离。”[1]P150但是,当她知道丈夫方理要对女儿卉卉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章成辉带来的茶色玻璃被击得粉碎”[1]P151,她要“直面台风”[1]P151。至此,柳卡所建筑的暂时港湾也消失了。
而在《殊途》中,泠渝的情况更为特殊。她和张鲁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所以即使张鲁和别的女人发生了肉体关系,她依旧努力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这种心态甚至影响到她对出轨对象的选择。“事实上,泠渝被彤丹打动,他的身份也是原因之一。”[1]P180彤丹是张鲁的上司,对公司人事任命很有话语权,故而泠渝总会在与彤丹做爱时或做爱后提出某些有利于张鲁的请求。如当张鲁与白琳的丑事被揭发后,她要彤丹为他们善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泠渝的出轨其实并没有让她获得根本救赎,而只是让她在现实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一方面,她“心里有了一种纪念碑似的底气”[1]P182,另外一方面,她也在接受着现实的反复折磨。
综上所述,在郭海燕笔下,每当女主人公意识到对方的不忠诚后,她们基本上都没有采取激烈的态度,没有毅然决然的与其分手,而仅仅是拿对方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使自己处于不幸和苦痛之中。这不仅反映了她们的懦弱与胆怯,也表现了其对现实的让步与退缩。尽管她们也用同样的背叛进行反叛,并从中获取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支撑,但这种支撑也是不牢靠的,会因现实而倾斜甚至倒塌。
二、从梦幻中寻求出路——理想破灭后的暂时归宿
郭海燕笔下的女性都是理想主义者,她们所有的苦难无不是源自她们对现实的美好想象。一旦这种想象遭遇到现实的暗礁,她们必然会身心俱疲。她们对爱情和未来怀有期待,所以才会因另一半的叛变而黯然神伤。当被侮辱和被损害后,除了在性中沉浮外,她们有时也会借助梦幻来表达自己。
在郭海燕的小说中,有两种梦幻。一种是梦境以及女性在做爱或平时生活中的种种幻想亦或是联想,它们其实是女性对现实的一种潜在反应,可以帮助我们探求女性的情绪乃至隐秘心理和深层愿望。例如在《殊途》中,泠渝被强奸并获得快感时,迷乱中她看到了丈夫和姐姐赤裸交缠的场景,并看见了“天使们戴镣飞翔,魔鬼们振翅欢舞,黑色的、妖冶的蝴蝶密谋涅槃,水母样的磷火四处追寻童真、时光……”这种虚幻的想象恰是其光陆怪离的潜意识的表现。
另外一种则是女性自己构建起来防御外部世界侵袭的手段,尤其以《指尖庄蝶》中的表姐为代表。
《指尖庄蝶》这个标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梦幻感,它化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旨在说明真实和虚幻是相互混淆的、难以区分的。而小说中的表姐就是这样一个分不清现实与幻想的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就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

郭海燕
表姐的生活被时间分割成两部分。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是表姐夫的贤惠温和的妻子,而午夜十二点半到凌晨两点半,她则在臆想中成为TT演艺吧主持人安然的情人,尽管他们只有一面之缘。
通过后来的阅读我们知道,表姐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表姐夫屡屡嫖娼且累教不改。在白天,她知道自己不会和表姐夫离婚,因为“不可能中断已交付的日程,那也是一项工程,心血、青春已全投入,必须严格按照合同条款执行”[1]P239,且她也不能保证她遇到的下一个男人不这样。
尽管清楚地知晓这一事实,表姐内心仍有不甘。为了纾解内心的苦闷与不平,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假想成和安然谈恋爱的人,并杜撰了许多甜蜜的回忆。当她是安然的恋人时,她知道白天的事,但当她是阮强的妻子时,仿佛有人将她的记忆抽离,她会忘记深夜的幸福,否认自己认识安然。
《指尖庄蝶》中表姐的两次生病也很有象征性,代表了她在现实及虚幻中的两次转换。
第一次生病时,表姐在昏迷中无意识地喊叫着安然的名字,这意味着她沉醉在梦幻世界中不能自拔。第二次生病是出车祸后,她呼唤着丈夫阮强,表明她要回归到现实。但具有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阮强因为煤气中毒而死掉,表姐的回归也成为梦幻的泡影了,她最终只能孤独地活在世上。
也许正是因为现实太过丑恶,所以表姐才会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遨游,这样的她无疑是可悲的。因为遨游的结果也不外乎梦醒和破碎,等待她的将会是更加无望的现实。同时,这种方式本身,也让我们从中窥见了其委曲求全、向命运妥协的性格。
所以,女性借助梦幻也很难实现理想,拥有完美人生。而且,现实和梦幻是生活的正反面,假如我们沉溺在反面,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在回避着正面。
三、在善良中坚守——人性的立足点
正如其他70后的作家一样,郭海燕“擅长表现成长的疼痛、青春的伤怀,绝望的爱情、极端的情欲,空洞的生活”[2],她的很多作品在风格气质上具有相似性,并且缺乏相应的高度和深度,没有将读者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为了实现自我突破,拓展小说的视野和表现力,近些年来,郭海燕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而不是局限在男女两性的狭小范围内。相应地,这种转变也使她的小说人物没有以前感性和立体,甚至少了某种心理深度。但不论题材如何变化,女主人公的性格总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女性的善良。这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美德是她们的生存之本,往往帮助她们在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找到心灵的栖息地。
《春嫂的谜语》是郭海燕的转型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她塑造了一个善良、质朴、坚韧的底层农村妇女形象。她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与坎坷,如中年丧夫,大女儿未婚先孕,二女儿辍学打工,儿子骨折住院,以至于最后自己也身患胃癌。但春嫂的朴实善良使她从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顽强地在生命长河中跋涉,并找到前行的办法,收获宝贵的情感。
丈夫死后,为了养育孩子,支撑家庭,春嫂到城里的庄吉文家当保姆。她万事为东家考虑,即使在被庄母怀疑偷钱后仍旧任劳任怨,最终,温厚纯真的她获得了庄家上下的喜爱。
王金宝是春嫂进城时认识的指路男人,孤独的城市生活让他们二人有了交集和共同语言。纯善的春嫂待人以诚,回家过年会给王进宝捎米酒,王进宝患急性肝炎后,总会给他带鸡蛋补充营养……最终,春嫂收获了王进宝的爱情,在癌症的面前也有了坚强的后盾。
《理想国》中,蔚小壮在壮志集团度过了六年的青春岁月,她经历了壮志从起步、兴盛、低迷到衰落的全过程,因而她是作者表达自己对国企发展问题思考的关键性人物。壮志破产后,蔚小壮为生计问题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但沧桑过后,她善良依旧。她会将买断工龄的钱全部拿给弟弟用于结婚买房,会买大堆的食品专程看望昔日故人、如今已在狱中的他红强,也会原谅曾经对不起自己的前男友李纯,甚至还考虑要不要帮助他度过财政危机……正是蔚小壮的这种美好品性,支撑她度过困苦岁月。
其实除了上述作品,郭海燕描写男女情爱的小说中也会传达出女主人公的仁善之心。尽管这不是作者要着重表达的部分,可能只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不可否认,作为女主人公内在的有机成分,它们必然会影响到她们的人生选择和生命走向。
在《秋分》中,柳卡主动帮助章成辉对门的女孩抢救昏迷的嫖客;当得知丈夫的情人傅晓丽是宫外孕后,她不仅陪着傅晓丽做人流,还一声不吭地承担了所有的费用;虽然对丈夫很失望,却始终细心照料中风的公公,尽好媳妇的本分。
《指尖庄蝶》中,由于“我”的失误,致使表姐夫死于煤气中毒,表姐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为“我”作证,向警察强调丈夫的死属于意外,且“我”也没有理由杀死阮强。
可以说,女性的善良是郭海燕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这也许是作者对女性如何应对生命困境的另一种思考,可以传达给读者很多正能量,使其从中汲取力量。但不可否认,作者在强调善良的时候,是在忽视反抗,因为她不着力书写女性那种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与一切斗争到底的决心。
总体来说,郭海燕小说中的女性基本上都没有获得根本层面上的救赎,作者也很少赋予她们幸福的童话式结局,因为现实是出其不意的并且总是布满偶然和波折,这从她作品的故事性布局就可以看出来。
而且,她的小说其实体现了女性解放的另一面以及不彻底性,即表现了相当一部分女性对命运的妥协,以及她们的无奈感和无力感。
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有一批女性实现了自身的觉醒,其主体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激发和增强。她们敢于挑战不公正的男权社会,勇于用身体、用性来呈现自己自由的生命意志和恣肆的生存情态,她们是现代的、先锋的、前卫的。这类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在林白、陈染、卫慧等人的笔下看到。她们的小说属于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带有 “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叙事的倾向,擅长对女性的私人经验特别是性经验作大胆直露的描绘,并以此达到抨击、对抗整个男权社会的目的。
尽管郭海燕的小说有和她们相似的地方,如诗化、典雅的语言,跳跃、片段式的叙述等,但她却很少这样处理女性,她有着自己独特的写作个性。她塑造的女性往往集传统和现代于一体,不完全传统,也不十分现代,她们是被生活激流所裹挟的女性形象。即使是性描写,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女性犹豫彷徨、脆弱逃避的一面,而非暴露和冲击。
所以,郭海燕刻画的女性其实是没有获得完全解放的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从中反映了其对女性心理和女性命运的别样思考。
[1]郭海燕.理想国[M].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2]蔡家园.“突围”中的郭海燕及其他——湖北新锐作家阅读札记之四[N].文汇报,2014-06-13.
昨日风景
以创造的积淀铸成文学风景回眸不是怀旧而是擦洗眼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