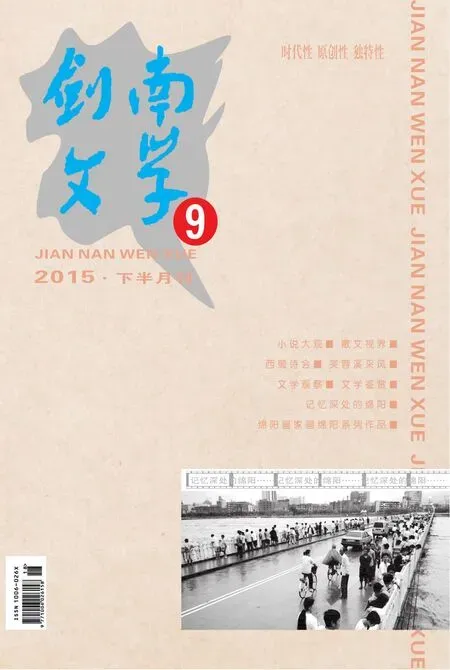看到的都成为了风景(外六首)
2015-11-22■灵鹫
■灵 鹫
入眼的石头都被体内的药水泡过
而无法正常热胀冷缩
所有语言的偏瘫和神经的麻木都被风沙养育
而无法完成灿烂的昼夜交替
古丝绸之路上宁静的舌苔
好像要变味了
最普通的石头和最没有规律的沙子
都自觉地成为身体的戈壁
干枯挺拔如白杨
这凉沁的孔雀河
要等一个季节才能看天鹅起舞
跳西北痛苦的芭蕾
十一点的夜路是城市边缘的黑幕
比风还不会调情
去助人缩小对西北荒凉的偏见
而司空见惯的星星呢
放在戈壁的上空
它们都不会跳下来撒泡尿
浇灌口渴的红柳
夜晚
肋骨挤出的野花
叫人无处安放
库尔勒的栅栏
让我吹不到海边的台风
喝不到盆地狂妄的雨水
所有的动荡不安都要在车轮上辗转
而天空再也举不起来
远方已经落下的帷幕
走出他的绝缘地带
如若沉默
就如秃鹫爆炸
于密密匝匝的日光下
如若修造“宫殿”
便要扎进盆地
便要走回一个斜坡
走进暗沉
走出天堂一样的呼吸
走出产卵的高原
走出嚣张的山口和张开嘴却说不了话的峡谷
如若干渴
便要趴在拉萨的河滩上拆线放水
看背水姑娘湿漉漉地现身
如若委屈
便坐在山的秃脑袋上发呆
给沉默止痒
把求来的风光抠掉一块
若想了无痕迹
便要走出他的绝缘地带
走出酥油经幡嘛尼石刻的悄悄话
藏地迷人而我难以脱胎换骨
成不了仙却走火入魔
藏地日月同辉冷热交替
生和死在冻土层里碎了一地
藏地从不缺乏歌咏者
而我狭窄的声带挤不出高原的颤音
藏地白日敞亮夜晚迷惑
让爬升和下降都气喘吁吁
闲时无需有条不紊——小鱼的生活
在旁人看来她已经混乱了 离经叛道了
她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学会了抽烟喝酒 足不出户不拘小节语无伦次
而她浑然不知
而只有当她面对自己的时候才有空有条不紊滔滔不绝
她没有心思说客套话奉承话打理枯草一样的长发
走路也不像常人那么认真
甚至她对吃饭睡觉 旅游 观光也不感兴趣
所以我没有把她赶到沙漠 湖泊里去
我怕只要我不看着她 她极有可能跟着驼队走丢
或者掉进湖里
她说她只是来看我脸上有没有荒凉的样子
开始我还半信半疑
当她从绵阳到库尔勒坐了近50个小时的硬座后
我才认为她的决定有点认真
我想离奇和偏执都应该覆盖一层保护膜
在她身上不急于看到芒种和秋收
福地广场
从26楼望去
温暖如橘色的路灯照耀着奔命的城际卡车和无法睡觉的司机
白日小摊小贩包围了这座3.5环的商品房
现在在小区的中庭回荡着繁忙的余音
我的哥哥
某医院的一名医生
在工作之余骑着三轮车戴着安全帽贩卖淘宝山地自行车
越过大街小巷 穿过斑马线和天桥
我的哥哥
也在为他即将到来的孩子奔命
他越来越像一家之长那样宽大厚实
去荫蔽妻儿老小
从26楼望去
温暖如橘色的路灯折射出深秋的寒意
这雾和霾混合排练的迷障恰好演绎着城市的似真似幻
我蜷缩进水泥墙
仿佛窗帘遮盖了噪音
听西蒙·波娃诵经
你铸造女性意识的塔尖
却没有背上女人的躯壳
一切就在宣战中
搭建自己的圣经
可怕的女人
一定要说身体的真相
向着天空请求云朵
我应该亲睐于我选择的天空
请求降生云朵
控制住时间的轻度撩拨
脱离集体主义的嗫嚅
一门心思向着远方
在陌生的城池里变幻出各种瓷器的杂音
永恒而调皮的旅人
不知收敛败坏的习气
慢慢退至卧室
这床幽灵要睡
乞丐不能睡
盗贼不能睡
缺钙的女人不能睡
仅一处庭院
独身寓所
你偶尔发情
又突然按下停止键
楼上的嘎吱声回声荡漾
大脑从此受到打击
不再是第一个睡觉的夜晚和第一个被吵醒的人
各种词语相互撞击
泛滥于此
第二天
你说
肚子发胀
怀里揣着一个多余的词
原来
满纸荒唐言
都是个人意义的废话
你还想把私人汉语用船载到外省
或者用飞机运走
去南极北极或者非洲
到达毛发厚重的男人和皮肤白皙的女人的枕头
跟他们一起回忆贝多芬伍尔夫
西蒙·波娃 西尔维娅·普拉斯
马尔克斯 切·格瓦拉
现在都没有确定要成为他们中的哪一个
又是半夜
你跛脚起来喝茶
喝多了像个水肿的棺材
在房间摇摇晃晃
边走边流水
你永远都站不直
不听妈妈最初的指示
不管怎么长
都是一棵歪脖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