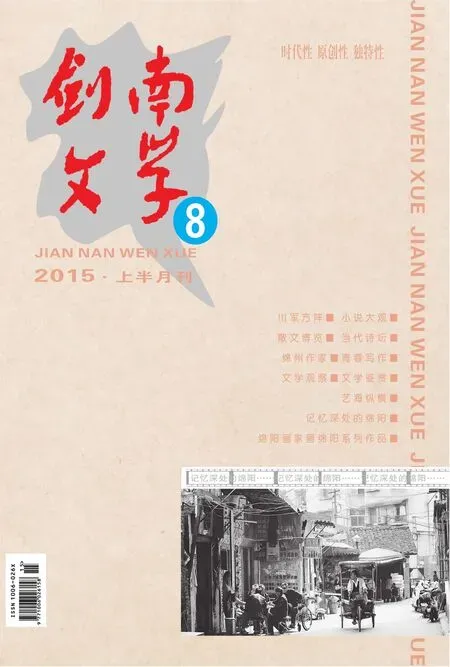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主题
2015-11-22赵蕾
■赵蕾
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主题
■赵蕾
本文试图通过对于艾米丽·迪金森众多诗句的分析,来讨论其诗歌的主题特点,揭示出其诗歌不同寻常的主题阐释方式。
艾米丽·迪金森认为 “诗歌就像是一个圆”。而诗歌的主题自然就是圆心。她的诗歌像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想了解这个神秘国度里最美丽动人之处吗?作者自己是不会告诉你答案的。我们必须要通过理解这个“圆”里各种意向来理解她的 “神秘国度”。诗歌“I gained it so—”和 “It dropped so low—in my Regard”里,中心点都是“it”。艾米丽·迪金森的诗句在这个中心点周围反复徘徊,一直试图接近诗歌想要讨论的主旨,但是又不直接切中目标。艾米丽·迪金森在她的 “I watched the Moon around the House”当中也是这么做的,“月亮”被比喻成一个“陌生人”、一个通过长柄望远镜观察的“监视者”,一朵“无茎的花”。因为无法触摸,我们从来都无法确认月亮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在艾米丽的诗歌里,我们了解一样事物不是通过这一事物和我们生活当中熟知的东西有多少相似性,而是通过其不同和距离感。
这种不可侵犯的自我觉醒意识成为许多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的基本准则。在 “I reason,Earth is short—”中,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在每段的最后一行采取了陈述和反陈述的表达手法。在“Before I got my eye put out”中,中间三段诗的每段最后一行逐渐将焦点从 “世界”缩小为“自我”。而“自我”也成为整个段落主旋律下的微弱音符。在那些“自我”逐渐隐匿的诗歌里,比如“I felt a Funeral in my Brain”,很难说诗歌主旨到底变成了疯子脑中的臆想还是一个美好的神秘国度,又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诗歌早在我们找到答案之前就已经戛然而止,只留下意犹未尽的回味。总的来说,艾米丽·迪金森和玄学派诗人们保留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之间的距离感,而浪漫主义诗歌则试图填充这个距离。一个浪漫主义诗人通常会把这种疏离感隐藏起来,模糊诗歌读者和意向之间的界限和区别。正如华兹华斯1805年在Prelude中所作的那样:“What I saw/ Appear’d like something in myself,a dream,/A prospect in my mind”。 玄学派诗人建立主客观联系的方式则有所不同。如同一只鸟,起初看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只有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进行类比,这些不同才逐渐消失。
与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不同,艾米丽·迪金森认为和辞藻的选择相比,对于主题的整体看法更为重要。对于她来说,一行诗中有多少个词并不重要,都能很好地表达出既定的意思,尽管每个词的意思可能千差万别。她对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有很强的结构性暗示。她的情节并不刻板,也不会体现一首诗中各个细节之间的强烈联系。在“I never lost as much but twice”中,有一系列重复的形象,人们很难从逻辑上或是语言之间的联系上去理解它们。这一系列意象在诗歌主体部分是突然出现的:“Burglar!Banker—Father!”这一行诗中包含了意象的剧烈过渡,互相之间看似毫不相关,然而掩藏于意象之下的模式,每对之间都是相同,在诗歌当中是一个整体:窃贼-受害者,银行家-债务人,父亲-孩子。每组词在力量上逐步弱化,但如果要说这首诗的主题即此似乎又不大适合。“Loser”,这首诗中的人物角色试图从远距离探寻离奇的失败。而这失败藏匿于诗歌之中。
艾米丽·迪金森热爱这种在主题周围徘徊,但是从不直接切入或者点明主题的表达方式。这种做法在“To hear an Oriole sing”当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诗歌的第一段落,列出黄莺的两个相反特征,这一段的最后一行针对前两行提出了一个矛盾的维度。这一模式贯穿全诗。第一段提到的鸟儿在第二段被否定或在即将切入主题的时候故意绕开话题。各个意象之间否定表达的使用起到了帮助意象不断转换的作用。诗歌的第三段开始深入,但是未至诗歌主旨,只是在主题周围打转。每个段落之间保持着存在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疏离感。每个段落的中心都是黄莺歌声中未言明的主旋律。这个未曾言明的主旋律也是作者留给我们的悬念。这首歌是属于鸟儿的,歌声隐而未宣的主旨是属于她的听众的。然而诗歌的第三节通过给声音添加颜色在歌的意义和听众之间建立了模糊的联系:“The Fashion of the Ear/Attireth that it hear/In Dun or fair.”这里元音的省略再次制造了听众的疏离感, “whether…whether.”诗歌外部找不到其真实意义,又不能完全相信感觉,在理解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还能依赖什么呢?怀疑的态度成为迪金森诗歌中模糊或被省略掉的中心的佐证。诗人自己也承认很难在黄莺这首诗中读出确切的主旨或是找到明确的中心。
玄学派诗人的兴趣点在于灵魂和躯体的二元性。这一点在多恩的“The Dreame”和艾米丽·迪金森的“No rack can torture me—”当中都有所体现。第一段落引入一个身体隐喻,“the knitting of bone”(织骨)来描述灵魂:“Behind this mortal Bone/There knits a bolder One—.”第二节的叙述没有接续但以不同方式重申了第一节的意思,平凡的意象和异国情调结合起来:“saw”和“Scimitar”结合起来。第三节进入了一个新的圆周,是观察者新的阵地:巢中的鹰和天空中的鹰。诗歌中心灵魂和躯体的二元性已经逐步在第三节当中开始模糊:“The Eagle of his Nest/No easier divest—And gain the Sky/Than mayest Thou—”。 在第四节中出现了自由和束缚两个矛盾存在,鹰既要飞上云霄又受到巢的牵绊。在 “No Rack can torture me—”中,缺失的背景或者说被省略掉的诗歌中心是诗歌结构的要求,用两个悖论连接起诗歌的第三第四节。
这种由内至外的转移在“I felt a Funeral, in my Brain”中是灵魂发展的方式。在诗歌末尾,灵魂最终找到归宿。诗歌头两节戏剧化地原地踏步,第三节到第五节加快速度。动作伴有声音,和 “A Route of Evanescence”与“I heard a Fly buzz—when I died—”中表现出来的一样。在头两节的静止和空间限制之后,有人拖动棺材,发出吱吱的响声,之后钟声响起。第四节有很强烈的灵魂四周的空间拓展,像是被摇摆的钟强制打开似的,通过这个开放空间,灵魂开始飘荡,轻点主题之后全诗结束。与其他玄学派诗人不同,艾米丽·迪金森对于主旨和周遭环境的分离更感兴趣。当主旨离开语境,诗歌结束。诗人的视角很孤独,从外到内,从一扇窗到另一扇,在时光中被迫移动。艾米丽·迪金森的宗教背景使得她不愿轻易总结人类对于上帝的所知。清教徒对于上帝的认识来自于日常熟悉的事物,他们认为上帝是神秘的,人类不可随意揣测上帝的意图。要通过类比的方式来看上帝。艾米丽·迪金森在诗歌中去除时间感,使用剧烈而使人出乎意料的动词来连接一个个时间段落,因此我们在迪金森的诗歌中,被迪金森所使用的被动动作吸引,而忽略了从一个意象进入到下一个意象所需要的时间。
在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中,读者要使自己从已知中抽离出未知。这么做的目的并非要使目标更明显,并非要全面看清,而是要从多个角度看到永恒。迪金森诗歌的主题从不轻易告诉读者,而是需要读者在接近主旨周围的距离当中不断地徘徊,揣测,靠近。
(内蒙古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