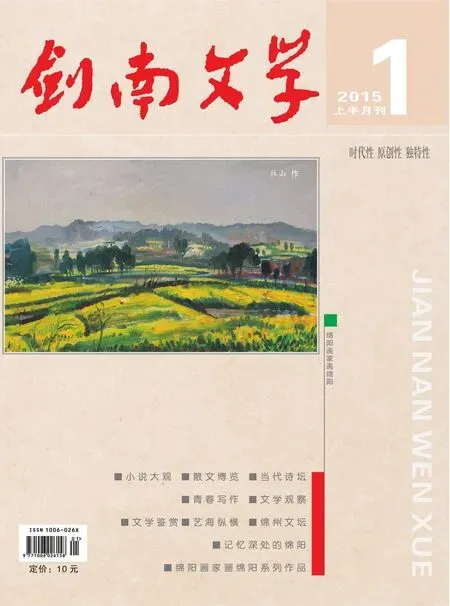向 死 而 生——浅析肖江虹小说中两辈人的生死观
2015-11-22■杨倩
■杨 倩
生与死是生命形态的两个方面,对死亡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生命观念。文章考察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的几部丧葬礼仪题材的小说,以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对于生和死的不同看法,来探究不同生死观背后表现出的不同的生活态度,同时也反思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生命价值的看法。
肖江虹是贵州本土的青年作家,09 年在 《山花》杂志上发表《百鸟朝凤》后获得国内广泛关注并取得较高的荣誉。小说反映的是城市文明的入侵使得传统的乡村文明的逐渐衰落,在这样的巨大的历史变迁背景下贵州农村民间唢呐乐班的悲惨命运。几乎在同时,肖江虹又发表了 《天堂口》、 《当大事》、 《家谱》、 《我们》等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肖江虹总是将乡村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紧紧联系在一起,并给予了深刻的思考。评论者多是通过小说中的民俗文化和乡村社会变迁来阐释小说的主题,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给予全面的肯定。但在肖江虹的小说中, 对于人类生死问题也特别的关注,对人生、人性以及诸多生死问题的思考也表现出作家对于生命的执着。本文试图以丧葬礼仪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的《百鸟朝凤》、 《天堂口》、 《当大事》这三部小说为主,分析小说中两辈人对于生和死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拥有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观,探究不同生死观背后表现出来的对于生活的不同态度。
一
人们对于死亡常常是恐惧和困惑的, 但 “生” 与“死”是人生的两翼,是生命两种自然存在的形态,也正是死亡使得生命的时光有限,迫使人们去思考生命的价值。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与死是生命形态的一体两面,对死亡的不同理解就会形成不同的生命观念,所以,以死论生的方式似乎更能明白生命中所包含的奥秘。
小说 《天堂口》和其他三部不同的是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山区农村,而是在修县,但相同的是主人公范成大也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范成大是火葬场的火化工,同样是火葬场的职工,会计胖妹在食堂看见了范成大都会躲得远远的,还说这些人 “身上有死人味儿”。由于特殊的职业使得范成大对死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火葬场, “在火葬场做了八年的火化工之后,他就释然了, ‘这进进出出的人看得多了,人的想法也就变了’。”在范成大那里火化的都是乞丐、透水事故不幸遇难的矿工、外地来打工的农民工等等,看到一条条年轻的生命无情的被终结,久而久之范成大心里不再过多的泛起涟漪,而是更加用心的给死者擦拭身体,剃发、烧纸等等,但是看透了生死的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不管别人再怎么嘲笑、鄙视或是怒骂,范成大总是笑笑。
在生与死的这两个方面中,人们通常都只愿意谈论生的问题,而避讳谈论死亡,但人从一生下来就在面对死亡。在过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对于死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屈于 “死”的魔力,并且希望能从精神上追求克服和超越死亡的方法,这一点在传统的丧葬礼仪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葬仪是死亡的仪式,与死亡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小说 《当大事》就讲述的一个生者告别死者的故事。孟子曰: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但是看似平常的一场葬礼却因为村里缺乏年轻劳动力而无法顺利进行,虽然是 “大事”,但是 “大事”因为条件不足最后化成了 “小事”。老年人把 “死”看得比 “生”更加重要,相信灵魂不灭和彼岸世界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信生命的永恒。年轻人参加葬礼会懂得生的不易,会懂得更加珍惜生命,但老年人参加葬礼,总是带有一种自嘲,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躺在棺材里面的人就变成了自己,面对生死他们总希望能够找到超脱死亡的魔力。
二
在肖江虹的这几部小说中总是出现不论是人物的年龄、对待死亡的态度还是他们的思想等都出现严重反差的两辈人。与小说中老一辈的朴实、踏实相比,年轻一辈人的出现总是给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带来跌宕起伏。在 《百鸟朝凤》中,游天鸣成立游家班后出活儿的第一家便是毛长生家。到了长生家,天鸣问长生 “老人家什么时候走的”,长生喷出一口烟,笑着说: “这个月都死了三四次了,死去没多久又缓过来,直到昨天才算是死透了。”小说用了许多的篇幅来描写毛长生的慷慨,比如润嗓酒, “是瓶装的老窖”;乐师饭, “居然有虾”等。但长生最慷慨的还不是这些,而是 “看见我们卖力的吹奏时,他就会过来先给每人递上一支烟,说别太当回事了,随便吹吹就他妈结了。”长生对于他爹的死出乎意料的漠然,而请这些唢呐班也并不是真心的需求,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了炫富。长生家和之前唢呐班出活的人家完全不一样, 虽然他们给的礼金不多,但却是真心的尊敬他们。而天鸣的第二次出活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起先就是再卖力的吹也无法引起葬礼上人们的注意,后来没多久,老马的儿子从城里请来了 “洋乐队”,这是一种现代对传统的挑衅。这样的葬礼显得新鲜而奇特,老马的葬礼连起码的严肃都没有。
故事同样发生在葬礼上。在 《当大事》 中, 松柏爹去世后,春花娘走了三十里路去打电话通知城里上班的松柏,可是松柏 “在电话里头好半天屁都不放一个,最后说不好请假,来回一趟,位置就没了。”松柏没有能力为父亲办一场让他 “起死回生”的奢华葬礼,他最后就连父亲的葬礼都没有回来参加。松柏虽然是在城里工作,可是依旧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人,城市里有着农村没办法比的生存压力,松柏爹的去世看出了作为儿子内心的对亲情的冷漠。也许松柏回来,能够挑起主持这场葬礼的大梁,能让 “大事”依旧还是 “大事”,这样故事也不会如此的辛酸。最后王铁匠去求钻井队的小伙子帮忙抬棺材下葬, 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还说:“不是钱的问题,你说的那个是小事,我这个才是大事。”故事发展到了这里, “大事”又被赋予了全新的解释。对于死,他们一个比一个漠然,对于生命他们越来越不在乎,每天麻木的工作,麻木的思考,在这些背后都是他们感情的缺失。
与这些小说中的年轻人一样, 《天堂口》里的扇子最开始也是和他们一样。扇子根本看不起范成大的工作,甚至是产生了敌意,更不理解的是为何范成大都把那些无家可归、惨死他乡的人 “当做自己爹死了” 一样的重视。 范成大老了, 干不动了,扇子接手了范成大的工作,成为了一名火化工,并且和范成大一样的用自己的真心在工作。这是一个温暖的结局,扇子最终是体味到了人情的冷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人成长为一个用心对待自己的工作,用心对待每一个逝者的人。
常规的来说,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无论是持积极的人生观还是消极的人生观,都有着对死亡的本能的恐惧。但只有健康的年轻人,他们总觉得自己离死亡很远,才会以一种洒脱的无所谓的态度去面对生死。
三
在这几部小说中只描写了两辈人,老一辈总是直面死亡,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原生态民众的死亡状态, 符合大自然的规律, 显得是古朴又原始。游本盛比喻将死的自己是 “田里枯死的稻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游本盛一直躺在家里那张宽大的木床上, “父亲当年就在这张大床上降生,如今,他又即将在这张大床上死去,像完成了一个可笑的轮回。” “生与死,本就是一个统一的生命流程的起点与终点。”死去了的人已经不再,活着的人办完丧事也照旧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埋完松柏爹,松柏娘又回到了从前安宁的生活,坐在院子里偶尔回头,感觉松柏爹正看着自己呢。活着的人也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如范成大。
年轻人则完全不一样。因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已经深深触及到了农村,他们接受的教育也不同,老一辈 “生生死死”的传统生死观似乎逐渐淡漠,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现代的物质观。村里的年轻人对于老人的死表现出来的都是出乎意料的冷漠和随意,而其实这种冷漠背后更多的是一种亲情的缺失。因为年轻,所以不在乎生命;因为年轻,所以不惧怕死亡。而面对生活更多的是以物质条件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却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自然界的生命都不是静止的,而是生生不息的向前奔涌,一切都是相依相存的。”因而,自然地生和自然的死,是生命最美好的进程。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肖江虹对于生命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涉及到生命的开始,都是以生命的结束为故事主线。孔子曾经说过: “未知生,焉知死”, 但在肖江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 “未知死,焉知生”的生命内涵,他将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恐惧联系起来,阐述的是一种直面生命,重视现时的人生态度。
肖江虹在他的小说中对死亡有着独到的思考。一切都是未知的,只有死亡是确定的,于是人们向死而生。以死亡作为生存的参照,人们才会去千方百计的追问生命的意义。老一辈的死去意味着某些传统坚守的东西也随之逝去,而欣欣向荣的年轻人总是以一些独特的方式去诠释着他们对于生和死的看法,我们也在肖江虹黑色幽默似的表达中感悟到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