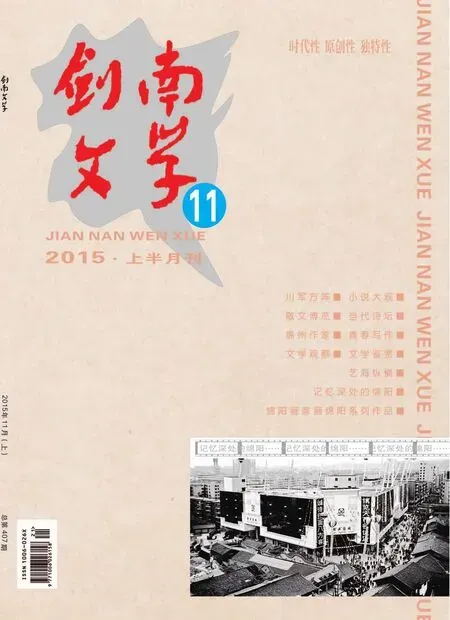分裂与建构:自我的救赎
——通过镜像理论解析卡夫卡《乡村医生》
2015-11-22朱梦梦
■朱梦梦
分裂与建构:自我的救赎
——通过镜像理论解析卡夫卡《乡村医生》
■朱梦梦
精神分析是解读乡村医生的重要参照,本文试从精神分析的另一代表人物拉康的镜像理论出发来解读《乡村医生》,既是对弗洛伊德式的解读做一定的补充,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小说丰富内涵以及卡夫卡在写作中的自我救赎。
《乡村医生》营造了一种梦幻的氛围,它的内容与卡夫卡曾经在日记中提到的真实的梦有着相似之处,加之他本人对弗洛伊德学说的了解,让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者释梦的角度去阐释这篇小说。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一个对精神分析特别熟悉的人去写一个梦,可能会避开他认为明显可以通过理论来解析的道具或者场景。但这篇小说与精神分析又是有关的,所以我试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可以来解读《乡村医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拉康既是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又是反叛者,并且可以确定卡夫卡并没有读到过拉康的理论,不用考虑他精通此于反倒避开了我们的线索。
在拉康的表述中,镜像阶段,正是所谓“主体”的形成过程。拉康的描述,同样被一个三分结构所支撑,在自我与他人二项对立之外,出现了第三个点:主体。主体并不等于自我,而是自我形成过程中建构性存在。主体建构过程正是把自我想像为他人,把他人指认为自我的过程。形成“镜像阶段”的前提性因素,是匮乏的出现、对匮乏的想像性否认及欲望的产生。
《乡村医生》中存在着双重的镜像,第一层是卡夫卡本人/叙述者“我”,第二层是“我”/男孩。前一重镜像已不需要论证,前一重镜像已不需要论证,作者在建构文本或者说这一梦境里的人物“我”的时候,一定有着自身的投射。让我们来看第二重镜像,“我”/男孩。作为读者,我们以为自己保持着旁观者清醒的角度,但是进一步看,可以发现我们是循着文本中的“我”的目光和描述在看小男孩,也就是说小男孩是由“我”这个他者建构的。第一重镜像中的“我”代表了身体的卡夫卡,而第二重镜像中的小男孩又是“我”的镜像,那么就可以理解为是精神的卡夫卡。从小说中来看,肉体的“我”已经是一个老人(象征了卡夫卡早衰的身体),然而精神的我是一个患病的小男孩,这对应也非常符合卡夫卡的真实情况。再来看小说中的提到的“我”,“非常忠于职守,甚至有些过了分。我的收入很少,但是我非常慷慨,对穷人乐善好施。”这与生活中真实的卡夫卡也很接近,他的朋友韦尔奇曾经说过卡夫卡是一个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
理清这两重镜像之后让我们先从小说中最耀眼的伤口开始来看,这朵如花的伤口实在太惊艳。那么这伤口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来看写作这篇小说的期间,他本人所写的一些书信:
1917年9月5日他致信勃罗德说:“但是我不诉苦……我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你记得《乡村医生》中流血的伤口吗?”九月中旬,他在信中又对勃罗德说道:“显然,这里的还是那个伤口,其象征仅仅是肺之伤口。”
1917年9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真如你所断言的,肺部的伤口无非是个象征,伤口的象征,F(菲莉斯)是它的炎症,辩护是它的深度,那么医生的建议(光线、空气、太阳、安静)也都是象征了。抓住这个象征吧。
1917年9月卡夫卡写给勃罗德的信中说道“有时我觉得大脑和肺在不为我所知的情况下取得了相互的信任。’这样下去不行’,大脑这么说,五年后肺宣布站在大脑一边。”1920年卡夫卡在给密伦娜的信中也写道:“我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疾病不过是我的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
通过卡夫卡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把那朵像花一样美丽的伤口理解为卡夫卡对自己的一种诊断,而菲利斯是他的炎症。结合前文的镜像分析,男孩是卡夫卡的精神投射,小男孩的伤口也就是卡夫卡精神上的创伤。卡夫卡提到的菲利斯也就是那位他两次订婚又两次退婚的姑娘,事实上菲利斯果断而且乐观,“从伤口深处蠕动着爬向亮处”或许就象征着菲利斯对生活积极而单纯的追求,而这对于卡夫卡而言却是致命的伤口。正是如此,他把这伤口看得这么美,明知道与死亡和痛苦联系在一起,却依旧把它比作是一朵鲜红的花。“可怜的孩子,你是无可救药了。我依旧找出了你致命的伤口;你身上的这朵鲜花正在使你毁灭。”这是小说中的“我”给小男孩下的结论,也就是卡夫卡对于自己的精神的病下的结论。
回过头来看小说的开篇,没有交代任何理由,事件就开始发展,“‘我’感到很窘迫,我必须赶紧上路去看急诊,一个患重病的人在十英里外的村子里等我。”因为患病的人正是这个“我”的投射,所以“我”不需要任何提醒或是暗示就意识到了有个病人在等“我”,精神的“我”在等待有着实际身体的“我”的拯救。我得去“患病的小男孩”那里完成自我的拯救,然而找不到马,也就是“我”不知道怎样拯救,“根本没有马,我自己的马就在头天晚上,在这冰雪的冬天里因劳累过度而死了。”这里体现了一种焦虑的情绪,焦虑的根源是欲望得不到满足,也就是拉康所谓的匮乏,它构成了镜像的前提。因此他通过写作中镜像的分裂,来满足这种匮乏,正如他曾在信中说过“我的意愿并不专在写作。倘若我能像蝙蝠那样挖洞来拯救自己的话,我就会挖洞了。”
医生说“开张药方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了解却是件难事。”小男孩明确告诉医生,让他死吧,然而他所有的亲人都在为他挽留。这一方面意味着小男孩的亲人们对医生的不理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小男孩本身的不理解。身体和灵魂都无法被拯救,然而这种痛苦别人不会理解。对此,小说中的“我”感到深受折磨。那句歌词“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可以理解为是卡夫卡因外界期盼而产生的压力的投射。“我”脱掉了衣服,目的是与小男孩也就是“我的精神”更加接近,躺在床上聊天的时候,两者最接近一致。
小说中医生说“你的伤口还不算严重。只是被斧子砍了两下,有了这么一个很深的口子……”看似晦涩,但可以与前面对伤口的分析相结合来看。伤口是菲利斯对卡夫卡的精神带来的炎症,“被斧子砍了两下”恰好可以对应于两次订婚及解除婚约。通过“我”的解说,小男孩静静地安息了,在一定程度上灵魂得到了自我的安慰。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我”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了麻烦,永远都回不了家。还有一个是时间的速度问题,《乡村医生》中的时间很不合逻辑,有时候是一瞬间的功夫,有时候却要用上很久,非常缓慢,令人费解。但是与卡夫卡本人所言结合起来就可以理解了,他曾写道“内心的始终以一种魔鬼的或异常的或不管装怎么说是非人的方式追逐着,外部的始终断断续续走着它寻常的路。”卡夫卡对时间的感受本身就不是一致,他是以自己的感受作为逻辑的,小说中的时间是他自己主观感受的投射。
通过镜像理论较为完整地理清这篇梦境般的小说《乡村医生》,可以看到双重镜像(即卡夫卡本人/叙述者“我”,“我”/男孩)是卡夫卡对自我的分裂和重新建构,用一种梦境般的形式隐喻真实的世界和情绪。或许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写作对自我的救赎的。
(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