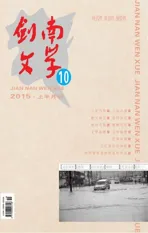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一小时的故事》
2015-11-22吴明玉
■吴明玉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一小时的故事》
■吴明玉
以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分析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历程,揭示父权制对女性婚姻的束缚,体现出女性的意识觉醒及其对自由的追求。
1.引言
凯特·肖邦是19世纪末美国重要的女性作家,也是女权主义文学创作先驱者之一。她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表达了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主题,是其一系列描写女性觉醒与反叛作品的序曲。作品讲述玛拉德夫人获悉丈夫死讯,到丈夫突然返家,惊愕之下心脏病发作猝死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主题深刻,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揭示出父权制对女性婚姻的束缚。作者描写了传统观念背后女性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变化,体现出女性的意识觉醒及其对自由的追求。
2.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创新的领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将女性写作的差异纳入作家心理和性别同创造过程关系的范围,它关于心理和女子自我的理论吸收了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性别差异模式,所谓女子心理或自我是由身体、语言的发展及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性别角色形成的”。十年间,女性主义批评的焦点从强调男女平等转变成承认两性之间存在差异,强调女性心理的独特性。基于这一观点,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中的“阳物崇拜”论进行猛烈批判,进一步否定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凯特·米利勒在其代表作《性政治》中反对弗洛伊德生物学基础的女性心理结构观念。她探讨了男性气和女性气的社会化过程和角色差异的文化根源,认为弗氏理论集中体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男权中心主义。埃莲娜·西苏强调女性写作必须要通过 “躯体写作”,“必须让人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解除女性的压抑,发挥女性的潜能;“夺取讲话机会”,“打进一直以压制她为基础的历史”,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和历史,确立女人自己的地位。
3.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西蒙·波娃认为,“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制社会不断压抑着女性,使她们长期处于被贬损、被支配的地位。在菲勒斯中心主义影响下,男性和女性处于一种主动与被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之中。男性是主宰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女性是附属品,是次要的,依附于男性而存在。这种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标准具有强制性,迫使女性隶属于男性,屈从于父权和夫权,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从而丧失了女性的话语权。
布兰特雷·玛拉德是父权社会的代表。他表面对妻子关心爱护,实质上却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妻子并使其屈从,无视妻子人格。作为被凝视的对象,男人眼中的他者,玛拉德夫人长期以来逆来顺受,毫无自由可言。她的真实自我始终处于缄默与缺席状态。刚得到丈夫去世的消息后,玛拉德夫人“暴风雨般”大哭起来。“暴风雨”表面上形容她的哭势迅猛强烈,深层却在暗示她的悲伤如暴风雨般来得猛去得快。窗外自由祥和的景象烘托轻松愉悦的气氛,暗示其获得自由后的愉悦心情。丈夫死了,妻子却看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色,暗示了主人公往昔的生活是何等的压抑、沉闷与平庸,暗示着主人公独立意识的觉醒,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丈夫的“死”使她失去了逆来顺受的环境,唤醒了她的反叛意识。玛拉德夫人期待的自由又因丈夫“死”而复生而失去,导致了她“喜极”而亡。小说揭示了男权社会力量无比强大,使人难以看到希望,也表现出女性解放道路的艰难与漫长,甚至需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4.女性意识的觉醒及悲剧性命运
作为父权制度下的女性,玛拉德夫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她”,而是被男性权力定义的“他者”。她别无选择,不得不屈从于父权。在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后,玛拉德夫人悲痛之余,埋藏在心中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为自己不再成为丈夫附庸,为自己获得自由而兴奋不己。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了象征和反讽的技巧帮助深化故事主题,剖析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小说中“门”象征着她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分界线。进门后,主人公打开了窗户,象征着她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期望获得婚姻生活以外的自由,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到了房间之后,她身心疲惫,内心却汹涌澎湃。她看到了窗外春天的景象:树梢、小鸟、远处传来的歌声……可是这些都是心情愉快的人才能感知到的。丈夫的“死”给玛拉德太太带来了自由的曙光,“自由”才是玛拉德太太“真正的长生不老的药呢”!当玛拉德夫人经过自由思想的洗礼,精神顿悟。打开门之后,眼睛里充满的是“胜利的狂热”,举止也如“自由女神”一般。强烈的对比突出了玛拉德夫人女性意识觉醒之后极大的愉悦。
小说结尾处的反讽富于戏剧性。玛拉德先生的“死”曾让玛拉德太太获得新生,而他的生还却让她心脏病发作猝死。反讽的技巧体现小说中种种矛盾性的对照,生与死的对立揭示出两性之间生与死的较量,女性渴望自由的心声最终难以实现。
5.结语
小说向读者呈现了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其产生的根源并不是女性天生被阉割的缺陷,而是深深植根在强大的父权势力统治下的深严的社会制度。迫于父权势力的无处不在以及自身的迷茫,主人公始终无法真正获得自由,找到作为真正女性的主体定位。由此可见,女性想要获得真正意义的自由,需要人们消除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源,真正从精神上尊重和关心女性。
(新乡学院大学外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