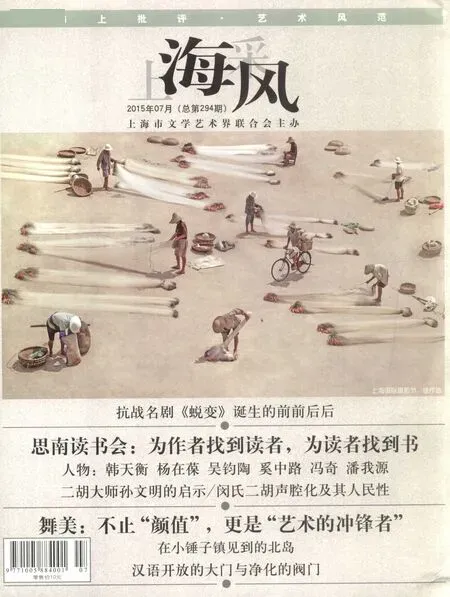闵氏二胡声腔化及其人民性
2015-11-19采编
采编/曾 凌
闵氏二胡声腔化及其人民性
采编/曾凌
闵惠芬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二胡演奏家,她的音乐不仅风靡海内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几辈音乐爱好者,是我国二胡音乐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今年5月12号是闵惠芬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为了颂扬这位大家,日前上海民族乐团特地举行了音乐纪念会。随后,由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办公室主办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届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论坛——从闵惠芬的二胡艺术谈当代民族音乐创作的人民性”在沪举行。此论坛邀请了民族音乐各界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学者,以二胡大师闵惠芬的艺术成果和艺术精神为起点,展开当代民乐创作“人民性”的探讨和思考。不仅缅怀、追忆这位为中国音乐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家,更为民族音乐发展和传承、民族音乐的出路和方向,做进一步思考。
闵惠芬老师常讲,“我有使命感,我有责任感”,她的人生践行证实了:只有贴进时代、扎根人民,才能弦韵永存。这是民族音乐创作的今天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音乐是要拉给老百姓听的”
杨光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秘书长):闵惠芬一直在人民之中,从1963年在“上海之春”比赛中获奖到2014年离开我们,她始终没有离开舞台、离开观众。50多年的演奏生涯中,作为艺术家在舞台上时间跨度之长、演出场次之多、观众受众面之大,当属中国之最。有一个小统计:从1994年至1997年上半年三年半的时间里,她举行了65场独奏音乐会和专题讲座,参加为中小学生和“民乐会知音”等普级音乐会共687场,人数达628410人。这个数字是一个艺术家贴近人民的真实写照,无论有无报酬,即便需要颠沛赶路,或者演出条件艰苦,她都和大家一起,从不搞特殊,也从没有怨言。她把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作为人生的充电。就在她去世前,她的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了,但她仍坚持参加“长三角地区二胡艺术节”的活动。
刘天华先生讲,“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工具”。这种寻常百姓家的平民思想是闵惠芬老师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是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闵惠芬老师常讲,“我有使命感,我有责任感”,她的人生践行证实了:只有贴进时代、扎根人民,才能弦韵永存。这是民族音乐创作的今天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
顾冠仁(著名作曲家):闵惠芬同志有她的追求,她把手中的乐器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和武器,她用她的行动实现了她经常表白的:“除非动弹不了了,我要一直坚守在自已喜爱的舞台上,为观众拉琴,为人民服务。”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每次外出演出,无论是到学校、工厂、农村,还是到剧场,无论条件再简陋、再艰苦,她都要去,而且都是认真地作好准备,拉好每一首曲子。她演出的曲目多,风格多,所带的乐器也就多。每次外出演出,她总是左右肩各斜背着一个大乐器箱,琴箱带交叉在胸前,简直像“五花大绑”,手中还拖着个大行李箱。我真担心乐器、行李把她压塌了,就对她说:“你是不是可以把乐器装箱托运,或让年轻人帮您拿。”她率直地说:“乐器是我的宝贝,托运或让人拿,我都不放心,坐车、乘飞机我都是随身带着的,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能保证演出。”她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肩上背着二胡、手中拖着行李走南闯北,把美妙乐声播向四海。
邓建栋(二胡演奏家):闵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音乐是要拉给老百姓听的。从她创作和改编的作品一览表中,就能对她的追求一目了然:《老贫农话家史》《忆江南》《宝玉哭灵》《游园》《卧龙吊孝》《洪湖主题随想曲》《阳关三叠》《寒鸦戏水》《逍遥津》《红旗渠水绕太行》《珠帘寨》《音诗—心曲》。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均采用群众喜闻乐听的音乐语言,表现各个时代的现实生活,选取最富于时代意义的题材,结合时代特征,并认真从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中吸取营养,将其发展变化成特有的二胡音乐语言。先生在她的文章里提到:“人民需要艺术,而艺术更需要人民。”她用雅俗共赏的作品,秉承紧贴人民群众、服务老百姓的方向,真正把二胡拉进了“寻常百姓家”。
刘光宇(重庆市歌剧院院长):改革开放之初,“向西看”和“向钱看”充斥社会,民族音乐无人问津,在“娱乐第一”中,人文精神流失。在此背景下,闵惠芬深刻意识到,大国崛起,一定包含文化的崛起。她进行抢救式的推广和普及,哪怕是“三无”(无人邀请,无人委派,无有报酬)义演!她把青年拉了回来,两根弦、一张弓的劝化和心灵按摩,使民族音乐薪火相传,这是闵惠芬的历史贡献。她把音乐普及到儿童,将音乐会变为故事会。她的信念是“凡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去演”——哪怕有一次,观众只有13个人。2004年她策划了徐州国际胡琴节,其中12辆二胡花车和1500人的二胡齐奏及长达4公里的大游行,创吉尼斯纪录。自2005年起发起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汇演,第一届400人、20支队伍,第四届1800人、50支队伍,第七届已是3000多人、76支队伍,并吸引了海外和国内其他地区参加。闵惠芬实现了艺术人民性的政治担当。我们要像她那样真正懂得文艺的本质和规律。
闵氏艺术开启现代民乐的寻根之路
徐坚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在听某个现代派作品的音乐会上,中场休息时,闵老师非常谦虚地跟我谈:“徐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小提琴和二胡两个乐器哪个优秀?”我一下子被震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思考片刻后对闵老师说,这两件乐器不太好比。如果要比的话,那就要看作曲家怎样写。如果一个作曲家写二胡曲的时候,是用四根弦的小提琴思维来写,那么,这二胡都可能是缺点;但如果一个作曲家充分发挥二胡两根弦的各种独特的演奏技巧,那么二胡就是很优秀的!闵老师听我这样一说深表赞同。接着她又问我,现在中国科技这么发达,有没有可能把二胡改造成四根弦?这又把我问住了!闵老师见我愣住了,就很谦和地启发我说,现在的高科技甚至搞出5根弦、6根弦的拉弦乐器,但为何二胡至今还是两根弦呢?徐先生,你从中国道家的哲学去想想吧!我一听,大受启示,立即回答闵老师说,哦!我明白了。因为我们中国是讲阴阳之道的,两根弦也有可能代表阴阳两极。如果西方需要四根弦来完成人间情感的喜怒哀乐,中国人则用两根弦的二胡足矣。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胡与小提琴哪个更优秀、更智慧,就一目了然了。说到这里,闵老师和我都会心地笑了……我认为,闵惠芬老师以她超凡的战略眼光和勤奋钻研、虚怀若谷的宽广之心而达到的音乐最高境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岳峰(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如果说,音律是音乐的宗法和基础,那么,在国人把转基因食品视为洪水猛兽的今天,我们的民乐创作辛辛苦苦了一个世纪,是不是在悄然走着一条自我转基因之路?曾经有一位印度的音乐家访问我们的音乐学院,当他看到我们的琴房里摆满了钢琴时,便十分诧异地说:“你们的律制和西方律制不同,为什么会以钢琴作为音乐基础呢?”那么,由此推断,以钢琴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方乐学体系,是不是中国音乐自我转基因之路的起点呢?中国民族音乐转基因的代价又是什么?
就拿二胡这件乐器为例: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二胡已经从贩夫走卒手中的一件“响器”,变成了登堂入室、走进高等学府的一件“乐器”;而后又成为登临世界舞台、象征民族精神的一件“道器”。在身份转变中,独奏二胡极力摆脱对原有声乐唱腔的依附,做着专业化、器乐化的努力。然而,今日之二胡,已经由世纪初刘天华先生的“调和之路”,逐渐走向了小提琴化、钢琴化、交响化的“西化之旅”,二胡的创作作品,越来越让黎民百姓听不懂,以致于有人惊呼,警惕二胡有“生之民间,败之庙堂”的危险!那么我们又要问,中华民族音乐的根是什么?寻找民族音乐之根的意义是什么?华夏民族音乐的DNA又是什么?……事实上,闵惠芬二胡艺术的成功之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就在脚下;“路”,也就在脚下。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才是我们民族器乐真正的老师。闵氏二胡声腔化的本质,就是开启了现代二胡的寻根之路,开启了现代民乐的寻根之路。这种集一世之功修炼而成的艺术智慧,值得行走于竞技时代的二胡今人深深思索。
事实上,闵惠芬二胡艺术的成功之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就在脚下;“路”,也就在脚下。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才是我们民族器乐真正的老师。闵氏二胡声腔化的本质,就是开启了现代二胡的寻根之路,开启了现代民乐的寻根之路。这种集一世之功修炼而成的艺术智慧,值得行走于竞技时代的二胡今人深深思索。
陈春园(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副系主任、二胡演奏家):我认为现在探讨“人民性”就是探讨民族音乐对根源的回归。民族音乐应该有所担当,引导大众更多地回归到民族性的思考,回归到爱我们中国人的根、爱我们自己的民族这个主题,有更多的表达。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处在互联网时代,发生着巨大变化。我认为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和艺术灵魂在于对传统音乐元素的继承和坚持,从民族音乐艺术创作、演奏等方面严格恪守传统文化的审美要求,同时将这样一种传统的审美韵味作为主题更多地进行推广,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获得回报的行为,而是要通过一代乃至几代民族音乐人的努力。现在年轻观众甚至专业人士,对传统艺术缺少兴趣、缺少研究,如果与一些同样拥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相比,理性地、满怀敬畏地守护传统文化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闵惠芬老师从来不是一个守旧的人,她热衷于创新,但你会看到她一生都尊重这门艺术的根本,你可以发现她搞创新也是利用民族文化的姊妹艺术,利用民族性本身的艺术特征作为主流,因为她知道,这是这门艺术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
从声腔化的文化价值看,它固守了中国人的宗姓。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在经济的世界“通婚”中,如何保障文化上自己“基因”的独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固什么基,上层建筑和文化界必须牢牢把握。声腔化恰好以中国式的创新做到了这一点,它以一种精神家园的坚守,呼唤民族性的复归。
李祖铭(著名京胡表演艺术家):闵惠芬对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的贡献当之无愧。闵老师能把声腔用二胡来体现和演绎,这是她最大的一个贡献。她独创的“器乐演奏声腔化”的理念以生动多样的“歌唱性”打动人心,具有广泛的流传性,深受人民的喜爱。
当时这一想法是毛主席提出来的,那时全是样板戏,毛主席想听那些老戏,说能不能拿乐器来形容各个流派。所以当时找了民乐界的闵惠芬、徐仰德等很多有名的人物,来学生旦花脸等各行当名段。当时也找了很多京剧界有名的老前辈教他们,正好闵老师就分到我父亲这一组。我印象挺深的是,闵老师上我家来,头一句就问,怎么拉才能出高派的味。我父亲跟她说,就把唱片翻出来听几十遍,听完了再往下说。比如听一个《父子门》,闵老师得自己先能哼唱,体会出到底高派的味道在哪,然后再拿二胡来找这个味道,一遍不成两遍,一直到味道对了再往下走,然后再是节奏,我觉得闵老师太用功了。闵老师可谓开创了二胡艺术的新格局。
李明正(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闵惠芬提出的二胡演奏艺术声腔化,是从二胡接近人声、富有歌唱性的特点出发,更重要的是,深入到以戏曲声腔音乐中来,走了一条探索二胡以民族民间音乐为本体的发展道路。
用二胡演奏戏曲音乐唱腔,既是她的首创,又是深入到高难度艺术领域的开始。把演员在舞台表演的戏曲唱段,移植到二胡的演奏和表演上,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闵惠芬用二胡演奏的戏曲音乐唱腔,所体现的是以戏曲意象美学为代表的民族音乐传统,探索的是以乐本体和以中国古典艺术魅学“意象”为中心的美学原则与综合艺术观念。
在闵惠芬五十多年的二胡舞台艺术生涯中,在面对新时期的现代派音乐、无调性音乐时,她始终没有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传统。其美学思想和二胡艺术声腔化的音乐主张,为二胡演奏艺术通向浩如烟海的中华音乐传统架起了桥梁,为中国二胡艺术的宏观走向开辟了宽广而辉煌的发展道路。
刘光宇:今天我们来看闵老师二胡艺术的逻辑规律:演奏技艺的境界神韵是“起”,创作演奏的作品是“承”,声腔化突破创新是“转”,艺术目的最终为人民是“合”。闵惠芬首先从主观上塑造。这里仅观察以“情、气、格、韵”统领下的“声腔化”美学价值——声腔化源于对戏剧的研究,戏就是人,反映人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深度。闵惠芬掌握着戏剧的基本要素,即:主题思想、最高任务、怎么贯穿和思想的目的,从而揭开了戏剧寻找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若干谜底。说到底,是建立了二胡的灵魂:“歌唱性—器乐演奏声腔化”体系,使二胡呈现出更富民族性、艺术性、更动人的中华民族音乐品格。再从声腔化的文化价值看,它固守了中国人的宗姓。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在经济的世界“通婚”中,如何保障文化上自己“基因”的独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固什么基,上层建筑和文化界必须牢牢把握。声腔化恰好以中国式的形式创新做到了这一点,它以一种精神家园的坚守,呼唤民族性的复归。声腔化扎根中国,为了中国,忠于中国。这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的民族归属。
闵惠芬精神对民乐创作道路的启示
陆在易(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闵惠芬曾患上凶险的黑色素恶性肿瘤,五年时间内,动过6次大手术,15次化疗。但她不仅没有被病魔击倒,而是用旁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气与病魔作斗争。在第一次手术后不久,她即投入到协奏曲《长城随想》的练习之中,此时的她,伤口还未愈合,每次的练习,疼痛都使她大汗淋淋,但她坚持练习不止。当作曲者刘文金考虑到她的身体,想在创作时尽量不给她造成太大的难度时,她大为恼火,说:“艺术怎能向难度妥协?只要能表达出应有的气质和神韵,再大的演奏难度我也要拿下!”就这样,闵惠芬在1982年5月第十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成功地首演了长达30分钟的《长城随想》,宣告民乐史又一经典曲目的诞生。同年7月,她又随团赴山东、天津、北京巡回演出,11月,她在京举办独奏音乐会,原定只演一场,然而一发而不可收,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等学府连续为她举办了六场独奏音乐会。北上南下的仆仆风尘,使身患重症的闵惠芬极度虚弱,领导、同事、家人劝阻她,可她总是一句话:“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让我演吧!”因此,我认为,闵惠芬的一生,是顽强拼搏的一生。与此同时,闵惠芬身上又一具有的精神,便是在艺术上永不停息的学习精神、钻研精神、探索精神、开拓精神。
以上说到的闵惠芬的两种精神,是相互相承的,从根源上说,都出自于闵惠芬对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记得在她去世前几个月,她还到过我家,和我研究上海音协二胡专业委员会的班子构成,我曾对她说:你的身体也不太好,电话中谈谈即可,何必专跑一次?她说不行,非慎重见面不可。谈完后,望着她下楼梯时的艰难步履,我心中深受感动。闵惠芬离我们而去已有近一年了,她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开创了二胡演奏艺术一个丰硕的闵惠芬时代。她留给后世的不仅是艺术财富,还有精神财富。
许舒亚(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我觉得闵惠芬在中国音乐史上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尤其她一生中,跟随中国的艺术团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演奏,在国际乐坛上也被认为是世界出名的弦乐演奏家。二胡这样一个中国国粹得到西方主流媒体如此高的评价,有闵惠芬的一份功劳。她用自己的身心加上对音乐的理解和开拓精神,把二胡演奏推向新的时代高峰。与此同时,她自己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除了这些年来《长城随想》《洪湖主题随想》的演奏和创作等,还包括70年代接受的“特殊任务”,为毛泽东先生录制一批京剧唱腔。这一阶段她一直没有放弃器乐演奏声腔化的探索,一生对二胡演奏的技巧和美学思想等诸多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刘锡津(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创作,仍然是我们民族管弦乐发展的瓶颈与短板。借此2015上海之春民族音乐发展论坛的机会,我想说几点多年创作的感受:一、成功的作品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民族音乐,首先必须深深地植根于自己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二、当代音乐家要想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还必须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全世界。但是,民族特色,是绝不可忽略的。智慧的音乐家,在学习人类共同遗产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与自己民族音乐相结合的根本,这样才能不断创作出既是世界一流,又深具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三、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作曲家都知道,写作到一定程度,技术已不是主要问题,而写作思想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文化、历史、对各类姊妹艺术的熟悉与了解,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等等,都是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与关键因素。四、很多艺术家都有这样的感慨: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创作空间。愿我们的作曲家,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勤奋努力,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杨易禾(浙江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民族音乐要向前发展,最重要的是创作。要多出新作品,关键是机制。谈民族音乐创作方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并不是创作本身,而在于创作的激发与管理机制。不管是行政、管理机制,或者是奖励、激励机制,希望能很快地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艺术创作机制。上海民乐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一直引领着中国民乐的发展,孕育出了闵惠芬、俞逊发等一批演奏家,也出了很多好的作品。上海民乐团是否能再度起到引领作用,从你们这儿率先产生出一个艺术创作的机制?就比如说集结作曲家们去实地考察采风、体验生活;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契机;完善新作品的激励、奖励等管理办法等,来探索民乐创作生产力提高的新路子。我国民乐创作的现状基本是散兵游勇式的,缺乏规划性、组织性。说实话,时代的大背景下近几年上海民乐团没有出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很惋惜。今天的民族音乐创作论坛开得及时。如果能进行艺术作品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大胆尝试,建立一个完善的艺术创作管理机制,或许会有一批民乐的新作品、好作品出来。这是我们民乐人的期盼。
智慧的音乐家,在学习人类共同遗产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与自己民族音乐相结合的根本,这样,才能不断创作出既是世界一流,又深具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