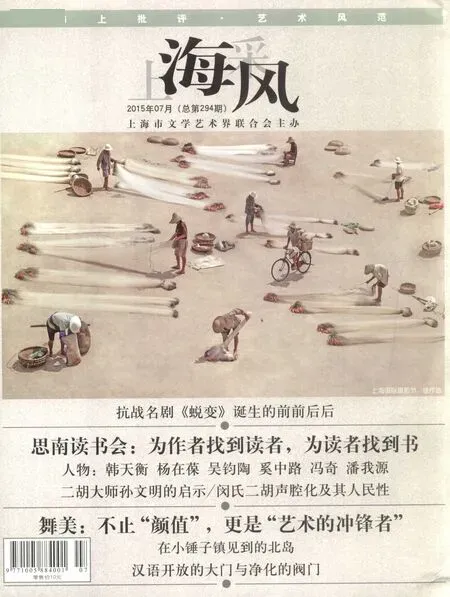“女子越剧”创造了独特的女性文化
2015-11-19文/姜进
文/姜 进
“女子越剧”创造了独特的女性文化
文/姜进
最近出版的30多万字拙著《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试图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语境中,探寻和思考越剧的意义。女子越剧也许是中国近代唯一保存至今的单性别舞台艺术,其清一色女演员的舞台呈现及其以女性为主的观众群使之成为20世纪中国表演艺术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一看似奇特的现象却是中国女子社会角色和地位发生变化的一个体现,绝非偶然。女子越剧又是在近代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兴起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越剧在上海的成长,表征了中国女性进入都市空间、参与塑造都市公共文化的历史性功绩。
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忽略了这个为数不少的人群以及她们所创造的越剧文化。这一忽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精英”们对大众文化的偏见。在精英们看来,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文化将俗世和个人的生活作为关注点是自私、琐碎的,甚至是有危害的,因为它使人沉溺于私人情感而不能献身于民族国家的事业。大多激进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和国民党学者对民国时期通俗文学的各个流派均持批评态度,一律贬称之为“鸳鸯蝴蝶派”。同样的,在大众演艺、娱乐方面,近代以来的上层政治精英对其不无鄙夷,或者试图规范和控制之,或者在规范控制的同时力图将其改造成宣传工具。然而,与精英的偏见相反,大众文化从整体上并不反对建造一个现代、富强的中国,许多通俗文化作品自动将其故事置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下。不同在于二者关注的焦点:精英意识形态视民众为国家的附属品,通俗作品则聚焦人民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领域因此而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结构,这种结构可能与精英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其对现代国家的国民建设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后者,是史学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跳出精英意识形态的壁垒,把立足点转移到人民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领域,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如越剧这样的大众演艺是主流,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吸引和主导着民众的思想感情,而精英意识形态在此显得遥远而不甚相干。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对大众文化和女性文化的歧视还与一个方法论问题相关,即对文本和印刷史料的高度依赖。因为这类资料绝大多数出自男性政治和文化精英之手,主要是精英活动和思想的记载,对这些资料的依赖就不可避免地使历史研究偏向于这些资料的生产者。传统史学一路走来,硕果累累。虽然我们不能仅仅因其对文字史料的依赖而否定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但由这些成果的累积而形成的历史知识,会过分强调精英分子的影响,而将大众的活动视为只是对精英意志被动的反应,或抵抗或追随,从而形成具有严重偏颇的历史书写。也就是说,来自文本以外的广大非写作人群的声音的匮乏,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将人民大众置于精英意图的受众位置,抹杀了大众的主体性,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则成了一句空话。同样,中国女性的失声,使她们成了历史书写中的边缘群体,也使有关中国妇女的女性主义研究不能真正探讨女性的生活和意义世界,而只能满足于对男性精英利用妇女问题来建构他们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揭露和批判。因此,发掘文本之外的史料,通过口述和演艺等资料来发掘边缘人群的声音就变得至关重要,而越剧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之“发现”越剧其实是一个上海女孩童年经历的再发现。1962年,我上小学时,母亲被分配到上海越剧院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每当有演出而家里又没人照看我的时候,母亲就会带我去戏院,把我安排在前排为她留的座位上,自己到后台工作。我的同学和朋友对此都非常羡慕,因为当时越剧很红火,经常是一票难求。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们,也包括对安排她去越剧院工作不满意的母亲,都看不起地方戏,认为它们落后、过时,编演的都是些琐碎、庸俗、无足轻重的爱情故事。不可避免的,我在1978年初进大学后便沉浸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不再关心越剧,一段童年经验便沉淀在了记忆的深处。直到199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研究的熏陶下,这段童年的记忆忽被唤醒,于是将女子越剧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希望能在历史记载中留下这些女性的声音和功绩。
1995—1996年,当我回上海搜集论文资料时,惊奇地发现母亲也喜欢上了越剧。退休后,她喜欢听越剧和京剧的录音带,而且每天都会看电视上的戏剧频道。我父亲也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新文化人,还是个“话剧迷”。虽然年轻时的他认为地方戏落后、封建,但如今观看戏剧频道成了他的爱好。在众多的地方戏中,越剧和京剧是我父母的最爱,母亲喜欢越剧甚于京剧,而父亲则喜爱京剧甚于越剧,折射出中国戏曲中典型的性别分野。母亲甚至后悔当年没有用心写一个越剧剧本。父母从来没有解释这一转变的个中原因,似乎对传统戏的兴趣是自然而然、无须任何解释的。他们从安排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革命和革命话语中退休。现在他们可以静静地享受生活,可以从任何能够引起他们情感共鸣的艺术中找到乐趣,而不必用外在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感受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他们对戏曲的欣赏,并不是出于对戏曲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感悟。他们对我选择“越剧”来做博士论文甚感疑惑,因为在他们看来,博士论文的选题应该关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而不是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娱乐形式。虽然母亲非常敬佩她在越剧院的演员同事,视她们为独立、聪明、勤奋的女性,我访谈的很多对象也都是母亲介绍的,但她仍然认为我应该选择一个比越剧更重要的课题。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越剧演员和观众,似乎并不介意精英话语影响下人们对越剧的不齿,而是在她们自己创造的价值体系中、以自己的视角来做出价值判断。越剧言情剧毫不脸红、永不疲倦、绝不吝啬地将整个舞台用作渲染爱情、人情的空间,而越剧迷们则毫不掩饰地、有时甚至是无节制地在公共场合对自己喜爱的女演员和剧种表达出强烈的情感,虽遭一般人耻笑亦不顾。精英们在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中无法理解越剧的世界,看不到越剧的意义。要进入越剧的世界,历史学家就必须深入了解越剧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将意识形态留在门外。正如彼得·富勒所指出的:“勇敢地坚持对经验的忠诚能够在一定的情况下打破意识形态的框架。人的经验并非完全为意识形态所决定,反而常常与之相悖,在意识形态冰山内部不断造成断层和裂片。”因此,对越剧的实证性研究,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生疏而又熟悉的女性世界的图景,将女性的经验纳入史学研究中,丰富和刷新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
以演员和观众的访谈及越剧戏目的研究为基础,辅以档案、报纸和其他史料,我试图重新构建一个对于演员和观众充满意义的越剧的世界。丰富的口述和演出资料为我进入越剧女性经验与想象的世界提供了入口,舞台表演、公众的反应、演员对自己生活和艺术的讲述、观众有关越剧对自己影响的叙述,都是我绝好的资料,极大地帮助了我分析和理解所谓的“越剧现象”——在快速成长的都市社会中女性情思公然的自我表达。
我们通过这样的研究路径看到的是一个与精英史学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越剧不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拙劣的玩笑,而是应新兴都市社会需求而产生的重要的文化生产形式。越剧言情剧代表的是对在迅速现代化的都市中急剧转变着的性、性别、家庭关系的思考和探索,是帮助都市居民理解并学习如何应付这种变化的一种努力,因而受到女性和一般民众的喜爱和支持,逐渐成长为在全国和华语文化圈颇具影响的大剧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等经典剧目,对现代中国民众对于情爱、性别、家庭,以及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伦理和审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大众文化史的目的是在历史研究中让边缘化的人群发声,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工作是由历史学家代其完成的,并不是由失声者自己完成的;而大多数历史学者所写的历史主要还是给同行看的学术书。然而,正如斯图亚特·海尔在论述克罗齐时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平行的民众运动’把参与的民众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将他们的影响力扩展到专家阶层,形成……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社会团体,就不会有相应的新理论、新学派的构成。”这就是说,“边缘群体”事实上已经在社会上发出了她/他们的声音,产生了影响;她/他们不需要专业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些民众和她/他们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书写的历史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故事融入更广阔的历史叙事中。我研究女子越剧,没有企图和声称是在为创造“越剧现象”的人们代言,只是将越剧人的经验和对生活的认识载入史册,并试图理解这些故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之重要性的一个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