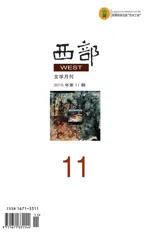碎红
2015-11-19史晶
史晶
小说天下
碎红
史晶
终有一天,月光会漂白一切细节,我将披着月光离尘而去,留下满地碎红。
——题记
2003年夏乌鲁木齐
旁边那栋二十二层的楼把夕阳全挡住了,房子里光线很暗。虽已经过了立秋,天气却比夏天还要闷热,屋子里一丝风也没有,隐约闻到一种霉味。吃过中饭,老头子拿着给贱货买的衣服出去了,梅惠珍心里很烦,一直坐在坏了一条腿的沙发上发呆。
那只老钟的指针摇晃着指向八点,梅惠珍赶紧走进厨房做饭。她洗好米放进电饭煲煮稀饭,把咸鸭蛋剥好,再切了一小盘葱丝。老头子是山东人,每天家里都得吃馍和大葱。大葱的味道熏了她三十多年,她很讨厌。
梅惠珍不用想也知道这会儿老头子和那个骚狐狸打麻将正打得高兴呢。骚狐狸烫着头盘着个牛屎髻,穿大花连衣裙,还抹着红嘴唇画着细眉毛,把老头子迷得不得了。“老娼妇,贱货。”梅惠珍狠狠地骂了一声。几十年了,老头子却从来也没给她买过东西。梅惠珍越想越气,拿起一只碗就摔在地上。啪,碗碎成了三片,她随即又心疼起来,蹲下去一片一片捡。她恨恨地想,离了婚的女人都不是好东西,就会勾引别人的丈夫。何况这个贱货并不老。这让梅惠珍更加痛苦。
梅惠珍换下身上的大背心,出去买馍。看到有卖黄纸的,就买了一些,母亲死了三十年了,她还从没给烧过纸。以前老头子总说:“给
你那个资产阶级老娘烧纸,想翻天呀。”拿着黄纸的一瞬间,梅惠珍突然难过起来。再过几天,就是她六十岁的生日了。
吃饭的时候,她跟全家人说:“六十岁大寿,我想过一下。”
老头子吼:“过什么过!”
“老贱货过生日你陪着又买东西又吃饭!”
老头子一巴掌打来,梅惠珍闪得快,没打上。老头子摔门出去了。大儿子和儿媳互相看了一眼,小儿子白了她一眼:“找骂。”
洗完碗,她坐下来清点今天的账目。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压了几年的货已经开始糟了,再不处理掉就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了。梅惠珍的货是三年前进的,原以为捡了便宜,谁知道人家给她的是次品,卖也卖不脱。自己贪小便宜吃了大亏。
梅惠珍抠门是有名的。从家里到货摊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她拖着个大麻包挤公共汽车,因占地方,她每次都要和别人吵架。去年冬天,她从车上摔下来,摔了个脑震荡,差点老命都没有了。住了一个星期院,家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来送饭,老头子还说:“住院花那么多钱!”
这个家就像个无底洞,钱总是不够用。先是婆婆生病,后来是两个儿子要娶媳妇买房子,老的是个甩手掌柜,小的个个都是寄生虫。
夜深了,小儿子还不见影子。梅惠珍一直很宠这个儿子的,这小子最像自己,打小就精。梅惠珍还把小儿子的户口迁到了上海。
从那以后,二哥二嫂没少写信打电报告状。有一回打加急电报非要她去上海接儿子,电报上写着:你的儿子我管不了了,出了事情我们不负责。一向吝啬的二哥在电报上写了那么多字,梅惠珍一看非同小可,马上就上了火车,结果去了一看根本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小儿子在上海混了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就又回来了,天天和街上的二流子们混在一起。
梅惠珍关了灯,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半辈子都因为出身资本家而抬不起头,可到头来却是个彻彻底底的穷光蛋。自己原本是一朵玫瑰花,世事却把她变成了玉米秆,人真是抗不过命呀!
立了秋,夜里就有点凉,院子里打麻将、聊天的人早就散去了,连门口的灯也熄了很久了。只有圆圆的月亮在一朵薄云边静静地看着大地,月光流进屋里,泻了一地,像银色的溪水。已经两点多了,白亮亮的月光闪过高楼居然照进来了,她抬头看月亮,玉盘似的月亮正在二十二楼的顶上看着她。月亮这么圆,应该是阴历七月十五了吧。
王惠难得上一次街,天不太热,她也就慢慢逛起来。在二道桥细细看了窗纱、床单,顺便想去金店看看。她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大十字,乌鲁木齐的变化太大了,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起来倒像是电视里的上海。
王惠早先在大十字的东风商店当营业员。大大小小的精品店开起来后,东风商店开不下去关了门,后来被拆除建了大厦卖皮货。她在东风商店卖了二十年针织品。那是个窄长的商店,是解放前的苏联式建筑,还铺着木地板。针织部在最里面,光线挺暗的,她每天就在最暗的角落里呆着,侧着头看店门口晃人眼的阳光,偶尔进来一个人就好像披着一层光。有时她也会到卖食品的柜台去,和古丽仙聊天,顺便也会对经过商店的路人议论议论。她一直心满意足地在柜台后站着,等着退休,可没想到还没退休就下了岗。
王惠心想既然都到大十字了,就去皮货
中心看看古丽仙。古丽仙下岗后一直在这儿卖皮衣,生意挺好的。王惠想给正康买件皮背心,古丽仙就把她领到梅惠珍的摊位上。古丽仙介绍说:“你们两个都是上海阿拉子。你就在她这儿挑吧。”梅惠珍很热心地拿出几件皮背心让王惠挑。梅惠珍给她推荐了一件黑色碎皮背心:“这种耐穿,虽不好看却结实,在家穿又保暖又实惠。”付钱时,梅惠珍随口问王惠:“侬也是上海人,哪个区的?”“浦东的。”“噢,乡下人。”
同是上海来的支青,市区的看不起乡下的,中心区的看不起其他区的,就算是同一个区的,也要分是哪条路的。在这方面,梅惠珍总是有优越感,虽然有一阵资本家不吃香了,可上海人总还是看得起资产阶级大小姐的。
梅惠珍又问:“你是哪年来的,在哪个团?”“1964年,我在五一农场。”“五一的啊,不错。我是1962年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分到塔里木了。”“阿姐,侬还是大学生!我才初中毕业。”“哎呀,家里老爷子是资产阶级,条件还可以。”王惠依着上海人的习惯把比自己年龄稍大的都叫阿姐,一声一声的“阿姐”叫得梅惠珍心里那个舒服,不由得就想多说几句。
王惠今天心情特别好,梅惠珍终于卖了一件东西,心情也好。“侬不晓得,我家里住花园洋房的。”“阿姐,侬好命呀,不像我生来的乡下人,上个初中就不错了。”
梅惠珍这一天都很高兴。有多少年没有这样用上海话好好聊天了,难得有人肯好好听她说说话。
以前,她喜欢对人说自己穿着白纱洋装在租界自家花园里散步,可没人有兴趣听。再后来,工厂闷热的车间、吵死人的机器声让她自己都不愿意再想这些了。
1940年代上海
从弄堂里看月亮,有一种特别的样子。每天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梅惠珍总是在井口边洗这个洗那个。夏天的晚上,半弯的月牙秀秀气气地斜倚在屋檐上,微笑地看着她做完所有的活。她在月下洗完头,会坐在弄堂里吹吹风看看月亮,楼上王小姐窗口的茉莉正散出幽幽的香气,那一刻阴沟里泛出的臭味似乎也没有那么令人作呕了。
从月牙到满月,从月圆到月缺,一年年过去了,王小姐变成张师母搬走了,茉莉花却一直在开着。梅惠珍也从妹妹头长成了长辫子,每天放学后,她依然在月下井边洗这洗那,月亮就是她唯一的朋友,梅惠珍哭也好,笑也好,月亮总是微笑地安慰她。
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青石板上,就像母亲呜呜咽咽的哭声。母亲总是在哭,有雨的日子没有月亮,梅惠珍就怕听到她哭,心里慌慌张张的。母亲带着她们兄妹四人住在小弄堂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木头楼梯又陡又暗,弄不好就会跌一跤,木地板走上去咯吱咯吱响。
每天月亮还在天上的时候,她就要把马桶拎出来放在弄堂口,然后到井边淘米、洗菜、洗衣裳。她对同学讲:她的父亲是在美国上过大学的,她的母亲是名门闺秀,可她的底气是不足的,她生怕有一天同学们会看到她父母真实的样子。
梅惠珍的父亲梅贵宝是宁波乡下人。他十一岁那年,被他母亲送到城里表姨家的杂货铺里学做生意。表姨没有儿子,只有一个抱来的女儿,就是梅惠珍的母亲。他十八岁那年娶了表姐,成了杂货铺的老板。生了三个儿子后,梅贵宝突然觉得不能再在这个阴沉发霉的木头店里呆下去了,他害怕有一天,这糟了的木头会朽了,整个屋顶会塌下来把他埋进
去。只要在这个铺子里呆一天,他的老婆就会在他的头上骑一天。人都说上海满地都是黄金,他就卖了杂货铺带着一家人离开宁波到上海发洋财了。
刚到上海,他们一家在苏州河边上搭了一个小窝棚,梅贵宝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夏天卖桂花赤豆汤,冬天卖小馄饨。梅惠珍就是在那个小窝棚里出生的。靠着宁波人的精明与节俭,梅贵宝三年后就有了一家小铺子,虽然还是卖杂货,但在上海,钱却格外好赚。梅惠珍四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就搬到了现在这条弄堂里。梅贵宝当时给全家人讲,过不了多久他会买花园洋房给大家住的。
两年后,梅贵宝买了花园洋房,不过不是给梅惠珍她们住的。梅贵宝娶了一个姨太太。母亲叫那女人“白骨精”。“白骨精”是一个小老板的女儿,梅贵宝在吞掉那个老板公司的同时把他的女儿也一起吞了。据说“白骨精”年轻漂亮,还是个大学生呢。
梅惠珍和母亲在洗衣裳或是剥毛豆的时候,邻居的阿婆们就会给母亲出主意:“侬要会拢拢男人的心,伊可是年轻漂亮哩,侬黄皮寡瘦的,哪能斗得过伊。”母亲就会提高声音:“我伲在宁波的时候也是一枝花呐,伊拉讲我是铺子西施,求亲的人把门槛都踢破了。”接着她就会讲她娘家的铺子有多么大,她坐在柜台后面引得多少男人来买东西。母亲说着还不时会在梅惠珍头上打一下,骂她一句:“大人讲话,小姑娘听什么,丧门星,家都让你哭穷了。”
梅惠珍的生日是阴历七月十五,乡下人认为中元节生的姑娘会克人、晦气。母亲认定是梅惠珍的丧门星样子才让自家男人讨嫌了她。她见不到“白骨精”,就常常打骂梅惠珍解气。母亲总是骂呀骂,梅惠珍也认为是自己生得不好,倒了家里的运气。
自从父亲娶了姨太太出去另过,就几乎没有回来过。母亲过一阵儿就会让大哥去找父亲要些钱。梅惠珍只记得父亲是一个矮胖子,黑而结实。
八岁那年,母亲突然要带她去找父亲,一路上母亲再三嘱咐她:“到时候你就哭,大声点啊。”
邻居王小姐给母亲说要让梅惠珍上学,但母亲从没想过要让梅惠珍去上学,因为她自己就没有上过学,她认为儿子上了学可以找个好事情做,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上学白费钱。王小姐开导她:“你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再说学费也应该由他出。”母亲觉得有道理,自家男人挣的钱,不能全让“白骨精”花光了,不供自家女儿倒要省下来便宜别人。所以母亲就决定带着她去找父亲要学费。
母亲在跟父亲诉苦的时候,会时不时掐梅惠珍一下,梅惠珍就哭两声。梅惠珍的眼睛始终盯着“白骨精”和她的女儿。“白骨精”穿着月白底有暗金花的旗袍,她那一岁多的女儿穿着白纱的蓬蓬洋装。她们在花园的草坪上玩,根本就没有理梅惠珍娘俩。只是在梅惠珍哭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会看她一下。梅惠珍心里恨透了她们,她恨“白骨精”为什么会这样美丽,恨她对自己和母亲的漠视,也恨那个小孩子穿得那样漂亮。然而她更恨母亲那土里土气的宁波腔和自己身上缝了补丁的衣裳。自己受的所有苦都是因为那个看也不看她们的女人抢走了父亲,母亲不高兴当然要打自己了。同是父亲的女儿,那个小东西凭什么住洋房穿好的吃好的,而她却要天天倒马桶、在潮湿的都是小坑的井边做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还要时不时被母亲打骂。母亲认定是梅惠珍给家里带来了霉运,而梅惠珍清楚地记住了是那个女人和她的
女儿让她苦了一辈子。
2003年秋乌鲁木齐
中秋节的时候,二哥又打来电话,让梅惠珍把她的户口迁到上海,再就是催问“白骨精”生的那个女儿找到了没有。
1952年,父亲带着大哥去了香港,把其他人都留在了上海,母亲打那时起就开始有点神经兮兮了。十几年前,大哥和二哥联系上了。大哥继续做着父亲留下的生意,二哥说大哥比父亲还吝啬。
三年前,二哥和三哥到香港去了,回来后羡慕得不得了。二哥打电话给梅惠珍:“那都是爸爸留下的,我们也都有份。你给老大打电话说说,应该分给我们一份。”
梅惠珍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梅家的人一个比一个精。二哥又劝她:“你做生意多辛苦啊,有了钱就可以休息了。”她心想,正好儿子们要结婚买房子,于是她经不住劝就给大哥打了电话,但大哥没有表态。
后来,大哥提了个条件:要找到“白骨精”生的那个女儿,他说那是父亲生前的意思,都是儿女,要分都有份。二哥说:“老大门槛精,不想分给我们就找了这么个借口。可惜现在这些财产都在老大名下,不是老头子的遗产,打官司我们是打不赢的。咱们几个齐齐心,一定要找到那个女儿,逼逼老大。”
二哥和三哥积极开始寻找。父亲走的时候也没带“白骨精”母女,因为那时候他又有了别的女人。二哥终于打听到那个女儿的下落了。
“白骨精”后来又嫁了人,把那个女儿送人了,听说那个女儿后来支边到了新疆。二哥在电话里讲:“我们这边的任务完成了,下面就看你的了。人肯定是在新疆,你一定要快点找到,老大没几天活头了,到时候小的们更舍不得拿出钱来了。”
梅惠珍家里人却对这件事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大儿媳说她妹妹的同学在派出所搞户籍,可以请她帮忙。老头子则天天分析“白骨精”的女儿可能会在哪里。
秋天的月亮瘦起来,清瘦得像梅惠珍一家的亲情。
二哥说老弄堂要拆了,让她把户口移回来,这样他可以帮忙给她搞一套房子。按政策,知青退休后可以落户上海的。
记忆中青石板被细雨一滴滴激出一个个的小坑,如针的细雨落下开成了一朵朵细碎的花。梅惠珍突然特别想触摸井边的那一片青苔,五十年过去了,那种滑腻温润的感觉似乎此时就在指间。
1970年代塔里木
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姑娘们渴望找个人搭伴过日子。上海姑娘心气高,都想找会计之类坐办公室的小伙子。
月半弯,路边的钻天杨哗哗地拍着手,梅惠珍和小张就在路上走。小张刚刚探家回来,他给梅惠珍带了一条白色的真丝长围巾。那白色就像月光流过水面泛着粼粼波光,那白色比白姨太的旗袍还要耀眼,衬得斜绣的一枝红梅越发腥红,那是一种怎样的白呀,白得让她心都碎了。梅惠珍一直用手摸索着长长的流苏。她从来都不敢梦想能拥有这样美丽的东西,现在确确实实是属于她的了。把纱巾轻轻环在两臂,梅惠珍觉得就好像在父亲的花园里散步。
小张吞吞吐吐地说:“这是我妈压箱底的,她说给儿媳妇。”梅惠珍低头不语。小张顿了顿,说:“小梅,让我们组成革命家庭吧。”梅惠珍没有想到自己听到这句话会如此平静,她想,这或许就是外国小说里的浪漫求婚吧。这
一时刻,梅惠珍似乎等了一辈子。她抬头紧紧盯着月亮,半弯的月亮泛着柠檬色的光,有点朦胧,好像也有点害羞。
小张拉住了她的手。这是她第一次被异性握着手。梅惠珍一直没有说话,她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两人就一直握着手,直到听到吹灯号响起。
那一晚,她看着窗口的月亮想了很多,这种农民式的生活好像永远出不了头,自己难道要在农场种一辈子地吗?梅惠珍把白丝巾还给了小张,从此,小张再也不找她散步了,黄昏的时候,小张就在他宿舍里吹《抬头看到北斗星》。梅惠珍给在乌鲁木齐的同学写了一封信,让同学帮忙找个对象。秋天,搭上送甜菜的车,梅惠珍到乌鲁木齐去相亲了。远远地,小张站在路边,车子开动走远了,他还站着。
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个开大车的司机。梅惠珍终于可以离开土地了。塔里木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在她的一生中,只有那时的生活是彩色的,天空是蓝色的,没有了童年的阴郁,也不像现在灰蒙蒙的。梅惠珍想起那条白丝巾,它比月光还要温柔,比梦还要美丽。
1960年代兵团农场
准儿媳小李晚上来家吃饭,王惠忙了大半天。一家四口人其乐融融地吃晚饭。饭间小李说起,有同学托她找一个当年的上海支青,和王惠一样大,也是1964年来的。当听到要找的那个女人的母亲姓白,父亲姓梅,三岁时送了人,王惠一下明白是找自己的。正康口快,对着王惠大叫起来:“太巧了,要找的这个人不会就是你吧?”
1964年,十六岁的王惠初中毕业了,没有什么出路,养母就让她支边,有个工作。她模糊记得自己的生母是个美丽又会发嗲的女人,穿着月白底有暗金花的旗袍。生母把她送给了家里的娘姨(上海话指老妈子)后又嫁人了,娘姨带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从此她就管娘姨叫妈。娘姨没有孩子,男人也死了,她们两个就相依为命。养母比生母对自己还要好,王惠从小对她就很依恋,突然让她离开养母到新疆去,她不愿意,哭了好几次。可养母狠了心就让她走。养母抱着她哭:“人家都知道你是资本家的女儿,你抬不起头做人的呀,到新疆去重新做人吧。”在离开上海之前,养母把她带到城里和生母见了面。生母又生了孩子也当了继母。见到她们,生母大吃一惊,而且明显地不高兴,不停地说:“怎么找到这里来了?”生母把她们带到小吃店里一人要了一碗大馄饨。生母还是那样白净,穿着蓝色的春秋装,短发用小黑卡别在耳后,很利索的样子,只是明显老了。王惠发现自己长得很像生母。生母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从此在王惠的生活中,这个人就消失了。
王惠在农场种了许多年的啤酒花,当然也打土块、割麦子,她还学会了开康拜因。到底是苦孩子出身,繁重的体力劳动对她来说还受得了。一个月她有三十二元的工资,但王惠很节省,她一直穿着打了好多层补丁的衣服,她把钱存起来,过一段时间就给上海乡下的养母寄回去。
正康是从乌鲁木齐来的学生,他在相邻的公社接受再教育。正康的父母是领导干部,他人长得又魁梧,是很多姑娘心中的理想对象。王惠是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别人都成了家,可她还小呢。因为小,王惠受到大家的宠爱,成了家的人经常请她到家里吃饭。在这里,没有人提起她的出身,人们都知道她省下钱是寄给养母的,都夸她是个孝顺的女儿。
1971年秋天收完了啤酒花,正康不顾母亲的反对和王惠结了婚。结婚两个月后,正康
的母亲就把他调回了乌市一所学校管广播。正康很高兴,说很快就会把她也调到乌鲁木齐,结果这一等就是十年。
“文革”结束不久,正康以夫妻分居的名义把她调到了东风商店站柜台。正康的母亲和媳妇处理不好关系,和自己的婆婆也相处不好。正康的奶奶近八十岁了,正康的母亲还总是和她吵。于是,正康就和王惠商量把奶奶接来一起住。王惠腾了一间房子,奶奶在正康这里住得舒服,九十六岁那年在正康家里寿终了。
王惠从来也没有怨恨过婆婆,她觉得所有的一切与正康对她的好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如何,她养育了正康,把这么好的一个正康给了她,自己怎么能恨她呢。
2004年夏乌鲁木齐
小李帮着约好了见面。
梅惠珍提前到了,坐在蛋糕店里慢慢吸着一杯雪碧。她在努力酝酿着自己的情感,让自己放松,千万要压下心中的怨恨,但不觉又想到了“白骨精”的白旗袍。
正康来到蛋糕店,看到一个胖胖的老女人坐在那里愣神。梅惠珍对此行越来越有把握,没有与“白骨精”的女儿直接见面,让她觉得很放松。天下没有不爱钱的人,凭空白送给一大笔钱,搁谁谁都会乐死。
没想到,正康却答复:“王惠说她不认识姓梅的。姓梅的东西她也不会要的。”梅惠珍急了:“你让阿妹要拎拎清,这可是一大笔钱。”“我们虽然没钱,但也不会白拿人家的钱。”正康坚持道。梅惠珍没办法了,她觉得自己太轻敌了。看来,王惠和她那“白骨精”老娘一样,不好对付。梅惠珍第二次又约了王惠出来,王惠依然不来。于是,梅惠珍决定上门亲自会会这个妹妹。
一进门,发现两人居然见过,梅惠珍大喜。她热情地拉着王惠的手大叫:“有缘分,有缘分,都在一个城里,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你们也不来找我。”王惠上次就知道这个老乡看不起人,现在知道她是梅家的人,心里更厌恶,但是进了家门都是客,就客气地让茶让座。话不投机,气氛很快就淡了下来。王惠留她吃饭,梅惠珍不客气地说:“好,我今天就尝尝我妹妹的手艺。”
这顿饭吃得梅惠珍舒服极了。正康和王惠对她还是很客气的,小志一口一个姨姨地叫,梅惠珍听起来很顺耳。
梅惠珍喝了些酒,有些飘飘然,觉得脚下轻得好像走不稳,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了公共汽车。坐在车上,梅惠珍想:自己现在居然要向仇人低三下四,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这个王惠为什么总是好命,小的时候比她强,如今坐在家里享福,人家的老头子不知道要比自己的强多少倍。更让她生气的是,人家的老头子是那么体贴,那么会心疼人,自己这辈子真是投错了胎。想着想着,不觉悲从中来,大哭了起来,哭声空洞而嘶哑,在车厢里飘浮,车上的人很奇怪地看她,有人说:“神经病!”
梅惠珍一进门,全家人都在等她。问完她情况,家里人都埋怨她没有用,这样的事都搞不定。大儿媳自告奋勇去做小李的工作:“就算老的不爱钱,小的总会爱钱,再说结婚是要花钱的。”大儿子说:“咱们能不能和上海的舅舅商量一下,不要钱还非得求着给,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不给不行吗?咱们还能多分一些。”小儿子手脚快,马上就把电话打通了。梅惠珍跟二哥一五一十都讲清楚了,然后就问下面应该怎么办?二哥想了想说:“你就让她写个声明,说是自动放弃继承权。不要就不要,真好像求她似的。就怕老大再想花头。”
大家又讨论了一会儿,儿子儿媳说了一大堆话,老头子却一直不吭声。突然老头子开口了,他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你妹子。”第二天,梅惠珍夫妻两个买了两包水果和几大包麦片,手里拎得满满的到王惠家去了。老头子买东西很大方,掏钱掏得梅惠珍心疼,两件皮背心算是白卖了。老头子还带了笔和纸,路上叮嘱她说:“待会儿你别让她写放弃继承权,就写委托让你处理,记住没有?有好处也是咱的,不能便宜了你哥哥。”
一进门,老头子就妹子长妹夫短的。王惠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来了,沏茶让座后就看着他们,正康陪着东拉西扯地聊。说到了正题,王惠说:“梅家的事我管不着,你别跟我说。”梅惠珍两口子不停地劝过来劝过去,最后,正康说:“让她再考虑考虑,完了我们给你们回话。”还是老头子会讲话:“打虎不离亲兄弟,你们是亲姐妹,有啥好说的,我是个粗人不会讲啥道理,反正你姐不会害你。你们是好人,不贪钱,反正你们也不要钱,就让你姐去处理吧。”王惠觉得也有道理,就写出了委托书。回来的路上,老头子得意洋洋,梅惠珍心里也挺高兴的,路过超市,破例买了不少东西。
2004年秋上海
梅惠珍立马就给上海打了电话。二哥挺高兴,说让她到上海过中秋,大家跟老大摊牌。
上车的时候,一家人浩浩荡荡来送她,大儿媳还买了饮料和烤鸡。梅惠珍想:拿到这笔钱,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起来,起码儿子儿媳看在钱的份上也会孝敬她。天下哪有不爱钱的人?有了钱,自己的下半辈子算是不用愁了。幸福的火车在梅惠珍的幸福憧憬中向大上海奔去。
上海之行纯属一场闹剧,大哥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他说他是开玩笑的。一番斗争,梅惠珍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她只想着能歇歇,可事态的发展并不能让她喘口气——迁户口手续繁杂,二哥和三哥抢着让她要把户口落在自己家。
出来久了,她倒牵挂起新疆来了,想吃盘拉条子。自己想想都可笑,刚到新疆的时候,总想着能回到上海,吃不上大米还哭呢,这回又想吃拉条子。四十年后,自己倒成了上海的新疆人,连邻居山东人都叫她新疆人了,真是世事莫测啊……梅惠珍坐在藤椅上乘风凉,这个从小住惯的弄堂越来越拥挤,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但那种杂乱与潮湿,弄堂上空杆子上飘着的“万国旗”还是与五十年前一样。再过一个月,这里就要拆了,梅惠珍不免伤感起来。晚上坐在弄堂口,月亮还是从东边的檐顶上升起,大半个脸侧着,朗朗的清辉让闷热的空气都清凉起来,空气中飘来茉莉的花香,梅惠珍下意识地看了看王小姐的窗口。那里现在堆着山东小夫妻蒸包子的家什。
吃过饭,二哥拿出一万元钱,说是给梅惠珍的搬迁费。梅惠珍急了,一个户口九万元,她和儿子两个人应该有十八万元才对,还有每个月一千元的过渡费呢。二哥说:“小妹,你不懂政策,你是有户口无房,而且也没有单独立户口,所以没有过渡费,搬迁费是以后折在房价里的。”二哥又说:“老母亲最后是你两个嫂子侍候送了终的,你从来也没给过老母亲生活费,我们就不计较了,但上次父母合葬,你钱也没出,都是我们替你垫的。再说,你的儿子在我这里也养了好几年。你嫂子说你在新疆不容易,给你一万元补贴补贴生活,回去的车票也由我来买,来的车费我让老三给你。”梅惠珍的脑袋嗡得就大了,她想反驳,可一肚子的话憋在嘴边出不来了,憋得她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她的心嘭嘭乱跳,眼前一花,就听不清他们在
说什么了。
醒来的时候,梅惠珍是在医院里,她的高血压犯了。
2004年深秋乌鲁木齐
在火车上,梅惠珍心里堵得很。拿到了钱她并没有原先预期的兴奋。不过梅家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自己也是明白的,有钱总比没有钱好。梅惠珍不时就会按按藏在短裤里的钱。身上有钱,她也不敢睡觉,稍微眯一会儿,就惊醒了。
全家人都到火车站来接她。她告诉大家:“没分到钱。”家人的情绪一下就低落了下来。路上大儿媳说:“不会吧?”梅惠珍说都是因为合葬没有回去,也从没有给老母亲生活费。老头子当即破口大骂:“上海人比泥鳅还精。”小儿子马上给上海那边打电话证实这事。放下电话,儿子说:“舅舅说有一万元。”梅惠珍急了,说那一万元是给王惠的。儿子们吵着要把钱分了,老头子不让分,说那一点儿钱他们还要留着养老。老的少的为一万元吵得热火朝天,看着他们吵,梅惠珍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快意,有一种报复后的成就感。儿子们把钱抢走了,分完钱他们就不来家了,老头子从此也不出去了,成天哀声叹气的,骂梅惠珍,骂上海人,骂儿子们。一个星期她都故意在唠叨:“当年要是你们让我寄一点儿生活费,我也好有理由讲得出口。”梅惠珍让老头子跟她一起到王惠家去。“把事情总要跟人家讲清楚吧,要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拿了多少钱,占了天大的便宜。”这回老头子是死活不肯去了,梅惠珍明知他肯定不会去,但她就是想看看他那个样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出出一辈子受的恶气。
梅惠珍这回还挺想跟王惠一家说说这件事的,她心里恨得不行了,可却没有机会讲出来。话是早就想好了的,梅惠珍坐在王惠家的客厅里,不停地诉说,连细节都没有漏掉。王惠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听着。梅惠珍讲着讲着又生起气来:“这还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你说人都成什么样子了,为了点钱,连脸都不要了。”王惠两口子一直静静地听她说,劝她:“算了,阿姐,钱算个什么,你没听人家说情意无价,一个家人平平安安地活着就比什么都好。”梅惠珍一怔,说:“忙活了半天,也没有给你搞来一分钱。”正康说:“不能这样说,这不还多了一门亲戚呢。”王惠说:“就是呀,你不要想那么多,阿姐。”梅惠珍心头一热,泪水漫上眼睛。
2005年春节乌鲁木齐
元旦过了,很快就是春节。洗洗煮煮,忙了一天的王惠帮着正康剔羊肉。这是小志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两口子准备请亲家来做客,所以早早就准备上了。
大年初一,亲家来做客。突然电话响起,王惠接起来,是梅惠珍的老头子打来的。“你姐疯了,要跳楼,我管不了了,你们娘家人来看看吧。”
正康和王惠立即搭车赶到梅家。梅惠珍已经被绑起来了,凌乱花白的头发散贴在脸上,看起来又苍老了许多。
王惠给她解开绳子。“我没有跳楼,我就是想去给小孙子送毛衣。”梅惠珍拿起沙发上的一套小毛衣递过来。“孙子都满月了,他们不让我见,说我有精神病。阿妹,我真的没有呀。”
那是用六七种杂色毛线拼凑起来的婴儿毛衣,扣子是用口服液的盖子改制的,一条裤腿比另一条宽大许多,袖子也不一样长。“阿妹,你帮我送去吧。当奶奶的总要给小孙子送见面礼,你看,我织得多密实。”梅惠珍举起毛衣,拉过王惠的手让她摸,“我天天织到半夜呀,拆了织,织了拆。”梅惠珍细细地摸着,一脸
幸福。
“阿姐,我送你去老年公寓吧。”
“我不去,这是我的房子,我才不走呢,死也要死在这里。”
正月十五在鞭炮声中热热闹闹地来到了。王惠这几天心里一直惦记着梅惠珍,早上一起来,她赶快打了电话问候,梅惠珍说自己好着呢,但王惠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她对正康说,明天去想看看梅惠珍。
过了正月十五,年算是过完了。一年的鞭炮似乎都要在这一夜炸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味道。王惠一家去广场看完焰火,小志也和邻居们比着放了一气鞭炮。烟花又一次缀满了天空,此起彼伏的噼啪声掩盖了世间的一切声音。突然,一切喧嚣与绚烂一下子都结束了,安静得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星星点点的细小如米粒的雪花无声地在白月光中轻舞飞扬,月光寂寞地穿过夜空,在雪地上留下孤独的身影,洁白如银,真实而纯粹。王惠睡不着,倚在窗口想心事。月光如河,天空遥远,心事也如河水静静流淌,被风吹乱的一生,此时仿佛都回归到月光之河中。窗上凝结了霜花,那些泛黄的往事在她的心中飘散。夜未央,香飘冷月到帘栊。打开窗子,硫磺味道散尽,清新中隐约有一丝花香的甜味。
第二天,王惠起晚了。飘了一夜的雪,越来越大了。两口子坐公交车去看梅惠珍。楼前围着一些人,一个老头在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楼前的雪地上有一滩暗红的血迹,相比起一地的鞭炮碎红分外显眼。
王惠的心一紧,拉住那个老头问。老头说,他一大早起来看到地上趴着一个人,开始以为是谁喝醉了,出来一看是顶楼张家的老婆子,人早就断气了,敲了半天门她家也没人开,只好打了120,把人拉走了。
大片的雪花扑在脸上,冰凉凉的。王惠和正康谁也没有说话,呆站了好一会儿。新雪渐渐厚起来,盖住了一地的碎红和那滩暗红。
街上人们或快或慢地走着,一个个小店比着吵架似地叫卖。远近有鞭炮零星响起,没赶在十五放完的鞭炮,这会儿赶快偷偷摸摸地放掉。
在一片嘈杂中,王惠听到一个纯净的声音在唱:“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这歌一下刺进了她的心里,两行泪唰地涌了出来,流在脸上分外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