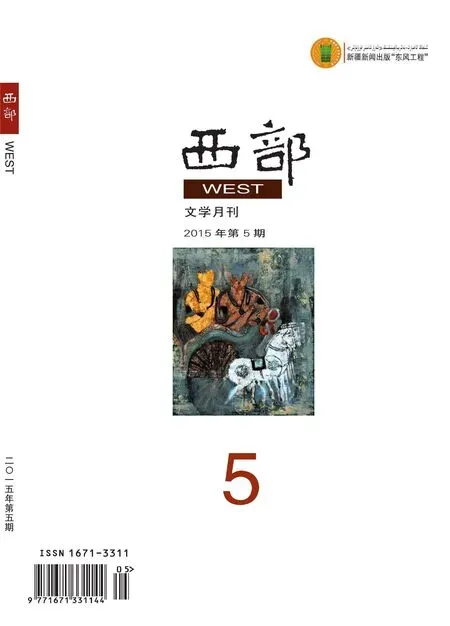亲属
2015-11-18以色列阿摩司奥兹钟志清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亲属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1
村庄笼罩在二月傍晚那提早降临的黑暗中。苍白街灯映照下的公交汽车站,只有吉莉·施提纳一人。村委会办公室门窗紧闭,附近房屋的百叶窗里传来电视机播放的节目的声音。一只流浪猫轻轻抬起毛茸茸的脚掌走过垃圾箱,它竖起尾巴,肚子圆鼓鼓的。它慢慢地穿过公路,消失在柏树影里。
特拉维夫开来的公共汽车每晚七点钟抵达特里宜兰。吉莉·施提纳博士差二十分七点就来到村委会前。她在村里的医疗基金诊所做家庭医生。她在等姐姐的儿子、她的外甥吉戴恩·盖特,他在服兵役。他在装甲部队培训学校接受培训时发现一个肾有问题,需住院治疗。现在他已经出院,他母亲送他到她乡下的妹妹这里休养几天。
施提纳博士是个瘦削、干瘪、形销骨立的女子,头发短灰,相貌平平,戴着副方形无框眼镜。她充满活力,但看上去比她四十五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她在特里宜兰被视为出色的诊断医师,几乎没出过诊断错误,然而大家说她态度冷漠,生硬粗暴,对病人缺乏同情心,只是个专注的听众。她从未结过婚,但她那个年龄段的人记得她年轻时曾恋上一位已婚男子,他死于黎巴嫩战争。
她独自一人坐在公交汽车站的长凳上,等候她的外甥,时不时费劲儿地看看手表。在黯淡的街灯下,看不清表针,她不知道还要等上多久公共汽车才能来。她希望车不要晚点,吉戴恩会上车。吉戴恩是个心不在焉的小伙子,完全可能上错车。现在他大病初愈,定会比原来更为心不在焉。
与此同时,施提纳博士猛吸着这个干冷冬日的晚间凉气。犬吠声声,村委会办公室的屋顶上悬着一盘即将盈满的圆月,为街道、柏树和树篱洒上一层骷髅光,光秃秃的树梢一片迷蒙。吉莉·施提纳近年来注册了由达丽娅·列文在特拉宜兰村文化厅开设的两门课,但在那些课上没有学到想要的东西。她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许外甥的到访可以帮她找到某种情趣。两人会单独相处几天,坐在电热器旁,她会照顾他,就像他小时候她所做的那样。也许他们可以进行一场谈话,也许她可以帮这个小伙子恢复体力,这么多年她一直疼爱他,将他视如己出。她往冰箱里放满了好吃的,并在自己卧室的隔壁——一直是他的房间里为他铺好床铺,还在床尾铺了一条毛毯。她在床头桌上放了一些报刊杂志,还放了三四本她喜欢并期望吉戴恩也喜欢的书籍。她还打开了热水器,为他备好洗澡水。客厅里光线柔和,电暖器开着,桌上放着水果和干果果盘,这样吉戴恩一进门就会感受到家的温暖。
七点过十分,从奠基者街方向传来公共汽车声。斯提纳博士起身站到了车站前,她精瘦结实,神情坚定,瘦削的肩膀上披了件黑毛衣,脖子上围了条黑色的毛围巾。先是从后车门下来两位上年纪的妇女,吉莉·斯提纳跟她们有些面熟。她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予以回应。阿里耶·蔡特尼克从汽车前门慢慢走下来,他身穿一件对他来说有些过大的军事作战服,头上的帽子遮住了前额和眼睛。他向吉莉·斯提纳道过晚安,开玩笑地询问她是不是在专门等他。吉莉说她正在等在部队服役的外甥,可是阿里耶·蔡特尼克并没有在车上看到任何军人。吉莉·斯提纳说她在等穿便装的军人。说话的功夫,另有三四位乘客从车上下来,吉戴恩没在其中。汽车快要空了,吉莉问司机米尔金是否看见在特拉维夫上车的人当中有一个又高又瘦、戴眼镜的小伙子,他是正在休假的军人,容貌相当英俊,但有点心不在焉,也许身体不大好。司机米尔金不记得有这么一位乘客,可他半开玩笑似地说,别担心,斯提纳博士,谁今天晚上没到,明天早上肯定到,谁明天早上没到,明天中午肯定到,大家迟早都会到的。
最后一位乘客亚伯拉罕·列文下车时,吉莉·斯提纳问他大巴上是否有个小伙子可能下错了车。亚伯拉罕说,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没有注意。我在想心事。
他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一路上经过了许多站,许多人上上下下的。
司机米尔金主动提出让斯提纳搭车回家。大巴每天夜里就停在米尔金家门外,早晨七点钟开往特拉维夫。吉莉谢了他,说愿意走回家,她喜欢冬天的空气,现在既然知道外甥没来,她就没理由急着往回赶了。
米尔金道过晚安,关上车门,排放出一股气流,开车回家了。吉莉·斯提纳转念一想,很可能吉戴恩坐在大巴后座上睡着了,没有人留意,既然米尔金把大巴停在了他家门前,关掉了车灯,锁上了车门,吉戴恩就会被囚禁到第二天。于是她朝奠基者街掉转身去,精力充沛地在大巴后面阔步前进,要抄近路穿过笼罩在黑暗中且洒上苍白月色银辉的纪念园。
2
吉莉·斯提纳走了二三十步,心生他念,实际上,她应该直接回家给司机米尔金打电话,让他出去查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大巴后座上睡着了。她还可给姐姐打电话,弄清楚吉戴恩是否真的出发来特里宜兰了,是不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旅行,但转念一想,为何让姐姐没有必要地担心呢?她一个人担心就已经足够了。要是孩子真的提前下错了车,他一定会想办法从某个小村子里给她打电话的。这是直接回家、不一路追到米尔金家的又一个原因。她可以告诉吉戴恩,不管在哪里都要乘坐出租车,要是他钱不够,她当然会付的。她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再过半个来小时小伙子就会乘坐出租车到她家的情形:他像平时一样腼腆地微笑着,柔声柔气地道歉,说自己稀里糊涂,她会像吉戴恩小时候那样抓住他的手,安慰他,原谅他,把他带进家门,洗澡,吃她为两人准备好的晚饭,晚饭有烤鱼和烤土豆。他洗完澡后,她会迅速地查看一下他的诊断报告,她已经要求吉戴恩把诊断报告带过来了。她只相信自己的诊断,有时甚至连自己也不相信,不完全相信。
尽管斯提纳博士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接回家,可是她继续迈着坚定的小步走上通往村文化厅的奠基者街,抄近路穿过纪念公园。潮湿的空气让她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她摘下眼镜,用围巾擦了擦,又将眼镜推回到鼻梁上。不戴眼镜的她,模样立刻显得不呆板不干巴了,而是显得有些柔和、有些生气,就像一个小姑娘遭到了不公正的责骂。但是在纪念公园里,没人能看见她。我们只是通过无框圆形眼镜里的寒光来了解斯提纳博士的。
纪念公园伫立在那里,安详、静谧而空旷。草坪和一簇簇九重葛之外,是一片松林构成的浓密黝黑的板块。吉莉·斯提纳深深地吸了口气,加快了步伐。她的鞋子吱吱嘎嘎地踩在石子路上,好像踩到了某种发出短促尖叫声的小动物。吉戴恩四五岁时,他的母亲带他来和刚开始在特里宜兰做家庭医生的姨妈住在一起。他是一个昏昏欲睡、耽于梦幻的孩子,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一个人玩游戏。他玩三四种简单的东西,一只杯子,一个烟灰缸,一副鞋带。有时他会身穿邋里邋遢的短衫坐在屋前台阶上,冲着天空发呆,只有两片嘴唇在翕动,似乎讲述着故事。吉莉姨妈不喜欢让孩子沉浸在孤独中,想方设法给他找玩伴,可邻居家的孩子觉得他很无趣,一刻钟后他又一个人待在那里了。他没有尝试着和他们交朋友,只是坐在长廊的扶手椅里发呆,不然就是把钉子排成一排。她给他买来一些游戏和玩具,可是孩子玩不了多久,就回到平日的消遣之中:两只杯子,一个烟灰缸,一个花瓶,几个回形针和汤匙,他按照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某种逻辑在毯子上排列这些东西,接着将其打乱,又重新组合,他的嘴唇一直动着,似乎在给自己讲故事,这些故事他从未和姨妈分享过。夜晚,他手里攥着一只褪色的小玩具袋鼠入睡。
有那么几次,她为了不使孩子孤单,建议到村边田野散步,到维克多·爱兹拉的小店买些糖果,爬一爬由三条水泥柱支撑着的水塔,但他只是耸耸肩膀,好像对她突然莫名其妙的举动感到诧异。
还有一次,那时吉戴恩只有五六岁,他母亲带他来和姨妈小住,姨妈那几天休假。可是吉莉接了一个急诊,要到村外给人看病,孩子坚持一个人留在家里,在毯子上玩牙刷、头刷和一些空火柴盒。她不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坚持说他要么和她一起去,要么留在诊所让接待员吉拉照顾,可是他固执己见:要留在家里。他不怕一个人待着,他的袋鼠会照顾他,他保证不给生人开门。吉莉·斯提纳突然勃然大怒,不光是因孩子固执地坚持要一个人在毯子上玩游戏发火,而且也因他一贯的奇怪举动、他懒散的样子、他的袋鼠,以及他与世界的脱节生气。她大声叫嚷,你现在就跟我走,就这么着了。吉莉姨妈,我不。孩子说,声音耐心而轻柔,好像奇怪她怎么领会得这么慢。她伸出手,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之后,令她吃惊的是,她继续用双手打他的头、他的肩膀、他的后背,气急败坏,就像在和仇敌打仗,或者是教训一头桀骜不驯的骡子。吉戴恩在一阵暴打面前,一声不吭地蜷缩身子,脑袋缩进肩膀,等候结束袭击。接着他睁大眼睛抬头看着她问,你为什么恨我呢?她惊愕不已,含泪拥抱他,亲吻他的脑袋,允许他独自和他的袋鼠待在家里,她过不了一个小时就会回来,她请他原谅。孩子说没事儿,人有时候是会发火。可是他从此倍加沉默,一言不发,直到母亲两天后来接他。他和吉莉谁都没说他们争吵的事。他走之前,从毯子上捡起橡皮筋、书本、盐瓶、医用棉垫,将它们放回原处,把袋鼠放回抽屉。吉莉弯腰亲热地亲吻他的双颊。他闭紧双唇,礼貌地亲了亲她的肩膀。
3
她走得更快了,每迈一步都坚信吉戴恩确实在后排座位上睡着了,如今被锁在了停在米尔金家前过夜的黑黢黢的大巴里。她想象,他在寒冷和突如其来的沉默中醒来,试图从大巴里出来,推着闭紧的车门,使劲儿捶打后边的窗户。他也许像平时一样忘带手机了,就像她离开家前去公交车站等他时忘记带手机一样。
霏霏细雨开始洒落,几乎让人察觉不到,轻风不再吹拂。她穿过黑黝黝的一簇簇松树,来到纪念公园橄榄街口的黯淡街灯下。一个打翻的垃圾箱绊了她一下,她小心翼翼地躲开垃圾箱,轻快地走上橄榄街。百叶窗紧闭的房屋笼罩在迷蒙的雾霭之中,精心照管过的一座座庭院似乎在冬寒中沉睡,四周环绕着女贞、香桃木或金钟柏树篱。零零星星可见建在老屋废墟上的豪华新别墅探出街头,为爬行植物所掩映。最近几年,城里的富人们到特里宜兰购买老式的单层住宅,将其夷为平地,在上面建起镶有飞檐与凉棚的大别墅。吉莉·斯提纳暗自思忖,很快特里宜兰就不再是村庄,而是会变成有钱人的度假胜地。她将来要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外甥吉戴恩,已经就此立好了遗嘱。她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吉戴恩了,身上裹着温暖的外套,不安定地睡在停在米尔金家门前、上了锁的大巴后座上。
拐过犹太会堂广场时,微风吹来,她冻得瑟瑟发抖。细雨已经停了。一只空塑料袋在微风的吹拂下翻滚着,吹过她的肩膀,犹如苍白的幽灵。吉莉·斯提纳加快了脚步,从垂柳街走向墓园街,大巴司机米尔金的家就在街那头,老师拉海尔·弗朗科和她年迈的父亲佩萨赫·凯德姆就住在他家对面。吉戴恩大约十二岁那年,有一次突然一个人出现在特里宜兰姨妈家里,因为他和母亲吵了一架,决定离家出走。他考试不及格,他母亲就把他锁在家中,他从她的钱包里拿了些钱,从阳台上逃出,来到了特里宜兰。他随身带了个小包,里面装着袜子、内裤和一两件干净的衬衣,他请求吉莉让他进屋。吉莉拥抱了他,给他弄了些午饭,拿给他小时候玩的那个磨损了的袋鼠,而后给他母亲打电话,尽管姐妹俩关系不好。第二天,吉戴恩的母亲赶来接孩子,没和妹妹说一句话,吉戴恩服服帖帖,伤心地和吉莉道别,一声不吭地拖着脚步,一只手被紧紧握在盛怒的母亲的手里。还有一次,大约三年前,吉戴恩约摸十七岁,他来姨妈这里小住,为的是在乡村的宁静与孤独中一门心思准备生物考试。她本来想帮他准备考试,可他们却像一对同谋者,没完没了地玩跳棋游戏,多数情况下是她赢。她从来不允许他战胜她。每次输了棋,他都懒洋洋地说,我们再下一盘吧。他们每天晚上并肩坐在沙发上,膝盖上盖着毯子,看电视里播放的影片,很晚才睡。早晨,吉莉·斯提纳到诊所上班,在厨房餐桌上给他放一些面包片、沙拉、奶酪和两个煮鸡蛋。回到家时,她发现他和衣睡在沙发上。他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他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午饭后,他没有准备考试,他们又一起下跳棋,一盘接一盘,几乎一句话也不说。晚上,尽管开着电热器,他们还是盖着毯子并肩坐在沙发上看英国喜剧片,二人一起放声大笑。孩子回家了,尽管他几乎没有复习功课,但两天后设法通过了生物考试。吉莉·斯提纳给姐姐打电话,骗姐姐说她帮他做了复习考试,他准备得很充分,他很用功。吉戴恩给姨妈寄送了一本耶胡达·阿米亥的诗集,在扉页上感谢姨妈帮助自己准备生物考试。她回赠他一张从水塔顶上鸟瞰特里宜兰全景的彩图名信片。她感谢他赠书,并说要是他愿意再来和她一起学习,比如说再有别的考试,不要羞于开口,他的房间永远为他留着。
4
司机米尔金,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屁股鳏夫,已经换上了家居服,身穿一条宽大的运动服裤子和一件为某家公司做广告的T恤。斯提纳博士突然来敲他的家门,问他能否出来和她检查一下是否有位乘客睡在他大巴的后排座位上,让他十分吃惊。
米尔金是个块头宽大、行动笨重的男子,他喜兴,待人亲切。他咧开嘴巴乐呵呵的,露出参差不齐的大门牙,舌头有些凸出耷拉到了下嘴唇。他猜想斯提纳博士的外甥一定在沿路的某个车站上下错了车,现在正搭车往特里宜兰赶呢。在他看来,斯提纳博士应该回家等候她的外甥。然而,他同意拿上手电跟她去确认一下没有乘客被困在停在那里的大巴上。
他肯定没在那里,斯提纳博士,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去查查看。干吗不呢。
你不记得一个又高又瘦戴眼镜的年轻人,一个有点心不在焉但非常有礼貌的年轻人吗?
我看见几个年轻小伙子上了车。我记得有个爱说爱笑的人,背着大背包,还带着一把吉他。
他们都没有到特里宜兰来吗?大家都在中途下了车?
对不起,博士,我不记得了。也许你有什么灵丹妙药增强我的记忆力?我最近什么都忘,钥匙、人名、日期、钱包、文件,要是这样下去,我会把自己是谁也给忘了。
他按动台阶下面一个秘密按钮,打开大巴,费劲儿爬上车,检查每一排座位,手电筒来回晃动搅起舞动的阴影。吉莉·斯提纳跟着他上了车,他沿过道往前走,斯提纳差点撞着他那宽大的后背。当他来到后排座位时,低声惊叫了一声,他弯下腰捡起软绵绵的包裹,展开一看是件大衣。
这也许是你客人的大衣?
我不确定,也许是吧,看着像。
司机用手电筒照照大衣,接着又照了照医生的脸:她一头灰色的短发,她的方眼镜,她坚定的薄嘴唇,说年轻人可能已经上了车,下错了站,把大衣忘在车上了。
吉莉双手抚摸着大衣,闻了闻,接着又让司机再用手电筒照照大衣。
像是他的大衣,我这么想,但不确定。
拿着,司机慷慨地说,拿到家里去。要是明天有另一位乘客来找大衣,我毕竟知道你住在哪里。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吗,斯提纳博士?很快还会再下雨。
吉莉谢谢他,说不需要,她走回家去,她已经在他休息时麻烦他许久了。她走下车,司机跟在她的身后,用手电筒给她照路。她一边下车,一边穿上大衣,完全确定那是吉戴恩的大衣。她从去年冬天就记住了那件大衣,一件短款棕色皮衣。她高高兴兴地穿上皮衣,立刻,她感受到大衣保留着小伙子的气味,不是他现在的气味,而是他小时候的气味,淡淡的杏仁香皂和粥的气味。大衣摸上去柔软舒服,只是对她来说有些大。
她再次感谢米尔金,他再次说开车送她回家,但她说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她转身离去。即将盈满的月亮再次钻出云层,给附近墓园的柏树梢披上苍白的银辉。村庄一片沉寂,只听得水塔那边传来奶牛的低吟,远方的狗报以回应,那长长的阴暗吠叫化作了长嚎。
5
但也许这根本不是吉戴恩的大衣,他很可能取消了旅行,忘记告诉她了。也许他的病情加重,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医院。她从姐姐那里得知,他在装甲部队培训学校受训期间,一个肾出现感染,在医院的肾病学科住了十天院。她想去医院看他,可是姐姐不让。长期以来姐妹二人关系不好。由于不知道外甥的病情,她十分焦急,因此在电话里让他带来他的病程记录给她看看。在做诊断时,她一概不信任别的医生。
也许他没有生病,而是上错了车,睡着了,等车开到了终点站、某个陌生的小村庄时才在黑暗中醒来,现正不知究竟如何去往特里宜兰。她必须赶快回家。如果此时他正设法给她打电话该怎么办?也许他已经设法来到这里,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她。他八岁时,有一次母亲在寒假期间带他到姨妈家。尽管姐妹长期不和,但姐姐还是会带他来和姨妈住。第一天夜里他做了个噩梦。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推开姨妈的房门,爬到姨妈床上,睁大眼睛,身子因害怕而发抖:他的房间有个恶魔,恶魔咯咯笑着,冲他伸出十只长长的手臂,手上还戴着黑手套。她抚摸他的脑袋,把他贴在自己单薄的胸前,可是孩子不接受安慰,继续发出阵发性的狂叫。吉莉·斯提纳决定祛除造成他恐惧的原因,使劲儿地把一声不吭、吓得呆若木鸡的他拽回他的卧室。孩子边踢打边挣扎,但她并不灰心,紧紧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进房间。她打开电灯,告诉他,造成他害怕的根源只是一根上面挂了几件衬衣和一件毛衣的衣架。孩子不相信她,挣扎着要脱身,他捶打她,她抽了他两个嘴巴,一边一个,让他不要歇斯底里。她立刻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把他抱在怀里,将他的脸颊贴在自己脸上,接着让他带着那磨损了的袋鼠和她睡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他似乎在想什么,可他没有提出回家。吉莉跟他说,他妈妈过两天就来接他了,夜里他可以和姨妈一起睡。吉戴恩对噩梦只字未提。当天夜里,他坚持睡在自己房间,只是让她不要关他的房门,别关掉过道里的灯。凌晨两点,他又爬到姨妈床上,浑身颤抖,躺在她的怀里。她躺在那里,再没有睡着,呼吸着她头天晚上为他洗头发时用的香波散发出的淡淡气息,她知道,孩子与她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无法言说的、根深蒂固的永久联系,她爱这个孩子,胜于她曾经爱过的世上任何生灵,胜于她会爱的任何人。
6
夜晚,村外看不到一个生灵,只有流浪猫聚集在垃圾箱周围。电视播音员焦虑的声音从关紧的百叶窗里传出。远处有只狗汪汪直叫,似乎奉命要扰乱村子的宁静。吉莉·斯提纳依旧裹在米尔金给她的那件大衣里,急急忙忙地轻快地走过犹太会堂广场,又沿着橄榄街前行,毫不迟疑地抄近路穿过纪念公园那黑沉沉的松林。黑暗中一只夜鸟冲她厉声啼叫,池塘里蛙声一片。此时她确信吉戴恩正在黑暗中坐在她上了锁的前门台阶上等她。可那样的话,她现在穿着的大衣又怎么会落在米尔金的大巴上?也许她归根结底穿的是一个陌生人的大衣。她边想边加快了脚步。吉戴恩一定穿着他自己的大衣坐在那里,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当她走出小树林,吃惊地看到一个身影笔直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动不动,领子翘起。她犹豫片刻,突然壮起胆子决定上前探个究竟。只是一根掉落的树枝,斜卧在长椅上。
斯提纳博士回到家时已经快九点了。她打开门厅的灯,关上电热器,急急忙忙检查电话和手机里有没有留言,她把手机忘在了厨房的桌子上。没有留言,不过也许有人曾经打过电话,什么也没说。吉莉拨打吉戴恩的电话,听到留言说电话无人接听。她因此决定放下自尊给特拉维夫的姐姐打电话,搞清楚吉戴恩是不是真的出门上路了,还是决定取消旅行而没有告诉她。电话响个不停,但无人接听,只听见留言机中自动说请在嘀声后留言。她犹豫了一下,决定不留言,因为她想不出该说什么:要是吉戴恩走丢了,现在已经搭车或者坐出租赶往她这里,没必要让他的母亲担惊受怕,要是他决定留在家里,肯定会通知她的。也许他觉得,没有必要今天晚上就给她打电话,明天上午上班时再给她打电话。也许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又住进了医院?也许又发烧了,出现了感染?她立刻决定不顾姐姐的反对明天下班后就去医院看他。她会去医护人员办公室与科室头头谈话。她会要求允许她看看检查结果,形成自己的看法。
吉莉脱下大衣,借着厨房的灯光就近打量。大衣看上去很熟悉,但还是不能确定就是吉戴恩的。颜色基本一样,但领子略有不同。她把大衣摊在桌子上,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共只有两把椅子,仔仔细细地检查。她准备好的晚饭:烤鱼和烤土豆,就放在烤箱里准备加热。她决定继续等待吉戴恩,与此同时,她把电热器开到小档,电热器加热时电阻丝发出零零星星的柔和声响。她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刻钟,而后站起身走进吉戴恩的房间。床已经铺好,床尾铺了一条毯子,床头桌上放着她为他精心挑选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吉莉打开小小的床头灯,把枕头弄得圆鼓鼓的。她立刻感到吉戴恩已经来过这里了,他睡了一晚,起床收拾好床铺离开了,现在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就像他每次来访之后她独自一人留在空落落的房子里。
她弯腰把毯子角塞进床垫。她回厨房切了些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和奶酪,打开开水壶的按钮。水烧开后,她打开放在餐桌上的小收音机。三个声音在争论持续不断的农业危机,粗暴地相互打断对方的见解。她关上收音机看着窗外。房前的小径光线暗淡,悬在空旷街道上方的月亮正漂浮在一块块低矮的云层中。他有女朋友了,她突然想,正是,所以他忘了来,忘了告诉她,他终于有女朋友了,因此就没有理由再来看我了。这一想法使她内心充满了近乎难以忍受的痛苦,仿佛她已经被完全掏空,只有枯萎的空壳依然作痛。他实际上并没有答应她一定要来,他只是说会尽量赶末班车,但要她不必在公交车站等他,因为要是他决定今晚来,自己就会找到她家,要是他今晚不来,近期会来,也许下星期。
纵然如此,吉莉·斯提纳不能摆脱这些想法:吉戴恩迷路了,吉戴恩上错了车,不然就是下错了车,现在也许一个人被困在一个偏僻的场所,冻得瑟瑟发抖,蜷缩在铁栏杆后的铁长椅上,一边是关了门的售票厅,一边是上了锁的报摊。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来到她这里。她有责任马上,这一刻,起身走进黑暗,寻找他,找到他,把他带回家。
大约十点,吉莉·斯提纳暗自思忖,吉戴恩今晚不会来了,她确实没什么可做的,只有把烤箱里的鱼和土豆加热,一个人吃,然后睡觉,明早七点之前起床到诊所照管她那些烦躁不安的病人。她站起身,弯腰从烤箱里拿出鱼和土豆,扔进垃圾桶。接着她关掉电热器,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摘下无框方眼镜,哭了起来,但两三分钟后她止住哭泣,把破损了的袋鼠埋进抽屉,从烘干机里拿出洗净的衣物。快半夜了,她把所有的东西熨好,叠好,放好。半夜时分,她脱衣睡觉。特里宜兰开始下雨,雨整整下了一夜。
栏目责编: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