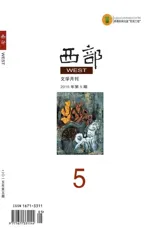“且去填词”:读《纪弦回忆录》
2015-11-18胡亮
胡亮
“且去填词”:读《纪弦回忆录》
胡亮
中国诗人还没有写出过一部伟大的回忆录。换言之,现有诗人回忆录还配不上他们遭遇的苦难。“时间”和“现实”是一对磨盘,足以让勇气和以勇气为前提的信史化为一小把齑粉。是的,有很多次,我们已经看到,诗人们具备了洞察能力,然而可怕的是,他们同时也具备了荒废这种洞察能力的能力。而且,他们愈趋年迈,特别是愈趋成名,对于艺术的苛求反而愈趋放松。此种委顿局面,试比于俄罗斯文学里伟大的回忆录传统,甚或其分支——伟大的遗孀回忆录传统,如何能够望其项背?
考量胡适以来的历史,最有可能写出伟大回忆录的诗人,亦不下数位,纪弦就是其中之一。此翁生于1913年4月27日,殁于2013年7月22日,终得享百岁遐龄。其人祖籍陕西,出生保定,长于扬州,曾流落香港、上海,后出徙台湾,复定居美国,由富贵而饥寒,由流离而安闲,其阅历不可谓不多舛而多艰。如纪弦撰写回忆录,则不唯是一部新诗的通史,亦是一部中国乃至世界的断代史。远在1966年下年,或是1967年上年,纪弦还住在台北龙江街,诗人痖弦就已经当其面提出此类倡议。迟在三十余年之后,亦即1997年5月,纪弦已有八十四岁高寿,方才动笔响应痖弦的倡议,到2000年11月杀青,所获者三卷五十余万言,名之《纪弦回忆录》。2002年1月,该书由台北市文化局出资,并由联合文学出版社付梓。然则,此书亦不得称为伟大回忆录,因为诗人终于没有将对自由的追求与对某种狭隘政治观的坚持区分开来,而个人意识的膨胀则严重影响了他对时人和时代的洞察,至于文风的夸张和自鸣得意,倒还在其次。但是,我们仍然发现,此书确实会在某些方面矫正并满足我们的期待。笔者试图围绕纪弦个人史与新诗史的瘤结般的交错,来展开这篇迟到的文章,并且稍稍瞻顾一下自己的青春: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也许正当洛夫带领的台湾诗人团赴旧金山为纪弦祝贺八十大寿,笔者读到诗人的复沓之诗《你的名字》,为其角度之刁,譬喻之奇,与节奏之美,而发出了难以掩抑的赞叹。
1
纪弦本名路逾,自云乃是汉儒路温舒之后,其父路孝忱却以武功名世。值得一提的是其祖父路岖丕(字山夫,号笑逢,被称为中宪公),性格孤傲狷介,作画作诗以自给,有《苇西草堂诗草》二卷传世。后来的事实证明,纪弦颇得隔代之遗传。
1929年9月,纪弦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只一学期,就于次年转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其间因父丧而留级,后毕业于1933年7月。这次转校让诗人遭遇到美学的保守派。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长颜文朴梁早年留法,即以水彩和图案享誉巴黎,其作品注重光与色,颇有印象主义“点画派”之风,但在总体上仍坚持写实主义。而纪弦却认为,武昌美术专科学校推行的野兽派和后期印象主义才是正途。争论由此而起。纪弦不准备屈服,他甚至这样回忆道:“对于未来、立体、构成、超现实等新兴画派,我也颇感兴趣。”(《纪弦回忆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均见此书)从纪弦1934年所作自画像,可以清楚看到现代风留下的啮痕。
大约就在转校前后,纪弦开始写新诗,其同学校友徐京、王家绳、林家旅亦有同好。纪弦早期笔名“路易士”,即由林家旅的戏称而来。纪弦之弟路迈,则用笔名“路曼士”,亦写作亦翻译。由此亦可见当时西风之盛。当年,纪弦曾集徐京与沈绿蒂之句,得到一首“虚无主义诗”:“管他妈的花谢花开,管他妈的春去秋来,我从女人的裤裆下,看见了一切的政治”,已经显现出重要症候——“调侃”和“相对论”,此二种症候后来可以大体上标明纪弦的美学身份。
然而,我们切不可认为,现代派的旗手纪弦生而为现代派。他本人亦供认,其二十岁前作品深受当时新月派影响,“十之八九为格律诗”。查诗集《摘星的少年》所录“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作品”,尚存四首六行诗,可知事实确乎如此。新月派引英国维多利亚诗歌为圭臬,具有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各种“延异性”,并引导彼时新诗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地质层。一者,部分新月派诗人开始豢养自己的象征主义之兽,比如徐志摩之于波德莱尔,邵洵美之于魏尔伦,而同属新月派的卞之琳甚至成为现代派的先驱者;再者,现代派的其他先驱者也自觉地从“新月派氛围”出逃,在“形式”之外,试图以内心的探秘作为对白话诗的反对和拯救,比如戴望舒,当他开始厌恶《雨巷》的音乐性,事实上就已经转向法国象征主义。对此已有公论,自然不必赘述。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在此前后开始写作的纪弦不但没有摆脱,甚至还服从和证明了新诗史上那个特殊阶段的“延异性”宿命。
据纪弦自述,其早期作品由于受到王家绳及其南京同学的影响,“偶尔还带着点左倾的色彩”,由于作品散佚,已经难以印证,但是,后来他却拒绝为左翼刊物投稿。
如要研究纪弦,以上两点不可不察。
2
大约是在1933年底,或是1934年初,纪弦在上海四马路现代书局买到戴望舒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同时订阅《现代》杂志。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于1929年4月,从集内三辑作品来看,已经开始从音乐性向非音乐性缓慢转变。《望舒草》则主要收录新作品,也保留了《我的记忆》里的非音乐性作品:这表明戴望舒对新诗美学模式的最后选择。戴望舒的语言态度给纪弦带来了“更具决定性”的影响,让他从新月派的“旧锦囊”里一跃而出:他决定废止格律诗,写作自由诗。戴望舒在《望舒草》附录《诗论零札》——此文作于1932年,原以《望舒诗论》为题,此前已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发表——开宗明义就讲到,“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纪弦却不排斥这个概念,他认为,“自由诗的音乐性高于格律诗的音乐性;诉诸‘心耳’的音乐性高于诉诸‘肉耳’的音乐性”。两者的观念是扑干格的吗?显然不是:纪弦用反对的方式沿袭戴望舒。心耳肉耳之论,看似胜出一头,实则仍未跳出戴望舒的轨辙。不管如何,从1934年开始,纪弦迎来他的自由诗时代,当年《现代》5月号就刊出其新作品《给音乐家》,9月号又刊出其另一新作品《时候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35年春天,也有可能是夏天,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二十二岁的纪弦与三十岁的戴望舒在上海江湾公园坊见面了:“他脸上虽然有不少麻子,但并不很难看。皮肤微黑,五官端正,个子又高,身体又壮,乍见之下,觉得很像个运动家,却不大像个诗人。”两人一见如故。1936年4月至6月,纪弦曾赴日本游学。他狂热地搜罗西书,借日本诗人堀口大学的译诗集《月下之一群》,得到法国现代诗更多更直接的炙烤,“深受阿保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之影响”,自此眼界大开,戴望舒自然也越来越缚他不住。在东京,纪弦写出《致或人》,此后不久又写出《火灾的城》,均自称为超现实主义作品。很多年以后,纪弦也拒绝承认他的风格与戴望舒存有相似性,“一点儿痕迹都不见”。从种种信息来看,纪弦或认为戴望舒仅取法国象征主义,而他兼收法国象征主义和美国意象主义。“然则戴望舒给我的影响何在呢?曰:自由诗的精神而已。”我们不妨如此表述:前者是在观念而不是风格上影响了后者。然而,观念和风格之间的复杂因果又不免让我对这种表述心存狐疑。戴望舒死于1950年2月28日,享年四十五岁。到1990年,纪弦写下《安魂曲: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祭》,一连写了两首,“附有后记,说明一切”。
这里还要说说《现代》。该刊创刊于1932年5月,由施蛰存任主编,戴望舒和杜衡(本名戴巍,又有笔名苏汶)做编辑。根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工作报告》,当局曾认为这个杂志具有“半普罗”性质(王文彬:《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然而就杜衡个人而言,他似乎不但要做到“非普罗”,而且要做到“非政治”,于是引发了关于“第三种人”的论战。纪弦坚定不移地支持杜衡,他甚至认为杜衡之敌鲁迅,在论战中已经被人利用。“较之施蛰存,杜衡是更加欣赏我的才华的”,所以当1935年12月,纪弦出版第二部诗集《行过之生命》,杜衡欣然作序,并为诗人的虚无主义作辩,“并不是虚无的思想造成这丑恶的二十世纪,而是丑恶的二十世纪造成这虚无的思想”。纪弦与杜衡就此结下友谊:一起避难香港,一起滞留上海,一起流亡台湾,可谓如切如磋,如胶如漆,如兄如弟。但是杜衡也并未做到非左非右,其长篇小说《叛徒》(在《现代》连载时以《再亮些》为题)曾得纪弦激赏,仍然坚持右翼立场。到台湾后,他放弃文学,转而研究经济学,更加顽守右翼立场。杜衡死于1964年11月17日,享年五十七岁。纪弦称之为“三十年代保卫文艺自由之英雄”、“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兼批评家”——这可能含有友谊的拔擢。在《现代》诗人群中,纪弦与徐迟或许最为相惜。大约在三十年代,徐迟就曾写有一首诗《赠诗人路易士》(蓝棣之编选:《现代派诗选》),说在纪弦的黑西服的十四个口袋里都藏着诗,并且说,只有当纪弦握住他的手掌,他才能想到自己也能歌唱。此后两人走上不同的道路——纪弦认为是左翼诗人马凡陀“拐走了”徐迟。1985年,当纪弦出版自选诗第八卷《晚景》,徐迟曾专门去信“对之大为赞美”。1993年,《纪弦诗选》在大陆出版,徐迟作序,认为这些作品“比现代派之现代派还现代派”,同时还盛赞其“宇宙意识”(刘登翰、朱双一:《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1996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同济医院跳楼自杀,享年八十二岁。纪弦在美国获得消息后十分悲痛,当月31日就写下《哭老友徐迟》。
1935年1月,《现代》改为综合性杂志,其后只出版两期,就告停刊。到1936年10月,由戴望舒另主编《新诗》月刊出版。戴望舒出一百块钱,纪弦、徐迟各出五十块钱,后二者不愿意担任编委,实际上仍然参加编务。这个杂志的新意和美意在于,终于跳出《现代》门户,试图从更大范围来总结和展示现代派的成就。按照纪弦的谱系学,当时的先锋诗人可以大致按照居留之区域和作品之精神分为两派,“南方诗派”与“北方诗派”,南方诗派即以《现代》诗人群为主,包括金克木、玲君、南星、侯汝华、陈江帆、陈时(此人被纪弦视为“后起之秀”)、徐迟、路易士、戴望舒,北方诗派则包括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可以看出,北方诗派以后期新月派为主,强调通过格律来实现克制的抒情。为了强调南方诗派已经率先唤起自由诗之魂,纪弦还强把居住在上海的邵洵美纳入北方诗派,把居住在北京的冯文炳(废名)纳入南方诗派。这是纪弦的蛮横。纪弦认为,《新诗》创刊以后,北方诗派都渐渐“南方化”,而从1936年到1937年,“南方精神的胜利”为新诗迎来一个收获季。只有林庚是个例外,因为“在他写了不少自由诗之后,忽又开起倒车来,发明了所谓的‘四行诗’,而竟回到唐诗宋词元曲的天地里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88年下年,纪弦却忽然开始写俳句。这可能与他的留日经历有关:俳句正是日本最为流行的格律诗。这样,我们就看到有趣的场景:纪弦一边写俳句,一边反复自嘲:“使用了五七五俳句的形式,虽说东西写得还算可以,但我不打算常用,因为俳句也是‘定型诗’之一种,这违反了我一贯的‘自由诗’的立场。”
3
战事起了。
1937年7月,《新诗》出罢7月号,8月《新诗》社特约印刷所就遭到日军轰炸,徐迟诗集《明丽之歌》和李白凤诗集《凤之歌》的原稿以及校样,均化为灰烬,再也不可觅回。纪弦带着一家老小溯长江而西上,由上海而武汉而长沙而贵阳而昆明而河内而香港,1938年初到香港,就认识了胡兰成。胡兰成曾如此记录这次见面:“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从云南而来,在杜衡处见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贫血的、露出青筋的脸,一望而知是神经质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紧张、多疑、不安与顽强的自信,使我与他邻居半年而不能丢开矜持。”(《路易士》,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下引胡兰成观点,凡未注明,亦见此书)1942年夏天,纪弦回到已沦陷的上海,而胡兰成早在1939年下半年就已被汪精卫召去南京。纪弦回到上海,生活陷入困顿,曾赴南京见胡兰成。胡兰成喜欢简静安闲的里巷生活,自云“没有劝过一个人参加汪政府”(胡兰成:《今生今世》),并说他的朋友穆时英(新感觉派小说家)也是自己主动要求参加(后来遇刺了)。胡兰成有没有劝过纪弦,后者的表述很含混,接着就写道,“他很尊重我的决定,并未加以强留”,两人在丹凤街石婆婆巷的胡公馆里,“只谈文艺,不涉政治”。几天后,纪弦回到上海。他亦承认此后多赖胡兰成接济。1943年,胡兰成从南京回到上海,1974年,又从日本去往台湾,这两个时间段,纪弦是否与之来往,双方回忆录都没有记载。
关于纪弦,胡兰成至少写过两篇文字:《周作人与路易士》和《路易士》,虽不及《今生今世》来得幽深灵异,却也自是不凡,或可视为关于纪弦的最好文字。胡兰成认为,“路易士的诗在战前,在战时——战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总是中国最好的诗,是歌咏这时代的解纽与破碎的最好的诗”,又说,“《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碎的时代”。胡兰成独拈出“破碎”一语,恰恰触及痛痒,也许他已然明白,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块壤、瓜果和色香:啊,就这样,纪弦势必与民国时代一起“破碎”。纪弦亦言及,胡兰成曾说其诗“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和美国意象主义之影响,然后又有意识地摆脱之而有所独创”,但此语不知出于何处。虽然胡兰成对纪弦亦颇有微辞,比如个人主义,病态,读书少,生活经验缺乏,狭隘,固执,装作骄傲,做作得很幼稚,等等,而纪弦仍然视之为知己,“胡兰成评论小说,固然十分中肯,而对于诗,他也有独到的见解”。
后来,有人指认纪弦为“汪派”之一员,并说他到台湾后换笔名,正是为遁形。对此,纪弦力辩其无。回忆录至此,居然破口大骂。据纪弦举证,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想要个“胖”的笔名,遂改“路易士”为“纪弦”,并常以新笔名给《和平日报》写稿,该报副刊主编恰是纪弦的老朋友徐淦。
4
1948年11月29日,纪弦移居台湾,时年三十五岁。1953年2月1日,他主编的《现代诗》创刊号出版。这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大事。
纪弦向来热衷办诗刊,曾于1934年办《火山》,出版二期而止;1936年办《菜花》,出版一期而止;同年办《诗志》,出版三期而止;1944年办《诗领土》,出版五期而止;1948年办《异端》,出版二期而止;1951年办《新诗周刊》,出版二十六期而止①;1952年再办《诗志》,出版一期而止,乃是台湾第一家新诗杂志。《现代诗》似是这些诗刊合乎逻辑的结果。
然则事实并非全部如此:《现代诗》延续的乃是《现代》之香火。1935年,就在《现代》停刊当年,杜衡办《今代文艺》,出版三期而止,施蛰存办《文饭小品》,出版六期(纪弦误记为十二期)而止,戴望舒办《现代诗风》,出版一期而止;1936年,叶灵凤办《六艺》,出版三期而止,吴奔星、李章伯办《小雅》,出版六期而止,戴望舒办《新诗》,出版十期而止。从这些刊物可以看出,施蛰存、杜衡、叶灵凤的趣味在于整个文艺,而戴望舒则愈来愈坚持他的一门心思,或者说一门新诗。这些刊物(除《文饭小品》皈依明清性灵派)薪尽而火传,递交着被压抑的现代性,对纪弦的雕镌自是十分深刻。
到了1956年1月15日,纪弦组建现代派,加盟者计有八十三人,后来又扩充到一百一十五人,方思、白苣秋、辛郁、林泠、林亨泰、蓉子、郑愁予、罗门、罗马等赫然在列。为了区别于三十年代现代派,纪弦把这个由他领衔的现代派称为“后期现代派”,或“台湾现代派”。同年2月1日,《现代诗》第十三期刊出由纪弦执笔的《现代派的信条》及《现代派信条释义》,主张“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从此以后,纪弦开始推动“新诗再革命”,提倡“新现代主义”(在不同场合和不同阶段,他又称为“后期现代主义”、“中国现代主义”或“东方现代主义”),终于将现代诗的火种播撒于台湾,并延及香港、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结下累累硕果。这些已是常识,此处不必絮烦。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赴美女学者奚密的观点,可能会让很多大陆学者感到意外:“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现代派所代表的现代诗并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表征;恰恰相反,在诗的理论与实践上均体现了对后者含蓄的批判和反抗。”(《早期〈笠〉诗刊探析》)1996年5月,纪弦从美国回台湾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31日,给汪启疆颁发“八十四年度诗选奖”,余光中代表《八十四年度诗选》编委会致辞,却特别向纪弦致敬:“中国新诗复兴运动的火种,是由纪弦从上海带到台湾来的。纪弦当年大力提倡现代诗,为现代诗出钱出力,现代诗在台湾逐渐形成气候,才有像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
可是纪弦自己却认为,他从上海带到台湾来的火种,“是的,火种,火种”,却是他“行囊里有两期《异端》”。异端社的发起人,除了纪弦,好像还有其弟路迈(路曼士),作小说时笔名“鲁宾”或“鱼贝”,作诗时笔名“田尾”的便是。异端社宣言由纪弦执笔,印在创刊号封面,强调“个性”与“自由”,反对并反对服务于“偶像”和“独裁者”。现在看来,这份孤独、匆忙而偏执的短命刊物,无论如何,难以确立为《现代诗》的前身,——而纪弦自己,也没有完全践行其宣言,他五六十年代所作政治抒情诗,比如《在飞扬的时代》、《向史达林宣战》,可以作证;1975年4月5日后所作多篇诗文,尤其是长诗《北极星沉》,也可以作证。后来他亦未用反省来弥补既成。尽管连纪弦亦不免如此,台湾诗人林亨泰却认为《现代诗》已经将国民党倡导的“战斗文艺”压到最低限度了。
1964年2月1日,《现代诗》出版四十五期而止。借此终刊号,纪弦再次发表其代表性文论《论移植之花》,以示终不悔。该刊于1982年复刊,已与纪弦无涉。
要在这里补充的是,现代派早期成员罗马,其实就是商禽,他后来转入《创世纪》诗社,在《现代诗》趋于式微之际,会同洛夫等人,取道纪弦曾有尝试的超现实主义,终于促成了台湾现代诗的柳暗花明。
5
现在必须谈到纪弦和覃子豪的论战。
这两位诗人的美学分歧由来已久。1936年4至6月,纪弦曾赴日本游学。游学期间,纪弦先后认识两个四川诗人,一个李华飞,另一个覃子豪,三人时相过从,讨论艺术。纪弦和覃子豪都很热爱古典音乐,其他趣味则迥乎不同:画家,纪弦喜欢马蒂斯和毕加索,覃子豪则颇不以为然;诗人,覃子豪喜欢拜伦、雪莱、济慈和雨果,纪弦则喜欢艾略特、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瓦雷里和阿波利奈尔,“总之,他喜欢浪漫派,我喜欢象征派就是了”。由此可见,后来的论战并非偶然。
纪弦赴台不久,即与覃子豪重逢。1954年3月,覃子豪与余光中另成立蓝星诗社。到组建现代派时,覃子豪亦拒绝接受纪弦的邀请。据余光中追述,蓝星“是针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第17个诞辰》)1956年4月,余光中发表所译之史班德(Stephen Spender)之《现代主义派运动的消沉》。1957年8月,覃子豪发表《新诗向何处去》,针对纪弦主张,提出“六条正确原则”,纪弦答之以《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对于所谓六项原则之批判》。1958年4月,覃子豪复发表《关于新现代主义》,纪弦复答之以《两个事实》、《六点答复》。关于这次论战的具体过程及主要节点,大陆学者,比如古继堂、刘登翰、章亚昕,已有比较深入的清理,简而言之,就是“主知”与“抒情”的论战。纪弦强调“主知”,认为“诗乃经验之完成”。为了求得绝杀,双方,尤其是纪弦,将观点绝对化,颇不免意气用事。纪弦爱养宠物,养过猫,养过狗,还养过斗鸡,彼时之纪弦,与所养之斗鸡,大体上可以引为同志了。胡兰成曾说纪弦好比堂·吉诃德,而《蓝星》不免成为一架倒霉的风车。值得叙及的是,双方笔墨官司虽然如此热辣,见面时却依然礼节彬彬,言笑晏晏,亦堪称诗歌史上的佳话。
对于纪弦的反抒情,反浪漫,反表现,反确定,反格律,今日也不消再辩得。但是纪弦在论战中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无所为而为”,如剑悬顶,则尚未过时,“须知诗人兼充祭师、预言者、宣传员、人道主义者,或是社会改良运动家的时代老远地成为过去了”。
论战后双方各自反省,均有所修正。1960年,覃子豪为某青年诗人作《序》,亦转而强调“以知性来净化情感”(参读覃子豪《序》,云鹤《忧郁的五线谱》);1961年,纪弦发表《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后来亦转而强调“抒情与主知并重”。就在纪弦开始矫正其观点的时候,亦即1961年,坚持绝对现代立场的洛夫又与余光中发生关于“虚无”和“现实”的论战。这两次论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现代”与“传统”之争,其结果亦很相似:双方各个反省,均有所修正。洛夫后来亦认同笔者的观点,即这种论战可以视为洛夫与后来之洛夫,或者余光中与后来之余光中的跨时空辩驳,原是现代诗内部的和而不同。(参读洛夫、胡亮《台湾诗,“修正超现实主义”,时病:洛夫访谈录》,方明编《大河的对话》,台湾兰台出版社,第273-274页)痖弦甚至认为,《现代诗》、《蓝星》、《创世纪》共同“形成一个时代的风格”。1962年,纪弦宣布解散现代派。
覃子豪于1963年10月10日去世,享年五十一岁。11日治丧。众诗人公推纪弦撰写并朗诵祭文,据云读罢泪下如雨,“听者无不为之动容”。纪弦还写出好几首悼诗,而以《休止符号》为最佳,后来还曾当众称覃子豪为“大诗人”。想来覃子豪亦必含笑于九泉。
6
1963年5月,应“菲华文教研习所”之邀请,纪弦赴菲律宾讲学,认识了女诗人莫灵乐,后者赠以茉莉花,居然使得诗人很快完成一首苦思难续的未竟之作:《M之回味》。这是诗人成名后与世界交流的开始。1969年8月,应尤荪(Amado Yuzon)之邀请,纪弦再次赴菲律宾,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两次赴菲律宾,纪弦对这个民族的“色彩的良知”留下深刻印象。1970年6月,应许世旭之邀,纪弦赴韩国,参加“第三十七届国际笔会”。其间,曾听取川端康成和林语堂的演讲,并与韩国诗人许世旭、赵炳华等欢饮,与日本诗人草野心平邂逅,——纪弦曾翻译过他的作品。1973年11月,纪弦参与在台湾筹办“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此次大会共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代表参加,包括美国女诗人玛丽·纳恩(Dr. Marie L. Nunn)和魏金荪夫人(Dr. Rosemary C. Wilkinson),后者对此后历届“世界诗人大会”的召开颇耗心血。值得叙及的是,原台湾诗人吴望尧,此次作为越南代表参加大会,期间与台湾故友商议,欲以个人名义设立“中国现代诗奖”,得到广泛响应。1974年6月,“首届中国现代诗奖”出炉,授予纪弦特别奖。
1976年12月28日,纪弦移居美国,时年六十三岁。此后朝暮徘徊于旧金山西海岸:不见台湾,亦不见大陆。1981年7月,应魏金荪夫人之邀请,纪弦就近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五届世界诗人大会”。其间,纪弦获得世界艺术文化学院(World Academy of Arts and Culture )荣誉博士学位。1985年11月30日,纪弦首次用英文写出《Foggy San Francisco》(《多雾的旧金山》)一诗。自此以后,纪弦每有诗意,就必须先选择使用何种语言,如果用英文来写,就坚持用英文来酝酿、斟酌。他坚决反对先用汉语写,再自译成英文,认为那是“可耻行为”。纪弦将新写的英文诗呈示魏金荪夫人,后者遂建议他给《POET》投稿。该刊由印度诗人Dr. Krishna Srinivas主编,他也是世界诗社(World Poetry Society)主席。按规定,必须先加入世界诗社,方可在该刊发表作品,纪弦当即加入。恰好该刊的美国编辑就是玛丽·纳恩。世间之巧,人际之缘,往往便是如此。此后,纪弦就以加州诗人名义,频频在《POET》发表作品,并与玛丽·纳恩结下让人歆羡的友谊。1987年 4月,1991年8月,他们先后筹办两场朗诵会,朗诵者独一人,即是纪弦,听者亦独一人,即是玛丽·纳恩,地点都在玛丽·纳恩之家:从Pacifica到Napa。纪弦还为玛丽·纳恩写呈许多献诗,其中有首《三人行》,将太平洋拉进来,加上二者,遂成三人行。在纪弦看来,太平洋是位王后,而玛丽·纳恩就是位公主,上帝把她安放在“青天,碧海,和金黄色的沙滩”之间。
然则纪弦与世界交流,似仅限于礼仪与日常,并未获致诗学上的惊艳、猎奇与合金般的冒犯和错综。
九十年代初以来,很多大陆诗人亦去往美国。从纪弦的回忆来看,除老南、老刘、老夏外,他几乎没跟更多大陆诗人接触,笔者原本甚为期待的某种对话也就无从发生。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7
纪弦家族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其儿女、孙儿女、曾孙儿女总有数十人之多;而纪弦之创造能力,与之相比毫不逊色,到耄耋之年仍无衰退之势。张默早就说纪弦作品“当在千首以上”(张默编著,《小诗选读》)。而其晚期诗,最大收获就是宇宙诗,1985年的《宇宙论》和1986年的《方舟》即是代表,而1989年的《有一天》和《给后裔》,1991年的《玄孙狂想曲》、《空间论》,1993年的《宇宙诞生》,1995年的《物质不灭》、《恒星无常》、《早安哈伯》、《致木星女人》,1996年的《致水星》,1997年的《黑洞论》、《关于飞》,2000年的《圆与椭圆》、《诸神之足球赛》,也很重要。就在2000年,诗人编成自选诗第十一卷《宇宙诗抄》,这部诗集,可以视为他对1942年所作《摘星的少年》的衰年酬答。笔者之所以大量胪列纪弦晚期作品之目录,主要原因在于,此类作品大陆学者多所不知,很难得见。纪弦的宇宙诗乃是科学和神学从相互错扰达致和谐的结果。纪弦在少年时代便对天文学产生了很大兴趣,到1975年10月29日老母去世,乃遵照其生前愿望,接受施洗,加入信义会,此二者,当是纪弦此类作品的内在涌泉。
纵观纪弦一生之作品,或可如此拈出其最著之特征:曰调侃,曰相对论,曰神学和科学。
还有两首诗必须稍作介绍:1992年所作《预立遗嘱》,1999年所作《水火篇》(原名《死之设计》)。两次,纪弦均明确交代须将其骨灰撒入太平洋。纪弦喜滋滋如是设想:千年之后,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在旧金山海湾钓到一尾小鱼,烹而食之,终得其灵性,于是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了。
8
回忆录至2000年而止,传主之生命则至2013年而止:据云死前犹呼钓鱼岛。从头至今,纪弦都参与、见证了新诗的成长,再没有其他诗人拥有同等资历。那么,其新诗谱系是如何梳构的呢?他曾用两次演讲来回答这个问题:1986年8月16日在旧金山演讲《现代诗在台湾》,1989年4月2日又在桑尼维尔演讲《何谓现代诗》。纪弦认为,新诗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1919—1931),成长时期(1931—1937),消沉时期(1937—1949),复兴时期(1949—)。后来他又认为,消沉时期之作品,不是传单就是口号,只能算是“非诗”,于是对这个谱系进行调整,仍然分为四个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诗时期,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格律诗时期,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自由诗时期,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时期。而现代诗,亦可分为三个阶段:格律诗的自由化(戴望舒),自由诗的现代化(纪弦),现代诗的古典化(郑愁予,抑或余光中?)。可以看出,纪弦对冯至、艾青和卞之琳的无视,以及对于“隐秘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无知。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纪弦甚至将大陆“朦胧诗”亦归于“台湾现代诗影响下的产品”。这种简单的文学进化论让人十分讶异。无论如何,纪弦终于将“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雄视坚持到了最后。
附记:1963年4月,纪弦诗集《摘星的少年》由现代诗社再版。也许就在当年5月赴菲律宾讲学期间,纪弦曾将这部诗集赠给云鹤,后者就住在马尼拉。1987年1月,云鹤将此书转赠给流沙河,后者正研究台湾诗。后来,流沙河又转赠给杨然,杨然则转赠给笔者。花开花落几十度,这本诗集才辗转来到笔者面前,翻动发黄而变脆的纸页,陡觉时空翻转,永恒亦刹那,刹那亦永恒,便只好抛去秃笔,闲坐高楼,独对西山一脉深黛。
注释:
①纪弦本人已经记不起《新诗周刊》出版期数。据张默《台湾新诗大事纪要(1900-2002)》:“《新诗周刊》借《自立晚报》副刊版面创刊,每周一出版。至民国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休刊,共出刊九十四期。此为迁台后最早出现的一份新诗期刊,第一至廿六期由纪弦主编,第廿七期以后由覃子豪主编。”张默《台湾现代诗笔记》,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334页。
栏目责编: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