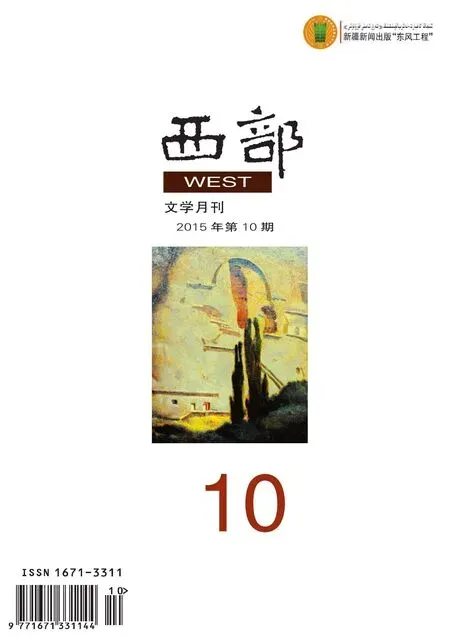散文五题
2015-11-18周涛
周涛
跨文体
散文五题
周涛
牧人和农夫
骑马的妄自尊大的牧人和谦卑的荷锄种地的农夫,打眼看过去没什么区别。都是和土地打交道的人,都是成年累月风吹日晒黑黢黢的人,衣服一年四季洗不了几次,手掌粗大、手指僵硬,走起路来全身摇晃很不协调,头发像黏在一起的杂草那样,说话含混不清,一句话,都是受苦的人。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认为差异很大。
农夫住在村子里,他那个小社会叫“村落”。牧人住在毡房里,他那个松散的社会叫“部落”。看来人跟鸟一样,都得找个地方落一落。有一天,牧人找到农夫,他要用一只羊换一袋粮食,农夫答应了。换完以后,农夫请牧人坐进他的小院,一起吃刚摘下来的西瓜。牧人很高兴。他们聊起来。
“你养了多少只羊?”农夫问。
“两百多只。”
“那么多羊长得一样,你都能认出来?哪只丢了,哪只让狼吃了,你咋能知道?”
牧人不答,反问农夫:“你们这个村子里一共有多少人?”
“也是两百多人,大的小的都算上。”
牧人说:“这么多人,哪个死了,哪个丢了,你能不能知道?”
“当然知道啦!”农夫说,“这个村的人我都认识啊!”
“那就对了,这些羊我也都认识。”
“可是人和人长得不一样呀。”农夫说。
“我看到的羊和羊也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长相不一样,性情脾气也不一样,连叫声都不一样呢!”牧人说。
农夫一听,乐了:“日它家家的,啥人眼里看啥呢!”于是招呼老婆弄些酒菜。
牧人说:“我们穆斯林是清真的,你知道。”
农夫说:“凉拌皮辣红没问题吧?”
牧人说:“行,喝酒。”
半瓶子白酒下肚,两人高兴了,话多。
农夫说:“哎,人家政府给你们盖了那么漂亮的定居点,咋不好好住撒?一天到晚赶上一群羊,这个地方住上十天,那个地方住上半月,跑啥呢跑的,不嫌泼烦吗?”
“住是住了,不行。夏天想着牧场,冬天想着冬窝子,受不了啊。有的人跑掉了,有的人闷坏了,喝上些酒,大男人哭得像狼嚎一样……自由惯了的人,定居要生病呢,你们不懂。”
“哎呀呀,啥人么,就是个吃苦的命!”
“你呢,你不吃苦吗?守上两间土房子,一个鸡窝,还有巴掌大的几块地,一辈子拴住,像马拴在树上一样。马拴在树上还可以休息,你呢,从早到晚刨土坷垃、浇水、上肥、打虫……你比我苦得多!”
“那年大旱,山干火燎的,你的牛羊赶到山里光吃空气不吃草,你忘了吗?”
“你也完蛋了,种啥啥死,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脸吊得马脸那么长。”
“哎哟哟,都是受苦的人,都在老天爷的指头缝里活命呢。来,喝一个!”
农夫说:“咱们这里的人说地球的把把子快磨断了,说是苏联专家测出来的,正拿电焊机焊着呢。”
牧人说:“能焊住么?焊不住咋办?”
“能焊住吧,要焊不住麻烦可就大了——地球把把子一断,地球那还不碎零干了?”农夫夹了一筷子菜送进嘴里,“我的房子、地、老婆、孩子还不知碎成啥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老婆孩子还有牛羊也一样!”
“地球会不会爆炸?”牧人害怕了。
“爆炸可能不会,它肚子里又没装火药。”农夫的解释似乎有理。
“外江,胡达不管吗?”
“嗨……先把酒喝了。”
就这样,农夫和牧人聊着喝着,天色渐渐晚了。农夫把牧人送出院门,看着他摇摇晃晃地上了马,忧心忡忡地走进暮色里。
农夫看着牧人骑在马背上越来越远,人和马连成一体,看过去像个怪物,一摇一晃的,马也像喝醉了。远远地,晚风断断续续送过来几句歌声。
“这个放羊的,地球都快零干了,他还唱歌呢……”农夫叹了口气,心里忽然酸酸的,“哎,说啥呢,都是受苦的人……”
可怜的牧羊人
可怜的牧羊人!你为什么非要从城里过呢?难道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转场时从城市走过的牧羊人是可怜的,但不一定是愚蠢的。也许你认为只要是道路的地方都可以通过,除了太高的山和太深的河,你和你的羊群都可以通过。
但是这次你错了,你有些愚蠢。
你根本不知道,也不了解城市是什么。
你不知道,比高山更险峻、比河流更湍急的,是一座城市。穿越它,既是一种妄念,也是一种蠢行,它很可能摧毁你。
可怜的牧羊人!
你很可能是从南山的菊花台一带过来的,也很可能是想把你的几百只羊赶往古牧地或是北塔山,这都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从城市
穿过呢?
现在,你体会到难堪和尴尬了吧?你尝到硬着头皮继续前行的窘迫了吧?
这时正是秋天,城市还相当炎热。城里人还穿着短袖衣裙,光鲜漂亮。城里人在街上看着你,他们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野生动物。
你穿着皮袄皮裤,头上顶着那个标志性的防御暴风雪的狐皮帽子,你太不合时宜了,你穿得太厚了。你不出汗吗?就像一只企鹅突然出现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你完全走错了地方。
还有你骑着的那匹马,无精打采,低垂着头颈,鬃毛和尾巴上挂着干刺球。这可不是人家阅兵式上排列整齐的清一色骏马,这是一匹肮脏可怜的老马,在完全陌生的城市水泥路面上,它脚下踩出的声响就像农妇第一次穿上高跟鞋那样。马很明白,在这里自己很卑微,和骑在它背上的主人一样找不到感觉。
羊群更是慌乱、紧张,像一群衣衫褴褛的难民,拥挤在一起不知怎么办才好。有时互相呼唤几声,声音微弱,底气不足,在草场上那个劲头全没了。它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地面,没有一根草,也嗅不到土壤的气味,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末日的预感在羊群中传递。
两只硕大的牧羊犬,像两堆乱毛在行走,它们跟在羊群边上,完全不敢行使自己牧羊的职责。更多的时候,它们躲避街道上的人,顺着墙根低头溜着走。尽管它们非常低调,还是引起城里少年的注意,他们喊它,朝它扔石头,它连叫也不敢叫一声,头也不抬,匆匆躲避扔过来的石头,像过街的老鼠。它们偶尔抬头看一眼马背上的主人,却发现,主人这阵子比它们还可怜。
可怜的牧羊人。
他就是这样带领着自己的部属通过城市,像一群战俘,毫无尊严。没有经过任何一场战役,就已完全溃败。城市不发一枪一弹,不派一兵一卒,甚至连一句话都懒得说,就使牧羊人的内心像春洪冲击过的土崖那样坍塌了。
他的那张被烈日和暴风雪涂染而成的青铜色的脸,显得有些过于夸张,和目前的现实有些距离,使他更像一个古董或过去年代的遗物。他眯着眼,所以看起来就像没有眼。他稀疏的黄胡子也未经修饰,不伦不类,丝毫没有美感。
在这座城市无所不在的审视中,他自惭行秽,无地自容。不仅如此,他和他的羊群、马匹、狗,携带着过于明显、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强烈膻腥气和山野气。这气味在牧场上并不明显,似不存在,但是一到这里,立即膨胀,爆炸,令城里人面露厌恶,掩鼻而过。
城市正是这样,它会让你感到自己卑贱,在它面前,你会觉得自己连奴仆都算不上。它耸立在那里,是一座用金钱堆砌起来并精雕细刻的崇山峻岭,像一座皇帝的迷宫。它比它的统治者更直观,更让人敬畏。它在远处闪闪发光,宛如地平线上的一个梦境,吸引你诱惑你,一旦走近,你才能感到它巨大的排斥力,你会被震慑住,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此刻牧羊人就像一只刚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小动物,迎头碰上了这头巨兽,他一入迷阵,无处可逃,他找不到任何参照物,也找不到对手。他原本在旷野、山林间熟识最隐秘的路径,暴风雪也迷不住他。他还有一双金雕般锐利的眼睛,一双分得清密林深处野猪还是兔子脚步声的耳朵,还有百步之外指什么打什么的枪法,可是在这里全都没用了。他只能这么眯着眼睛茫然地向前挪动,不知什么时候穿过这座冷漠无情的迷宫。
出发是几天前的事了。他和他的羊群顺着一处峡谷出来向北拐过来,那块地方林木茂盛,背阴的山坡上立满了黑松林。那些松树认
识他,他回转头望那些松树的时候,感觉到了那些笔挺高大的松树也正凝望着自己,他点点头,向这些高贵的巨人表示感谢。沿着峡谷,一条小河一直追随他和他的羊群,河不宽,水却非常清澈。他看见一只野兔子跳过去,隐入灌木丛中,还看到几只旱獭,半坐在堆起松土的洞口旁,啁啾地叫着,叫声和它们的长相不太符合,像是禽类的鸣叫声。在那种地方,他随时可以选择居留之地,他停下脚步,用铁锨翻土,土质松软,是千百年的枯叶朽枝培育出来的沃土,然后他支起毡包,从小河里提一桶水,捡一些落地的干枯松枝生起火来,不一会儿,奶茶的香味就弥散开了。
晚上他睡在花毡上,枕头旁边和身体周围是青草和野花,鼻孔里充满了新鲜的草味和野花的香气。他躺在那儿,望着毡包顶上的天窗,深蓝的夜空近在眼前,星星还有月亮,也正在夜空里望着他……他耳畔是马嚼夜草的声音、牛喷响鼻子的声音、羊群走动的声音、狗偶尔吠叫的声音……
那时候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可怜过,相反,他很充实,也很自信,他是这空旷山野丛林草原河流的主人,也是这里所有小兽小鸟的帝王。他性欲充沛,他儿子女儿成群,而且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美男子。
但是现在,他陷入城市的困局,像个傻瓜一样找不到出路,他和他的羊群变得一文不值。
哎,可怜的牧羊人,你为什么非要从城里过呢?
林场有个狐子脸
既没有带斧子,也没有带锯子,四班的人被派到巩留林场去伐木。农场今年打的粮食多得运不完,决定盖一座大粮仓。盖粮仓需要木头,四班就担负起上山伐木的任务。林场在两百公里外的山上,坐着卡车,这伙人出发了,从草原深处向山林深处驶去。
一路越走越高,河流越走越细、急。山林的景象大不一样了,使这些来自开阔草原的人完全出乎意料。沿途的松林像接近战区的人员分布,开始还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像是撒出去的哨兵,在近山处游荡;渐渐开始出现一些小的群落,仿佛驻扎的连队;再往上去,群峦重叠,密密的黑松林一直铺向天涯;谁能想到此处竟藏兵百万千万,像是无数的集团军摆在这里!
松林是越往高处颜色越深,哨兵时是绿的,连队时是深绿,到了团旅师这一级,便是墨绿,大面积密集的集团军、方面军时是一望无际的黑绿,像山的黑茸毛。
一些石头,开始出现在松林树的稀疏处。巨石正如同卧牛立马,白的、褐色的、黑白花的。小些的石头像一些羊,聚散有度。看不出它们是看护着这些松林呢,还是依赖着呢。总之是静谧无声的。你会觉得它们在白昼化为石,夜晚则会又变成牛马羊在松林间游走。若是夜静月明,这些各种形态的大卧石,在松林的疏朗处蓦然闪现,反射着幽幽月光,猛地撞见真是会吓死人的。
待到了林场,乍一看去,像个疗养院。一幢苏式建筑座落在松林环抱之中,红顶黄墙,与这里幽静的环境颇为和谐。空气清新得让人直想打喷嚏,那水流也清冽得舀起来就可以喝。如此一个好去处,却寂寥无人,落寞得好似怕听到足音。
四班的人很快安顿好了,黑子烧火,塌头和艾买提做饭,剩下的老哈、兰毛、玉素甫、癞皮俊和我干活,田样板带队。
第一天在楞场上才和这里的工人见了面。工人并不多,人手一个扳钩,把伐好的原木去
枝后码在楞场上待运。那一根根原木,粗壮些的,像汽车轮胎那么粗,比一辆卡车还要重,就这么个小小的扳钩,怎么可能码得像一座座金字塔那么整齐呢?
我开始不太相信,看工人们干了一阵子,这才信了。那个扳钩像两颗牙,下牙是短的、死的,上牙是长的、灵活的,上下一抓,就像咬住了原木,绝不脱落。原木虽重,却是圆的,偌大一根原木在工人手下滚动、侧移、转向直至挪向高处定位,就像小孩垒积木那么容易。
有一个叫哈勒克的工人,他看起来很会干活,但情神阴郁,黝黑的脸瘦削、硬韧。他看起来像个阿尔巴尼亚人,浓眉,深眼窝像逃犯或游击队员,腰间插一把匕首,却从不多说一句话。对人恭顺避让,只会埋头干活。无论什么时候“卸车”,他都会出现在楞场上,原木在他手里驯顺地转动,变得像一只听话的小羊羔。
我看着他,想起南斯拉夫电影里那个阴沉的、会扔飞刀的杀手。别人问他的队长:“他会笑吗?”哈勒克确实从来没笑过,可能也不会,但是他像个有故事的人。
斧头向树借一根斧柄,
树便给了它。
形状美观的,裸露的,青白的武器,
从地母的内脏中伸出头来,
木质的肉,金属的骨,
只有一个肢体,只有一片
一片嘴唇……
几天之后,老哈、兰毛、玉素甫、癞皮俊和我都会用扳钩了,干得不错。尤其是老哈干得投入,他像一只阿尔泰山林里的哈熊那样,肥壮而又灵活,他似乎具有熊那种爱搬木头的本性。他吭哧吭哧,似乎从中找到了什么寄托。实际上,他的身躯在干活,思想却在翻弄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像看一本日记,偶尔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沉思久久。就在这当口,不知什么原因,堆好原木的一座“金字塔”忽然垮了。轰隆一声巨响,所有的原木滚落下来,就势从高坡向下冲,就像几百辆坦克冲撞、碾压过来。楞场上的人全惊呆了。坡下面只有老哈一个人,他站在那里、直定定的、傻了一样。我看到,他已来不及逃开,也无路可逃,而滚滚压来的原木顷刻便到。“老哈完了!”我张着嘴却喊不出声来,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老哈被生生擀成饺子皮啊!几百根原木,每一根都有几吨重,它们轰轰隆隆、争先恐后、势不可当、毫不留情地从老哈头顶上碾压过去了,它们滚动、弹跳、相互碰撞、势如破竹……直到很远,才被另一处山体拦住。只剩下老哈,趴在空地上。谁也没想到这时,熊一样的老哈竟然拍拍土站了起来。
我跑过去看着他:“你没事吧?”
老哈说:“没事,一点儿没事。”
“怎么可能?我们都吓坏了。”
“我当时也傻眼了,跑不及了,前面正好有个土坑,我就趴在坑里了。”
“几百根原木就这么从头顶上滚过去啦?”
“滚过去了。”老哈脸煞白,但似乎并不害怕。
黑子后来说:“老哈这个卖沟子的命大啊,命太大了!”
兰毛说:“急中生智,置诸死地而后生。老哈不简单,不然我们四班下山要少一个人。”
塌头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哈说不定以后要当官呢。”
我心里想,别看老哈这家伙平常憨憨的,实则内秀。面临大事有静气,既逃不脱便迎头上,不慌乱,知道坑能躲人。换个懦弱胆小的,吓懵了,当场碾成饺子皮,肯定惨不忍睹。
这事之后,林场的工人态度一变,对我们
这些大学生有些刮目相看的意思。后来慢慢接触多了,彼此渐无间隔,啥都说。有个工人名叫胡志联,人称“狐子脸”,面白脸瘦,像是工人中的风流才子,能谝闲传。“大学生?”他说,“我们林场也有一个呢,北京医科大学的,学了八年毕业的。学啥呢么,要那么长时间?好好把一个丫头学成老姑娘了。”
他一说,我想起来了,是有一个女医生,每天从那幢红顶黄墙的苏式建筑里进出,看起来非常孤独,落落寡欢,却很矜持,并不与人说话。我问:“是不是那个女医生?”
“就是么。”狐子脸说,“有一次,我们一个工人蛋疼,疼球得不行,跑去医务所。刚好那个女的值班,她刚分配来。那个怂工人一看是个女的,长得又白俊,转头就往门外走。人家医生把那怂叫住,让坐下,问他:‘怎么啦?跑什么跑?哪儿不舒服?’工人紧张得很么,又不敢直说,憋了半天说:‘肚子下面那个地方疼。’”
人家医生是干啥的嘛,一看就明白了:“噢,是生殖器疼,是吗?”
那个球工人哪知道“生殖器”,他听成“生着气”了,就给人家说:“生着气疼,不生气也疼。”
医生又问他:“小便颜色怎么样?”
工人说:“小便颜色……也就黑不溜秋的,和大伙差不多。”
医生一听,又岔了。就问:“睾丸疼不疼?”
工人说:“搞完疼。没搞时候也疼。就是搞的那阵子觉不出疼来。”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谁编出来这么绝的段子?总不会是真的吧?”
狐子脸说:“真的,要不咋让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结合呢,不结合,球都看不成!”
田样板听着忽然大腿一拍叫起来:“听听!这就是林场工人给我们讲与工农相结合的生动的一课!”
狐子脸瞥了田样板一眼,颇有些不以为然,说:“我还要给你们讲讲嫖风的事呢,那才生动呢。”
田样板说:“嫖风?工人阶级还嫖风?你不要胡说,那有损工人阶级光辉形象!”
狐子脸说:“工人么有个球的形象嘛,还光辉?挣上几个卖命的钱,图的就是嫖风么,文艺、体育都有了,要不活着还有啥?人嘛,活上一辈子,还不就是吃点、喝点、日个逼还有啥?”
黑子说:“哎,你有没有打过女医生的主意?”
狐子脸说:“你说的这是个啥话?人家女医生就不是给我们这号人预备下的么,想都没想。鸡踏鸡,鸭踏鸭,天鹅跟前没想法。”
黑子说:“嫖亦有道。”
狐子脸大约有三四十岁,他看了看这群二十多岁的学生说:“我寻摸着你们没几个闻过女人味,都是些生瓜蛋子。嫩黄瓜还没在缸里腌过吧?”
田样板不懂:“啥叫腌黄瓜?”
其他几个都知道啥意思,说黑子是长茄子,他腌过了。
狐子脸转头问黑子:“腌的咋样?”
黑子那么油的人,这时也不好意思了:“还行,还行。”
狐子脸可能念过几天书,开始卖弄起学问了:“《西游记》你们总该知道吧?”
大家说:“废话、谁不知道。”
“孙悟空有个金箍棒知道是啥东西吗?”狐子脸问完,看大家都盯着他不吭声,就笑了。“别看你们是大学生,想你们也不知道。我给你们解释一下,金箍棒明里是根棒子,实际上暗说的就是男人的生殖器。所以我说,金箍棒就是个球!”
“你想嘛,啥东西上面有箍?球嘛。你再想,
啥东西可大可小?还是个球嘛。所以说,孙悟空成天拿着个球乱晃荡,大闹天空,也只有球上的劲儿才敢闹嘛,是不是?悟空,悟什么空?色即是空嘛。《西游记》里最厉害的孙悟空,孙悟空靠得就是金箍棒,金箍棒实际上就是个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祖宗早就明白,球才是最厉害的东西,是球创造了世界。”
我心想,还真他妈的有点道理,大闹天宫,砸烂一个旧世界;西天取经,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不就说的现在的事吗?
一人问狐子脸:“你说的这个球理论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
“哪本书上也没有,我自己琢磨的,怎么样?”
“你算得上一个球理论家了!”我说,“可惜你这一套上不了台面啊。”
“上那个球玩意儿干什么,我都是瞎想,胡吹毛燎呢,哈哈。”狐子脸谦虚着,但也掩不住有几分得意。
说着话这阵子,黄昏来临了。
在深黑的夜里,嗅得见浓墨的芬芳,夜的书法笔力苍动,天地间龙蛇飞舞,鬼哭狼嚎,星光灿烂。山林一片寂静,隐约有黑暗的江河在流动,风声若有,细听则无,夜潮涨落,层次分明。迷离恍惚之中,有一无形之物在松林上下翩飞,冲腾疾走,喘吐凝视。
那是夜的瞳仁。它正注视着。
狐子脸的脸在夜幕陪衬下,更像了一只真正的狐狸,瘦尖脸上两目如灯,贼光闪闪。
1958:菊花台
那次是季柏头一次去南山度夏。那次度夏给季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是因为他顺利地考上了中学,学校正好组织为期半个月的南山驻营,父亲大概是奖励他,就让他参加了。小孩子不多,主要是一批年轻干部,男男女女,有吃有喝,无忧无虑,轻松快活。
帐篷搭起来了,野炊也点火冒烟了。
寂静的南山菊花台响起了手风琴声和快乐的歌声:“是那田野的风,吹动了我们的胸怀……”菊花台遍地野菊盛开,漫坡松林黑绿。天空蓝宛如刚刚用水冲洗过的蓝宝石。大地像富有弹性的女神丰腴的腹部,零零星星散布着一些牛羊马匹,它们低头吃草就好似虔诚的信徒对这位女神几步一拜……远处,山峦头顶雪冠,在夏日的阳光下闪耀银光。近处,雪水融化后形成的溪流已经汇入了河流。水从布满各种白色、鹅黄、褐红、浅灰鹅卵石的河滩上漫淹而过,脚步轻快。
季柏顾不上欣赏这些,他招呼了几个小伙伴,在一处平坦的草滩上踢足球。他足球踢得不错,曾经是小学校队右边锋,打遍周围小学无败绩。
正踢着,一抬眼,季柏看见一群当地的哈萨克小孩在旁边看。他们可能没见过足球,显得很新奇。季柏就招呼他们一块来玩。
玩了一会儿,其中的几个大一点的少年不干了,显得不高兴。
“怎么不玩了?”季柏问。
“踢那个东西,我们不行。你敢和我们摔跤么?”
“摔跤有什么了不起?”季柏想都没想,指着其中大一些的少年说,“摔就摔,三跤两胜。”
季家兄弟摔跤无师自通,少有败绩,上手一较量,几乎没什么悬念,三比零。正准备收兵回营,一个哈萨克少年忽然上前拉住他:“我想和你交朋友,可以吗?”
“当然可以!”季柏很高兴。
从那以后,这个名叫黑力力的哈萨克少年每天早晨天刚亮就来找季柏,一起去山背后的草滩上找他家的马。马绊了腿,放到草滩上,像瘸子那样一跳一跳地找草吃,走不了太远。早晨把马收回来,这是黑力力的活计。他提上几副马叉子,叫上季柏就去了。
果然,山后有四匹马。黑力力这时显出本事来了,他抓住马,给马戴上叉子,把一匹青灰色的缰绳放到季柏手里:“上去!”
季柏看着这匹光背马,那么高的背,被夜晚的露水打湿了,他上不去。
“这样上。”黑力力把他的马牵到一个坡下,从坡上一跃,骑上去了。
季柏看了,也学着他的办法,上了马。那是季柏第一次骑在马背上,很是兴奋。黑力力骑着一匹手里还牵着两匹,走在前面。季柏骑着青灰马跟在后面,一路上,黑力力不断示范怎样驭马。
到了毡房,黑力力拴好马,招呼季柏一起进家,还把季柏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奶茶烧好了,季柏喝了几碗,就回去了。
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季柏已经骑术娴熟了,可以自己给马解绊儿,上叉子,甚至和黑力力并驾齐驱了。他们在狭窄的山路上飞奔,互相追逐。那是季柏最快乐的时候,从那时起,他爱上了马并且深深迷恋。季柏想像黑力力那样,不上学,放马骑马多好啊!上学,没意思。
有一天,季柏正和黑力力在山间小路上策马奔驰,远远听见山下有人在喊:“快下来!你这小子,不要命啦!”
从营地回家后,季柏知道老红军告了他一状。父亲说起,倒没有大惊小怪,父亲学着老红军的口气说:“你皆个俄子呀,胆子太大啦!骑在马上疯跑呀,那么高的山,掉下来怎么办!”
“掉不下来。”季柏说,“我学会骑马了。”还把他和黑力力交往的事告诉父亲。
父亲没有责备他的意思,认为这很正常:“我的儿子嘛,肯定就是这样的。”
但是让季柏感到奇怪的是,他和黑力力是怎么交流的?他不懂哈萨克语,黑力力汉语也不懂几句,他们相处无碍,互相都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特定的环境里,心领神会,从未出错。少年的心呵,单纯,纯净,像一潭明澈的湖水,与晴朗的天空互相映照,一目了然。
连语言都似乎是多余的。
1966:黄长征
阿黄是季柏的大学同学兼好友。
阿黄的名字叫黄长征,可能是注定了他这辈子要长征一下吧。他长得很像那幅鲁迅留学日本时穿制服的照片,为了更像,他专门留了一点儿小胡子。
阿黄这个类似狗名的外号,是季柏给他起的。有一次黄长征捧着一本画报正呆看出神,季柏凑过去瞧,是一个战士训犬员和他的战友“阿黄”的合影。“阿黄”是一只德国黑背,蹲在战士腿边,正襟危坐,两耳竖直。
黄长征见到季柏过来,就说:“你看这只军犬有多么威风!”季柏看出他这会有点犯傻,就逗他:“有没有你威风啊?”他抬脸看了季柏一眼,只好说:“比我威风多了。”季柏又推进一步:“它那么威风,你佩不佩服它啊?”他说:“佩服。”季柏再继续往前攻:“你那么佩服它,愿不愿意和它结婚啊?”“愿意。”两人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季柏就叫他阿黄,此名遂广为流传,取代了黄长征,后来连黄长征的父母都跟着叫起阿黄来了。
那时阿黄呈现出一些革命浪漫主义的倾向,还有一点苦行主义的苗头。他特别崇拜保尔·柯察金,为了磨练意志,他在床头铺了许多鹅卵石,睡在上面,锤炼筋骨。大家都认为矫揉造作,无事生非。后来卫生委员说他这样做床铺不整,有碍观瞻,令其把石头扔了。他就与人换了一架铁床,只铺一床单,光背睡其上,一觉醒来,满背压出钢丝床的花纹,和九纹龙史进的背一样。
有一次阿黄对季柏说:“你看保尔和冬妮娅一夜相拥而不胡来,多么高尚呀。要是换了你能不能做得到?”
季柏说:“这件事比较难做到,两人独处,时间那么长,关键是人家冬妮娅也乐意,换了我,肯定把冬妮娅给干了。你呢?”
阿黄脸上现出像入党宣誓般庄严肃穆的表情,说:“我能做到。”
但是不久,他的庄严肃穆就露馅了。
一天中午他俩去江湖游泳,路过一个石头垒起的简易厕所,季柏说:“等等,我先去尿泡尿。”季柏一边讲一边掏家伙,一抬头,吓一跳,里边正蹲着一个年轻女子,他扭头就跑,亏是家伙还没掏出来,不然以为调戏妇女了。“哎呀我的妈呀!”季柏一路叫着跑回来,“没尿成。”
“怎么啦?大白天见鬼啦?”阿黄问道。
季柏说:“里面有个女的。”
“漂不漂亮?”
“好像挺漂亮,没敢多看。”
“那你等等,我去看看。”阿黄真去了。
一会儿工夫他回来了:“什么漂亮?老太婆!”
季柏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都只二十岁出头,身材细瘦颀长,白净面皮,若按古人审美归类,应是那种带有几分公子气的书生。阿黄说季柏是“哥儿郎两眼贼灼灼”,季柏说阿黄是“腿长腰短白杨材。”
一次,阿黄突然问季柏说:“我想出一句诗来,你能不能对上下句?”季柏说:“行啊,你说说看。”
阿黄说:“我这句奇思妙想,气魄可是宏大,估计你很难对上。”接着说,“你听啊,‘若将月亮嫁太阳’你对一下?”
季柏随口答曰:“那肯定是‘生下崽子满天星’喽,是不是?”阿黄遂叹服:“反应太快。”
那年冬天,又出了“新生事物”,几支红卫兵长征队步行串联的壮举震动全国。两报一刊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之后有了“到大风大浪中去学会游泳”的指示,一时间徒步长征闹得很火热,人们传诵着两句名言:“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育万年松。”学校有关方面积极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凡是报名的集体和个人,都可以领取各种所需装备,一时间学校里到处可见抱着各种装备兴高采烈的师生。
那个冬天多雪,雪花飘飘洒洒,若断若续,天空一直是阴暗的,像一张忧郁的脸。
季柏望着窗外,心情和天空一样忧郁。一方面他不大喜欢加入群众运动的洪流,凡是大家都踊跃去做的,他便不肯去做,他有点自命不凡,不愿与众人为伍;另一方面他深感自己像个懦夫,总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不能奋身投入。他内心承认这种行动所具有的浪漫性和感召力,失去机会,也许会终身遗憾。可
他就是不想去,内心非常顽固,要说是怕苦怕累吧,似乎也不尽然,他是对别人的号召缺乏热情。他总是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抱怀疑、观望的态度,这种心理往往使他与周围的环境不甚和谐。
季柏正在一间小教室里忧心忡忡,突然门开了,一大堆御寒之物从外面走进来,只看见两条腿在下面动。羊皮大衣、棉鞋、皮帽子、毡筒、棉手套,还有棉衣、棉裤、棉被、绒衣、绒裤、绒毯……好家伙,半个冬装仓库自己走进来了!
从这一大堆东西后面露出一张脸来,正是阿黄。
“以后不许再叫我阿黄了,我黄长征要开始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长征啦!”
阿黄已经领好了这一大堆东西,下定决心徒步从乌鲁木齐走到北京。他兴致勃勃,两眼闪烁出迷幻的光彩。万丈雄心、千古壮举以及想像中的沿途见闻奇遇,使他像一只临窗之鸟,恨不能立即飞上征途。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阿黄说,“只有和你结伴长行最能使我高兴,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吧!想一想,将来我们老了,回想起这件事该多么自豪!我们有过‘长征’的经历,一个老红卫兵,和现在的老红军一样啊……”
阿黄言辞恳切,几近哀求,他是真心地想要拉季柏去“长征”的,可是季柏不知从哪儿来的坚定,百般劝说,就是不为所动,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阿黄说:“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季柏说:“那是写诗。”
阿黄说:“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季柏说:“有赤兔马我便去。”
阿黄见说不动季柏,长叹一声,深情道:“那今天就算话别了。”说完,开始试征衣,一件一件全部套在身上,成了一只北极熊。手里若是再拿上一副弓箭,就是标准的爱斯基摩人了。
出门时,因为所穿太厚,阿黄竟卡在小教室门间,进退不能。他喊道:“快来帮帮我!”
季柏不动,故意站在门边看他那副滑稽样子。阿黄像个大棉包卡在门上,拱不出去。季柏在他屁股后面踹了几脚,稍有挪动,仍不得出。阿黄便退后几步,猛冲过去,一肩撞出教室。
“我会给你写信的……”最后阿黄在走廊喊着。
“对不起了……阿黄再见……”
阿黄走后,果然每到一大站便给季柏来信,并告回信到下一站的固定地点。
一两个月之后,许多长征队都回来了,因为大多数都坐了火车、汽车。据告,黄长征成了沿途闻名的人物。一是独行,二是拒不乘车,走到某地时,曾遇同校另系的一支长征队,被对方几番劝导,上了火车,车行间心生后悔,又跳下火车,往回步行几十里,至上车处,再往前重走。乘了火车的这一段路,他执意是不能算的。
季柏闻之,大为感动,始知阿黄此人日后必非凡器也。阿黄走到西安时,收到季柏一封信,内附一首专为他写的长诗,约有两三百行,题为《想说几句话,给阿黄……》,赞美阿黄的坚韧精神,自己也不免有忏悔之意,在这件事上,他觉得很有些对不起阿黄。
后来,黄长征独自步行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