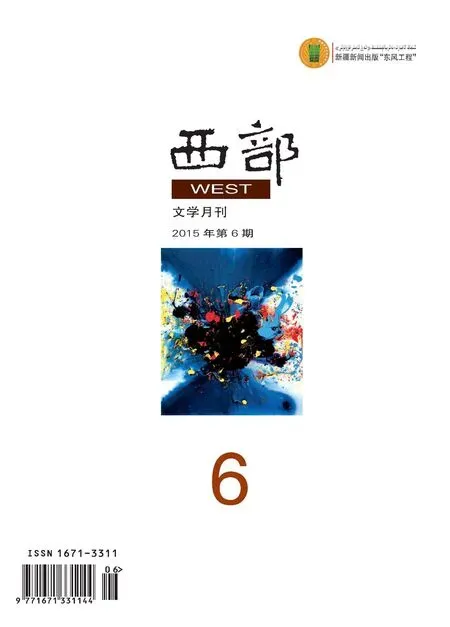黄毅的诗
2015-11-18黄毅
怀念自己
相信我还健在
肃穆的胡子 静止的芦荻
疏松的牙齿打开栅栏门
这遍野荒芜的家园
唯有语言在烛照
在西边的小镇
我怀想许多远方的人
从当地人那里我学会
羊肉的烹煮手法
洋葱和胡萝卜
还有地道的土盐
这种混合的吃法
容易让人忘了陌生和客套
我怀想远方的人
实际上也是在猜度
远方的人是否在遗忘我
我的健在意味着
许多人将相继离去
总有很多的时间
考虑自己的事
而先前许多人
总用毕生去思恋别人
趁现在是冬天
没有青草 羊很瘦
不会有人来打搅
我有充足的时间怀念自己
雪中即景
不明身份不明动机的雪
夜晚忽然劫持春天
白色恐怖之下
鸟雀噤声 高筑于枝桠间的巢
仿佛藏匿的监控器材
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只有树木夹峙下的一径小路
把未来引向风雪的深处
鸟都停翅了
我们却幻想飞翔
在一个多变的时节
即使拥有足够的财富和美女
也不能确保上天按照人的意志行事
麻将碰撞出清脆的欲望
红色指甲油愈发妖娆
谁的咖啡苦尽甘来
没有喝上的酒开始变酸变涩
一群不能按时起飞的人
无所事事又心事重重
看雪花狂舞 痒痒的腋下
似有翅羽萌出
雪依旧 春无迹
被囚禁的人质
是春天以及我们
时间之流速
那时的天空一定很混乱
在鸟翅的分配下
最蓝的一块给了村庄
每个人的头顶因此而阳光
每个人的阳光因此而有了姓氏
河水都找到了根
流浪四散的庄稼纷纷打听回家的路
流着汗水 吟着颂歌
谁的庄稼就散发谁的气味
拐着弯的河流
有着最直接的想法
能够留住人
就留住了牲畜
能够留住牲畜就留住了整个村庄
有人有牲畜的地方
才是有意义的流向
而时间流速均匀
而亿万年的时间
却流向无边无涯的荒芜
谁想起了村庄
只有忘记才可能想起
炊烟散尽
最后晚餐的余味
只有在下一次饥馑到来时
才被重新咀嚼
房屋坍圮
最后一宿交还的炽烈
只有在寒风四起时
才被再次忆及
村庄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村庄也不是一天就溃散的
逃离家园的人
总是行色匆匆不吭一声
总是把愿望和几块墙基石埋得很深
总是不肯再回一下头
总是让他们的子孙
在几百年之后一不留神吐出乡音
总是在无法考证的年代
説出天干地支
曾经用来支撑村庄的
直挺的梁桁和欲朽的椽子
横七竖八的样子
仿佛一地的胳膊和腿
先人们骨骼坚实的姿势
以及骨节粗大的形骸
让我们欲哭无泪
遥念那片土地上
未被时间掩埋的一切
想说永别的我们
只能说再见
还有什么比躺在大地上放心
还有什么比躺在大地上放心
一坡青草胜似我青春的狂乱
一坡阳光埋伏了若干年之后的煦暖
耳畔不绝于耳的小虫私语
若有若无的风带来巴尔鲁克山的夏天
还有什么比躺在大地上踏实
脊骨抵着潮湿的草地 渐渐觉出一种硬
此刻的心音 向大地的深处嬗递
轻轻重重的 回声来自一千年之后
还有什么比躺在大地上随意
近旁的一只牧羊犬侧卧成一种意向
打一个毫无美感的哈欠
大张的嘴 犬齿闪烁
中午的阳光肥美如手抓肉
还有什么比躺在大地上宿命
一坨新鲜的牛粪黄得耀目
它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等待阳光让它慢慢变白
最终冒出一缕蓝烟
还有什么比躺在大地上具有画面感
我 青草 牧羊犬还有一坨牛粪
构成很有表达的瞬间
成为时间的内容
时间流逝 我成为永恒
五月
堕入无边黑暗
手的摸索充满激情
这难以穿越的地方
绵软 耀眼 下陷 热气蒸腾
舌尖的那一束爝火
照亮你的头颅
在布满牙齿的通道
一切矜持的肉块
都被咀嚼成呻唤
两只鸽子 倦飞的鸽子
缄默无声 粉红的眼睛
被惊扰后睁大
这静止的飞翔
把动感凸为浑圆
坠入空茫
在相互攀爬 挣扎的
手臂 如藤如蔓
缠绕 纠葛 无所适从
颤栗的指尖走过
身后留下一片喘息
你这钢铁战士燃烧
灼烫 壮大 坚实 醒目
脚下是深不可测的黑
攥紧 牢牢握住
在漫长的瞬间 体味
一生的短暂
拥紧把自卑挤压出去
碰撞将勇气点燃
一万种设想赶不上一次
最卑微的行动
山草在春天葳蕤
溪水淙然 气象万千的山谷
远足者终于找到
那一隙秘境
无边的黑暗
进入者在忘记进入
柔软的包围 坚硬的突围
短兵相接的巷战
这两败俱伤的战争
胜利的只有时间
军号已吹响 钢枪也擦亮
太阳在急剧膨胀
欲喷欲礴的太阳突破
黑暗 凄美的霞光
只在一瞬间湮没
一生一世
沙滩上两尾鱼
两尾搁浅的赤身裸体的鱼
从此一生将经受大海的诱惑
一张鸡蛋煎饼还有
一张鸡蛋煎饼
被摊在同一口铁锅里
背负着一生的火与灼烫
疼痛而愉悦
无始无终 无边无涯
在鱼儿的呼唤中
一条鱼在水中呼唤我
远隔那么多重的水
我不知道还要走过几道门槛
天蓝的有些离奇
鱼儿怎么就知晓
星光在凋谢
水下难道也有震感
那些游动的族群
脊骨摆动自如
她们怎么了解我的椎间盘是否滑脱
还有我的名字
一见水就会融化
可她们依旧呼唤我
就算我不在山顶
也无法穿越雾霭
一条鱼在水中呼唤我
我在山顶呼唤谁
在鱼的呼唤中
我愈来愈年轻
愈来愈自信
愈来愈宿命
我感知到了一种宗教
布道者的宣喻和箴言
在水面升起
而我的影子总是飘曳不定
像早年的一场恋爱
内在的湖被鱼儿的穿梭打乱
我的定力只能让我成为佛寺门前的一棵树
听不见的呼唤
并不是没有呼唤
关闭耳鼓 割掉耳朵
我看见鱼儿的嘴仍在一张一合
我什么也听——不——到——
远徙之鸟
鸟的行走越来越迟缓
留在天空的脚印被雨水冲刷干净
天空朝地 大路朝天
人和鸟各走各的道
所谓飞翔
不过是远离一切
而接近某种情感
天空的瓦青色贴上翅膀
因此翅膀宁静而深邃
风洗白翅腋下的羽毛
像河滩涌动不止的芦花
结痂的箭伤重又被尖锐的山冈划破
骨头开始在肌肉里咔咔作响
充满阳光的翅管像灌浆的麦穗
因接近成熟而摇曳不定
太阳在身后倒下
鸟喙所指的方向
必定是明日站起的地方
而鸟越来越迟缓
鸟的坠落击碎万顷碧波
鸟的凋零裸露嶙峋的苍空
果与树
苹果的哭声谁也不会听见
被摘下的苹果 一截果把
一截脐带般的把柄 是一种永诀
最终将握在谁的手中
带着母体最后的余温和屁股上的胎青
回望一眼空空的枝头
精赤条条地从树上跳下
开始此生的漫游
所有的苹果都选择远方
远方的苹果已不是苹果
(自己落地的苹果离树最近
也最先腐烂成一坨酒香)
农用车汽车火车还有飞机
各种速度的运载工具让苹果饱尝
空间变幻带来的陌生孤独
在超市里 一只苹果
保持着最初的清纯
塞进菜篮子花布兜和塑料袋
听一个动作迟缓的家庭主妇
唠叨今年的苹果个头太小
(苹果们不自信地相互摸一摸
都有些皱巴巴的感觉)
被端上筵席或婚礼
水晶灯却使一个个出落得饱满而性感
比新娘的脸蛋红艳十倍
去皮器 刀子
再漂亮的衣裳被剥去
白色的酮体其实差不多
只要甜过只要香过
只要浑圆得没有一丝破绽
一只苹果就会有好的前程
一只苹果总会抵达命定的地方
就算有不愿去远方的苹果
幸运地砸在了牛顿的头上
一只大于宇宙的苹果
一只小于尘埃的苹果
苹果的定律便是
一直往下落
去了远方的苹果再没有音讯
从没有一只探望过生养它的果树
空空的枝头 秋霜濡红的叶片
也纷纷下落
再没有牵挂的枝桠
托举着巨大的晴空
从一个字出发的事情
喧哗与骚动
维系着内心的宁静
回忆一匹马童年的快乐
颤抖的手指
分辨家族的徽标
灵魂升天
肉体入地
从一个字出发的事情
到一本书仍不能完成
某一种格局
是芬芳与芬芳的对峙
丰盈与丰盈的抵抗
而在一种无端的消耗中
流星撕一道美丽的伤口
赠予何人
飞不走的鸟变成了云
吹不倒的草都是人
马蹄留下的空巢
谁来居住
被人抛弃的耳朵
栖满嗡嗡的蜂群
阳光尸横遍野的日子
想起秋收的季节
粉红的乳头和星星一起点亮
宽松的裙裾与鹰翅一同高扬
收获点什么已不重要
在一个遍地流金的九月
总难忘耕牛穿裂的鼻孔
点点下滴的黑血
那么你是谁
参差的手指
涡旋的螺纹 危险的下坠
头发指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眼睛掘出致命的陷阱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一些风启发了另外的风
一些眼睛点亮了另外的眼睛
由此而去
西风瘦马早已熄灭
惟古道之烛幽幽暗暗
惟朝觐的心愿明明灭灭
千英寻之外
蜕皮的道路
一节一节蠕动
一些疼痛在骨头里咆哮
铁器丢失了锋刃
锋刃丢失了光明
更多的红色在人的身体里奔走
不能相信河流会如期而至
无边的苍翠只容一足
而草在不断后退
家园的孤岛
牛哞替代了鸥鸟
人变成了鲨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