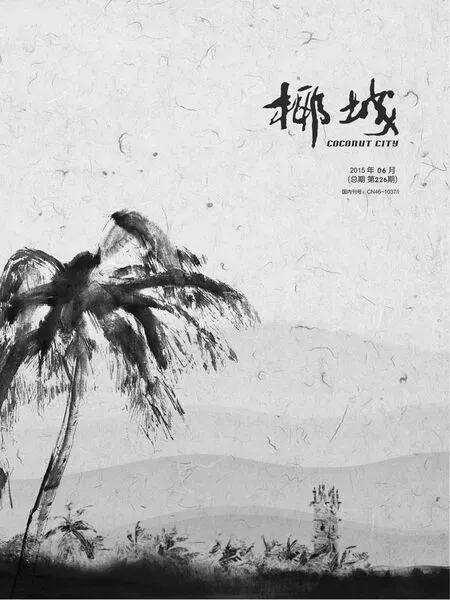青春在青橙里慢慢睡着
2015-11-17胡识
■胡识
青春在青橙里慢慢睡着
■胡识
这些天,我在集市上经常看到有卖栀子花和橙子的。
小女孩用粉红色的脸盆盛放橙子,用水浸着,摆在路摊边。
好久不曾尝过炒橙子的滋味了。这些时令的食材,每年只有这个时节才会上市。于是,我买了些栀子花和橙子,各炒了一盘,做成午餐,瞬息旧时家乡的记忆,又重上心头。
老家以前是种橙树的。一条大河,绕老家流过,村子三面环水,另一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河堤,逶迤延绵,沿河而筑。堤内是村子,堤外是沙洲。那时,堤内堤外,都是大片大片的桔树和橙树林。
清明前后,橙树和桔树开花,雪白的花朵缀满碧绿的枝叶间,远远望去,林子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初雪,隐约地渗透出几分仙风道骨。橙树和桔树开花时,整个村子都是甜蜜的。一株橙树,花香可以袭染半个村子,更何况到处都是成片成片的橙树和桔树。花香从橙树和桔树中轻拂而来,空气中似乎流动着隐形的香雾,漫过河堤,拂过门槛,渗入瓦缝,沁入心脾。整个村子在恬静的香味里惬意地做着梦儿。
年少时,每到橙树开花时节,我们便趁着放鹅时,把鹅赶到橙树林边的草地上,让它们啄食青草,我们便爬到树上去吮吸橙花蜜。橙花和桔花形状差不多,但比桔花要硕大一些,花芯里的蜜汁也要多些。村子的橙树和桔树都有几十年的树龄,粗大的要好几个人才能抱得过来,树冠高大的,可达三四丈。
那时,我常爱爬到靠近大河的那株橙树上去。因为它最高大,树荫占地近半亩,更主要的是它有许多横斜的粗枝靠近地面,便于攀爬,便于斜躺,便于摇动横枝荡秋千。爬上树,攀着橙花,一边用舌尖推开花瓣,一朵一朵地吮吸花蜜,一边听着河水流过沙滩的哗哗声,这种香甜的日子,要持续近半个月的时间,直到橙花谢尽。
橙花谢后,万蜂飞去,橙树归于清寂。
大概半个月后,便到了捡橙子的季节,树下又开始热闹起来。
橙花纷纷摇落后,枝桠间便开始结出青青的橙子。到初夏,已是青橙如丸,绿桔似豆。有时因风雨的摇落,有时因肥力不济,便常常有橙子从树上落下来。
而落下来的橙子,就成了大家争相捡拾的宝贝。
老家种植的橙树,原本是一种药材。丸豆大小的橙子,切开晒干后,称作枳实,是一味良药。也可以作为一种食材,加工成餐桌上的美食。
那时,上学放学的路上,我总会带着一个塑料袋,沿着河堤,到堤内地外的橙树林下去捡拾橙子。捡橙子,在那时真是一种乐趣。一拨人,像竞赛一样,在树下、草丛里、沟坎间,比谁最眼尖,手脚最利索。最难找的是草丛里的,青绿色的橙子和青草一色,很难发现。
有时,还要听觉敏锐。只要听见“扑簌簌”的响声,就知道一定是有橙子落下来了,就赶紧循着橙子落地声去寻捡。总是捡完一片树林,又赶紧跑向另一片树林。这时要比谁跑得快。跑在前头的先捡,落在后头的人能捡到的就不多了。有时也要比智慧,别人跑向这片橙树林,你就跑向另外一片橙树林,这样,你就照样可以先于别人捡到橙子。
放学回家,每个人书包里除了皱巴巴的几本书外,大多是一袋或半袋的橙子。
回家,便把橙子倒在竹匾晾晒。大一点的橙子,要切成两半,切面朝上摊开晒。小一点的直接晒,或是倒在脸盆里,洗净后,用井水浸泡。
浸泡上十来天后,橙子由青绿色逐渐变成了灰褐色,用手一捏,感觉橙子有些泥酥,水也由清水变成了浅酱色。这时的橙子便可捞起来做菜了。
把捞起来的橙子用清水洗净,在砧板上切碎。烧热锅,油热后,倒入蒜瓣和橙子,撒上盐,翻炒,然后加入适量水,焖十来分钟,再撒上辣椒粉,便可出锅了。
新炒的橙子,口感有些硬,可以在蒸饭时,隔碗放在饭上蒸一蒸,便会变得酥软。这时,橙子的味道更好。夹入口中,细细嚼之,微苦,稍停,一股淡淡的甘甜便会从舌根漫溯而来。据大人们说,经常食用橙子,可以消肠化积,有利脾胃。
值得一提的是,浸泡橙子的水,也不是毫无用处的。那时,乡下多喂养鸭子。每到清明前后,各家都要买上八九十来只鸭子,喂养大了好过端午节。喂鸭子,那时除了米饭外,一般多是挖蚯蚓喂食。而浸泡过橙子的水,带有橙子的气味。只要找到有蚯蚓排泄粪便的地方,倒下去,不出三五分钟,蚯蚓便会自己乖乖地爬出地面,这时只要赶着鸭子吃蚯蚓就行了,而不必动手刨地去挖。
农历六七月,便到了摘橙子的季节。这时,各家大人小孩齐上阵。小孩人小身轻,上树去摘;大人一般用竹竿绑了钩镰,在树下钩。顿时,扑簌有声,树下,青橙满地。
青橙摘回家后,便要在天晴的日子里,把它一个个用刀横切成两半,然后切口朝上,一片一片的铺晒在晒簟里。晒橙,是一件需要耐心且繁琐的事情。这时的青橙,已有半拳大小,内有瓤肉,一天两天不易晒干。因此每个晴日,都要把橙片倒在晒簟,铺开,一片一片翻转过来,使切口朝上。几担橙子,成千上万片,往往需要翻转几个小时,晒一次橙子,要出一身汗。
就这样,晒上半个月左右,用手指掐一掐橙片中心,瓤肉干燥,再掏一把橙片搓一搓,哗哗有声,青橙也就晒得差不多了。这时晒好的橙子叫做枳壳。上好的枳壳,应当是外皮青黑,肉色黄白,切口圆整,橙心似菊,有一股淡淡的橙子清香。
枳壳晾晒好后,便只需等待药材商上门来收购了。
老家的橙子,是药用的。夏季就摘下来了。偶有遗留在树上的,到了冬季,经霜后,便变成了橙黄色。虽然色泽诱人,但摘下来,剥皮入口,就会酸得人直流口水。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周邦彦的《少年游》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下了北宋京城橙子的流行吃法。据说橙子蘸盐吃,可以调减酸味,使口感更好。
周邦彦当年所尝的橙子,我想,定不会是脐橙。因为脐橙从国外引入中国,至今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从那酸味看,是不是老家那样的橙子,就不得而知了。若真是老家那样的酸橙,那可真是辛苦了北宋那些娇贵的口舌。
在一场特大冰灾后,老家的橙树桔树冻死过半,余下的在随后的几年也陆陆续续损毁殆尽,从此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恢复种植。每当初夏橙子上市,就会想起老家当初房前屋后堤内堤外一片片的橙林,就不由地心痛。心痛的不仅是老家从此失去了一项传统特色产业,更心痛老家再也没了当年橙林夹岸,橙花似雪,青橙满枝的胜景。
这些年,每每忆起故乡,总如青橙入口,亦苦亦甜。我想,这就是青春在青橙里慢慢睡着的味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