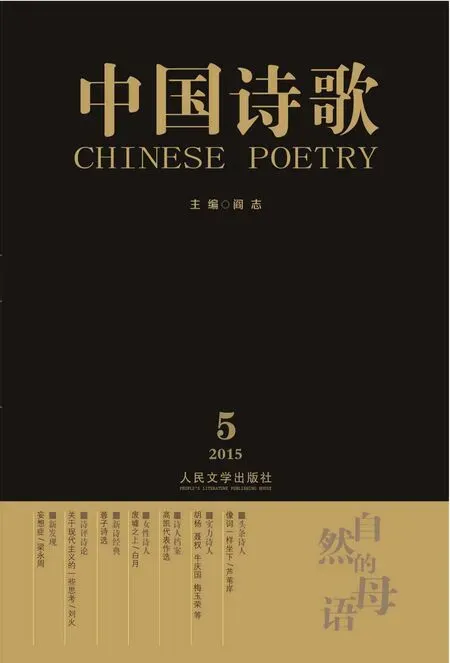诗学观点
2015-11-17孙凤玲
□孙凤玲/辑
诗学观点
□孙凤玲/辑
●张炜认为许多时候一个写作者应该有勇气让自己懒下来、闲下来,给自己一点闲暇才好。衡量一个生命是否足够优秀,还有一个标准可以使用,就是看他能否寂寞自己。寂寞是可怕的,一说到人的不快,常常说他“很寂寞”。其实正因为寂寞,才会有特别的思想在孕育和发现。
(张炜:《大天才总有大寂寞》,《文艺报》2015年2月9日)
●李建军认为公民性是现代诗人的重要标志。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公民,是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公民诗人。公民诗人即政治诗人。他应该具有现代的政治激情,能够敏锐地感知并表达自己时代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情绪。
(李建军:《尊严之光闪耀在讽刺的利剑上——解读曼德尔施塔姆的一首诗》,《名作欣赏》2015年1月上旬刊)
●车延高认为从创作角度看灵感是诗人想象空间里的一盏灯。灵感需要天分作祟,但不能只等“一片明月照姑苏”。灵感产生于在土地上生活的人类的脑体之中,是生活中偶然和必然碰撞后形成的意识和思维的原生态极光。可以刹那照亮读者审美的眼睛。
(车延高:《留心是另一只眼睛》,《诗刊》2015年1月上半月刊)
●杨匡汉认为“现代新诗”是一种文化立场和艺术态度。我们被形形色色的文化观念乃至意识形态所裹挟。作为现代诗人,须有:心灵的自由和独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提供与现代人生存有关的严格又新鲜的感觉;寻找新的情感逻辑和语言模式;有经过个性化处理的独特的心态和姿态。而这一切,都需要和现代生活、现代人的命运息息相通。
(杨匡汉:《诗学广场·堂郡絮语》,《诗刊》2015年1月上半月刊)
●帕斯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个族系,一个家族。它分散在几个大陆,两个世纪以来,它从我们经受的变迁和不幸——公众的冷漠、宗教、政治、学术和性的正统思想的孤立和审判——中幸存下来。作为一种传统而不是作为学说,它才得以存在和发生变化,并且具有了多样性:每一次诗歌冒险都不同,每一个诗人都在这片奇妙的语言之林里种下了一棵不同的树。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对现时的寻求》,《世界文学》2014年第6期)
●陈亮认为余秀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网络诗人”。她诗歌中的好与不好,都与“在网络时代写诗”这个背景有关。网络时代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平抑了信息的不对等。以前,经典作品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读到的,现在却可以随时在网上读到。网络上的交流互动也比以前多得多。这使很多人的写作可以在网络滋养下很快成长。这也正是余秀华这个被冠以“农妇”的诗人不写乡土诗、不写田园诗,反倒写得很“洋气”的原因。在网上,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在别处”。
(陈亮:《余秀华:在生活与诗歌的双重坐标中》,《中国艺术报》2015年2月4日)
●沈奇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享有“诗人”的称誉,早已不仅仅是单纯文本意义上的认领,而更多是基于人本意义上的指代——最终,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诗歌人格”的东西,及其所焕发的诗歌精神,感召并不断赢得普凡的人们,对这一过于古老的“艺术行当”依然心存眷顾和敬重。同时,在以日益矮化、平面化以及游戏化的“话语盛宴”取代“生命仪式”的当下诗歌写作中,对纯正超迈的诗歌人格与诗歌精神的重新关注与呼唤,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凸显在新世纪的现代汉诗之行程中。
(沈奇:《在游历中超越——再论张墨兼评其旅行诗集〈独钓空〉》,《华文文学》2015年第1期)
●余光中认为中文是非常优美的文字,我比较看重旧小说介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那份文辞之美,注重文字本身的美,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是中文写作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而对文学初写者来说,刚写诗歌时不要感叹人生,不写哲理,而写个人的、家庭的情感。诗要由一个主题、思念、感情出发,靠具体的形象表达出来。比如曹植的《七步诗》,正是用看得见的具体的东西,把握看不见的情绪的最佳案例。意象和节奏是诗歌表达的两大重点,学生不妨从锻炼意象开始。
(张丽凤:《访问余光中先生》,《华文文学》2014年第6期)
●范稳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扎根生活犹如在挖掘一口井,每个作家其实都在挖自己的井,前人挖到二十米深了,你挖到二十一米,你就比前人聪明,将来还会有人挖到二十二米、三十米,他又比你高明。面对一块蕴藏量丰厚的文学矿藏,不断地挖掘下去总是快乐的。在这个不断掘进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生活的源泉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活永远大于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力。生活总是丰沛的,它对热爱生活的人的回馈也是丰沛的。
(范稳:《大地是我的另一间书房》,《青海湖》2015年第2期)
●张光昕认为不同于西方的宗教语境为诗歌贡献的此岸和彼岸的概念,中国诗歌更擅长在世俗生活里表现切近和遥远的感受。汉语新诗经受近一百年的风雨历练,在神秘性的加减乘除中,诗人的写作如同跳房子游戏那样曲折展开,渴望在切近中生出遥远。这个词与物在交融之后再度分离的过程,是汉语诗歌进入现代以来开展精神转换的关键枢纽。
(张光昕:《消逝性小引——读李少君近作》,《创作与评论》2015年1月上半月刊)
●杨宗翰认为赵丽华的作品让网络众多博客议论纷纷,不满者嘲讽这些根本不算是诗,其中的口语更近乎废话;有些人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她是在“为中国诗歌受难”,诗歌应该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我举双手双脚支持创作自由,也赞同写作者可以适度以日常口语入诗,其目的在于提升语言的鲜活度,更可让读者倍感亲切;若在诗中毫无节制地滥用口语,或仅凭二三佳言警句就妄称是诗,那只是误把口水当成口语罢了。这种诗人既低估了读者也低估了诗。
(杨宗翰王觅:《与台湾新诗、评论的历史对决》,《创作与评论》2015年1月下半月刊)
●勒克莱齐奥认为一个作家再出名,也是有限度的。文学不是一切,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作家,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作家,越有名的时候,坟墓也会离你越近。真正要记住的,不是名声,而是对别人的责任。
(《文学和名声——莫言对话勒克莱齐奥》,《江南》2015年第1期)
●梁雪波认为长诗素来是考验一个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文体形式,一首长诗是否成功,除了叙述、结构、空间、时间等等需要考虑的因素之外,尤为重要的还有语气和语势的把握。中国古典文论中强调“文以气为主”,韩愈说“气盛言宜”,就诗歌来说,一首好的长诗应该是气韵贯通、一气呵成的,即在一首诗中,语象、语流与诗思应保持协同共振,语流的推进与涌动不能出现断裂……帕斯认为,长诗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整体中的变化,平直与奇异的结合。
(梁雪波:《一只虎的五种祛魅方式——读周伦佑长诗〈象形虎〉》,《扬子江》2015年第1期)
●马永波认为当下诗歌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精神的力量,过于陷入“抽象”之中。我用“抽象”这个词来指涉与现实脱节,心灵苍白等等现象。就我所阅读的范围(网络、个人诗集、官办与民办刊物、选集)而言,诗歌缺乏坚实的内涵,流于一种液态的难于把捉的情绪,这是最大的一个弊病。如果不是心灵本身缺乏尝试和敏感度的话,那可能就是积淀不够,不够踏实,有一点感觉就赶紧写成诗,所以诗歌不能像雕塑一样立起来,而是像泼在地上的水一样渐渐流失。
(马永波:《对难度写作的再倡导》,《诗林》2014年第6期)
●刘波认为诗歌应该是人生阅读乃至丰富实践的副产品,真正的“人生之诗”不是刻意写出来的,而是从内心流出来的。这样,写作是否凭借意志、兴趣或惯性,都无关紧要了。综合写作是中年之后的诗人在诗歌上的大道,笔耕不辍是前提,反思内海是必要的功课,锤炼技艺和冒险精神则是自我提升的关键。能担当得起“永恒的伟人”的诗人,当有大情怀和大境界,而不是亦步亦趋,那种多维度和综合性的禀赋都集中在他笔下时,惟有一种不妥协的力量会让他与众人区别开来,这种不妥协里有独立的立场、独特的审美以及独到的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经典诗人的素质和修养。
(刘波:《论新世纪诗歌的信任危机和精神突围》,《创作与评论》2014年12月下半月刊)
●邹建军、杜雪琴认为,江鹄诗歌是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一种独特的存在,以苦难为其重要的主题与情感的基调,并创造了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美学价值。其苦难的基调由少年的苦难、男性的苦难、女性的苦难与乡村的苦难四种主题所构成,并由此带来了以沧桑与凄凉为主导的艺术风格。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反映自我的生活并始终伴随以怜悯为主体的人道主义情怀,给当代诗歌创作以多样的启示。
(《苦难的光辉——论江鹄诗歌的情感基调及其美学价值》,《江汉论坛》2014年第10期)
●刘庆邦认为语言是一个作家的标志,也是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所在。如果语言没有个性、很平庸,就没有资格称为作家……我自己总结,好的语言应该首先是有味道。味道是精神性的,确实存在。第二是有灵气。文字是死的东西,你必须在里边注入作家的灵气,一看就是独特个性化的语言……这种气是作家的气质,会形成一种气场。再一个就是陌生化的语言。我总结了几条:不用陈词滥调,别人说过的语言我们尽量不用。尽量少用成语,成熟已经是封闭性的,能不用就不用。尽量不用流行语。在媒体上很热的时髦语言,到作家这里要排斥。
(刘庆邦:《坚实的树灵动的影善意的心》,《中国艺术报》2015年2月9日)
●肖水认为写什么样的诗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部分。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会被幻想所烘托,习惯高蹈而行,那时候“诗”“行”分裂情有可原。但当我们在年龄和气质上都已然成熟的时候,“诗”“行”不仅难以分裂,即便分裂了,诗所透露出灵魂的信息也定有大的损耗……在我看来,诗人,就如同蝙蝠——“这些似鸟/而不是鸟的生物,浑身漆黑/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子”——它们是丑陋的,也是无名的。它们在我们生活的阴影中翻飞,命运这个词因为它们在白日、繁华之世的隐身和匿名而变得陡峭和尖利。
(肖水:《某物之来临:我与〈西川诗选〉》,《名作欣赏》2014年12月上旬刊)
●臧棣认为诗歌中的谜源于一种独特的尊重——即我们不该浪费语言的直觉,诗应该以世界的秘密为素材。诗有两个特殊的伴侣:完美的睡眠,完美的清醒。诗的完美,取决于完美的睡眠的不完美。诗的高贵,取决于诗人如何定义完美的清醒中的悲悯。怀着谦卑受益于词语,这是某种力量在人生的孤独中教会我们做的事情。而诗歌要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怀着骄傲受益于词语。对诗而言,修辞的最隐秘的思想动机,不是用一个词拯救一首诗,而是用一首诗拯救一个词。
(臧棣:《“诗道鳟燕”选萃》,《诗林》2015年第1期)
●刘洁岷认为我们可以以逆反的思维来揣摩——诗歌不是什么。诗歌是围绕着“抒情”的——这种抒情包涵着冷抒情与反抒情——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核心和本源问题,只是在当代,我们在以经验代换、提升这种抒情。一种生存中积攒的能量构成一种澄澈的命名般的语言传达。新诗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本能地排拒了那种凌空蹈虚的高调,但我们也厌恶将诗歌等同于生活记录簿的“现实主义”。诗歌不是发癔症也不是模仿实在之物,诗歌的魂魄是在词语的内在旋律中找寻或创造出“诗性意义”。这里,诗人需要缪斯附体,而从事一种天才的劳动。
(刘洁岷《“爸爸惩罚核桃夹的方式”——对青蓖“非风格化”诗歌的印象与细读》,《作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