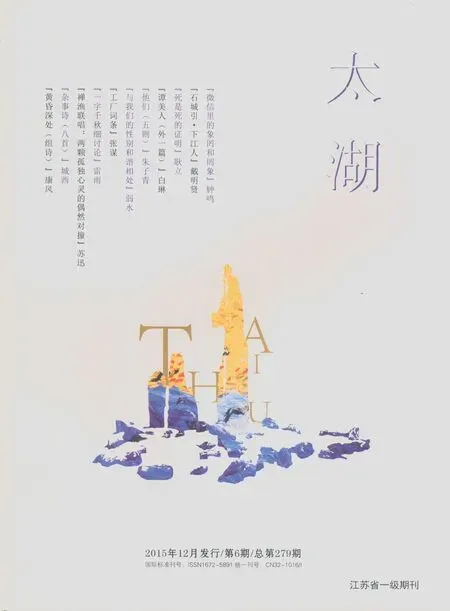各领风骚 殊途同归——民乐两巨星刘天华与华彦钧艺术人生媲美
2015-11-17邓仲威
邓仲威
各领风骚殊途同归——民乐两巨星刘天华与华彦钧艺术人生媲美
邓仲威
刘天华与华彦钧 (阿炳)这两颗民乐巨星、二胡演奏的一代宗师,是咱无锡的瑰宝,是中华民族音乐的骄傲。他俩都是非常爱国的中国人,都是为音乐而生的旷世奇才,他们各自走着不同的音乐之路,同时登临了民乐高峰。
两人是同时代的人,天华小阿炳两岁,可叹阿炳58岁死于肺痨,天华更可惜37岁就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人们很难设想,倘若上苍多给他俩几十年寿命,我国的民乐将会何等的辉煌。在人生的大海里,二人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那是1921年,天华27岁、阿炳29岁。那时阿炳的眼睛尚未失明,二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天华赞叹阿炳演奏的 《阳春》精妙绝伦,堪称无双。天华的二胡和琵琶技艺更令阿炳赞赏有加,对阿炳的琴技是一大促进。尤其是天华一声声的 “请问”、“讨教”,为人之谦恭,给阿炳很大教益。及至后来天华英年早逝,阿炳每念及此,总是拄杖慨叹 “可惜啊可惜”。
刘天华的 《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寒风春曲》、《龙船》等名曲,都是现代民乐的精品和极品,获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金曲殊荣,将永世留芳。综观两位艺术大师的人生轨迹,他们各自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天地里驰骋,是各领风骚、殊途同归。
两种不同的类型
两个都是为音乐而生的人,都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各种音乐、各种器乐都想学,只是受客观条件所限,致使二人各自涉及的范围和领域以及练就的器乐种类、艺术造诣、演奏技巧有所不同。
刘天华是典型的学院派文人,正宗的教育家、音乐家、作曲家,以二胡一代宗师著称,同时兼及琵琶、小号、军笛、大鼓、小提琴、钢琴。他自诩小提琴的功夫还要好过二胡,可惜一场猩红热使他猝然离开了人世,未能留下他优美的小提琴声。他是我国现代民乐的开拓者,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专业二胡学派的奠基人。
阿炳则是民间派,社会底层的草根艺人,是由道乐天地再进入民乐天地的民间艺人。阿炳长期在道乐天地里施展,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道乐高手,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二胡、琵琶前无古人,箫、笛、鼓、阮、三弦等也是技惊四座。阿炳作为现代民乐的先驱者,以 “三绝”二胡、琵琶、说唱而家喻户晓,尤以二胡 《二泉映月》盛名天下。阿炳对西洋音乐、西洋乐器以及音乐理论等方面的兴致其实也很浓,他什么都要学,只是客观条件压制了他的驰骋空间。阿炳的知音祝世匡盛巷大庭院里的钢琴等洋家伙不时吸引着阿炳,阿炳不会小号,可他的二胡演奏能出现清脆的喇叭声,《听松》一曲中更是军号声声,一片冲锋的号角。
创作意识和方式
一个是殚精竭虑,刻意而为之,一个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任由所为。刘天华是每当来了灵感,便边拉边记,作曲写谱,然后修订成曲,有时也倚马可待。如二胡曲《良宵》,1928年1月22日除夕那一天,他把一些无钱回家过年的师生请到家中团聚,由于大家一起勇敢地走过了残酷的1927年,此时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他对大家说:我想写一首曲子,作为今晚聚会的纪念。说着便随手拉出了优美的旋律,又随手在纸上飞快地记下了曲谱,不一会那首著名的即兴之作 《良宵》就这样诞生了。
阿炳则不然,他没有明确的作曲念头,甚至根本没有创作的想法,他只是随心所欲地拉出自己的心声,用琴声来叹苦经。阿炳总是说:我是 “瞎拉拉的”,那 (指 《二泉映月》)是我的随想曲、依心曲、自来腔。阿炳拉这首曲子,从39岁一直拉到48岁,随心所欲地拉了八年之久,才基本定型成曲,尚且还没给它起曲名。
传承途径
刘天华众多的传世之作,有赖众多出类拔萃的二胡和琵琶传人,诸如储师竹、蒋凤之、陈振铎、刘北茂、曹安和、陆修堂等人的欣赏与激励。天华的创作与传承,有课堂、有学生、有教材,讲课、排练、演出有条不紊,系统而又规范。1922年,北京大学创设音乐研究所,刘天华在这里从事了十年之久的 “改进国乐”的伟大事业,其音乐传承的途径远远超越了个体传承的范畴。刘天华把二胡演奏从随乐伴奏提高到独奏的地位,从民间草根艺人手里转移到高等学府,系统地编写二胡教材,并进行系统的训练,乃至亲自主编 《音乐杂志》传扬和声、对位与作曲法等音乐理论和技艺,此等涉猎广泛的音乐实践,以及其传承的深广,在中国音乐史上无人可与之相比。
阿炳没有团体,没有组织,他的一切演艺活动纯属个人行为。他是自己拉、叹苦经、诉心声,通过卖艺,街头往返,随情随心地 “瞎拉拉”自己的依心曲、自来腔,然后靠广大阿炳迷耳熟能详之后你哼我唱,口口相传,城乡递送,直至被伯乐慧眼认定为 “呕心沥血”之作,最后钢丝录音得以抢救,又经杨荫浏、吕骥等权威、学者及官方途径灌注唱片、课堂宣讲、电台播放等推广渠道才得以一飞冲天,名扬四海。
音乐实践的天地
一个在学校、课堂、办公室,书声琅琅,琴声悠悠;一个在雷尊殿、道观、道场,香火缭绕、道乐声声。
刘天华小时候常跟当地涌塔庙小和尚澈尘一起学习各种民族乐器,自打进入常州府学堂,便开始了正式的音乐追求与探索,学习小号、军笛和大鼓,接触西洋音乐,被聘任为常州五中军乐指导及音乐老师。20岁时,父亲病逝,天华开始用二胡来寄托他的哀伤并创作了 《病中吟》。24岁时,他演奏的琵琶曲 《十里埋伏》已经达到相当境界。25岁特意去开封学古琴。27岁进入北大的天华,开始了十年之久的 “改进国乐”的伟大事业,同时开始苦练小提琴至技惊四座的境地,且把二胡正式列为大学课程,改变了民间二胡的地位和声誉。一如其兄刘半农所言:“二胡原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刘天华在音乐领域卓有建树、盛誉乐坛。
阿炳双目失明之前的34年,尤其是因祸得福的童年和顾盼自雄的青年时代,他的生活几乎是固定在道观,在道教的天地里施展拳脚,在父亲兼师傅的华清和以及师爷朱老道的管教之下,最终炼成了道乐 “六场通”和民族器乐通才。阿炳一门心思、执着一念地追求他的功夫和神韵。失明以后的24年,为了有饭吃,开始彻底置身民乐天地,无论演奏或者说唱始终都是脱离乐队群体的个人行为,仅有催弟穿街走巷相依为伴,随心所欲地拉出了 《二泉映月》等一批民乐精品。
成才的途径
刘天华是上学、读书、练琴,小学、中学、大学,民乐、西乐,民族器乐、西洋器乐,爱好十分广泛,在音乐的海洋里滋生成长。
阿炳是8岁入道观,做小道童,颂经唱赞,潜心修练做道士的基本功、做法师的吃饭本领,天生的音乐胚子,兴趣又十分浓厚,整整34年,一直泡在道教音乐的天地里。自幼从道的阿炳,道乐的吹、拉、弹、打样样在行。双眼失明之后,才被迫改学新的谋生本领,一度心不甘、情不愿地从道教音乐的小乐队合奏的方式,逐渐以独自演奏二胡、琵琶、三弦等多种民族乐器的方式进入民乐天地。阿炳后半生上街卖艺谋生的24年音乐实践,是阿炳由道乐师逐渐蜕变蝶化为民乐大家的过程,这个由被迫到心甘情愿,终生献身民乐的过程,足以表明阿炳惊人的的韧劲、天赋和适者生存的本领,足以说明独一无二的阿炳现象的社会价值。
出身、门第
刘天华的江阴老家是一座二进十间三庭院612平方米的大宅。天华出生于一个清贫却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大家庭。父亲刘宝珊是清光绪的儒学生员,一位老教育家,曾创办翰墨林小学,颇富盛名。天华和他的兄弟刘半农、刘北茂一起接受了正规的早期教育。这是大户人家,书香门弟,正规学途,正常的家教。辛亥革命前后,天华读初中时曾一度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在家自学 《乐曲大宝》、《乐理概论》等专著,同时苦练多种民族器乐和西洋器乐。天华有出众的天赋,四岁起父亲开始对他启蒙教育,识字念诗,六岁时就能够作对咏诗,自小就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同样是一个为音乐而生的人,阿炳则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式的教育。他是私生子,无家,自幼丧母,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没有自家的庭院,寄人篱下,孤苦伶仃。他被送至东亭小泗房巷寄养,所幸春合村是当地有名的道士村,道乐声声熏陶着阿炳,奶妈杏娣滩簧、俚曲、小调整日哼哼唧唧耳濡目染着阿炳。奶妈的亲女儿、小阿炳三岁的彩彩,兄妹倆亲梅竹马,两小无猜,说说唱唱。阿炳可谓因祸而得福,在音乐的温床里成长。父亲华清和为雷尊殿当家道士,父子不敢相认。阿炳八岁时随父亲入道观当小道士,生活在道乐声声香火缭绕的雷尊殿里。除3年私塾学 《三字经》、《百家姓》、练习描红毛笔书法之外,始终生活在道观天地里。
创作行为和实质
一个是目的明确的创作歌曲,相当于命题作文。刘天华的 《良宵》、《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一大批曲子都是名符其实地创作出来的。天华短暂的一生创造了大批二胡、琵琶独奏曲,从1915年的处女作 《病中吟》到1932年5月最后一首作品 《烛影摇红》,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无人可比。天华的十首二胡独奏曲和47首练习曲,改变了当初二胡的先天不足、不能独奏、没有二胡独奏曲的命运,让二胡从此进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
阿炳的作品,史家一般认同有200来首的说法,但就创作的行为和实质而言,与文人学院派有所不同,他特具匠心,另辟蹊径,独树一帜。阿炳没有作曲的概念,他心里没有写歌作曲的念头,阿炳拉的、弹的许许多多花样繁多的曲子或曰片断、乐段,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曲子,他历来都是说 “我是瞎拉拉的”,这其实是阿炳的一句大实话。阿炳不像天华,专门学过《乐曲大宝》、《乐理概论》等专著,有扎实的乐理基础,系统地学过和声、对位与作曲法,天华对古代律吕学说,甚至昆曲、话剧、京剧等等烂熟于胸,可谓通晓中西音乐,学养深厚,作曲是手到擒来的事。阿炳不是科班出身,他的那点乐理知识是十来岁时,师爷朱老道教他击鼓、练琴时,给他教会的识工尺谱的能力。阿炳一生局限在民乐的范畴,对西洋音乐并无涉猎。文史资料中也不见阿炳有使用过五线谱的记载。尽管阿炳和他的师傅兼父亲的华清和一样,都是民族器乐的通才,但并未独立如天华一般文人学院派那样作曲,那是另一回事,是另一重天地。何况阿炳后半生双目失明,一个盲人,即使有创作的灵感或曰属于自己的乐段冒将出来,如何握笔记写,如何修改?阿炳眼瞎之后不可能再使用笔墨纸砚。综观阿炳钢丝录音抢救下来的那三首二胡曲和三首琵琶曲,他的作品都是在别人歌曲的基础上,凭他的兴趣、爱好和标准,来进行伤筋动骨、改头换面、脱胎换骨的改造,最后创新而成为属于阿炳特色的作品,《二泉映月》等六首曲子无一例外。这种得心应手、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一如最了解阿炳的天赋和才能的杨荫浏所说:“阿炳的音乐技术简直是 ‘无中生有 ‘,根本找不出一个真能与之相比的人。”阿炳是模仿、改造的高手,演绎创新的大师,这是阿炳现象 “中国的唯一”的另一个注脚。
刘天华、华彦钧两位民乐大师所走的路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惊人的天赋、毅力、智慧和才华,都有宽阔的境界和胸怀,都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搏精神,都是天才加勤奋的典范,都是非志无以成学的楷模。大师风范,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作者简介:
邓仲威,热衷于阿炳研究多年,江苏无锡人。已出版著作 《走进阿炳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