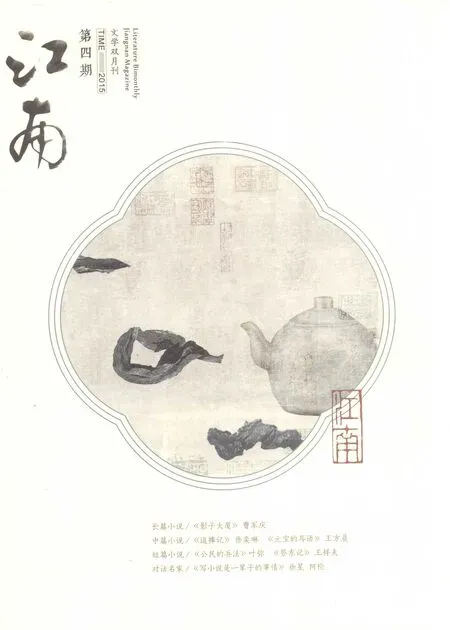登东记
2015-11-17王祥夫
□ 王祥夫
说到厕所,过去的大杂院,平房,机关大院,电影院,浴室,理发店,到处都有,在街上,走不远也都会有个厕所,没厕所能行吗?不行,人们吃了就要拉,一个人不拉屎能成吗?一天不拉还行,两天不拉这个人就会急了,三天不拉就得看医生了,如果十天半个月不拉那事可就大了,到时候你自己都会往医院里跑,找医生去为你灌肠,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没人愿意脱光了裤子让医生给你做那事。我们早先住平房的时候,那是很大的一个院子,房子是一排一排的,大门在北边,一进大门,左手是一排一排的房子,右手也是一排一排的房子,一共几排呢,左右一共十二排,也就是说左边从北到南是六排,右边从北到南是六排,这个院子不能算小,而那个大厕所在院子的南边靠东的地方,厕所当然会分男厕所和女厕所,男厕所在南边,女厕所在北边。厕所的门开在院子里,而可以掏毛厕的那些个粪坑却是在院子外边,那时候,乡下的老乡们会定期过来掏毛厕,也不会惊动什么人,在院子外边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我们那个院子的厕所很大,掏毛厕的一定会赶着一挂大车来,大骡子大马拉的那种大车。要是在夏天,下了急雨,雨水灌进了厕所,这就是麻烦事,就会破例要人去把话捎到乡下让乡下人进来一趟把粪掏一下。夏天的粪车上是许多大木桶,那木桶可真大,一个挨着一个,都还有盖子,是专门用来盛大粪的,因为是夏天,毛厕里的大粪是稀的干的都有,很不好掏,不像是冬天,大粪都冻硬了,硬得简直像石头一样,得要用工具把它们一块一块破开才能装到车上。所以,进城掏大粪最好是冬天,夏天干这活儿,谁都不会太愿意。但我们那个院子的厕所因为掏得勤,从来都不会稀汤洸水漾得满满的,除非是连着下几天大雨。乡下人进城掏大粪的时候,会在院子外的毛厕坑后边喊几嗓子,去解手的女人们就知道后边在掏粪了,该去的也就不去了,多走几步去别处解决了。
我们那时候住的大杂院通称“互助里”,这真是个很好听的名字,有劝诫的意思在里边,要人们凡事都互相招呼互相帮助着点。那时候谁都知道互助里是西门外一带的大里,分一栋、二栋、三栋、四栋,后来又有了五栋,每栋都有厕所,去厕所不会是个问题。而我们的小学校却只有一个,在三栋和四栋之间,那是一片空阔的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跑操踢足球,互助里五个栋的孩子们都在这个学校里边读书。学校里的厕所也是厕所门开在院子里,掏大粪的坑却在院子外。冬天掏大粪,可也真是辛苦,整个人要跳到毛厕坑里去,用铁钎子,铁铲子,“吭哧、吭哧”地把给冻得结结实实的大粪弄成一块儿一块儿的再装车。虽说是弄大粪,但这也是技术活儿,把冻得很结实的大粪铲成方方正正的块儿再装上车不是件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这时候一辆车恐怕不够,也许就来了两辆或三辆车。这往往是过春节前的时候,乡下那些勤劳而辛苦的人会把毛厕坑里的粪清理得干干净净,再把车装好了,然后,赶走了。这么一来,人们就可以过个很干净的年了。春节前清理毛厕大粪的时候,街道干部会出面,她们大多都戴着红胳膊箍,她们会每家每户去通知一下,“要起粪坑了,下边有人,谁也别去厕所,坚持坚持。”她们还会站在厕所的门口不让人们进去,当然是不让那些女人们进去,院子里的女人们也不会进去,“有人在毛厕坑下边呢。”那时候的毛厕里的蹲坑上都有长方形的木盖子,上边有根直棍可以把这盖子提起来或再盖上去。我父亲带我去厕所,总是一次次地教我在蹲坑的时候要把那个盖子提起来,拉完屎再把那个盖子给盖上。而父亲带我去厕所是我四五岁时的事,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院的厕所蹲坑也太大了,小孩子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父亲总是担心我掉到厕所里边去。父亲每次去外地出公差,走之前,总会把我的哥哥叫到跟前说,“你弟弟去厕所你们得带他,小心掉下去。”父亲蹲坑的时候总会抽上支烟,有时候还会把烟给旁边的坑上蹲的人一根,不用问那个人是我们一个院的邻居,有时候还会互相要张手纸,去厕所的时候急了,谁都有忘了拿手纸的时候,大杂院的厕所都很大,是一大溜儿蹲坑,还隔着墙,一边蹲坑一边隔着墙说话。我那时候还不会自己用手纸擦屁股,我早早拉完了,会一遍一遍撅着屁股大声喊:“拉完了——”“拉完了——”是要父亲给我擦屁股,父亲总会说,“急什么急?急什么急?”再到后来,我会说:“我要掉下去了——”我这么一说,父亲就会马上过来了,让我把屁股撅起来,那年我最多五岁。
再后来,我们全家都离开了那个大杂院,搬到了一个名字更好听的地方去,那地方叫“花园里”,那地方的名字不但好听,房子也好看,是楼房。很大的一个院子里,齐齐整整一共八栋楼。大院是个正方,南边一个院门,东边一个院门,北边却没有,西边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没人会想去问这个问题。院子东边有个菜铺,很大的菜铺,这个菜铺有多大呢?为了从乡下拉菜,菜铺的后院里居然还养着两头毛驴,因为这个菜铺紧挨着我家那栋楼,晚上睡梦中我都能听到驴在打响鼻,“扑噜噜噜,扑噜噜,扑噜噜噜,扑噜噜。”或者是听见驴在叫,“昂昂,昂昂,昂昂昂昂,昂——”每天都要来那么几声。母亲听了有时候会笑,会对父亲说,“听,吊嗓子呢。”父亲也是个笑,因为我们早先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有一位姓张的工程师,他喜欢唱青衣,每天早上都会吊那么一段儿,而且还是自己拉胡琴,是自拉自唱。我知道,我的母亲话里有话,是想起那个姓张的工程师了,但我们现在已经搬开了,不在那个大杂院住了,我的母亲和父亲都认为一个大男人“咿咿呀呀”唱青衣是件很好笑的事。这是菜铺,菜铺旁边,是一家小百货商店,就这个小百货店,里边几乎是什么都有,搬家之后,我们吃什么用什么一般都要到这个商店里去买,买干粉条,海带,黄花儿,花椒大料,酱油和醋,还有白糖和父亲爱喝的那种散装高粱酒,放酒的黑坛子上一律都盖着用红布做的那么个盖子。这个小商店还卖肉,卖肉的售货员姓岳,人瘦瘦的,见了面总爱和父亲说几句话。快过年的时候也是商店里最忙的时候,总是挤满了人,有些东西要排队才能买到,母亲让我去排队,“这么大了,也该给家里做点事了。”父亲却不愿意,父亲说:“那么多人挤坏了怎么说。”父亲会自己去排队。商店西边呢,怎么说,还有一个店,却是卖粮的粮店,人们买粮食就都去那地方。母亲要我去买两束挂面,因为家里来客人了,擀面来不及了。父亲说:“别蹭孩子一身白。”父亲又自己去了,父亲是太爱我了。不一会,父亲手里托着两束挂面回来了。刚搬到这个新大院的时候,父亲总说我们这个新大院好,好就好在买东西太方便了。
“要粮有粮,要菜有菜。”我父亲说。
我母亲在旁边马上会刺他一句:
“要酒有酒,再来二两。”
我父亲笑了,他就是爱喝那么一口。
“当然还有豆腐干。”父亲说,他这是逗母亲。
父亲喝酒的时候喜欢就几块豆腐干,而且还是那种熏干,母亲说那豆腐干是用马粪熏的。“也许连马粪都不是,是用驴粪。”母亲笑着对父亲说。“用羊粪熏我也照吃。”父亲说。父亲还喜欢吃毛蛋,那种死在蛋壳里的小鸡,剥开壳,团团的,毛烘烘的一个小鸡,父亲一边吃一边还会自己对自己说:“真讨厌,我怎么会吃这种东西。”他这是对自己的批判,对自己的批判归批判,但他还是照吃,总是煮一锅,味道有那么点古怪,花椒大料的味道之外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父亲吃毛蛋喝酒的时候总会叫上一个朋友,是个山东人,水暖工程师,长一个很大的糟鼻子,他那鼻子可真够糟的,像很大个儿的草莓。他们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自己动手剥毛蛋,蛋壳已经剥了一大堆了,但他们还在喝。他们可真能喝。但父亲忽然不喝了,他听到了什么,有人在外边一声一声地吆喝。
“是换鸡蛋的。”父亲听听,说。
“现在一斤鸡蛋换咱们多少玉米面?”山东大鼻子说。
“十斤换一斤。”父亲说。
“什么时候粮食才不紧张啊。”山东大鼻子说,“乡下人够苦的。”
父亲不说话了,我那天怎么就想起说话了?我本来在写作业,我忽然对父亲说:“乡下人怎么就不爱吃鸡蛋倒喜欢吃玉米面?”
父亲突然不说话了,看着山东大鼻子。
山东大鼻子朝我这边看,这就让我很不自在。
父亲忽然对大鼻子山东人说:“你瞧瞧,我这个儿子真够混蛋!”
父亲是偏爱我的,我对父亲说:“我怎么混了?”
“你还不混,说这种话?”父亲说。
“那他们为什么不吃鸡蛋,拿鸡蛋换玉米面。”
我父亲又把他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回不说“混蛋”,而是说“混球儿”。
“我儿子真是个混球儿,小混球儿。”父亲说。
“大了他就该明白了。”山东大鼻子说。
“不对。”父亲说,“好好儿饿他几天就明白了。”
我小时候挨过饿吗,没怎么挨过。只是在刚刚搬到楼房里住的时候有几次晚上去厕所,一下子从床上掉到了地上。还有就是去了厕所总是忘了冲马桶,我母亲说:“你拉屎让别人冲,你臭不臭,啊,你臭不臭?”
母亲想起排子房大杂院的厕所来了,说,“你要是再不冲就回旧院去解手!”
“我要是拉肚子呢?”我对母亲说。
母亲哈哈哈哈笑了,说:“你是你爸的心肝宝贝,拉你爸嘴里去。”
“还有这么说话的吗?”父亲听到母亲的话了,但他并不生气,他在喝酒呢。
“还是家里有厕所好,刮风下雨不用一踩一脚烂泥。”父亲说。
母亲说,“好什么好,你没见有人跑到对面墙角小便,多不雅观。”
父亲不说话了,好一会才又说,“可不是,这么大的院子,都没个厕所,让他们怎么办,总不能溺到裤子里。”
这一天,终于有事了。
直到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楼房院子再往北的那个村子叫做“宋庄”,宋庄那边有条铁道,有时候,晚上我会听到火车响,一阵一阵在梦中响过来,响近了,再慢慢响远去,还拉着一声一声的汽笛。有时候父亲出差去了外地,那几年,父亲总是出差,走的时候会对母亲交代好了,去几天,几号回来,回来的时候大致又会是几点的车。母亲会把父亲要带的粮票和零花钱数好了给父亲带上。父亲走一天了,走两天了,走三天了,走一个星期了,父亲要回来了。父亲要回来的晚上,母亲会在火车汽笛响的时候说:
“听,你爸爸就这趟火车。”
这样的晚上,母亲总是穿着衣服在那里等,而我们却马上又睡着了。
再说说宋庄吧,宋庄那边还有个小站台,站台上总是堆着不少东西,我们去那边玩儿,总是被站台上的人给喊开。站台东边,有个很高很高的高压线铁架子,但这个架子给废了,没有电线了,我们就可以爬到上边去玩儿。从上边往下看,下边都是庄稼地,玉米黑绿黑绿的,还有高粱,紫红紫红的,还有谷子,这些庄稼我都认识,各种的庄稼,各种的颜色,一片一片连着,很好看,一直铺排到西边的山那边,山那边总显得很寂静,连个人影都没有,这就让人心里很惆怅。我们爬到高压线的铁架子上去玩,可以看到下边的站台有人在搬东西、扛东西,停在那里的火车忽然又要开动了,开动之前要放屁,“吃吃吃吃”的。站在上边,我们还能看到下边的那个名叫宋庄的小村子,那条土路可真是白得晃眼,有人从村里出来了,是三四个女人,都挎着篮子,从村里出来,一拐,上了那座小桥,下了桥了,再一拐,往这边过来了,她们要走过这个高压线的铁架子,再从这里往东走,东边就是大同城,其实她们应该是先走到我们那个院子,因为我们的院子靠这边最近。和我一起出来的小伙伴说,“她们肯定又是去换粮食去了,用她们的鸡蛋。”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那几个女人挎的篮子里是什么了,是鸡蛋。我们待在高压线的铁架子上能把这些个都看得清清楚楚,没人从下边过的时候我们会在上边比赛撒尿,看谁撒得远,我们正撒着尿,下边忽然有人喊开了,有人突然从庄稼地里冒出头来了,他在地里做什么?这人手里拿着镰刀,他在地里割草,他朝我们喊,还把手里的镰刀朝我们举了举,“再往下撒尿小心把你们的小鸡鸡给割了!”这人喊完又不见了,又割他的草去了。这年的庄稼长得真好。我们继续在上边待着,就是不想下去,我们待在上边,什么也不为,就只想一直那么待下去。我们又看到了,宋庄村口停的那几辆马车,车辕都朝天立着,和我一起的小伙伴说那都是些个拉大粪的车,他这么一说我就又想起我们的平房大杂院来了,想起一到冬天就过来拉大粪的乡下人。“吭哧、吭哧”凿一整天大粪,然后围着那个小火堆吃点干粮,然后赶着他们的车走了,那头拉车的骡子,两个鼻子眼儿里一下一下冒着白气,天是多么的冷啊。我的父亲说,“这么冷的天,他们在外边吃?他们能吃什么呢?”“天这么冷,怎么也得喝点开水吧?”父亲又说。
我有点怀念我们的排子房大杂院,甚至还有点怀念我们那排子房大杂院的厕所。
我对我的小伙伴说,“我们那个厕所可真大!”
“你掉进去过没?”我的小伙伴说。
这是什么话,我说你才往那里边掉呢。
我们都不说话了,都看着下边,下边的庄稼真绿,都绿黑了。
那个割草的人又从地里钻出来了,他又去了另一边,到另一边割他的草去了。
我的母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去单位工作了,因为我的弟弟都五岁了,五岁了还不会走路,所以我的母亲只好待在家里照顾他,教他学走路,可他病了,发过一次高烧后永远不会走路了。所以有什么事,父亲就总爱带我一个人出去,比如出去钓鱼,比如出去挖蚯蚓,比如到城外很远的地方去找蝉蜕,比如去商店买这买那,那时候我简直就是父亲的跟屁虫。我的父亲,对生活总是充满了奇思幻想,这年的春天,他忽然想在院子的前边种一株葡萄,父亲带我去了一中,一中的校园里种了不少葡萄。父亲跟学校那边的人讨了两棵葡萄秧子,父亲对我说,“明年你就等着吃葡萄吧。”父亲已经在前边的院子里挖好了坑儿,那个坑不大,我跳进去,再一跳还能跳出来。葡萄秧子就要种在那个坑里,但这时候一个乡下人出现了,这个四十多岁的乡下人脸通红通红的,他到处走,到处看,一个圈一个圈地转,看样子,他急得不得了,急得不行了。他脸憋得通红,在我们的院子里问了一个人,又问了一个人。我父亲注意到他了,我父亲过去了,然后,我的父亲急忙忙放下了手里种葡萄的事,急忙忙把这个乡下人给领到家里去了。我跟在父亲的身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看着我的父亲把那个脸憋得通红的乡下人领进了我们家的厕所,父亲要我们都到屋里去。
“要不他会不好意思的。”父亲小声对我和母亲说。
我和母亲就都进了里屋,而且把门也关上了。
“要不他就拉裤子里了。”父亲又小声对母亲说。
“这么大个院子没个厕所可真不是个事。”父亲又说。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出去了,那个乡下人早已经不在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母亲该做饭了,她去了厨房,我们的那个厨房可真小,一进门是个案子,母亲就在这个案子上给我们做各种吃食,面条啊,馒头啊,烙饼啊,饺子包子啊,切菜也在上边,紧挨着案子就是灶台,灶台上是两个灶眼,前边这个灶眼做饭炒菜,后边那个灶眼捎带着把一壶水就已经烧开了,转过身就是那个水泥池子,水池子上方有那么三个架子,我们的吃饭家伙都在那上边搁着。这样小的厨房是没办法放粮食的,我们家的粮食就都放在里边的屋子里,那是许多的袋子,放白面的一个,放玉米面的一个,放豆子的一个,放小米的又一个,还有一个袋子最小,是放大米的袋子,那时候大米可真少。母亲去了厨房,母亲要做饭了,她忽然喊了一声父亲,母亲总是把父亲喊做“老王”,母亲说:“老王你来。”母亲发现了什么?我马上就也跟着去了厨房,我可是对家里的什么事都感兴趣,在厨房一进门的那个案子上,那是什么,那是鸡蛋,十颗鸡蛋。母亲对父亲说,“你怎么把鸡蛋放这地方。”但母亲和父亲马上都明白了,这鸡蛋不是父亲买的,这鸡蛋是那个乡下人留下的。
父亲马上去了一趟院子,东看看,西看看,那个乡下人早就不在了,快中午了,快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了,父亲还在那里站着,他希望那个乡下人出现。父亲站在那里自言自语:“这么大个院子没个公共厕所可真不行,这么大个院子没个公共厕所可真不行。”父亲自言自语的时候我就站在父亲的身后,那时候,我可真是父亲的跟屁虫。父亲又说,像是在对我说,“厕所是要修到东边的,可我们院子的东边是商店菜铺和粮店。”我问父亲,“厕所为什么非要修到东边?”但我马上就想起来了,我们旧院的厕所可不就在东边。父亲说,“古时候人们把去厕所叫‘登东啊’。”我再问,我再问,“为什么叫‘登东’?”?父亲说因为厕所在东边啊,我再问,我再问,
“为什么厕所要在东边?”
父亲被我问住了。
“都快过了吃饭的时间了,咱们回去吃饭吧。”父亲说。
吃饭的时候,父亲又对母亲说,“这么个大院,没个厕所可真不行。”
“吃饭吧,吃饭呢。”母亲说。
“还是旧院好。”父亲又说。
我知道父亲在说什么了,我马上也说,“还是旧院好。”我看了看父亲,父亲正看着我,我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下边的话我就不说了。但我不得不说,我又想起什么来了,我对父亲说:
“我们学校的厕所也在东边。”
我父亲不再说这些了,却和母亲说葡萄的事,说葡萄第二年就会结果的事,“你们就等着吃葡萄吧。”我对吃葡萄的事不感兴趣,因为要结葡萄也是明年的事了,我吃完了,我出去了,院子里什么也没有,院子里很静。
“那个乡下人在哪儿呢?”我站在那里想。
“那个乡下人现在在哪儿呢?”直到现在,我还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