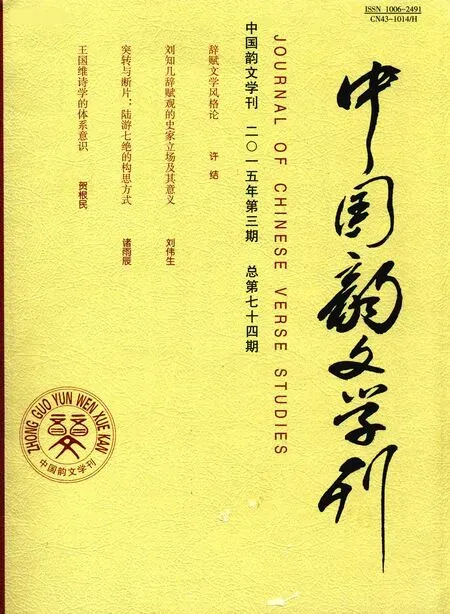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文学特性研究
2015-11-14孙欣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3-0049-06
*作者简介:孙欣婷(1987- ),女,山东临朐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词学。
碧城仙馆是清代钱塘文人陈文述的居所之称,陈的第一部诗集《碧城仙馆诗钞》即是以此命名,他的座下女弟子也被称为碧城仙馆女弟子,与袁枚的随园女弟子遥遥呼应。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除了陈文述的女弟子吴藻、张襄、吴规臣等四十余人外,还包括了其妻妾龚玉晨、管筠、文静玉、薛纤阿、女儿陈苕仙、陈萼仙及儿媳汪端,她们与碧城仙馆女弟子一起构成了以陈文述为中心的文学群体,代表作为《碧城仙馆女弟子诗》。这个文学群体可以说是一个由男性文人引导,女性文人组成的家庭式与公众式团体的结合性群体,在地域上将苏杭两地的文化融合了起来。其中知名者有:
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仁和人。著有《花帘词》《香南雪北词》《花帘书屋诗》。俞陛云在《清代闺秀诗话》中将其与徐灿、顾春列为清代女性词人三大家。
张襄,字蔚卿,又字云裳、兰卿,蒙城人,苏州参将张殿华之女,吏部主事汤云林之妻,善骑射。著有《支机石室诗》(收入《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中)《锦槎轩集》《织云仙馆词》。
吴规臣,字飞卿,一字香轮,金坛人,长洲知县顾鹤妻室,工诗词,善书画,精医理,通剑术,著有《晓仙楼诗集》(收入《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中)。
钱守璞,字藕香,又字莲缘、莲因,江苏常熟人,能诗善画通音律。著有《梦云轩诗》《绣佛楼诗稿》。
辛丝,字瑟婵,山西太原人,著有《瘦云馆诗》(收入《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中)。
管筠,字静初,一字湘玉。初为陈文述妾,后为继妻。因姓管,又慕管仲姬为人,遂以“小鸥波馆”名其诗集,著有《小鸥波馆诗》。
文静玉,字湘霞,本高氏女,后改姓文,陈文述妾。善画、书学晋人。能诗,有《小停云馆诗钞》。
陈文述对前辈袁枚十分推崇,后仿效袁枚招收女弟子,支持女性文学的发展。因此,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与随园女弟子群有一定关联,而在文学成就上,亦有同异之处。在研究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的作品时,不妨将二者作一比较,就中可以更好地看出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在文学上对于前辈随园女弟子的继承与创新。
一 讲求真情灵性
冒俊为汪端所作《自然好学斋诗钞》序中云:“论诗于闺阁中,才綦难矣。无良师益友之取资,无名山大川之涉历,见闻所限,才气易孱,加以沉潜高明,性不能无偏倚,丰亨否塞,境不能无穷通,菁华不舒,巾帼通病。” [1](序)这一段话可谓闺阁文学的真实写照,闺阁生活的局限影响了女性写作思维的扩展,因此才女笔下多为吟风弄月之作。但另一方面如黄友琴为恽珠诗选所言:“女子之于诗较男子为尤近,何也?男子以四方为志,立德立功,毕生莫殚吟咏一端,宜其视为余艺。女子则供衣服、议酒食而外固多暇时,又门内罕与外事。离合悲喜之感发,往往形诸篇什。” [2]女性文人一心作诗抒怀,较男性更为重视诗词中的情感表达,因此即便是描摹琐细之事,全心倾注,也会别有风韵。限于阁楼与后花园的圈禁,才女们纤细的心理上更能自发地追求一种轻灵的境界,发之于诗,则易为真性情的流露。她们从秋风里感受到落叶的悲凉,从春花中体会青春的寂寞;虫声唧唧使她们不眠而烦恼,燕语喃喃又使她们多情而自伤。历代的男性文人试图用女性的心理去摹写自身的凄凉,却永远不能替代她们去亲身感受闺阁的落寞与哀愁。
就两大群体的成员构成而言,随园女弟子主要以官吏之妻女,和普通良家女子为主,常有夫妻唱和、母女唱和之乐。碧城仙馆女诗人亦是以大家闺秀为主,且多是名门之后,如汪端出身汪氏大族,许云林出身许氏大族。吴藻虽出身商贾之家,但家境富裕,能为之延师聘教。可见无论是随园还是碧城群体,这些女性大多受到过良好的艺术教育,尤其是碧城仙馆女诗人,除了诗词卓有成就外,多数人还精通书法、绘画等各种艺术。这种身份和教养也使得她们的诗词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真情灵性。江南之地杏花烟雨,小桥流水,春华秋实,禽鸟鱼虫,特别符合温婉柔弱之女性的审美情趣,也使其诗风趋于性灵一派。
同时袁枚所提倡的“性灵说”也影响了这些女性文人的创作,袁枚论诗主真、重个性,反对拟古不化,“性灵说”反对摹拟诗歌,而要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选材方面也灵活广泛,力求生活化、个人化。此说不仅对随园女弟子影响颇大,即使在后来“性灵说”衰微之际,由于其符合女性的审美及创作需求,仍然被众多女性青睐。许多女作家的文学主张或许与性灵派不尽相同,但灵活性的作诗之法是一致的,且不知不觉地会在创作中体现出性灵派的艺术特色。她们强调诗歌表现自我,抒写个人的真性情,往往从日常闲适生活中选题,亲切真实,笔调清新自然。随园女弟子受袁枚“性灵说”影响,作品中绝少人工雕琢,以自然清新为主,如女弟子席佩兰的诗歌,通篇几不用典,词句流畅,有清新自然之风。
而在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方面,其领袖陈文述对于诗法也有议论:“盖用笔之道,正写不如侧写,实写不如虚写,浑写不如碎写,浓写不如淡写,写阔大处不如写纤细处,写繁缛处不如写幽冷处。” [3](P56)陈文述早年师法吴梅村、李商隐,行笔绮艳;后期偏爱许浑之“神骨清秀”、邵尧夫之“和雅”与“自然”,兼及元白,诗风趋向平淡清柔。碧城仙馆女诗人们受其影响,作诗讲求用笔流畅,不事雕琢,发乎性情,以笔传心,这一点与随园女弟子相同。汪端在其所著《明三十家诗选》凡例中指出“诗不可不清,而尤不可不真。清者,诗之神也……真者,诗之骨也。” [4](P435)她的绝句也写得玲珑剔透,如“晓
雨嫩凉蒲蕖长,蜻蜓碧点水痕圆”之句。其七岁作《家大人命同诸兄伯姊咏春雪》一诗:
寒意迟初燕,春声静早鸦。
未应吟柳絮,渐欲点桃花。
微湿融鸳瓦,新泥殢钿车。
何如谢道韫,群从咏芳华。 [1]
笔调老练,很难看出是七岁儿童之作。其中“渐欲点桃花”五字可谓点睛之笔,将新雪报得春光之意尽显于人前。
而其《田家》一首,意境优美:
一夜梨花雨,田畴新水生。
邻家饭黄犊,荷锸出柴荆。
妇子供晨饁,儿童话午晴。
萧萧竹林外,布谷又催耕。 [1]
又如管筠《题桃花扇》之诗:
丝竹苍凉酒一尊,南朝遗事写温存。
江山谁堕新亭泪,花月空销旧院魂。
公子才名归党局,美人消息种愁根。
不堪重话青溪事,落叶如鸦冷白门。 [5](P517)
桃花扇一事源出南明秦淮妓李香君,明末国事破败,遭异族入侵,虽有仁人志士奋起反抗,但仍不免衰亡之运。满目山河空败落,后人对此景当有感叹怀古之心。管筠此诗是咏怀南明诗中的一首,最后一句“不堪重话青溪事,落叶如鸦冷白门”中“青溪事”是用青溪小姑之典,青溪小姑被奉为南京织神,在这里用青溪事是为南京之代称,与后文同样指代南京的“白门”相映。“白门”一词从字面上看已是凄清,更兼落叶如同飞鸦,更觉悲凉。今南京中山陵附近多有古木参天,尤以梧桐居多,深秋时节漫步其间,落叶萧萧,最能使人念及前朝往事。
再如文静玉《月夜放鹤亭听鹤唳》诗:
放鹤亭中鹤,霜寒夜不眠。
仙心出云表,清响答琴弦。
我访巢居阁,因停罨画船。
梅花三百树,素月正横烟。 [6](P3123)
文静玉之诗多收于《清诗汇》中,以写景咏物为主,这首诗咏鹤,以写鹤唳而抒己之仙逸情怀。“梅花三百树,素月正横烟”一句尤绝,将月夜梅花氤氲之态尽显,由鹤而梅,与林逋“梅妻鹤子”萧然出世之态相辉映。
钱守璞诗今存《绣佛楼诗稿》两卷,细读之,觉守璞为人一若其名,纯朴真挚,人淡如菊,其诗也清简淡美,有隐者之风。其咏梅名句“素心千点雪,太古一枝春”十字内将梅之高洁与清雅凸显;《三十初度述怀》其一之“好古性情荆布惯,与时装束不相宜”、其二之“信天不觉襟怀澹,守道还须学力坚”更是对自身简朴性情之刻画。钱守璞曾属意于陈文述,但陈文述以年老为由辞之,后嫁丹徒张骐,张骐后官广西巡检,官位并不显赫,因是守璞的家居生活十分清俭,但她心境淡泊达观,并不以清苦生活为累,于家计外犹自吟诗作画,怡然自得。其《闺中元夜词》之四写道:
负他明月到贫家,读《易》挑灯夜煮茶。
自笑寒酸风味别,饱餐虀粥咏梅花。 [7](P32)
相对于汪端的安适娴雅与吴藻的愁闷反叛,守璞之诗中所流露出的是一位平凡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足与达观,又有着从困境中寻得的诗情画意。人生虽有所不同,而平凡往往是众生之常态,若能在粗茶里咀嚼出诗意的滋味,在虀粥之外还能欣赏梅花的美好,却是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境界。同样《偶成》一诗也是如此:
碧花红穗绘新秋,晓起桐阴露欲流。
忆到清贫犹自慰,不曾典却玉搔头。 [7](P43)
钱守璞因其天性淡雅,集中不少诗作都充满了田园风味,如《清明即事》之七:
葱韭瓜姜杂菜畦,药苗野草望中齐。
好邀月色兼山色,乱石墙垣故筑低。 [7](P61)
陶诗之所以能够感动无数后来人,陶渊明之所以是真正的隐士,是因为他是真正地融入到了现实生活中去,采菊南山的背后也有带月荷锄的辛苦。读钱诗,往往使人觉得守璞亦是真实地活在日常生活里,当其他闺阁女子在吟咏柳絮繁花时,守璞却可以看到田中果菜药苗,她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升华到了诗意的地步。钱诗虽然多白描,语言清浅,但十分注意格律的严谨,对此,好友袁绶在其《绣佛楼诗稿》卷首评价说:“或谓君诗尚格律而纬以性灵,似不专主随园先生者,不知规规于绳趋矩步者,非善学先生者也,惟其格律之严,益见性灵之妙。” [7]袁绶是袁枚孙女,对性灵诗风自是赞同,在她看来,性灵并不代表不注意诗句格律,而是不受其过分的约束,同时钱诗的严谨或是对性灵诗风散漫的纠正。
女弟子中辛丝曾遭家变,贫病交加,竟至于典衣鬻书。其《瘦云馆诗》中有《病后检书觅售,以供药饵,感书一绝》一首:
萧然四壁掩柴门,典及牙签泪暗吞。
犹幸未经池墨涴,可怜曾覆掌茶痕。
秋风扫叶成何事,斜日牵萝更断魂。
但遇知音休遇劫,芸香珍重伴长恩。 [8]
对于这些生活封闭的女性来说,书籍是最能安慰其心的事物,是诗思得以涌动的源泉,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鬻书以供药饵,万般无奈,如同将知音付与他人,生离死别一般,故后有希望书籍得遇识者,能像以前一样被珍重爱惜。此诗中女诗人没有反复强调生活之苦,而是将书籍作为友人去怀念,也是别具一格。
二 抒发闺阁雄音
胡明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中提及:“纵观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作品,在她们的生存环境并不太恶劣时,更多的主题便是床帏绣幌,银烛妆台,窗头明月,园中落花,云里孤雁,青丝脂泪。生活内容的苍白枯乏决定了她们不痛不痒的闺阁况味,也决定了她们附风弄雅的审美趣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她们作品里自觉求解放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9]因此中国女性的文学作品很少有杰出之作,内容千篇一律;即使她们跨出了闺阁的门槛,也往往无所适从,觉醒的时机还未到来,只能作一些离经叛道的呼声。稍有觉醒的女性往往会把种种悲剧的根源归因于女子的身份,她们不满于自身才情的被埋没,面对性别角色带来的不平等,深感性别成了追逐人生梦想的障碍。因此像男子一样生活,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成了许多清代女诗人的向往,从清初的顾贞立到清末的吕碧城,无不发出要与男子等肩的呐喊。
如果说在随园女弟子阶段,女性的自我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她们诗作中还多是传统的闺怨题材,那么到了嘉道时期,社会风气有了新的变化,女性的诗词中多充斥着反叛的声音。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继承随园女弟子又超出其局限的就是她们诗词中自我意识的体现,有不甘于现状而作的“闺阁雄音”,有效仿男子建功立业的雄心伟志。写作自然风物时清新雅丽,抒发壮志时又豪情满怀。她们在诗歌的领域内大胆蔑视陈规旧俗,大大助长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在一些诗词创作中树立的女性形象是以男子的胸襟气度、所作所为为尺度的;她们笔下的女性人格往往表现出与男性人格的趋同。
碧城仙馆女弟子中有二人堪称脂粉英雄者,即张襄与吴归臣,《名媛诗话》云:“闻飞卿善舞剑,蒙城张云裳善骑射,二人诗皆清绝尘氛。真碧城门下‘女英雄’也。” [10](P520)张襄是将门之女,其父美名曰“丽坡将军”,受家风熏陶,张襄于骑射之事精通,这在当时的女性中难得一见。其性情豪爽又过常人,诗词中亦有不同于一般闺秀伤春怨秋的幽咽之气。如其《支机石室诗》之《登灵岩山》一诗:
胜地甲三吴,风云想霸图。
绮罗西子径,烟雨范公湖。
故苑悲麋鹿,空林响鹧鸪。
登临无限意,落日下平芜。 [8]
古意沧桑,未减唐人风范。
陈文述曾修建西湖三女士墓,众弟子多有和作,其中以张襄诗风最为别致。其《奉和颐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诗》其三云:
但经小谪到尘寰,几处红心吊玉颜。
词客定能参慧业,美人才合葬名山。
前因已了埋香去,旧恨都空破梦还。
一笑蓬莱诸女伴,惯留惆怅在人间。 [8]
相比于其他吊古之作,张襄并没有困于悲叹红颜薄命的窠臼中,而是以赞许的口吻言出“美人才合葬名山”之句,言下之意,即是所有之悲欢离合已成过往,无须再斤斤计较于前缘旧恨中,而湖山有幸,美人葬于此处也是佳事。在诗之末尾还以谑笑之语劝告诸女伴,何须“惯留惆怅”,一个“惯”字,不仅道出了吊古伤今诗中难免哀怨之音的老传统,还表现了自身不落窠臼的大胆与不俗。
另一女弟子吴归臣精通剑术,兼及医理,屡随父游名山大川,穿云蹑翠,采叶寻松,几忘其为女儿身。其《晓仙楼诗》之《黄鹤楼题壁》云:
天风吹袂羽衣单,江上梅花怨晓寒。
他日我来横玉笛,月中只解跨青鸾。 [8]
自古题黄鹤楼诗者颇多,吴归臣此诗仅有四句,却清疏爽朗,末尾一句直言吹笛跨鸾之状,气势颇为狂放,是闺中难得语。
在词的方面,要属吴藻之词最为洒脱,其《花帘词》前有张景祁、陈文述、魏谦升、赵庆熺多位名家为之作序。陈文述在《花帘词序》中评价她的词:“顾其豪宕,尤近苏辛。宝钗桃叶,写风雨之新声;铁板铜弦,发海天之高唱。不图弱质,足步芳徽。” [11]。
且看其《金缕曲》一阕: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忍偏磨灭?从古难消豪士气,也只书空咄咄。正自检、断肠诗阅。看到伤心翻失笑,笑公然、愁是吾家物。都并入、笔端结。 英雄儿女原无别。叹千秋、收场一例,泪皆成血。待把柔情轻放下,不唱柳边风月。且整顿、铜琶铁拨。读罢《离骚》还酌酒,向大江东去歌残阕。声早遏,碧云裂。 [11]
吴藻生于商贾之家,相较于汪端书香门第的出身而言,她所受儒家礼教的束缚要少,性情也更自然,因此可以在词句中将愤懑不平之气尽情发泄。这首词起句即言“闷”而非“愁”,因为她在检阅《断肠诗》之类的闺怨之作时发现似乎“愁”是闺阁女子的专有之物,而这种“愁”只是女儿之愁,境界狭隘而浅薄。吴藻自身因为婚姻不幸,其夫连“天壤王郎”亦不如,因此写有大量的幽怨之词。而此时她却觉得不平,因为“英雄儿女原无别”,为什么女子就要局限于闺阁之愁怨中去呢?因此她毅然舍弃“风月”之作,而转向豪放之声。即便是所遇非佳,也不可妄自断肠。此中的“风月”与“铜琶”出自宋俞文豹《吹剑续录》,原是风格上的婉约与豪放之争,吴藻借此典来言女子也可写出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这样具有男性风范的豪放之作。王恭曾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12](P196)而与词中所言相应的是,吴藻果真创作了《乔影》一剧,借剧中人物“谢絮才”,发尽不平之气:“我待趁烟波泛画桡,我待御天风游蓬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 [13](P133-134)吴藻不仅在诗词剧作中抒发牢骚,在现实中也曾着男装,与众多男性文人诗酒唱和,还一同进入秦楼楚馆,《花帘词》中即存其赠歌伎之《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一词。
又如其词《水调歌头·孙子勤〈看剑引杯图〉,云林姊属题》一阕:
长剑倚天外,白眼举觞空。莲花千朵出匣,珠滴小槽红。浇尽层层块垒,露尽森森芒角,云梦荡吾胸。春水变醽醁,秋水淬芙蓉。 饮如鲸,诗如虎,气如虹。狂歌斫地,恨不移向酒泉封。百练钢难绕指,百瓮香频到口,百尺卧元龙。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 [14]
与其他女诗人相同,吴藻也有大量的题画诗词,在其题画词中,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跳出画外,借咏画抒心声,读这等词时能让读者忘原画而醉于其词。此词一开始便是“长剑倚天外”的雄壮定格,大有倚天一出,谁与争锋之势;又写饮酒之酣畅;继而讲述铸剑之精,宝剑锋芒一经铸出,如同千朵莲花出匣,光芒万丈;加之美酒相佐,酒剑相交,将生平意气一齐激发出来,“云梦荡吾胸”。此时春水变若美酒醽醁那样芳美,淬剑之水淬在剑上,剑气蒸腾,剑身像芙蓉出秋水一样凛冽,寒光四射。“饮如鲸,诗如虎,气如虹”连用三个三字句,将饮酒与赏剑时的豪放气势渲染了出来,宝剑与美酒的使命便是跟随主人乘风破浪去完成胸中壮志。此词写剑与酒,气势豪壮,实则写人,持剑之人必要乘风破浪一展宏图。吴藻作为女子,自然不能作战场之将军与江湖之侠客,但用此词之语,当可视为胸中志气之发,纵不能实现于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洒落于诗词,以尽吾志,方不为一世豪情,凌云之志。
到了钱守璞,对时事的关怀成为诗的题材之一。钱守璞随宦粤西,时值粤西战乱,钱守璞倾尽家产犒劳军队,在《壬子二月纪事诗时贼围粤西省城》中说:“漫言女子敢谈兵,倾家欲雪同仇耻。”《闻金陵警》《自粤西避乱至吴途中怀述四首》两篇皆是为此而作。如果说吴藻是以张扬的反叛行径来表现自我,那么,钱守璞则是以实际的行动及诗作来关注社会和人生。
三 耽于参禅问道
由于陈文述中年以后好道信佛,其家人与女弟子多受其影响,转为耽禅信道,其中不乏虔诚者,如皈依者就有女弟子吴规臣等九人,汪端、吴藻等更是自言将摒弃文字,潜心学道。
人生天地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即便是男性文人,也多有命途多舛之叹。何况是旧时代的女子,即便才华横溢,也不能与命运相抗,生活往往不能如愿,生命亦以悲剧收场。随园女弟子中不少早卒、早寡之人,生活清苦。碧城仙馆女诗人中,女弟子王兰修早卒,张襄背井离乡、随宦远域,汪琴云早寡,吴藻、汪端迭经忧患,晚年皈依净土。她们不是没有觉醒,但如鲁迅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她们也曾注重自我意识的表达,却找不到表达的现实之路。因此她们往往容易把生命悲剧归因于宿命,在抗争不成功的情况下自怨自艾,信心殆尽。而佛家的清静出世、道家的逍遥无为正好迎合了她们不满现状、渴望逃离又无路可逃的心。既然有心抗争又无力改变,那就只好躲到青灯古佛的殿梁下,不去想也就无所烦恼,也许皈依对她们来说就是唯一的逃脱方法。前辈梁德绳有语“心为伤多才学佛”,吴藻称“讳愁无奈学忘情”。这种参禅慕道,是女诗人们集体“逃离”的行为,是饱经风霜苦痛之后不约而同的选择。
虽然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于袁枚的随园群体有很大的借鉴和延续,但不同时期的女性有着不同的心态,在文学上的表现也是不同,相较之下,碧城仙馆文人群体在吟咏之外更迷恋于修禅奉道。陈文述曾以门下女弟子多参禅修道一事引以为傲,认为袁枚门下女弟子不能与之比较。从早期的“金钗问字图”到后来的“桂苑讲仙图”,陈文述与其弟子们在本质上作了一些转变,这也影响到了他们的诗风。
陈文述尝上书议论海运,遭人诬诟,历经宦海沉浮,遂一心归隐,在修道事上由兴趣转为痴迷。其后皈于闵小艮门下,对其极度信仰,还带领众多女眷、女弟子虔诚奉养。陈文述辑有《西泠仙咏》一书,吟咏仙人仙事,其中咏女仙六十人,还将自己的亲友也纳入其中。他的这种迷恋状态也感染了碧城仙馆女诗人们。除了跟随陈文述参禅学道外,她们还写了大量相关的诗词,诗风趋向平淡冲和。如辛丝的《天台桃源》一诗:
隐隐琼台隔晓霞,洞门深锁万桃花。
寒苔绿浸清溪碧,来访天台玉女家。 [8]
吴藻早年诗词具有闺阁雄音,直抒胸臆,但后经人事变迁,逐渐敛才收声,趋于沉寂。曾经不满女儿身,反抗礼教的她也有了诸如“欲哭不成还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犹是说聪明”的词作。且看其《金缕曲》一词:
生本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收拾起、断脂零黛。莫学兰台悲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 拔长剑,倚天外。人间不少莺花海。尽饶他、旗亭画壁,双鬟低拜。酒散歌阑仍撒手,万事总归无奈。问昔日、劫灰安在?识得无无真道理,便神仙也被虚空碍。尘世事,复何怪! [11]
在此词中,虽然在上阕有“一洗女儿故态”之语,似乎仍可算作是闺阁雄音,但是到了下阕,就有了“万事总归无奈”的言词。到了《香南雪北词》中,这种灰暗消极情绪更加明显,她在《香南雪北词》自序云:“忧患余生,人事有不可言者,引商刻羽,吟事遂废,此后恐不更作。因检丛残剩稿,恕而存焉……自今往后,扫除文字,潜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净土。” [14]
汪端亦是如此。据陈文述小传,汪端起先不信佛道,及闻管筠等家眷礼佛诵经,遂发愿为高启诵《玉章经》;后陈文述病,又为陈氏夫妇诵经祈福;等到陈裴之客死他乡,汪端更是心灰意冷,数年来闭关,数月不出,礼诵各种经文数十万卷。并将所居小楼命名为涵真阁,皈依陈文述族妹陈兰云为龙门第十三代弟子,派名来涵。汪端此前节录明史,搜采逸事,著成《元明逸史》八十卷,后学道乃悔此痴迷之误,因取稿本焚之。陈文述先是于其子陈裴之死时梦裴之跨白鹤而去,后汪端殁,《孝慧宜人传》内又记她房内“白气蜿蜒作,□檀香气自卧室达于大门,经十三层屋而上升,乃瞑目不语,若入大定” [1]。这些事迹在陈文述看来是他们成仙之兆,同时也加深了陈文述及其家人弟子对于修道参禅的痴迷。汪端奉道后尝语人曰:“名士牢愁,美人幽怨,都非究竟,不如学道。” [1]这是碧城仙馆女诗人后期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
碧城仙馆女诗人群体作为继袁枚随园女弟子群之后颇具影响力的女性文学群体,代表了男性文人扶持下的女性文学发展的一面。这个女性群体与随园女弟子群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她们的诗风上对随园女弟子有一定的继承,同时又发展出自身的文学特性,无论是讲求真情灵性,还是抒发闺阁雄音,以及后来耽于参禅问道,她们的文学风格在清代的女性文学群体中都有着鲜明的特色,这一群体也因此在女性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