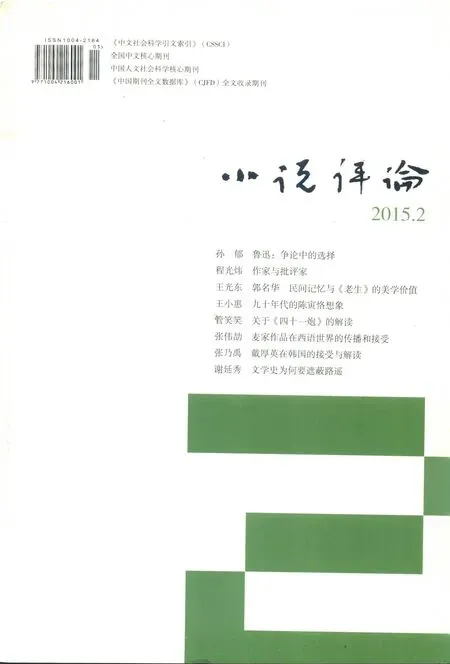论《碧奴》的神话重述与意象叙事
2015-11-14袁文丽
袁文丽
论《碧奴》的神话重述与意象叙事
袁文丽
在当代小说史上, 苏童开拓了男性作家写女性的新的境界,从他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妇女乐园》, 到《红粉》、《武则天》、《像天使一样美丽》、《米》, 再到近期的《碧奴》,无不渗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苏童自己曾说:“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 “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 在苏童敏锐的思维、灵动的语言、诗性的想象所构建的小说世界和个体诗学中,他的写作得以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得到新的阐释。《碧奴》的诞生是对苏童女性主题的深化,对人性思考的一种升华。苏童通过意象的更新和重组, 运用中国古代深厚的象征体系, 刻画了一个非常朴实而又极不平凡的民间女子在遭遇人类生存的苦难和悲剧命运时所表现出的卑微、执着而又不屈。另一方面,在当代的文学文化语境中,神话传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却遭受到了现代主流文学话语叙事的不同程度地拒斥,苏童的《碧奴》通过对民间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在神话重述中重新演绎对人心、世界、命运的思考,不愧是对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积极探索和对当代主流写作的有益补充。
一
孟姜女故事在后人不断的演绎和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历史视角的阐释,但今人比较接受和认可的解读有两种:其一,这是一个旷世经典的爱情绝唱,“孟姜女形象”和“哭长城”意象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经典“符号”,不断地呈现在后人的诗文和艺术创作中,并被反复吟唱。正如白雪的歌声中所传唱的“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孟姜女”被诠释为一个“忠夫”和“爱情”的母题和典型反复被书写和叙述。其二,这是一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意味的民间反抗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行为和“长城倾塌”的结果无不隐喻着一种最底层和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力的反抗,是百姓对于封建王朝繁重徭役和赋税不能承受之重的缩影和表现,坚固城墙的崩塌象征着封建王朝大厦的倾塌,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君民关系的政治思想。
然而,苏童在重述及与孟姜女故事的重新相遇过程中,并没有被一个古老的故事束手束脚、甚而述而不作,而是以一种极强的驾驭力融注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及自我生命的体验,以超越的哲学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完成了对故事叙述的人性思考和性别诠释,正如其在自序中写到:“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永远是横在写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孟姜女,我对孟姜女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一个性别的认识,对一颗纯朴的心的认识,对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我对孟姜女命运的认识其实是对苦难和生存的认识。”可见,苏童在“故”事“新”编的基础上,以“孟姜女”这一女性独立的性别角色和心理体验嵌入故事叙事的核心,通过对孟姜女作为个体的苦难人生命运的叙述进而拓展到对整个人类苦难和生存的认识,借传统的故事外壳演绎着现代人对生存困境的思考及现代性的解读方式。
在小说《碧奴》中,故事的基本框架仍然是碧奴寻夫和千里送寒衣的故事。苏童在整个故事层的营造过程中始终是在遵循着古老的故事框架,碧奴寻夫事件的起因源于丈夫被抓去修筑长城,事件的结果仍然以长城被哭倒而结束。但故事的筋骨血肉在作者精心地细节编织过程中,被灌注了新的生命和意义。
作为诞生于封建社会中的“孟姜女”形象,表面上似乎在歌颂女性柔韧、执著、坚贞、刚强的美好品质,“孟姜女”成为了中国文学中 “贞妇”、“痴情女”或“神女”的典型代表。然后仔细审视,我们可触摸到故事本身在漫长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隐含着强烈的“男权视角”和政治意识,甚至孟姜女故事的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符合了男性社会的审美标准,忠贞、奉献、痴情、柔韧等品质都是父权制社会的家长(丈夫/男人)对女性/妻子最基本的要求,“孟姜女”当之无愧地当选了男权意识宣传的绝佳材料。正如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的精辟分析:“对我们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进行公正调查后,我们发现,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如马克思·韦伯说的那样,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经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人。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而且它往往比任何的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加严酷,更加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孟姜女”传统形象成了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想象和欲望,是男性塑造的希望现实中的女性模仿和成就的对象。
在小说创作中,苏童没有把这个传奇的爱情故事塑造得浪漫、唯美,轻快、飞扬,而是用凝滞和厚重的笔法,使得小说处处充斥着血和泪。整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碧奴”,故事的核心情节就是碧奴寻夫路上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男主人公岂梁至始至终都是“缺失的”,是“不在场的在场”。丈夫岂梁的失踪,引发了“碧奴”义无反顾北上追寻的决心,甚至是抱着“有去无回”的誓死态度。小说情节的处理貌似遵循了传统的男性视角和男权思想,男人是天,女人为男人殉情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作者偏偏虚构了另一种截然对立的情境和背景解构了传统的预设,碧奴的千里寻夫,无论是在其家乡“桃村”还是在“寻夫路上”,都只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这里无疑隐射着作者某种现代性境遇的思考和批判,同时也开拓了写作的另一种更宽广的视角:碧奴千里送寒衣的故事,并不限于丈夫和妻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人性和生存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底层女性的故事,碧奴追寻的可能是当代人已经缺失的而恰恰是弥足珍贵的、最本真存在的某种“东西”——人们失落的精神家园。
作家怀着对女性深深地敬意,在对碧奴“千里送寒衣的动机、信念/路上行人的嘲讽、欺压”等一系列精神和生存困境的细微体察和把握中,通过叙事策略的不断推演,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却在不断被奴役、欺压中强化和建立起来。碧奴千里送寒衣,更多的是一种简单情感的主动诉求,是出于人与人之间朴实的关怀和挂念。在寻夫过程中,碧奴遭遇了人情的冷落和人性的失落,感受到了彻底的生存的悲哀和孤独:桃村人的挤兑和瓜分东西,人市上的凄凉和猜忌,鹿人的愚昧和凌辱,信桃君府的残酷、压榨和奴役……毫无疑问,文本把碧奴所生存和面对的困境呈现和撕裂在观众面前,这是一个男权社会主导的世界,是一个人心涣散、价值信仰崩溃、世态炎凉的社会,但碧奴却通过“眼泪”的力量,凭借自己的执着和本心,在“吃人”与“被吃”的境遇中,一一化解了危机,并逐步树立和强化了自我的生命意识。其“眼泪”背后所隐射的,既是人性和人情的力量,亦是女性特有的宽容与爱的温情力量。作家既表现出对传统男权社会和女性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亦表现出对女性温情文化的肯定和构建,对其“救赎”主题的颂扬和重铸。
作家的笔法时而是温情的,比如对碧奴眼泪相关的大篇幅的描写,碧奴的眼泪能“化人”,能唤起鹿人对家乡和亲情的回忆;时而又在冷静中夹着后现代精神式的残忍破碎和怪诞虚无。碧奴千里送寒衣这一行为在文本的现实境遇中并没有可行性和实际意义,作者多次借路人之口进行解构,特别是当鹿人把“寒衣”侵占和撕裂之后,碧奴的行为更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种失去根基的“寻夫之旅”实质上成了后现代式的绝望的寻找本身,碧奴生存的方式——“追寻”和“在路上”实质上也是一种变相的逃离和自我流放,疏离和隔膜了传统文化符号所赋予的贞洁烈女的合法性;最后当碧奴驼着巨石向目的地爬行的时候,这种强烈的“西西弗神话”的荒诞无稽感更是达到了高潮。诚然,苏童对“碧奴”千里寻夫的行为具有着肯定和质疑的双重疑虑,但这并不存在悖论,正如苏童自己创作的初衷:“其背后所潜藏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问题”,苏童试图一面显示人类生存的苦难、当代社会的荒诞虚无感,但另一面又似乎在鼓励人们不要绝望和颓废,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意志。
二
苏童强调说“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诚然,作者秉持着现代人阐释的历史视角,带着对女性及其生存境遇的深入体察和思考,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叙事策略编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孟姜女故事,独特而又丰富的“意象”的介入恰恰就是其神话重述的关键之处,也是其小说创作中惯用的叙述策略。
杨义先生曾把意象的叙事功能概括为凝聚意义、疏通脉络、保存审美意味三方面,主要突出了其在叙事内容和叙事阅读方面的意义,然而,通过对苏童作品的进一步细读,我们能发现意象在叙事作用与艺术效果方面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苏童的《碧奴》在神话传说的诗意想象与哲思创构中,呈现了一个意象纷呈的世界:眼泪、葫芦、桑树、青蛙、冬袍、鹿人、马人、石头等具体物象意象;桃村、百春台、大燕岭、人市等场景空间意象;“寻找”、“在路上”、“孤独”、“逃离”、“死亡”等人类抽象的母题意象。这些庞大意象群的交织碰撞使得小说文本在视觉层面呈现出梦幻瑰丽的复调空间,各种意象符号的文化隐喻和象征意蕴之间在作品中发生神秘的关联和互文性,形成一个强大的意义场域,小说结构中涌动着妙不可言的情绪和意境。小说《碧奴》就是一个女子寻夫的故事,小说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碧奴寻夫路上”的描述上,故事根本可归结为“寻找”和不断“在路上”的主题,而此主题叙述的完成却离不开与其它的具体意象如“眼泪”、“青蛙”、“冬袍”、“鹿人”、“大燕岭”、“人市”等交媾成一体,正是意象的块面化使小说具有了叙事性,而叙事的意象性使小说负载了更丰富的精神意蕴,拓宽了小说的隐喻空间,表达了对人类存在世界和生命深层次母题如“孤独”、“死亡”等的审美观照。
小说呈现了一个执著寻找和不断上路的主题意象,而此行为和动作的执行者就是“碧奴”这样的女子,对“碧奴”的隐喻和塑造,作者又是
通过“葫芦”和“泪水”两个具体的核心物象完成的,作者描写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实质上是在叙述“葫芦”和“眼泪”的故事。碧奴所经历的苦难仍然是今天许多人的苦难命运,“在路上”成为人类的宿命。她的执着的寻找、不断上路,实质上是一场没有结果和归期的逃离和自我流放,她从故乡逃离、从日常生活里逃离。“逃离”成为对既定命运的反抗、对惯常生活逻辑的背离、对自我生存新的可能性的追寻。这其实也是现代人的命运,永远在路上的困惑和寻找,不断地逃离,企图完成对自我的拯救。碧奴面对的是一个无根社会里的个体生存悖论,她历尽千辛万苦所要追寻的最后还是一场空,她经由所有的苦难寻找到的仍然是无法完成的心愿。碧奴的生存环境、她在寻夫路上的际遇,其实更接近当下的社会寓言。作为一个底层的弱女子,她不断受到的是被剥夺的命运,她的社会不仅人心不古,而且人被强权与欲望所异化。作为一个对人性有深入探索的作家,苏童的批判锋芒最后指向的是人性恶的本质:人性本源的丑恶、卑贱,人心的冷酷,人与人的疏离。诸如对“鹿人”的隐喻和批判:“他们一味地提醒她提防狼群、毒蛇和蓄须的男子,却没有告诉她孩子也要提防:可怕的孩子,半人半鹿的孩子,他们用恶魔般的童真唤醒了碧奴的眼泪。......泪水从眼睛里出来,那双眼睛就要永远地闭上了!”诚然,他的人性书写常常基于对一种性别和命运的日常描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恰恰是碧奴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神奇的女子,用哭泣和眼泪呼唤着人们被异化的灵魂,用最淳挚的情感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三
在原始思维万物一体的视角下,作者一开场就通过葫芦和桑树的意象隐喻了碧奴和岂梁的前世今生的命运,把读者带入了无限时空的冥想当中,碧奴是葫芦变的,岂梁是桑树变的,葫芦必须挂在桑树上,“葫芦离开桑树的怀抱,就像碧奴离开杞梁的怀抱,藤舍不得,树舍不得,人更舍不得”,这就为碧奴千里寻夫的决心和夫妻俩生死与共的结局埋下了伏笔。葫芦的意象一直隐含在文本之中,从《青蛙》、《桃村》到《鹿王坟》、《掘墓》,其每一次出场都具有特别的意蕴,同故事情节的高低起伏紧密相连;作者对意象的设置也是独具匠心的,葫芦的符号表征对碧奴——民间女性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隐喻和象征作用。葫芦,是一种茎蔓生的草本植物,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攀援性和旺盛的繁殖力,被视为生殖崇拜的信仰物。苏童之所以选择葫芦意象,恰恰是因为葫芦所具有的依附性、他性(奴性)与生殖崇拜性(神性)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底层女性形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正是这种双重矛盾复合体,使碧奴完成了千里送寒衣的艰难使命,这种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和英雄行为推进了她成为女神的进程。她的神性在哭长城时被彻底激怒而爆发出来, 神圣的泪水哭倒了坚固的长城,摧毁了由男性世界所搭建的封建塔楼以及传统女性所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然而,“葫芦”又是盛水用的,自然又与“泪水”意象生发了紧密的关联,两者合力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泪水”意象是统领全篇和作用于碧奴形象建构的最核心要素,文本关于“泪水”的意象叙事也表明了苏童女性意识的一种写作姿态。“眼泪”——“女人”——“水”具有隐喻层面的互指同一性。“眼泪”是人情绪激动时刻的一种自然的生理表现,常与感性、柔弱、忧愁等情绪相连,女人爱哭啼,从性别和生物性的角度而言,女性确实比男性更为感性、脆弱和善感,而从文化的角度讲,古人云“男儿有泪不轻弹”,自此“眼泪”与女人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关系。如《碧奴》中所言:“好男儿泪往心里流,是天经地义的约束……最容易冒犯哭戒的往往是来自地上的女孩子们,这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有关哭泣的故事也总是与女孩子有关。”而曹雪芹一句妙语,“女人是水做的骨肉”,之所以轻而易举地打动了整个男性世界,就因为水的优势与缺点在女人身上一道粉墨登场。
“水”意象在对碧奴苦难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的展示当中充当了重要的叙事者和介质作用。苏童通过对眼泪大胆夸张的虚构和处理,运用递进的方式一步步加强了泪水的作用,并尝试用“眼泪”这种直观的事物,抽象地解决关于生存和困难的问题,甚至达到了宗教净化的意味。苏童在序言中说:“她用眼泪解决了一个巨大的人的困境”。碧奴从“哭的禁忌”到“哭的解放”,眼泪的力量愈来愈强大,这是其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和成长的过程,也是叙事高潮不断推进的过程:碧奴不会哭(《北山》)——学会手脚并哭(《哭泣》——用乳房、用身体哭泣(《鹿人》——学会用眼睛哭泣(《吊桥》、《树下》、《掘墓》)——泪水如泪箭,灼伤了关兵(《青云关》)——泪水如镜子,映照人心,催人反省和忏悔(《城门》)——泪水哭倒长城(《简羊将军》、《追捕》、《长城》)。
在眼泪、水、女性的多重演绎中,水意象丰富的修辞内涵和叙述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对人物形象的建构方面。水的无形、柔美、沉静、坚韧与碧奴形象柔弱、不屈、顽强的个性形成文化层面的呼应,同时,对碧奴寻夫的决心和执著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和强化作用。其二,对主题意旨和文化价值观的象征和表达方面。从创生生命的角度而言,“上善弱水”,水是万物的本源,水同女性一样都是生命的赋予者,具有创生、爱、净化的品质和力量。在小说中,“泪水”意象的反复呈现隐喻和代表了对人类最本质情感的一种追求和颂扬,“泪水”可以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激发起他们早已麻木的情感;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懂得忏悔与救赎。尤其在当代社会人心涣散、价值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时代中,这样本真的情感更是弥足珍贵。以此逻辑,碧奴的“眼泪”不仅仅是一种反抗的力量、瓦解的力量,同时,更本质上则意味着一种人性的“召回”,呼唤人们建构一种如碧奴般最原初的淳朴和善良品质的美好愿望。
袁文丽 广东金融学院
注释:
①[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33页。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7-323页。
③⑤苏童:碧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65-66页,7-8页。
④吴雪丽:苏童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第53页。
本文系广东金融学院文艺学重点学科阶段性成果;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12AZW001]、全国艺术科学规划文化部项目“流行文艺与新生代农民工核心价值观的接受机制研究[13DH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