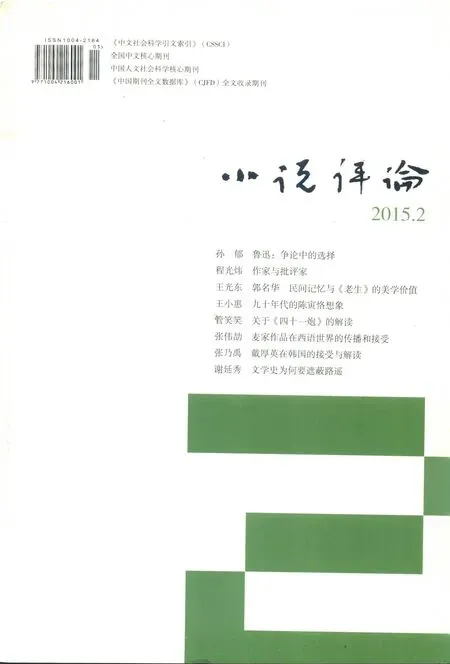论现代性视域下的莫言“乡土文学”观
2015-11-14彭在钦段晓磊
彭在钦 段晓磊
论现代性视域下的莫言“乡土文学”观
彭在钦 段晓磊
什么是乡土文学?鲁迅称当时一批作家“在北京忆叙故乡的事情”而书写乡愁情怀的文学作品为“乡土文学”。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进一步指出,所谓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在文学研究会和语丝社等社团的倡导下,为了迎合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任务,在1923年前后陆续出现,它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充满了“地方色彩”。随着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发展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提出,若“乡土文学”单单是刻画特殊的风土人情,那就“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只是一种对人的好奇心的满足。他提倡作家应该将笔触放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更加强调“乡土文学”中的“普遍性”,以及人类对于“命运的挣扎”。进入现代社会,乡土文学概念进一步深化并逐渐演化出了三个层次:首先是乡村或田园的文学,其对立面为都市文学,例如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和孙犁的荷花淀派的作品;其次是地方或地域的文学,其对立面为主流文学,如,鲁迅的小说多以浙东地区作为写作的范本,沈从文的则是湘西世界,而莫言在他一系列的小说中刻画的山东“高密”等;最后是本土或民族文学,其对立面是外来文学,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聂鲁达的《西班牙在我心中》等。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中创造了“高密”王国,它不仅仅是山东的,也是中国的,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认可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从《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十三步》中对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亦步亦趋,到《蛙》、《酒国》书信式的新颖叙事手法的尝试,再到《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红树林》、《檀香刑》、《生死疲劳》和《丰乳肥臀》中张扬生命意识以及对人性异化的揭示,总有一种新奇且涌动的气息徜徉在他的文字里,貌似丑陋的书写以及对现实的嘲讽并不仅仅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清高。火红的高粱、激情奔放的高密人形象、混杂着丑恶与真善美的较量,还有一种更加高尚和阳光的东西隐藏在他的笔下。莫言的“乡土文学”不仅仅关涉到民族文化,它更是一种在现代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悲悯情怀造就了莫言特殊的“乡土文学”观,这悲悯不仅仅属于佛教,也属于基督,更属于全人类。因此,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对莫言的“乡土文学”观进行讨论无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形式与民族文化
“本土的”与“民族的”问题讨论最初是在20世纪40年代,最终演变为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口号在当时提出来无疑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处理“民间文艺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将“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才得以创造出一种“新鲜活泼的”并且能够被中国普通老百姓接受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胡风根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将“民族形式”问题予以深化,“‘民族形式’,它本质上是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一方面使主导的基本点争取前进,一方面使这主导的基本点受到妨碍的弱处或不足争取克服:是这一争取发展的道路。它的提出,原是由于形式的能动作用能够达到内容的正确的把握而且前进这一方法上的意义,也只有在实践里面固守住这一意义才能够取得战斗的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左”的意识形态日益严重,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更加突出,文学的功用在于其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性,这无疑造成了革命文学和五四传统的一种断裂。
相比于鲁迅笔下的文化批判式的乡村景象,以及沈从文等作家所建构的“乡村乌托邦”甚至是50到70年代间的作品中对当代乡村生活的政治图解,莫言的视角都是传统而新奇的。莫言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作品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产物。笔者在论文《接受美学视域下莫言对“讲话”的继承和突破》中曾对莫言的“中西相结合”的视野做过系统的论述,“除了从十七年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马尔克斯和凯尔纳也对莫言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可以说,莫言笔下的‘乡土’,并非闭门造车,他是立足于世界的,他的作品是一个到处洋溢着生命和活力的田野,是一种对人性的诠释。”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说:“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莫言在自己作品中的大胆实践是对“本土的”与“民族的”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他继承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对所谓的“民族文化”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现代都市文明的不断侵蚀下,传统的乡村社会再也无法维持原本的自给自足状态。中国乡村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痛苦的现代化过程进程中,处于一种不中不洋的尴尬生存状态中: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残存,封建遗老遗少仍怀念着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另一方面,扩张式的机器文明凭借武力迫使乡村无法回到原初的封闭状态。中华民族在这样的一种“被迫”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遭受列强的蹂躏,也可以说,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文化是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与余占鳌、《檀香刑》中的钱丁、《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和《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等,他们坚守着传统的信念在现代社会中痛苦挣扎,可他们既无法逃脱旧思想的束缚,也不能摆脱现代力量的羁绊,他们只能放弃个体的自我寄希望于“我们”的力量。在战争年代,个体的“我”凭借“我们”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然而革命结束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逐渐沦为不可靠的“幻影”,个体的“我”依然在痛苦地挣扎着。
二、洞穴“幻影”的破灭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左翼作家们毅然举起了“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旗帜。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强调所谓的“具体人性”只能是人的“阶级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我”必须无条件的屈从于“我们”的意志。在高强度意识形态下凝聚起来的“我们”的力量使得抗日战争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甚至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意识越来越成为“我”的自由的束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次提出洞穴“幻影”的隐喻,“洞穴”中的人固步自封,无法认识自己与他人的身份,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墙上的影子反倒成为了真实的自己,人就这样把自己囚禁在了“幻影”中。“我们”是否就是“我”的“幻影”呢?
莫言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许多节日庆典活动,例如《丰乳肥臀》中的“雪集”,《檀香刑》中的“叫化子节”,《四十一炮》中的“肉食节”,《酒国》中的“猿酒节”等,充满着荒诞、调侃、笑谑、怪诞、变形,“雪集”中的“雪公子”摸乳,“叫花子节”中的黄袍加身,“肉食节”和“猿酒节”中的胡吃海喝,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小人物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来说,“狂欢世界”甚至理想于现实世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蕴含了狂欢的色彩,反抗着“我们”强大意识形态对“我”的压迫,但是这种反抗却充满着悲剧色彩,因为反抗的行为并非某个个体“我”的有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面具下力量相对弱小和边缘化的“我们”来反抗掌握主流话语的“我们”。这似乎是在洞穴里面建造了另外一个洞穴,逃避了前面洞穴的“幻影”,却又自我安慰地创造了另一个“幻影”。鲁迅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一副“个体”淹没于“群体”的图景,“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区分,且欲致之灭绝。……精神益趋于固陋。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廓尔也有过类似的话,“从属于公众的单个的个人没有一个能做出一个真正的承诺,……当个人什么也不是的时候,由这样一些个人所组成的公众就成了某种庞然大物,成了一个既是一切、但又什么都不是的、抽象的、被遗弃的虚空”,“公众是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是,是最危险的力量,但又是最无意义的东西。”市场将人本身所固有的欲望无限放大,作为群体的“我们”在个体的利益面前显得越来越不真实。《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官员以权谋私、《四十一炮》中放纵的肉欲和《红树林》中被金钱驱逐的淳朴,小人物们的欲望苏醒了,但他们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被驾驭和折磨。狂欢对于个体来说是暂时的,而现实中无法逃避的痛苦则是漫长的。
在莫言给出的偌大狂欢场景中,无论是语言、场景亦或者是小丑加冕式的人物狂欢,都好似是一场梦,梦醒后必然是一场空。全民狂欢的场景,不受官方世界束缚的第二个世界,这些都是蒙蔽人眼的假象,舞动的群体在狂欢过后除了返回现实世界重新做回自己的角色别无选择。当个体由虚幻的群体中苏醒过来再次面对舞动的群体时,油然而生的失落感是不可避免的。在生命根本价值的问题上,只是听从群体性的时潮,得到的只能是一种价值假象,只有从个人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穿越公共世界中的价值假象而独立抉择出自我生命真正信从的价值原则。
三、“自我”的复归
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人”的存在,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个体的“人”也苏醒了,“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是伴随着“人”的权威的增强,失去上帝庇佑的人并没有能很好地“认识自己”,人而神的现象大批出现。希特勒在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后将其他种族判为劣等,大批的犹太人、波兰人被投入集中营像猪狗一样被宰杀;同样癫狂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大和民族身上,明治维新之后天皇被奉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神。万能的上帝已经死掉了,莫言毫不犹豫地戳破“幻影”的泡沫,“我们”也只是假象,人剩下的唯一依靠便是“自我”。
在他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的生动的农民形象,他们固执地坚守着“自我”的信仰。《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土地改造运动中宁可选择离开妻儿也要守护自己的“私田”,《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历尽千辛养育着自己的儿女们,《红高粱家族》中的罗汉大爷为了“大义”遭受日军剥皮的酷刑,《红树林》中的无依无靠的珍珠和小海,《檀香刑》中起身参加义和团的孙丙等。当然,与这些坚守者相比,沉沦者也存在着。《檀香刑》中的异化为杀人机器的刽子手赵甲,《丰乳肥臀》中具有“恋乳癖”的上官金童,《四十一炮》中“肉欲”化身的罗小通,《红树林》中顺从和公公“扒灰”的林岚,《酒国》中的“食婴”事件和《蛙》中的“代孕”行为等等。科恩在《自我论》中指出英语“the self”指的是“自我性”,而这样的词汇常见于费希特和黑格尔以及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所谓的个体自我,在希腊语境中是一种相对于人类整体性而产生的一种自觉意识。欧洲近代的自我意识的兴起离不开文艺复兴以来对上帝的解构。当笛卡尔指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后,此世的人的主体性置换了彼岸的上帝的全知全能。“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样的问题在笛卡尔看来这首先是一个认识“自我”的问题,“我”在思考的同时意识到了“我”的存在,我可以怀疑一切,却唯独不能怀疑这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然而在洛克看来,意识决定着“自我”,人的职业可以随意改变,甚至自身的一部分肉体可以丧失,清醒时或者是醉酒的状态下,人依然可以认同自己改变前后是同一个自己。在意识的支配下,痛苦或者快乐才能够被“自我”感觉到。而幸福或者不幸的感觉只不过是意识对自己的关心的程度不同而已。鲁迅将优秀的悲剧比作“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在莫言在自己作品中直接将“我”撕裂给“我”看。《红树林》中的林岚和《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与其他人物形象是不同的,他们在精神上的苏醒抵不过肉体欲望的惰性,林岚顺从了公公的“扒灰”,上官金童无法摆脱乳房对他的诱惑。清醒者痛苦着,沉睡者沉沦着。然而生长在高密乡土的农民们却固执地坚守着,《红高粱家族》罗汉大爷和《檀香刑》中的孙丙笑骂着面对酷刑,《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昂着头承受命运抛给她的一切……他们同样痛苦,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充满激情和活力,他们是生命意义的坚守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没有了上帝,那么人的一切行为就都是被允许的”。没有了上帝的制约,没有了“我们”的束缚,“我”也就无须对什么东西负责,因而就能尽情地在虚无中遨游吗?人能够在虚无中生存,但是他无法在其中生活。“这没有爱的世界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加缪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他始终在拒绝着价值虚无主义,并且自始至终坚持着对人的一种信念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无论他自身的处境如何艰险,他始终由衷地赞美着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美好。莫言笔下生命意义的坚守者无疑都是怀有人间信仰的,对亲情的留恋、对信念的坚持、对正义的忠诚等都足以让他们平淡地看待世间的繁华和骚动。
四、结语
人是一种意义和价值性存在的动物,这就意味着个体的人不可能彻底地脱离群体,完全脱离外部世界而获得有意义的存在。然而,过于沉重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枷锁,以及上帝之手对人类的思想钳制,必然导致人的内心的不满。在莫言的故事中,坚守者与沉沦者碰撞着,坚守者依然坚守着民族文化中精粹的传承,沉沦者在现代社会的牵引下无情地瓦解着世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这是一个看似互相矛盾过程,现代性亦是这样,一方面它崇尚“无所不能”的工具理性,而另一方面却对工具理性充满怀疑,甚至是对抗。莫言获得诺奖并非意外,他本人的文字功力无疑是深厚的,其笔下的故事代表了山东高密,更代表了中华民族。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由西方拿来的“各种主义”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成了现代性视域下的莫言“乡土文学”观,它在向世界标榜中国文化的同时,又推动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创新与现代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现代性与本土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1039);湖南科技大学科技创新团队:“现代性与当代文学新潮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彭在钦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段晓磊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16.
②茅盾.关于乡土文学.[J]文学(第6卷第2 号),1936.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④胡风.胡风评论集(中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19.
⑤⑥段晓磊,彭在钦.接受美学视域下莫言对《讲话》的继承和突破[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7):164.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6.
⑧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68.
⑨彭小燕.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D].北京师范大学,2005.
⑩科恩.自我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9.
⑪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09.
⑫阿尔贝·加缪.鼠疫[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