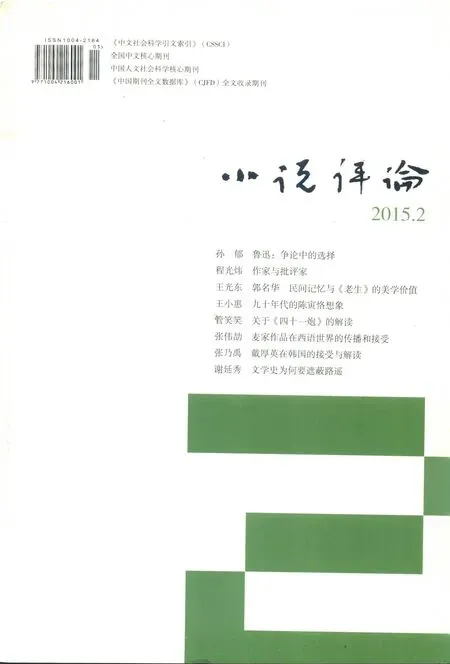张学东论
2015-11-14李丹梦
李丹梦
张学东论
李丹梦
张学东是个很有韧性与潜质的作家。他的创作历程大体和新世纪并行(自1999年开始),一个文学极度边缘化的区间。写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数量之丰、题材多变及品质的精细却有目共睹。倘非对文字、文学情有独钟者,实难做到。从内里的气质讲,这是个比较单纯的作者。他擅长发掘、描绘成长中的迷惘与阵痛,其书写构思的冲动无不维系于此。一个相对孱弱的根基,多少担心它会突然折断,却眼见它抽条发芽、青枝绿叶……虽然不甚新颖轰动饱满,却也是生命、文学的奇迹了。张学东被称为宁夏文坛的新“三棵树”之一。从其创作的顽强伸展与突围看,倒是很有点沙漠新树的气象:其貌不扬,在贫瘠的土壤中不断掘进,寻找能提供生长或文学廓大的机遇与能量。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张学东作品里对儿时经验的珍视与生命始源的追溯,对世界小心翼翼的探勘,舒缓的记述节奏,以及对善与温情的“网开一面”(愈到后来善的分量愈重),都跟沙漠的生存状态相应,一个资源稀缺、环境闭塞、气候干燥、生活格局比较单一的所在。特别是作者对善的处理,那不啻为沙漠生存念想的本能流露。愈是环境恶劣的地方,对希望的渴求、肯定愈是坚韧,如同戈壁滩上的涓涓细流。张学东的作品中不乏幽冥晦暗危险之处,却终究不致飘忽怪异狰狞,恐怕亦要多拜这种刚正明朗的生存之念的引领铅坠。
笔者不想鼓吹什么环境决定论,佛家讲,“境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环境与精神(文学)本是整体,二者相互依偎、彼此映照。《华严经》上有句话,叫“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情,指有情众生,包括人、动物等有情识的生物。至于无情,则指草木金石,山河大地。为什么说二者“同圆种智”呢?在无情的分上,它有法性;在有情的分上,则称佛性。法性与佛性是一个性,只是名词不同。这听来玄奥,但在日常感悟、用度中,我们一直在不自觉地贯彻着它。“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便是典型的无情与有情、法性与佛性相通统一的例子。将张学东的创作与沙漠新树类比,即贯穿了上述思路。沙漠树,就像张学东创作精神的“造化演示”,它为我们理解后者提供了有效的参照。
在张学东的作品中,成长是贯彻始终的基本母题。读他的故事,总能感觉到有对敏感惶惑的孩子的眸子在字里行间游移闪烁。它或者来自某个主人公(如《扑向黑暗中的雪》里的绫子),或者是叙事人(如《跪乳时期的羊》中的“我”),抑或二者兼具(此系张学东作品中最多的一种类型。《放烟》中的“我”便既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或者就是那种特别的语调、情境。以《未来的婆婆》为例,虽然写的是中年妇女,但那对衰老的惊惶以及从母亲到婆婆身份转化中的尴尬,分明是成长的改妆版。孩子的目光常常在意外、死亡与非理性暴力所造成的伤害上驻留徜徉,一面极端警惕害怕,一面又禁不住地好奇迷恋,仿佛在玩一个危险刺激的游戏,这让张学东的小说带上了纤细抒情、沉溺迷离的格调。其间氤氲着不祥的悲剧意识:世界遍布陷阱阴谋,却无法避免,每个人只能懵懂应对。由此作者把成长中的不适拉长、放大,释放了一段段来源不明、无以名状的恐惧与压抑。如果承认文学的魅力很大部分来自陌生化的体验,那么上述孩子般驻留低徊的“凝视”,当是张学东作品诗性(或曰文学性)的重要来源。
这种执着的文学感悟,从本质上讲是与世俗及日常经验相抵牾的,一种坚定的个人化视角,说白了即是带有青春特质的童年眼光。它让张学东能相当自如地涉猎犯罪题材,描摹少年犯(一个特殊的族群)的心理(《谁的眼泪陪我过夜》)。作者对底层生活的切入与纪实的反拨,亦立足于此。将少年成长的阵痛(《坚硬的夏麦》中的陆小北,《黑白》中的乐乐、《跟瓶子一起唱歌》里的草叶儿等)置入现实坚硬的底层躯壳,因了前者那恍惚多义的生命色调的感染,底层也变得文学化了:它不再是那个概念的“底层”,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的“底层”,而是一个与己相关、有切肤之痛的“底层”;底层的问题与青春、成长、人性的问题叠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诗性的“底层”。
读这类作品的感觉颇为矛盾,它的迷人与不足均在其视角本身。童年视角作为成人或世俗视角的一种补充或矫正,它含有智慧的潜质:譬如由童年视角观察引发的生态伦理及生命平等意识,《跪乳时期的羊》给人的震慑与感动至今难以忘怀。它的弱点集中于自我反思的匮乏,有时易陷入猎奇式的感觉铺张与才情浪费。《谁的眼泪陪我过夜》便带有这样的征兆:它的构思来自一篇犯罪报道。我并不反对写少年犯,但这篇小说的意义在哪里呢?若真像作者所说,是为了呈现报道中绕开的“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真实情景”、“那些不可思议的心灵历程”,那么这种人道关怀未免“人性的,太人性了”(尼采语)。我指的是那种对真实或人性立体深邃的固执认定与探测癖,它跟童年视角中猎奇的窥视、企盼与抒情欲望,张连呼应;而生活中的真实、深刻与意外,也许恰恰在于无可理喻的麻木恣睢。
这涉及到特殊经验的一般分享问题,本文所探讨的个体成长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亦可置换为特殊与一般的关联,包括特殊经验的传达、影响与效力,此即前文所讲的写作意义。倘若将少年犯以收敛的、侧面烘托的方式勾勒出来,如《坚硬的夏麦》(这是笔者目前看到的最漂亮的“底层小说”)对问题少年陆小北的处理——通篇以成熟的教师口吻叙述,他和陆小北的声音形成了对峙的、类似复调的张力关系——效果会好得多。而目前这种正面的对少年犯心理(作为一种特别经验)的大书特书,即便它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写入小说总免不了造作虚假之感。这不单是叙述技巧的问题,也不能仅归于读者的接受心理(当然,一部作品的现实意义与冲击力,跟它对读者心理的把握及二者间能否形成良性的互动有密切关系。就读者来说,对“一面之词”,哪怕它妙语连珠,总有些怀疑警觉),复调的叙述技巧中绽露的对童年视角的调整、反思,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叙述有意无意地敞现了一个交流、对话的立场,在孩子与成人之间,它当是创作个体试图融入、作用于现实或历史的讯号。
读张学东的小说一直有个疑问,如果说童年经验与成长的阵痛是文学性的重要支持,那么成长之后,文学性当栖身何处?是否总要让成长处于待完成状态呢?后者自是种简省的处理方式,但这将会遭遇窘迫的自我重复;再新鲜的经验反复咀嚼后也很难“个性”了。我以为,要让童年视角维持下去,必须把它与智性结合,而不仅仅是虚构生命之痛,调配善恶的稀罕组合,制造和满足于人性的传奇。
张学东有不少小说是围绕着伤害,一个疼痛点,酝酿敷衍开的:车厢中的一次争执(《海绵》),公务员的失控与大打出手(《应酬》),火枪打烂少女脸庞的瞬间(《寸铁》)……虽然未必是狭义成长中的伤害,但文学的感悟与思维是一样的。作者写得甚是耐心,他不动声色、一点一点地逼近伤口,然后突然将疮疤揭开,小说在疼痛、错愕中陡地结束……这让他的文本有种丝丝入扣的质感与张力。但问题也由是而来。这种疼痛作为短篇的发动是绰绰有余的,中篇亦可维持,但长篇则有些吃紧了。事实上这也是整个宁夏作家群的问题:对童年经验的重视、发掘,折射出生活格局的狭小与谨小慎微的处事态度。他们的作品就像一幅幅视野不大却精致有味的静物图、截面图(典型的短篇思维),缺乏流动感与整体透视。或者说它也有流动,但因节奏缓慢、模式单调,以致难以觉察了。
如何以有限的经验去观照涵容广阔的现实,如何在相对局促的视角中写出深重的历史、现实感?张学东于此的探索,值得借鉴。前文已探讨了作者对底层现实的处理与应对,下面看他的长篇。
迄今为止,张学东已出版了四部长篇:《西北往事》(2007)、《妙音鸟》(2008)、《超低空滑翔》(2009)、《人脉》(2011)。这在宁夏作家群中实属高产。它们都有一个成长的内核,其中有些异议的可能是《妙音鸟》:明明写的是一个西北村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怎么又跟成长搭界了呢?作者一席话道破了其中的“秘密”:
《西北往事》与《妙音鸟》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作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或两种时态:在前者那里,那段历史已经发生过了;在后者中,那段历史即将或正在发生。这样说来,我不过是那个贪玩的小孩,在该回家吃饭和睡觉的时候,继续在外面逗留,只为寻觅到那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
质言之,它们都是关乎自我的历史。《妙音鸟》中充斥着浓重的魔幻色彩,死魂灵们一次次粉墨登场,几乎到了堆砌的程度。这种想像与虚构跟《谁的眼泪陪我过夜》的构思是一类性质:它们系贪玩孩子的感觉沉迷与放纵。“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其实是孩子自我设置又苦心孤诣寻求的潘多拉魔盒。它被小心祭起,当作了自我历史的坐标或鹄的。
历史的自觉为张学东提供了长篇的动力,但如何切入与书写历史却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妙音鸟》中魔幻细节的反复涂抹,一方面是出于构思的惯性行为,另一方面亦是对历史把握乏力的表现,一种虚构或技巧的透支。我们看到一幅幅孤立的、技法相近的画面相互叠摞覆盖,却很难形成有机的连续整体。而要给人以历史的深邃印象,这种有机连续性恐怕不能或缺。
在张学东的长篇之旅中,短篇小说《送一个人上路》(以下简称《送》)功不可没。2003年,《送》在上海荣获优秀短篇小说奖。正是通过它,作者获得了历史的自觉,长篇的抱负与信心亦由此而生。它记述了当年的生产队长(“我”的祖父)为一个绝户的老饲养员韩老七送终的故事,被誉为“在精致的结构中再现了历史的沉重”。此语对张学东恰似醍醐灌顶。据他回忆,最初写《送》,是想尝试写写孩子记忆中死人的样子,一个不无离奇的细节,而且刻意要写得跟一般的死人不一样,于是便有了韩老七的怪诞形象。小说结尾处那段看似不经意的历史背景的补记,是随手添上去的,不想“正是这几十个字挽救了这篇作品”,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注意到了它,它让《送》“有了意义纵深的历史和道义感”。换言之,张学东是无意间撞入历史的。他从评论者的意见中领悟到:一个由孩子眼光铺陈的世界,居然能具有历史寓言的意味,这不正是对待历史的最便捷的方法么?一度陷入死角的《妙音鸟》由此插上了大胆想像的翅膀,把《送一个人上路》跟《妙音鸟》相比,那种由内而外的历史映射策略,显然明晰化了。
评论界对《送》的评价是不错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内外可以割裂开来,那种认为仅仅专注于呈现内部世界(个体的特殊经验),时代背景只要捎带一下,便能赢得历史或言外部历史即会召之而来的想法,未免天真了。张学东近来的发言一直强调“历史的担当”,但他的创作尤其是长篇,与其发言尚有距离。实际上,他在应对历史时采取的是迁就自己感觉惯性的、重内抑外的、避重就轻的书写策略。说来这种策略也未尝不可,但在阅读中很难抹去单薄、掣肘之感。从同情理解的角度,可以说这是不错的个人成长史,而它跟作者的写作抱负又不相吻合了。
以《人脉》为例,它的叙述者不断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转换,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乔雷。不少论者觉得这种转换相当巧妙,我倒是偏向认为统一用第三人称好。就作者在后记中的交代——这是对“一代人的生活写照”、是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望”——而言,第三人称更大气;而一种技巧的使用若过于触目频繁,总嫌不够自然。当然作者能从主人公“我”对自己新名字“乔雷”的生疏上,解释这种转换,但更深层的原因或驱策,我以为是第一人称(那种童年青春式的文学感觉、思维)在描述外界时的局迫、力怯所致,而作者又不忍放弃这种娴熟“来电”的写法,所以才有了上述“巧妙”的调和与转换。
《人脉》是张学东最出色的长篇,作者试图写出“成长后”的状态。乔雷对自我行为的反思以及作品向传统价值(仁义礼信)的回归,即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虽然回归的过程陡峻、直露了点,但这种行为无论如何值得赞赏,亦算是长大的勇气吧。小说中感觉不到多少80年代的气息,实际上叙述人并不关心这点,他对外是漠然的。在乔雷生活的岁月里,外面的世界(包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读者并不明了。仅在跟乔雷的日常生活或经验(如女友上官莲因嫌贫爱富背弃了乔雷;露天电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录像馆)相系时,我们才能感觉到外界的轻微蠕动与喧嚣。另外,作品中还散落着一些关于80年代的时尚符号:邓丽君的歌,崔健的《一无所有》,等等,它们飘荡在乔雷的记忆中,把一个人的青春装点、陪衬得不那么孤异了。这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呈现,不如说它是“去历史”的。
令叙述人难忘的是某些零散、动人而凝固的瞬间,它们像掉了线的珠子,很难穿起来。一忽儿还是乔虹那带着酒窝的甜甜的笑容(她和“我”是那么接近),一忽儿她便没了影子。再出现的时候,她就被一个傻子硬拉着莫名其妙地走掉了。一忽儿“我”和乔雨还那么针锋相对,一忽儿乔雨仿佛变了个人,她竟然跟乔雷之间萌生了一种介乎亲情与友情之间的牵系。这里断裂是明显的,有时不禁要问:当乔雷跟寡妇丁丽英如火如荼的恋爱之际,乔虹是怎么想的,她的精神难道亦如她身体的残疾一样哑默了吗?乔雨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进城读了一年大学就能让一个乖张的少女变得如此通情达理?
上述疑问在小说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唯一的解释或理由在于这是一种有天然缺陷的记忆,所有的人物、性格、细节都是按照“我”的情感需要拼在一起的。其实就小说的主要人物关系布局——乔虹、乔雨、丁丽英、上官莲都对乔雷有某种“爱”的联系——而言,已不难体会隐隐的自恋。这也是由童年视角发展而来的叙述的固有特质。为什么在乔雷的记述中,没有同性的伙伴关系?就笔者的经验,这是“70后”在回顾80年代(那时的男女关系还相对拘谨)时一个相当重要的记忆支点与维度。倘若要呈现“一代人的生活写照”,让乔雷担当起“一代人”的典型形象,这种伙伴关系是应该顾及到的。它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证明了叙述视角的自恋性。
《人脉》就像一首成长的叙事诗,弥漫着忧伤和迷惘。乔雷一出场就是个失去父亲的孤儿(《超低空滑翔》中的白东方亦是如此),他的姓氏漫漶不清。作者似乎以此暗示乔雷是个迷失了历史来路与方向的人,而乔雷在今后的生活中注定要屡屡通过回想过去来缓解孤独,尽管回忆本身痛苦不堪。在此能体会到叙述人对历史溯源及连续性的强烈渴望。这种历史的清流、梳理,跟自我的构建凸显及统一性认知,互为表里。
我一直不大理解为什么作者说他在《人脉》中最想表达的东西是:“乔雷一代人身上或深或浅都打着‘文革’后遗症的烙印”,这点在《人脉》里表述得既牵强又模糊。现在看来,所谓“文革”后遗症,当是自我历史来源处那犹似黑洞、深渊所在的表征或替代,《妙音鸟》对六七十年代的硬性虚构与进入,亦含有这样的追溯味道。如果作者把这种自我历史的记忆与组织本身以“元小说”的形态(即哪些是想起来的,哪些记不得了,哪些是不能记的,为什么只能想起这些,为什么是这样的记忆格局?)敞露出来,抒情可能更为动人吧?这种抒情诉求在作者那里明明存在,但在表述中它又和另一种概括、寓言历史的冲动(“人脉”的意思就是要为时代把脉)混合在一起,结果二者都有点不伦不类了。
究竟该如何由个体的成长阵痛切入现实和历史呢?这里有一个内外平衡观照的问题,不是在策略技巧的层面,而是在基本的态度上。如果说写内即是写外,那么反之亦然,写外即是写内。内外需要平等的顾及与眷恋。就寓言历史的冲动来说,倘若在《人脉》里加入些看似自然主义的风俗描绘,抑或将丁丽英这个带有民间精神的女性人格独立化,结果也许会浑朴厚重些吧?这并非单纯的内容层面的修改或增补,而是对外尊重与慈悲的本能外化。说来也不存在什么本质化的历史整体,我们讲,在作品中读出了宏大的历史印象,其实也就是对创作主体周到平等慈悲地关照世界的感应罢了。进而言之,历史的呈现,实为心相或境界的部分。心为见分,历史为相分。由于心、相原本一如。能呈现多大幅度、几许真实的历史(相分),取决于心地的平等涵容能力。
张学东的问题在于他太在意和珍惜自我的某些部分(包括经验、感觉、构思等)——这也是当下作家的普遍问题——以致原本互动一如的内外(心与境)割裂分离了,难以呈现开阔的历史气象。写作的辩证法在于:它一面需要自我,另一面也需要放下自我。只有善于放下,才能不断赢得独特的、不同凡响的“个我”与境界。这不单体现在对外的叙述或历史的营构上,即使就前文所说的“元小说”的抒情诉求来说,也是需要放下一部分自我的身段的。因为在敞现个体记忆的褶皱时,势必要暴露一部分自我的阴暗。这跟自我的反思性质一样,没有放下的精神是做不好的。至于抵达、呈现深远的历史,更是无从谈起了。
李丹梦 华东师范大学
注释:
①张学东:《谁的眼泪陪我过夜·自序》,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②周立民、张学东:《唤醒内心觉醒与人性回归之光——长篇小说〈妙音鸟〉访谈录》,《作家》,2008年第11期。
③陈思和:《在精致结构中再现历史的沉重——张学东短篇小说论》,《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
④补记如下:“韩老七,贫下中农。早年给生产队放过牲口,曾受命调驯队里的一匹爆裂的军马遭受意外伤害而永久丧失性生活能力……其时,祖父尚任生产队长。”,见张学东:《送一个人上路》,《上海文学》,2013年第8期。
⑤徐大隆:《张学东访谈录》,《红豆》,2005年第10期。
⑥张学东:《我的长篇小说之旅》,《文艺报》,2012年3月5日。
⑦张学东、夏烈:《一代人的文学宿命:直面真实与历史担当》,《百花洲》,2010年第2期。
⑧ 张学东:《人脉》,第311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
⑨参见《人脉·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