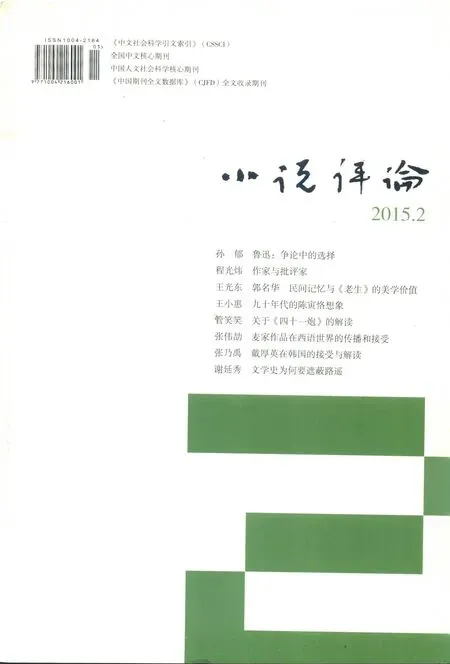九十年代的陈寅恪想象
——从《读书》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2015-11-14王小惠
王小惠
九十年代的陈寅恪想象——从《读书》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王小惠
90年代的“陈寅恪热”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当时推崇他的人,既不是史学界之人,也不欣赏他的“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更没有去看过他的学术著作,歌颂的只是附着于陈寅恪的时代想象。从《读书》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陈寅恪想象的建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本文以此为对象,来勘探陈寅恪与时代气质的相通之处,窥出90年代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正如克罗奇所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
一、1993年:“要找一个支柱”
在1993年前后,在知识界影响力处于顶峰的《读书》大量地刊发关于陈寅恪的文章,对此笔者采访了编辑吴彬,她说道:“借陈寅恪来说自己,当时人都很迷惘,要找一个支柱,当时思想界有一种莫名的隐痛与迷惘,找寻出自己的立脚点,定位自身的地位,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找自己今后应该安身立命之点。有一种背后的情绪在这里。而对于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关注社会,解决知识分子、学者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怎么解决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陈寅恪是一条很好的思路。”
在1993年,因陈寅恪诗句“最是文人不自由”在《读书》引发了关于读书人安身立命的讨论。葛兆光在《读书》1993年第5期,发表《最是文人不自由》感叹陈寅恪身上的数重悲剧,指出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许多文人都期望愈合“道统”与“政统”,从而从政救国,而陈寅恪只伏案于书斋之中,用“一张纯粹的书桌”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但他的学问不可能像鲁迅式的文人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因此他被人认定为“乾嘉余孽”。而吕彭在第8期发表《最是文人有自由》,他认为陈寅恪式的“书斋学者”在“述学”中享受着精神的自由,文人的本职工作是“述学”,而“‘议政’是不懂政治操作容易滑向‘骂政’,‘文化批判’又由于缺乏‘述学’之功底也容易变为‘道德批判’”,最后他得出结论“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社会并不是属于文人的……你的真正的实在只有在书桌之前才会出现。”二人对于“文人有无自由”的看法,殊途同归,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肯定陈寅恪的“为学术而学术”精神,反对知识分子追求的文化批判功能,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期望摆脱‘借学术谈政治’的困境。
据吴彬介绍,此次讨论,是与陈平原在《读书》1993年第5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联系在一起的。陈平原在文中,提出“学术”与“人间情怀”各自独立互不相扰的思路,认为“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而“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以及“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读书》当时试图处理“从政”与“述学”的关系,来探讨知识分子位置的问题,吴彬回顾:“当时知识分子处理学术、书斋等问题,想到前辈身上去寻找资源,以解决现实存在的一些困惑,当时基本上有这样一个目的。从陈寅恪这样老一辈的史学家或知识分子身上吸取一些精神营养,为眼下的突围寻求方向与策略。”后来《读书》刊发一些文章,用陈寅恪的事迹肯定了陈平原的“学术”与“人间情怀”独立的思路,论证陈寅恪“主要从事史学研究,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很难看出他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态度,而他却‘借诗篇议论了时事,借吟咏臧否了人物’。”同时陈平原在文末,希望“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果才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脱离实际”与“闭门读书”的陈寅恪正为9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近代以来,许多学人要么离开学术投身于政治世界如陈独秀,要么以学术来谈政治如梁启超。建国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的“反知识分子”的运动,让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迫切地渴望恢复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因而提出“复活五四精神”。这种“五四精神”就是“对社会抱有深刻的关心和使命感、以自己的学识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态度。”但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积极性,遭遇了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变故,这以后,知识分子重新开始定位自己,从思想转向了学术,从当下转向了历史,放弃八十年代那种学术主要作为社会、思想启蒙工具的思路,而是回归学术本位。吴彬回顾道:“93年的时候,大家对学术史非常感兴趣,知识分子开始自己检讨自己,对老一辈的学者,尤其像陈寅恪这种对学术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回顾的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些人。49年以后,这些人处于非常边缘的部位,不是特别受关注,甚至很多学者根本大家都不知道,也没有人读过他的任何著作。80年代上海古籍蒋天枢出版过《陈寅恪文集》,但太专业,不是太受人关注。90年代很多人关注不是由于对他的学术有多少了解,而是他对学术的态度,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骨受到大家的关注。”
90年代前,《读书》零星地发表有关陈寅恪的文字,大多称赞他的朴学成就,认为“开拓了清代朴学较薄弱的两个部门——史学和文学”,“开辟了以诗、文、小说证史和析史的新领域。”在1993年前后,《读书》对陈寅恪的定位发生很大的转变,推崇他“把书斋的学术当作‘精神之学问’,把学者的生涯当作实践‘道’的途径”的真挚的学术信仰。葛兆光称他“在信仰消失的时代恪守对学术的虔诚信仰,在没有精神的时代追寻‘精神之学问’,把终极价值与人生意义物化在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于是感到了满足与平静。”周一良认为陈寅恪处在“非驴非马之国”,“既能像柳下惠那样混迹于旧京茫茫人海之中,又能像伯夷那样,躲进西山之畔的清华园搞自己的学问”,因此“作为文化遗民,陈先生毕生坚持的信念,就是为人方面的三纲六纪和治学方面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这里的陈寅恪不再局限于史学大师,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模范性先驱,体现出知识分子的骨气。吴彬认为“史学大师只是一个学者,知识分子代表的是一种风骨。”
陈寅恪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骨,与 “人文精神大讨论”所提倡的“敢死队”精神是相通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在最后感慨:“在美国,研究数学的人自称为‘敢死队’,因为那儿数学教授的年薪最低。而这些人因数学而不悔,才有了人数不多却仍执世界数学发展之牛耳的美国数学界。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国学的美国尚且如此,以志于道为国学的中国就更靠这样的‘敢死队’来维持人文精神的活力,当然可悲,但是,倘若你还能看见一支这样的‘敢死队’,那就毕竟是不幸中之大幸,能令我们在绝望之后,又情不自禁要生出一丝希望了。”陈寅恪的“敢死队”精神也指他“秉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只趋真理,不认权威”。程巢父在《失落的人文精神》中说道:“陈寅恪先生宁肯著作搁浅不能出版,坚持不改‘黄巾米贼’四字,就是人文精神的表现。”“黄巾米贼”在革命年代被塑造为伟大的农民起义,但“硬要把迷信落后的乌合之众美化为农民起义,是意图伦理作崇,即在认识论上先确定一切造反都予肯定,不顾事实,违背学理,即凌驾学术之上的所谓‘站稳立场,端正观点’的权威指令干扰真理是非判断的‘学术病毒’,故陈先生不作分寸的让步。”
在《读书》1994年第4期刊发的《人文精神寻踪》中,张汝伦认为人文精神体现在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生命中,但这往往被“遮蔽”,“‘遮蔽’在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始终处于文化主流之外,遭冷落、受批评、被否定。二是指为主流倾向支配的思想史对这部分进行了排斥性解读,从而又添一层遮蔽。”高瑞泉也指出,陈寅恪等人都曾有过终极关怀,虽然在“当时受到冷落,却是符合人文精神的。”在“重估八十年代学风”与“人文精神讨论”时,知识分子在陈寅恪等前代学人身上见到了一种一直以来被遮蔽的道德伦理,这种道德伦理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而是退守书斋,潜心学术。据吴彬回忆,当年《读书》收到大量谈论陈寅恪“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存方式的稿件,这也证明了当时知识界企图从陈寅恪身上找到精神的凭寄,表明“他的已逝的经历又极富代表性地包含着了以学术与思想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欲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抉择自己工作模式与维护知识信念体系的问题。”
对此,李泽厚批判道:“90年代学术风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则被抬上了天。而从一些刊物的自我标榜看,仿佛有些人硬想回到乾、嘉时代去。”而吴彬认为:“《读书》不是引领,而是跟随,是反映。原处的面貌,有它的出发点,没有清晰的计划。《读书》反映读书界不同学者的思考,他所思考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读书》把他反映出来,影响到其他学者。但是每个学者的思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不是意图与计划。当时时代无法整齐地计划。”在竭力地推崇陈寅恪治学方式的学者如陈平原、葛兆光等,他们在90年代已经40多岁,是学术的中心,他们从小经历过建国后的一次次革命风潮,见到的都是革命的负面效应,并且经历了80年代大量接触西方学术,对前辈知识分子干涉社会所起到的作用表示质疑。他们的质疑,是基于他们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希望能让学术职业化,各司其职地完成社会分工。这里面的理论支撑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掌管道德,知识分子专攻学术”,拒绝政治介入学问世界。
二、1995年:“提供一个案例”
九十年代知识界在对八十年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背景下,《读书》从陈寅恪身上发现异于八十年代学术路径的学术精神,这与当时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主张用陈寅恪等学人来理清中国现代学术源流的想法是一致的。董秀玉从1992底开始全面主持三联书店工作,当时就提出编订陈寅恪的全集。而三联书店1995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发“倾城倾国地话说陈寅恪。”对于三联书店选择出版此书的缘由,笔者采访了责编潘振平,他回顾:“陆键东因为在广州,他对这段事情感兴趣,他是自己定的选题,94年他到北京来他主要采访吴学昭。他可能是从吴学昭先生那里听说三联书店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他来找我,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当时在中大出版社当社长。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写陈寅恪的传记,希望从三联了解一些情况。因为当时三联正在编《陈寅恪集》,他有可能从吴学昭先生那里了解到三联的情况。我去吴学昭先生见过陈家的两个姐妹,跟他们商量编《陈寅恪集》的事情,陆键东可能知道这个消息,跑到我们这里来问问有没有新的材料。他就来谈,谈得挺好,我就说,你这个稿子,写出来以后,给我们看看。可由我们来出。当时他还正在写。”据潘的介绍,此书在1995年印了6次,达10万册。而三联在此书上找到了如下两大兴趣点:
第一,用档案来描述历史。潘振平说到:“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以及人生中间的故事,在知识界有所流传。他建国后到了中大,关于他的传言有很多。去台湾,还是不去台湾?例外涉及到当时北京中科院组织中古研究所,要请他回来主持,他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有传言。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台湾的余英时先生专门写过这样一本书,关于陈寅恪晚年诗的考证,这个书当时在海外的影响比较大,广东这边有找人(冯衣北)组织写了文章与他进行讨论辩驳,这个事情也没有得到一个结果。大多认为冯是奉命而作。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看了以后。它大量地引用档案,而不是传说。当然它有采访,它有档案,它又有自己的思路,它又饱含感情的写法。那我们觉得这个书很合适三联书店。陆键东尽可能地给出了一个解释。通过档案,通过采访,把这些传说明晰化了,比如说陈给郭沫若,尤其是中古史研究所这个事情。汪篯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原件,陆键东找到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清楚了。他是一个什么态度,他提的是什么要求,清清楚楚。关于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没有可以进一步揣测。那个报告是他第一次从广东省的档案馆里找出来的。这个报告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只有中科院的领导们看过,郭沫若看过,竺可桢的日记也记载了讨论过这件事情。这些陆键东都翻出来了。我是学历史的,最吸引我的就是用档案的办法来描述历史,叙述历史,而不是道听途说。”
此书披露了1953年汪篯记录的陈寅恪自述《对科学院的答复》,比较敏感,当时很多媒体想采访三联书店,但都被回绝。当年汪篯带着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两封亲笔信,恳请陈寅恪出任中国中古研究所的所长。而陈提出担任其职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反对“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不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他在西方曾学过,但发现当时完全是引用毛主席语录来评价社会历史,他认为这种方式是有问题的。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多把学问当成是一种政治性的发言,陈寅恪始终保持学人的独立思考,例如在席卷学界的“批俞平伯运动”中,他留下了八个字,即“一犬吠影,十犬吠声”。陈寅恪不仅排斥外在的政治空间,而对当时地位显赫的政府官员陈毅、康生、周扬、郭沫若等始终保持疏离与对抗的姿态。例如周扬以“一个学人的心情去探访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老先生’”,但“谁料陈寅恪坚决不想见周,陈序经很为难,再三相劝下陈寅恪总算答应下来。”而康生的拜访却被拒之门外,不论“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陆键东用档案与采访的方式,展示在整个50、60年代陈寅恪不合作的态度,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解开了知识界对陈的猜测。1983年,余英时在香港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一系列文章,认为陈寅恪晚年“譬如在死囚牢”,后悔当年没有去台湾。对此,大陆方面做出了回应。在胡乔木的挑选与授权下,一位在中山大学就读的作家干部化名为冯衣北,发表《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等文,与余英时展开辩论,认为陈对国民党政权“失望到极点”,深信共产党,绝无去台湾之意。按余英时的话,此书支持了他80年代做出的判断,他说:“这里我要特别地感谢陆键东先生《最后二十年》对我的帮助。若不是他把胡乔木和写手‘冯衣北’的事调查得清清楚楚,并一一记录下来,我讨论第二次风波的‘官方反响’便会发生如何取信于读者的困难了。”
第二,涉及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潘振平说:“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是涉及到当时的政策,那么个体知识分子生存的状态是什么,在政治运动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典型的话,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要了解,你不也是去翻,翻也没法翻,事情都过去了。该遭的罪已经遭了,现在你把它弄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当时他们的想法与做法,在今天看起来自然各有各的想法。通过这些人的遭遇,今天的执政者、施行者,自己可以讨论到底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起码那种剥夺别人思考的东西,显然是不对的。该限制的,你可以限制,不可以限制的,尤其是对文化,对学术,不要过多地去考虑争锋相对。陆建东的这个书不是因为它所采取的态度,同情陈或者不同情陈,这对我来说,不重要,他的书最有价值部分对我来说,完全是根据档案来梳理的,书名我们是讨论过的,最后我还是坚持用这个,原来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但这名字比较地直白。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这本书不能解决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它最多只能提供一个案例。我们也没想去全面评价,这本书也做不到。”
“思想改造”是建国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政策,陈寅恪曾做《男旦》一诗讽刺道:“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认为“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只剩下在戏台上表演的“妾妇之道”。陆键东用档案展示了抗拒“思想改造”的陈寅恪,被关进牛棚、遭受批斗的不堪岁月。他被诬蔑为“比狗屎还要臭”,遭到“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以及“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的摧残,更要应付“那一群群突然而来的造反者登门批斗的悲惨场面。例如陈氏晚年已经双目失明,在文革时,“造反派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并且作者引用了梁宗岱夫人所写的文字来旁证陈所遭受的苦不堪言的摧残,即“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陈寅恪的经历,实则也是大部分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吴小如就指出:“这些经历,不仅伤了陈寅老这样大学者、老专家的心,也同样伤了几乎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作者所写的虽只是陈寅老的个人遭遇,实际上也触及了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在各自内心深处已经或者至今尚未完全愈合的创痕。”
作者对陈寅恪晚年不幸遭遇做了许多情绪化的渲染,按谷林的话讲,“只剩得同声一哭,不克回环咀嚼矣。”止痷也批判《最后二十年》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在虚张声势语境里讲陈寅恪,认为“他只是一个个案,不能说是范例,更不应该变成某种情绪化或鼓动化的产物。”这遭到程巢父的反驳,他认为陆著虽有缺陷,但此书所带来的“陈寅恪热”并不是任何情感上的炒作,而实在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情绪”的反映。程还引用畅销书的“编辑小语”来解释“共同情绪”,即“被推荐的书中,反思‘反右’、‘文革’的也占了绝大多数,这恐怕不是出于偶然或巧合吧?事实上,这类图书的出版已成了去年出版界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普遍情绪’的,从这一出版热点和专家们对此类图书的推荐中,也约略可以见些时代的普遍情绪吧?”90年代反思“反右”与“文革”的书非常畅销,这与当时“告别革命”的思潮是密切联系的。
陈寅恪的案例,展示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次次运动是反智的社会风潮,以“不断革命”与“彻底革命”来处理社会矛盾,最后走向了正义的反面,毁灭了有价值的事物。“陈寅恪的悲剧恰恰发生在以‘革命’的名义来无限制地推行某种理念,而这种理念又被大多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真诚与狂热地奉为正义的所谓革命的时代”。陈寅恪对抗于政治,并且殉道于这种对抗,这在90年代转化历经劫难后的荣耀,让人对这位坚守自由与独立的学术前辈不由自主产生敬意。《最后二十年》塑造的陈寅恪在高气压的政治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对学术专业抱有“殉道”的精神,这在整体性“告别革命”的时代情绪里,确实起到了“抚慰剂”的作用,让知识分子在陈寅恪的身上找寻到了某些同病相怜的沧桑感。
但潘振平提醒:“《最后二十年》这里面也讲到了陈毅等,他们对50年代知识分子的鞠躬、摘帽这些事情,也讲到陶铸怎么对待陈。其实陈寅恪的待遇是很高的。他获得的待遇是很不错的,牛奶呀,面包呀,这些东西都是特供,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多困难!包括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还保证了他。他有一个西式生活的习惯。黄油面包这些东西。当时特供给他。专门还给他修了路,他从一级教授来讲,他的收入也还是蛮不错的,能够维持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在整个50、60年代,他对中共的政策,他有一个不合作的态度。但领导人对他还是很关心的。不能光看到负面的东西”。对建国后知识分子反思,需要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在正视不幸的前提下,审视背后的复杂性。
三、1998年:“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披露了史学前辈的孤苦遭遇,但“此后陈寅恪的话题却始终在文人之间徘徊,强化旧式士大夫情绪,很少有文章触及更为深刻的层面,倒真成了一个问题。”1998年林贤治提出质疑,认为陈寅恪只是“文化遗民”,没有多少思想史意义,他说:“作为诗人学者,陈寅恪自由其存在之价值,但不必悬作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正如‘为学术而学术’自有其成立之理由,不必一定尊为学术之正宗一样。”对此,朱学勤提出:“即使如林所言,陈寅恪是个文化遗民——具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一个文化立场上的保守主义者是否可能同时出现自由主义倾向?如有这一可能,自由主义者又当如何面对?”
这一问题在王焱的《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得到解决。王焱此文,第一次从自由主义学理角度来处理陈寅恪,认为陈的“中古政治史研究,注重社会力量,但更将关注的重点移放到个人身上,着重为个人自由的权利辩护。如果说陈寅恪是保守的,这种保守也是对自由的保守。”王焱发现了陈寅恪的亲自由主义的古典主义思想。之后,在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中,摘录了陈寅恪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对科学院的答复》以及主张“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的《论再生缘》。李慎之在此书序言《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认为在北大庆祝百年校庆之时,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他说:“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在他看来,陈寅恪这样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而“今后随着中国的文明进步,这种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
从《读书》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发的“陈寅恪热”,为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本土资源。80年代末,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正面交锋,重挫后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主张解放思想,提出市场改革。自由主义也开始回潮,与权威主义的关系有些缓解,而“谈谈陈寅恪……无意中却‘挤出’了一条自由主义的言路。”李慎之明确地提出思想家陈寅恪,认为他“替为奴性所主宰的中国人立一个新的传统”,“为中国文化添上了一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统。其价值将愈后而愈显”,而这“今天已成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同时他反对陈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之说,他认为陈晚年表彰陈端生、柳如是的自由独立精神,并且她们一为罪妇,一位妓女,是社会底层之底层,而陈却“同情陈端生反抗‘当日奉为金科玉禄之君、父、夫三纲’,赞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对柳如是,则甚至夸奖其‘放诞多情’,称之为‘罕见之独立女子’。这岂是一个文化遗民,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说得出来的?”
同时,陈寅恪的自由独立精神也被纳入五四传统之中。王元化在《五四精神与激进主义》一文,提出:“‘五四’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继续‘五四’的什么精神?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这是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铭中提出的,很少被人注意,我认为这句话倒是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遗产之一。”并且他指出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最后演化为提倡做螺丝钉以及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反而陈寅恪保存了五四的自由解放精髓。陈思和也认为陈寅恪的自由主义精神与鲁迅的“现实战斗精神”处于同等的位置。指出“陈寅恪先生过去是被人看作保守派的一员,与新文化运动无缘,但从陈寅恪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成就而言,传统的文化模子根本就无法铸就那样的知识和人格,再则,虽然陈先生以传统文化的守护人自居,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说到底仍然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90年代后期让知识界出现“左”与“右”的区别,裂变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左派”认为近代历史中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以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其合理性,并指出当时社会的弊病是“西方病”、“市场病”,提醒要审视市场机制。“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没有对至“五四”以来的左倾激进主义思想进行清算,而只有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使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治国。“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引发了塑造国家主义与非国家主义的文化英雄。在“新左”挪用红色偶像之时,自由主义也开始建构处在主流边缘话语之外的英雄,他们“试图赞美那些在‘集权体制’下英勇斗争的英雄,并强调自由的知识分子必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遭受屈辱。”而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自由主义作为知识界的主要思想流派,对中国传统尤其是近代的思想资源加以改造吸收,而陈寅恪‘十字真言’正为此中佳选。所以,陈寅恪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形象一步一步被强化。他说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王小惠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吕彭:《最是文人有自由》,载《读书》1993年第8期。
③⑥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载《读书》1993年第5期。
④2014年9月23日笔者对吴彬的采访。
⑤朱新华:《“陈诗”急需“郑笺”》,载《读书》1994年第5期。
⑦佐藤慎一(日)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⑧2014年9月23日笔者对吴彬的采访。
⑨何新:《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读〈陈寅恪文集〉论陈寅恪》,载《读书》1986年第5期。
⑩⑪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载《读书》1992年第6期。
⑫周一良:《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载《读书》1993年第9期。
⑬王晓明、张宏、徐麟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⑭程巢父:《思想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⑮⑯高瑞泉、袁进、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踪》,载《读书》1994年第4期。
⑰㉞黄卓越:《历史迁流中的固执信念》。
⑱李泽厚:《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1998年,第270页。
⑲夏中义《谒陈寅恪书》,载《文艺争鸣》1997第6期。
⑳㉑㉒㉓㉖㉗㉘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96页,第128页,第266页,第345页,第452页,第460页,第460页。
㉔周言编:《陈寅恪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㉕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㉙吴小如:《读传记二种》。
㉚谷林至止庵函,止庵《谈传记》引录,载止庵著《六丑笔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㉛止庵:《作为话题的陈寅恪》,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7日。
㉜㉝程巢父:《思想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页,第36页。
㉟㊲李世涛主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
㊱林贤治:《文化遗民陈寅恪》。
㊳王焱:《社会思想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㊴㊵㊶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第3页,第3页,第220页。
㊷㊸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思想家陈寅恪》。
㊹王元化:《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6期。
㊺陈思和:《关于90年代文化思潮的一点想法》,载《山花》1998年第8期。
㊻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㊼《名社30年书系》编辑出版委员会:《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