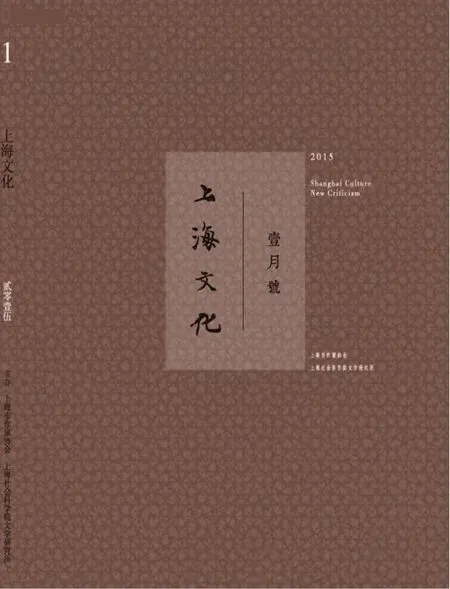帕斯卡·基尼亚尔:异域的文人
2015-11-14魏柯玲
魏柯玲
帕斯卡·基尼亚尔:异域的文人
魏柯玲
但“作家”一词似不足以形容基尼亚尔。不妨说他是最纯粹最古典意义上的“文人”
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1948-)是法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他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约五十部著作,涵盖小说、评论、随笔等多种体裁,多次获得包括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在内的主要文学奖项,且有提名诺奖的传言。他的许多作品已译为多种语言,并有几部小说改编为深受欢迎的电影(如《世间的每一个清晨》和《阿玛丽娅别墅》)。在中国,基尼亚尔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至今约有五六部小说和一部随笔集译为中文(如余中先译《罗马阳台,世间的每一个清晨》,张新木译《游荡的影子》,曹德明译《阿玛丽娅别墅》等),还有一些正在进行和筹备中的译介研究工作。
初见基尼亚尔,无论谁都会惊讶于他的目光:极为专注、纯粹而深邃,透明无碍仿佛洞穿一切,深不见底仿佛直达彼世,又闪耀着谦和与睿智的温暖光辉。他常穿一件黑色T恤,身子略向前倾,是聆听的姿态。事实上,基尼亚尔堪称当代隐士。他早年主修哲学,曾受教于列维纳斯和保罗·利科,兼具深厚的音乐和艺术素养,创办并主持过凡尔赛宫巴洛克歌剧戏剧节,却于1994年辞去伽里玛出版社编委的职务并推却一切外部事务,从此潜心写作。但“作家”一词似不足以形容基尼亚尔。不妨说他是最纯粹最古典意义上的“文人”:类似中国古代为“文”所化之人,亦是法语里的“lettré”(源于拉丁文litteratus),即浸淫于文字与文学、博古通今之人。基尼亚尔本人的话可谓夫子自道:“文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阅读古人。个体生命于是因原初本来的力量而强盛。[……]他是属于过去时态的人;他是游荡者;后缀者;文字的;边缘的。”无怪2004年在法国北部著名的瑟里斯-拉萨勒城堡(Cerisy-la-Salle)举办的以基尼亚尔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即命名为《帕斯卡·基尼亚尔,一个文人的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文坛相继受到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后现代等种种思潮的洗礼,到20世纪80年代后则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文本探险与叙事回归,理论探索与语言冶炼相互应和冲撞,构成一幅难以界定的“极端当代(extrême-contemporain)”的图景。在此情形之下,基尼亚尔以其熔历史想象、文学虚构、艺术审美、哲学思辨为一炉的创造性写作独树一帜,令人瞩目。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远离潮流与媒体的孤独创作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深受学界好评,也使他拥有了广大的忠实读者。仅在法国,对基尼亚尔的专门研究已产生了十几部专著,论文则难以计数。上文提到的2004年瑟里斯国际研讨会聚集了数十位法国国内外专家学者及作家本人,论文蔚为大观,亦已集结成书。十年后的2014年夏天,瑟里斯城堡又举行了第二次规模盛大的基尼亚尔研讨会。此外,在法国各地和其他许多国家也不断有关于他的研究活动、翻译及论著产生。
但总的来说,由于其作品卷帙浩繁,体裁多样,文笔精微古奥,加之作家旁征博引,跨域广泛,从古代拉丁作品直到中国和日本文学,从音乐绘画美学直到语言哲学,致使我们对之翻译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与其作品的规模与地位尚不相称。而基尼亚尔极具个性和创新性的书写及其融汇古今东西的创作,应该得到中国文艺界的关注,并且他对中国古代文艺经典有深刻独到的阅读与领会,也值得我们在复兴汉语文化的努力中借鉴。本文即试图提出一些对其作品的思考路径,以期引起更加深入的阅读和讨论。
体裁的超载与融合
小说——由意象组成——与文论一样具有思辩性,由论据、列举、隐喻、辞源、引文、警句、故事构成
对“体裁”或曰“类别”(genre)这一概念的再思考是当代批评的一条重要路径,它打破和颠覆了传统的界定方式,建立起与“性别(gender)”、“谱系(généalogie)”等概念的隐秘关联,为文学作品的解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基尼亚尔的作品在这一方面的探索与创造堪称典范。在他为数众多的著作中,有些标有清晰的类别提示,如“小说”,“随笔/文论”,“故事”,还有的直称“记叙(récit)”,更多的则没有任何标示,令人无从判定。而体裁的无从判定恰恰是其创作的鲜明特征。以他著名的多卷本《小论述》(Petits traités)为例,此标题暗含古代罗马演说家如塞涅卡的论说体裁,又穿越中世纪和近代的论辩风格,直到当今的文论类型;与此同时,其文本的混杂式叙述和多样化风格又指向虚构、自我书写、抒情散文,且不断游移于各种体裁之间及其边缘。论者因而称之为“无可论述的书写”(Bruno Blanckeman),“批评的虚构”(Dominique Viart)或“令人错愕的书写”(Michel Deguy)。但在作家那里,实际上不存在体裁间的分野与对立。他说:“小说——由意象组成——与文论一样具有思辩性,由论据、列举、隐喻、辞源、引文、警句、故事构成”(《猫和驴的续篇》,第12页。译文出自笔者,下同)。他以碎片式书写糅合格言警句、寓言传说、记忆玄想,徘徊出没于传记、评论、随笔、小说之间,上承古代希腊罗马作家文论风格,下接从蒙田、帕斯卡尔、卢梭直到普鲁斯特和布朗肖的伟大散文传统,深刻地更新和拓张了文体的界定与范畴,为文艺理论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在他那里,对拉丁文、词源学的引用,对古代作家及艺术家的偏爱与掉书袋无关,而是在精神气质上的相契合相融通,也是他着力呈现的一种纵越古今的性灵经验。他的文字极其简净质朴,如白描般寥寥静穆,更无浪漫派文学对心理世界的恣肆入侵,却在节制与俭省中直打入人心与人性的最深处。
自然生长并显现于各种形式,这些形式不是自然孕育的,毋宁说是自然在空间转动时的发明
语言的隐秘性与不可言说之原初经验
利奥塔对“后现代”的定义是所谓“宏大叙事”的不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基尼亚尔的写作可称为后现代的。但这种后现代书写并不是否定现代性的所谓先锋探险,它恰恰在于尝试回溯已然漫漶遗失的某种人类记忆的源头:如史前岩画或远古象形字符泄露出的隐秘“从前(Jadis)”,它无从返回,正如每个人都无法回归和见证孕育自身的时刻。这种不可追溯的原初经验仿佛上古黑夜般晦暗幽深,却偶尔涌现于此在的时空,于电光石火间令人一瞥难忘:如性爱,如海潮,如雷电风暴,如火山喷发,如猛兽捕猎时的突然跃起。这些欲辩忘言的时刻也正是基尼亚尔所称的“不可沟通之内核”,而他窥见此中真意的方式是在语言退却时逼近那隐秘,在无言中探寻语言难以抵达的幽暗境地。他的文字空间因而呈现片断化,又在空灵中拥挤着静默与空白,用以传达话语之前的声音,文字之前的痕迹。这再次证明他对词源的热爱和拉丁文的引用并非无端:那些大多被遗忘的古代文字与意义便是一种“从前”的浮现,还今天的语言以其意味深长的历史传承,也让今天的经验在断裂中连接到不可说的过去。他文字中感人至深的力量也许正在于此:《罗马阳台》中被毁容的版画家在凌绝的悬崖上放逐自己,一笔笔蚀刻大自然的面容,而每一笔都是心爱女子的线条;作家的笔锋亦如刻刀,锋利地划破万物表象,凸显奇崛的风景和亘古悲欢的记忆。
艺术在文本中的显现:绘画与音乐之域
基尼亚尔的作品拥有极为丰盈的艺术美学维度。他的多部著作专论绘画与音乐,其他作品中也散见对艺术的感悟。他的小说也多塑造艺术家的形象,如《罗马阳台》中的版画家,《世间的每一个清晨》中的音乐家。艺术在他的文本中得到几乎是现象学的显现:对音乐的描述,对绘画的描摹,对艺术家肖像的描写,让乐声和图像浮现于不可尽述的文字。艺术形象感又赋予语言以赋格和修辞,即让文字拥有符咒一般的寓示力,在比喻、换喻、暗喻的移位转换中实现多维度的发散力量,于简洁中蕴意深远,于素朴中超越话语的表述。文字中的节奏与韵律来自音乐,形象与寂静来自绘画。《罗马阳台》中的版画家说:“物质想象天空。天空想象生命。生命想象自然。自然生长并显现于各种形式,这些形式不是自然孕育的,毋宁说是自然在空间转动时的发明。我们的身体便是自然就着光线所尝试的一种形象”(《罗马阳台》,第34页)。这略显神秘的说法道出的其实是文学艺术的诗学起源:世界的想象源于艺术,或者自然源于艺术的双眼。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作品中的艺术维度还深刻昭示了语言与文字,声音与图像,文字与刻画,象形与符号,表音与表意之间的关联,——而这也是今天的文艺批评在文学、语言学和美学的重合与缝隙间所着力思考之所在。
东方艺术精神的烛照
基尼亚尔文字的简朴细腻之美令人联想到某种东方精神。事实上,他对东方——包括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深刻的体悟。东方精神游弋于他的文本,正如过去痕迹的影子游荡在明亮日光的间隙,又如毛笔点染的烟晕让纸的白色染上了灰暗的调子。在他断简残篇的书写中有着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和清少纳言随笔的影子。和他们一样,他钟爱所有在迷涣不明中唤起昔日时光和流逝生命的痕迹:残枝、裂纹、灰尘、不透明的水晶和浑浊的玉,栏杆上掉落的鸟灰,以及一切生命在静默的老去和欲望的焚烧中日复一日投射的影子。他也曾经以翻译的方式诠释公孙龙,对老庄思想加以阐发,援引李商隐,从石涛等人的中国古代文人书画中窥见艺术的奥秘,对《红楼梦》赞叹不已。他文字中深沉的古典气韵因此不单来自希腊罗马,亦深得东方艺术旨趣。他的文字境界不仅在于其落笔所至的实处,更在于其段落之间的空隙与留白,气息的流转与虚静,亦即其无言之境,象外之象。以西文何以达此笔墨境界,这也是基尼亚尔留给我们的课题。
“世界上有些地方自原初便存在。这些地方就是凝固从前之所在。一切都涌向那里,带着远古的炽烈。那是上帝的面容。那是原初力量的痕迹,比人巨大,比自然广阔,比生命更有活力,像先于所有这一切的天系一样引人入胜”(《罗马阳台》,第70页)。这些“从前”的凝聚之地,就是基尼亚尔的文字所显现的时刻。他的文学空间类似于普鲁斯特对过去的重建,只不过普鲁斯特在千回百转的绵长写作中将极度私人化的经验化为超越时间的记忆大厦,而基尼亚尔则以沉静内敛的笔法呈现出一个个画面、物体、肖像、动作凝结的瞬间,万物之源仿佛就在那里,婴儿从母体诞生的最初记忆仿佛也在那里。他写道:“在小说中充盈着一道奇异的光。在小说中时间不死。在小说中逝去的会再次出现。先于拥抱的往昔才是小说的素材。爱在那里,在小说里,因为在那里死者以其真正的面貌重现,在那里,画面在每个失落的画面中再次缺失,源头迷幻恍惚”(《猫和驴的续篇》,第49页)。
在某些时刻,基尼亚尔与20世纪文学异人布朗肖有相似之处:关于黑暗,关于静默,关于死亡,关于秘密,也关于炫目的明亮。文字似乎清澈见底,意义却指向某个幽深晦涩的去处;愈是明晰,愈是晦暗,愈是简朴,愈是迷雾重重。读者被引入奇异的空间,阅读在这里不在于解释和找寻意义,而在于努力逼视飞流直下的湍急文字之后深不可测的不可读与不可见。在于跟随其文字流浪:“在阅读中有一种期待,却并不寻求抵达什么。读书即漫游。阅读即游荡”(《游荡的影子》,第50页)。
编辑/张定浩
在小说中充盈着一道奇异的光。在小说中时间不死。在小说中逝去的会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