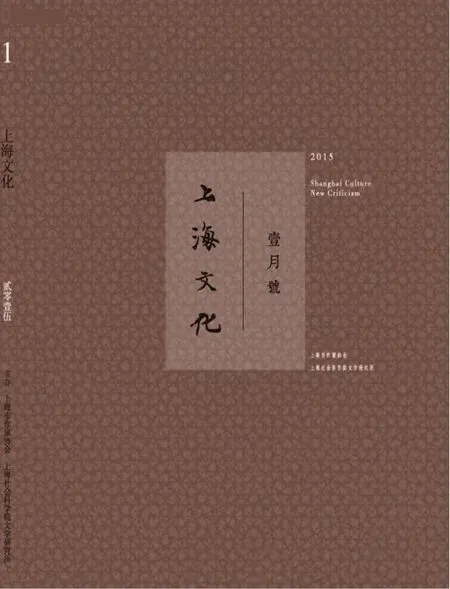《被禁锢的头脑》的里里外外
2015-11-14孙传钊
孙传钊
《被禁锢的头脑》的里里外外
孙传钊
《被禁锢的头脑》虽然属于随笔文体,米沃什在1953年巴黎出版的波兰文版的序言中还特意说它属于“一种政治论文”,而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并没有说《被禁锢的头脑》是虚构作品)。米沃什在波兰文版的序言中还说:“这里罗列的四位波兰作家是谁?可能会成为读者难解之谜。不采用真实姓名来叙述,对外国读者来说关系不大,也可以让这几个事例来一一驳倒教条的哲学。再说,并不是我首次曝光这几个人物的秘密,在华沙文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代号为阿尔法、贝塔、伽玛、戴奥特四位作家的真名依次是:J.Andrzejewski(1909-83)、T.Borowski(1922-51)、J.Putrament(1910-86)、K.I.Galczynski(1905-53)。]
我想,隐去真名主要原因是米沃什执笔时这四人都还健在。米沃什在第四章“阿尔法:道德家”中批判“阿尔法”亲眼见到监狱中关押了许多参加过华沙起义的、或参加过从属伦敦临时政府军队和抵抗组织的青年——完全是无辜的,却无动于衷,回避现实,在描述战争时期的作品中把讽刺、批判的矛头指向参加抵抗德、苏联国侵略的爱国的知识阶级。为此,他认为凡是记叙极权主义体制下的悲剧,最好不要采用虚构的小说体裁:
我很难谴责阿尔法,我自身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道路。我逃离波兰时,践踏了许多可以使一个人获得价值的东西。因此我要严厉地责问自己,尽管我的罪责与他不同。也许我们的命运不同,在访问华沙废墟或在窗中见到那些囚徒所谓瞬间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中已经注定了。我感到除非我写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否则我就不能去写。可以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去写,唯独不能用虚构的小说体裁来写,写德国纳粹占领华沙时期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如此。
以后,1980年代西德学术界曾有一场围绕极权主义体制的“历史学家的论争”。那场论争又引发西方文学界讨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真实的表象及其界限问题。当时美国学者萨尔·弗莱德兰德(Saul Friedlangder)、比尔·兰格(Bere Lang)等人认为艾普尔菲尔特、大卫·格罗斯曼、策兰等人运用现实事件虚构的文学创作手法,对真实性做出的挑战,并不是不能取胜的。而这种以不寻常力量和形态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米沃什当年显然对这样题材作虚构的写作缺乏自信,因为怀疑论不仅来自斯大林主义权威。
米沃什青年时期是上世纪30年代,那是整个欧洲知识分子左倾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对青年最有吸引力的时代。米沃什也承认自己早年曾是倾向于左翼文学的青年,虽然他最终也没有加入波共,因为让他作为一个非党员诗人担任驻西方大国使馆文化参赞,有利于人民民主共和国展现一种温和、文明的形象——也献身于战后的“新波兰”。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在1940年代末看到斯大林主义在渐渐吞噬整个波兰时,不仅清醒后决心反叛,而且在批判文学界同行的同时,他意识到也要严厉责问自己,感觉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所负的罪责,而这种罪责最容易用各种借口推卸。他要以行动洗刷自己的罪责,作为一个文学家、诗人,最好的行动是写出事实的全部真相。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认识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说出自己应负的罪责,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那意味着否定自己人生的历史和抛弃现实的社会地位。1950年代初,波兰国内的文学界面临暴力威胁的高压和物质利诱的怀柔(作家工资不亚于部长),但是,离开了波兰,在西欧或北美发表《被禁锢的头脑》这样的著作也要有极大的勇气。米沃什在法国写作该书的1951年,法国的知识界对斯大林主义的崇拜达到了巅峰。那年阿贝尔·加缪的《反抗者》出版,虽说相当畅销,给了米沃什等流亡海外的文学家很大鼓舞,然而遭到代表左翼主流的萨特、弗朗西斯·让松等人的激烈攻击(详细,可以参见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第38至第40章)。且不说来自法国共产党的攻击了(1946年法共党员占了国民议会中186席位,成了第一大党,可见影响力之大),“在他的‘家庭’、即非共产主义左翼阵营里,他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感到自己受到众人的围攻”(《加缪传》,591页)。当1954年伊凡修基埃维奇(Jarosław Iwasz-kiewicz,1959-1962年任波兰作协主席,诗人、作家)访问巴黎时对萨特提起《被禁锢的头脑》,和居高临下鄙视加缪缺乏严格哲学训练、以哲学家高人一头的姿态蔑视加缪《反抗者》一样,萨特不屑地拿出哲学家架势说:“光有知性还不够,思辨还必须要有智慧”(《被禁锢的头脑》日文版,317页)。和萨特相反,加缪给了他支持的力量。1960年加缪逝世的第二天,米沃什在悼念文章中说:这个《反抗者》的作者——与巴黎意识形态相反,是少数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人之一(《欧洲精神》,351页)。
在批判文学界同行的同时,他意识到也要严厉责问自己,感觉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所负的罪责,而这种罪责最容易用各种借口推卸
诗人或者作家虽然不是道德家,也不能抛弃普世价值和判别善恶的良知
米沃什流亡法国前后,法国还围绕苏联是否存在古拉格争议先后引起两起诉讼。即逃亡美国的苏联间谍维克多·克拉夫钦科(V.Kravchenko)自传《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法文版1947年在巴黎出版后,法共《人道报》以造谣等名义发起批判。为此克拉夫钦科以损害名誉罪起诉《人道报》社长和执笔记者安德烈·韦由尔姆塞尔,审判一直延续到1949年初。1949年11月,亲历过集中营苦难的、战前属于托派的大卫·卢塞(D.Rousset-d)出版了《集中营的世界》(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提出调查古拉格的计划,遭到《人道报》刊载文章攻击,卢塞也诉《人道报》诋毁名誉。
两个案子原告虽然都胜诉,但是《人道报》一方只得到象征性的微不足道的处罚。审判过程中,原告一方的证人或本人、或亲族因为是脱离共产主义的“叛徒”,继续受到左翼媒体的轻蔑评价。而否定古拉格存在的群体中,不少是非法共党员的左翼知识分子“同路人”,包括萨特、梅洛·庞蒂那样的非党员的文化界大腕。他们在公众中更有公信力、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后原告并没有取得舆论上的胜利。所以,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半个世纪后专门谈到这两个案子时,说:“萨特那样的‘同路人’比共产主义者更危险!”(《异国他乡的人》,日文版)米沃什在法国也陷入孤立的境地,不仅离开了波兰的读者们,因为无法用母语语言写作,是“生命中最大的痛苦”,经济上“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欧洲精神》,34-37页),而且人格上还要忍受委屈。1959年,在法国的波兰人(涅兹布热斯基)还要求美国驻法使馆取消他赴美签证,理由是米沃什是“一个卧底的共产主义者”,“苏联鼹鼠”(《被禁锢的头脑》,日文版,317页;《米沃什词典》,72页)。《被禁锢的头脑》虽然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但“从没上过书店书架”,他出版的另一本诗集《伊萨谷》在法国一本也没能卖出过(《米沃什词典》,72页)。
托多罗夫曾对雷蒙·阿隆和加缪对抗斯大林主义的行动特点相异之处作了评判。他认为加缪对来自莫斯科的谎言宣传保持警惕,最后与他的左派朋友绝交是出于一个文学家、作家和思想家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对读者有传达真实的义务。而阿隆力求在掌握事理和严密研究世界基础上,达到言论与客观一致是最重要的。阿隆的写作与法国实际政治生活保持密切关系;加缪则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主要精力从事文艺创作(《越境者的思想》,日文版,341页)。托多罗夫所说的加缪的特征用于米沃什也是十分恰当的。
米沃什认为,虽然《被禁锢的头脑》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完全是另外一个角色,我是个诗人”(《米沃什词典》,154页)。但直到1978年获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他才为自己诗人身份真被美国同行认同感到舒坦(1996年波兰文版序),“政治永远不是我的强项”(《欧洲精神》,28页)。诗人或者作家虽然不是道德家,也不能抛弃普世价值和判别善恶的良知。在《诗的见证》中他援引好几段西蒙娜·薇依1941年对法国文艺界的批判——放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良知,不辨善恶的、反对价值的虚无主义盛行,是法国(德国占领下维希政府)和时代的不幸,这样的思潮还扩展到全世界(74-77页)。1996年初莱泽克·柯拉科夫斯基在为巴黎波兰文刊物《文化》(kultur)写稿时,还提到法国左翼文化界在战后延续不断的这种逻辑倾向:当有人提到斯大林主义暴政时,就有些以“中央情报局的谣言”来搪塞;谁说起古拉格,就会被套上“冷战支持者”的帽子,法国也步入“谎言大国”,而这些舆论制造者往往是国家政治学院和巴黎高师出身者,让人难以置信——一直到1970年代这样的思潮依然如故。托多罗夫在2002年也说:“战后三十年是政治思想在法国遇难的三十年,知性被铅板屏蔽的三十年,对所有的言论都依照左派教条来评判,粗制滥造的意识形态统治了知识分子世界,拥有很大权力,其他的声音都被赶到边缘去”(《越境者的思想》日文版,184-85页)。晚年的米沃什还感叹,“由于全巴黎知识分子都相信了社会主义制度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我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一种自我毁灭行为,似乎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米沃什词典》,59页)。可以想象,米沃什做出流亡巴黎的决定需要何等勇气。
1950年代在英国也是左派控制了文化界、学术界的主流。那时代,恪守斯大林主义的党员和左翼知识分子,说起“变节者”、“叛徒”、“转向者”来,比对纳粹分子还要厌恶和憎恨。库斯勒《正午的黑暗》战后在法国成为畅销书,卖出四十万册。法共为了阻止其流传,甚至不惜把它全部买下,不料导致该书在黑市流通价格暴涨。可是在库斯勒流亡的英国,他及其著述就不那么受欢迎(那时代的英国,连奥威尔的小说销售量也很小),文化界主流对他反应冷淡。据《斯蒂芬·斯彭德(也有翻译为斯皮尔伯)日记》(S.Spender,Journals),一天祝贺左翼作家约翰·莱曼(John Lehmann)生日,英国一流作家、文化人三十余人聚会,库斯勒迟到,只得蜷缩在角落里,全体与会者都以憎恨的神态对待他。某天库斯勒在伦敦街头遇到自由主义作家彼得爵士(Lord Peter Death Bredon Wimsey),被对方骂作:“为三十英镑出卖灵魂的人。”两人就此绝交。1939年流亡英国的前波共党员多伊奇(I.Deutscher)在1950年为《上帝跌倒了:西欧知识分子的体验》(R.Crossman,ed.)写的书评“转向者的良心”一文中,并不是出于为同样脱党的库斯勒等人辩护,分析道:许多脱党者是因为不能在党内占据要职而脱离组织,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掌握作为批判证据的党内实情和经验,还有人把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批判斯大林主义时也表现出与斯大林主义同样的宗派主义,反过来依然是斯大林主义者。
1953年《被禁锢的头脑》法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出版后,米沃什也遭到英国的波兰侨民的攻击,怀疑他是一个来西方卧底的共产党员(《欧洲精神》,36-37页)。美国虽然那时候正起“麦卡锡反共狂澜”,但是文化界圈内的反麦卡锡主义的势力也很强大。比如,麦卡锡发表臭名昭著的演说正好是在钱伯斯(Whittaket Chambers)检举国务院第三号人物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一案判决的两周后,导致美国知识界倾向于,只要是右翼,言论的公信度就大打折扣。很多人不相信希斯是间谍,并要对钱伯斯等原共产党员(Ex-Communists)反击。钱伯斯长期陷于孤立,几度尝试自杀(详细可以参见托尼·朱特《重新评价: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Reappraisals: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中第18章《美国的悲剧:钱伯斯事件》)。所以,米沃什回忆道,“假定那时候去了美国,因为反对派声势强盛,恐怕《被禁锢的头脑》写不成;法国虽然环境也不好,因为是外国人的著作,出版倒没有受到干涉”(《被禁锢的头脑》日文版,317页)。
库斯勒《正午的黑暗》中写到斯大林大清洗时代,预审官伊凡诺夫审问老布尔什维克胡巴切夫时,胡巴切夫要在两种认罪中做出选择:承认违反党规定的“政治道德”原则的罪过和另一种唤起了内在“同情、良心等”具有人性普遍道德价值的赎罪。当这两种伦理观发生冲突时,斯大林主义不允许个人向良心屈服,要求恪守“政治道德”。米沃什也受到伊凡诺夫所说的“道德观”的影响,晚年回忆道:“我与华沙政府决裂,写出《被禁锢的头脑》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我破坏了每个人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米沃什词典》,59页)。米沃什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文学家的创作及其作品应该与传统伦理责任是一致的。正像汉娜·阿伦特指出的,极权主义体制与以往所有专制主义最不同之处,是彻底颠覆了人类三千年以来传统的伦理价值,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在发挥作用。《被禁锢的头脑》中四位文学家也面临这一重大的道德考验。
“阿尔法”,即安杰耶夫斯基及其作品中的道德信仰随着时代不断改变。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写作“主要兴趣集中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上”,最初作品中体现了超越世俗的基督教道德观,一种“知识分子的天主教”伦理观。出于良知,他与反犹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决裂,与资助他的右翼断绝往来。二战爆发,打破了他这种概念性的、脱离现实生活的写作的支柱:“真实的事件使得他想象、虚构的悲剧相形见绌。”在抵抗运动中,他既不接受伦敦流亡政府的“地下国家”,讽刺向往西欧脱离民众的地下知识分子群体,也拒绝听从莫斯科的小圈子的指示。特别是牺牲了二十万抵抗战士的华沙起义,使得阿尔法笔下的主人翁道德回到了世俗道德,但依然用宗教道德来解释:抵抗战士牺牲精神来源于宗教的忠诚——传统的美德。然后,眼见战后抵抗战士给关进了新政府的牢狱,阿尔法感到无奈,苏联控制了波兰社会生活的一切,他只能归咎于“历史”的安排。屈服于强大的“历史”之后,他又回归到战前创作的弱点,追求道德形象却又背离现实社会。他的小说又开始塑造高于现实的道德人物。阿尔法受到了新政府的欣赏,他获得了别墅,成了道德权威。于是“他的作家朋友们出于嫉妒他的贵族语调给他带来的成功,叫他‘可尊敬的妓女’”。但是阿尔法,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内心分辨善恶、追求终极善的良知没有泯灭,只是为“历史”的强大所迷惑。他不是道德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者,和米沃什、柯拉科夫斯基、齐格蒙特·鲍曼一样,1950年代后半起,阿尔法越来越鲜明地追求出于人性良知的善——争取天赋的权利。比如:1964年他在安东尼·斯沃尼斯基(Antoni Slonimski,1956-1959曾任作协主席)起草的、三十四个知识分子署名的要求政府“修改文化政策”请愿书上签了名;1970年在历史作家雅谢尼茨墓前作演说,批判对犹太作家的迫害;1976年又在斯沃尼斯基起草的抗议宪法改恶的声明上签名。同年夏天,还成为工人保卫委员会(KOR)十四名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在1980年催生了团结工会。1976年斯沃尼斯基车祸身亡后,作为作家群体德高望重的前辈、好几年占据畅销书头牌小说《烟灰与宝石》(Ashes and Diamonds,1948)的老作家,替代了斯沃尼斯基在群体中的作用。1981年米沃什回到故里,受到阿尔法——安杰耶夫斯基的欢迎。安杰耶夫斯基1983年因心脏病在华沙去世。2006年9月23日,他获得波兰总统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追赠的重建波兰骑士十字勋章。
《被禁锢的头脑》中的“贝塔”是博罗多夫斯基。和安杰耶夫斯基不同,他没有宗教信仰。牵涉抵抗运动,他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九死一生幸存下来。战后也是为了用母语写作,犹豫再三,1946年底才回到波兰。以后他转向了散文创作,认为诗歌已经不能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他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被冠名为《别了,玛丽娅》出版发行。其中的大多数故事都是以第一人称写奥斯维辛里的一个囚犯。这些小说描述了每天的恐怖导致的道德上的麻木,囚犯们试图活下来,通常相互关系是冷漠与卑鄙。而他,博罗多夫斯基在集中营里享受了非犹太囚犯的“特权”,善的追求及英雄主义在作品中丧失殆尽。米沃什看来,这样的作品是虚无主义的、不道德的和颓废的。阿伦特、托多罗夫都注意到并强调集中营、古拉格制造恐惧是极权主义体制的特色,这样的恐惧足以使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在原始求生的欲望支配下,抛弃所有属于人性的品质。米沃什的叙述中忽视了这种恐惧对博罗多夫斯基后来人生带来持续的阴影。博罗多夫斯基为了摆脱恐惧、为了更“安全”,最终加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干脆离开文学创作,散文也不写了,投身媒体成了记者,写起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的政论文。他天性是“豪气和谦卑的某种混合”,能屈能伸,不利时会“羞怯地藏起他的利爪”。正像米沃什和其他文学界的友人在很多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他在公共言论中的言说和他敏锐智慧感觉之间的落差与日俱增”,当这种落差到了极顶时,虚无主义就不能安慰自己了。他最后一点良知显露出来,是他的一个生死与共的密友被政府监禁并遭受拷打。博罗多夫斯基试图以他的名义出面阻止——还是个讲义气的哥儿,但最终失败,他不仅彻底失望,还知道恐怖马上又要降临到自己身上。1951年7月1日,即他的妻子刚生下他们的女儿三天之后,他从煤气炉吸入大量煤气自杀,时年二十八岁。
另一个诗人戴奥特——高什斯基,曾写过攻击米沃什的诗,“给一个叛徒的诗”。但是,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没有提起这件事。也许米沃什知道其实高什斯基是有奶便是娘的墙头草,“并没有真正明确的政治倾向”而不屑一顾,也体谅他的华沙这位朋友是出于恐惧表白自己(《米沃什词典》,58页)。战前虽然高什斯基曾有反犹的右翼倾向,那只不过为了取得右翼民族主义杂志支配权的一笔金钱生意,而民族主义会使得杂志发行数大大增加。他关心的不是他到底写什么东西,最多考虑的是用诗来追求最大盈利。自身有犹太血统的他并不从种族主义出发敌视犹太人,只是敌视那些追求诗歌纯贞的犹太诗人罢了。米沃什认为他“是骗子、酒鬼,然而又是个出色的、有魔力的——尽管失之轻浮——诗人”;正确地说他是“废话大王”、文学界的小丑,他的诗具有谵妄的幻想的特征。战后,他又开始了过去的生活循环:酗酒和吟诗。在巴黎和布鲁塞,他写取悦众多波兰侨民情绪的爱国诗和反俄诗,向每一家流亡者机构榨钱。两三年后,当他作品的出版可能性微乎其微、成了一个落魄潦倒的离乡背井者之时,华沙政府的特使向他招手:波兰一切都在趋于宽松。他们向他保证,他将受到热情的接纳,战前的右派过失将得到宽恕。终于,“他得到了一个最慷慨的庇护人,那就是国家”。“他如同一个魔术师,永远能从帽子里拎出适当数量的兔子,而所有的兔子都有你需要的颜色”。于是他比谁都热情地歌颂苏联的一切,但是这个东家并不那么好伺候,他诗歌的虚无的风格,背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久他谋生的活计开始动摇了,只被分配到一点翻译莎士比亚的活儿。但是,过了两年,诗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豢养价值,旧时的投靠右翼罪行将要得到清算。诗人敏感到末日来临。1953年12月,高什斯基突然死亡,按照官方宣布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突发(米沃什在法国写《被禁锢的头脑》时也只知道这个说法)。可是到他家去复制面型的雕塑家在以后的证言中说:颈部有绳索的勒痕,是自杀(《被禁锢的头脑》日文版,317页)。雅恩·帕托什卡等捷克知识分子幽默地把20世纪后半叶称作“面包的时代”,日常生活的面包成为大家唯一追求的对象,尊严、责任、良心以及其他精神生活都可以放弃的。哲学家帕托什卡长期靠当保管员、操作工等低微工资勉强维持家庭生活,后来也分配到翻译一些愚蠢的文章,每一页的稿费仅合四法郎。帕托什卡靠骨气挺过去了,高什斯基没能熬过去。
伽玛,即普塔拉梅特,米沃什的同乡、大学的同学、战后的上司,彼此最了解,所以在书中的篇幅也最长,遣词也最尖锐,甚至可以说刻薄。米沃什把他叫做“历史的奴隶”——战前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完全无条件向“历史”的安排降服的奴隶。1939年苏军占领属于波兰的立陶宛后,属于中产阶级的父母和几个十多岁的妹妹被强迫流放到西伯利亚集体农场,父亲死于途中,临死还诅咒这个没有良心的儿子,因为他到处向同胞作演说,宣传苏联人带来美好生活。当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有威望的老共产党员诗人W.B遭到清洗时,为了撇清自己,表示忠诚,“伽玛”发表声明指责W.B等人是法西斯主义者。德苏开战后他抛弃了妻子和女儿,撤退到苏联。在苏联的指挥下,在那里成立了亲苏的波兰政府和军队,“伽玛”也成了高级干部。战争末期,随着苏军回到波兰,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清洗、迫害波兰内战时亲伦敦临时政府的抵抗战士。米沃什并不感激“伽玛”对自己的提携,说那是“伽玛”“要把新的罪人投入羊群,是减少内心保持自由人的人数的一种方式,而被提携者会根据自己的生存状态感恩地对他进行评价”。米沃什说自己之所以最后还能脱身,因为“伽玛”过高估计了米沃什对依靠母语写作的文学生涯的依恋,乃至最后上司“伽玛”决定用阴谋和暴力对米沃什下毒手前夕,他才有偶然机会留在法国。我想,“伽玛”完全可以说自己坚持了如同《正午的黑暗》中预审官伊凡诺夫强调的忠诚,忠诚于党规定的“政治道德”,而米沃什是叛徒。但是,“伽玛”信仰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做出了回答:1981年6月米沃什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华沙时,被众人视为民族英雄(《欧洲精神》,40页)。
《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开首就极力推崇波兰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1885年2月24日—1939年9月18日)1930年出版的小说《贪得无厌》。在《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米沃什又提到维特凯维奇(以前在《米沃什词典》中也提到)。小说的故事是通过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烦恼男孩齐普乔的眼睛去看待西方文明的瓦解过程。英俊的男孩继承了波兰的一个大酿酒厂,自己却是个空想主义者。他在两位求爱者的亲近过程中变得腐败堕落。颓废的公主爱琳娜,她追求的是他的钱;另一个是疯狂的同性恋僧侣,看中的则是他的处子之身。随着这展开的故事,充满了色情的性描写,而这种狂热的性描写正是为了突出动物性肉欲泛滥是社会腐化的特征。
小说描绘现实波兰知识界宗教界/政界/军界全部腐化,精神文化——形而上的、高雅东西全部被色情、性欲、金钱、奢侈的物质取代。为何会变得这样?当时波兰边境——波罗的海附近已经被支那、蒙古军队占领,乌烟瘴气已经蔓延到波兰内地,最后波兰被支那、蒙古军队攻占。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未来世界——遭受中国攻击的东欧,充满了黑色幽默、性爱嬉戏以及被讽刺的社会经济学教条,援引不少现代哲学的词句,被称为“未来主义派”的作品。米沃什称赞维特凯维奇小说《贪得无厌》预言准确,还提到维特凯维奇在德国入侵波兰不久自杀身亡——安眠药加割腕。
虽然目前没有《贪得无厌》中译本,但是已经有不少网民已能通过盗版看到小说改变的波兰电影《贪得无厌》(2003年)。从网上的反响来看,大多人都不懂这电影的真实价值,把它作为同性恋的黄片看待,有个网民的留言还恨作者维特凯维奇把全世界精神生活堕落归咎中国人,说当年苏德两国应该永远灭了波兰。这个网民的心态与希特勒、斯大林倒是一致的。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