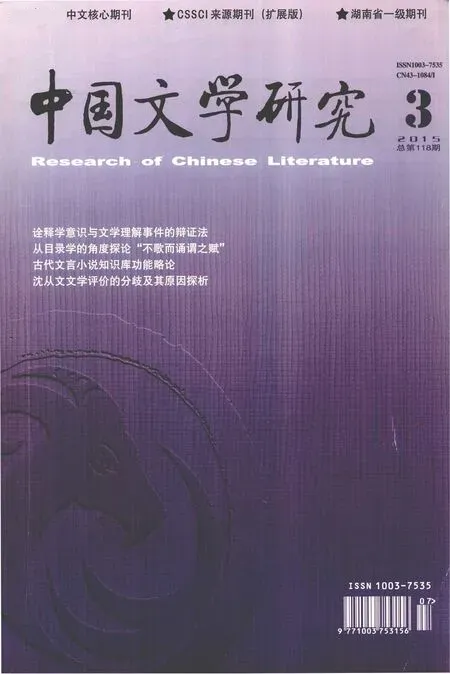那一代人的“怕”与“爱”——论《雷雨》的情感伦理
2015-11-14唐伟
唐 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在谈及《雷雨》的创作发生时,曹禺曾坦言,“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这‘怕’本身就是个诱惑。”,观照整部话剧,我们不难发现,曹禺所言的“怕”以及“情感的憧憬”不仅构成《雷雨》创作的内在动因,其实也是《雷雨》作为叙事诗的结构法则。也就是说,勘察《雷雨》的人物心里图景,我们同样会发现这种难以言说的“怕”及“情感憧憬”也如影相随地傍着话剧人物始终——毋宁说剧作家就是以一种象征寄托的方式,将创作主体心里投射在了蘩漪、周萍甚至是话剧所有人物的身上。换言之,在《雷雨》中,剧作家和话剧人物取得了某种同构的心理形构。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剧作家的“怕”以及所谓“情感憧憬”的内涵探究,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创作发生学的策略阐释,同时也是向话剧人物心理纵深挺进的迫切需要。
“怕”和“爱”的耦合
《雷雨》人物的“怕”,在话剧的一开场就被凸显了出来。在话剧的第一幕,从鲁贵详尽的叙述中,我们得知了周公馆闹鬼的事实,公馆闹鬼为接下来出场人物的“怕”做了最好的注解。从最日常的生活角度说,人怕鬼,怕那些实则并不存在的亡灵与精怪,反之似乎亦然,鬼也怕人,也见不得人。虽然,周公馆的“鬼”不能以实存本体的方式来理解,但如果从“鬼”是人之所怕的对象这一角度而言,称周公馆闹鬼其实并非无稽之谈——《雷雨》中的“鬼”当然不是狰狞恐怖的青面獠牙,而是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换言之,“秘密”是周公馆里鬼的肉身。秘密的生成以及最终暴露,即是《雷雨》中“鬼”的现身及活动过程。
话剧中的第一个“鬼”出现在周萍和蘩漪心里。当两人的乱伦成为既定事实之后,他们两人的“怕”也随之产生,二人心里有了一个共同的“鬼”:无论是蘩漪面对丈夫周朴园和儿子周冲,还是周萍面对父亲周朴园和弟弟周冲,怀揣不可告人秘密的二人有着共同原始本能的怕,他们怕东窗事发而受到道德上的严厉谴责以及身体上的严酷惩罚——而从根本上说,这种怕乃源自其所承受的人类对于最原始惩罚的畏惧。周萍和蘩漪触犯的是人类最古老的乱伦禁忌,弗洛伊德认为,“对于人类最早的刑罚体制我们可以远溯到禁忌时期”,禁忌本身“包括了神圣的和超出寻常的及危险性的等意义。”当包涵危险的禁忌像潘多拉魔盒那样被打开之后,禁忌的严惩会找上门来,肇事者的怕也就随即产生。周萍和蘩漪显然知道,如果奸情败露,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实在不敢想像,那将会是怎样一种不堪的后果。但在《雷雨》中,有意思的是,触犯乱伦禁忌的肇事者,对刑罚的怕本身,其实是源自另一种怕的催生,换言之,乱伦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也是“怕”本身催化作用的结果。
追溯周萍和蘩漪的乱伦心里根源,二人的媾和其实不单是出于两性间的吸引,周朴园的蛮横专制也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蛮横的父亲面前,软弱的周萍畏惧有加,但敢怒不敢言,他怕严厉的父亲,即使内心存有反抗念头,也不敢公然挑战父亲权威。但不能公然正面挑衅,并不意味着在其潜意识里不存在反抗意念。在弗洛伊德看来,“女人被视为反抗父亲的起点”,在弗氏对古希腊神话的分析中,他认为像Attiis,Adonnis 和Tammuz 等神的观念的产生,其实就是“为了违抗他们的父亲而与母亲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乱伦具有反抗父权的指向寓意——从这一意义上说,风流成性的周萍,即使不是有意识、有预谋地通过蘩漪来反抗严父,至少也在乱伦之后得到了一种象征式的弑父满足。而对蘩漪来说,“在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面对周公馆唯一合法的专制者,面对她那威严得不近人情的丈夫,蘩漪自然也是畏惧三分,对这个崇尚自由的女人来说,反抗夫权是情理之中的事。简言之,周萍和蘩漪相互的男女之爱里都包含着“怕”的成分——对周朴园的畏惧,两人也最终因反抗共同“敌人”的需要而暗通款曲走到一起。
如果说周萍和蘩漪的“怕”,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畸形的爱的发生,那么三十年前的周朴园和鲁侍萍,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类似的怕而葬送了两人原本美好的爱情。从周朴园的家庭格局布置及他跟鲁侍萍三十年后见面时对当时鲁的评价来看(很贤惠,也很规矩),我们不难看出当年周对鲁的至深情感。由剧本所知,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关系是因双方身份的不对等而遭到周家极力反对。这里潜藏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周氏家长极力反对他二人的来往,那么,为什么鲁侍萍在第一个孩子出世时没被赶出门而要等到第二个孩子出世才被周家扫地出门?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在鲁侍萍的第一个孩子降生至第二个孩子出世期间,尽管两人关系遭到周氏家长的极力反对,但周朴园一直都在努力向父母求情以争取对他和鲁侍萍关系的认可——周朴园显然不忍心将和自己有了爱情结晶的鲁侍萍扫地出门。而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后,可以想象,无论周朴园再怎么努力争取,最终还是未能顶住周氏家长的压力,因害怕触犯家长制权威和周家利益而不得不忍痛抛弃侍萍。他们两人的爱,最终也因“怕”而被迫中断了结。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因怕而中断的这段爱则又衍生成彼此心里的另一种“怕”。
在《雷雨》中,周朴园的心里有两种类型的“鬼”:第一类是鲁大海所说的“矿上死的工人”,这类鬼或许由于周作为一名民族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而现形,但他所担惊害怕的并不在此;纠缠他的是第二类或者说是第二个鬼——这个“鬼”远在南方无锡,但却形影相随地跟了他三十年,这个“鬼”既是他的心里负担,也是他的情感寄托,特别是在面对长子周萍以及现实生活中并不太美满的婚姻时,这个“鬼”更是成了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牵挂,他对远去的侍萍是既怕又爱。尽管鲁侍萍三十年前被周家无情地赶出家门,但从三十年后她和周朴园见面时的对其称呼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她对周朴园仍饱含着当年的深情,“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鲁侍萍离开儿女去几百里远的异地谋生,并非那里有更适合她的生计,而是她心里藏有一种深刻的隐忧——她怕在住居地见到她仍爱着的周朴园——她显然知道鲁贵就在周公馆做事。她的怕里包含着蕴藏发酵了三十年的爱,也就是说,三十年前的那段爱成了二人心中共同的怕。
可以看到,《雷雨》人物的怕和爱是互为因果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或因怕而生爱,或因爱而生怕。除了周朴园/鲁侍萍、周萍/蘩漪的爱—怕交织外,周公馆其他人也概莫能外。单纯的周冲爱得热烈,但“他爱的只是‘爱’,一个抽象的观念,还是个渺茫的梦。”,在对四凤的思恋中,周冲同样也担心害怕——他怕父母的反对,因此在跟蘩漪说出自己喜欢的女孩以及向周朴园请求将自己的学费分出一部分给四凤的时候,他显得犹疑不定战战兢兢。而心地善良,本分质朴的四凤在周公馆兢兢业业,心里本无“鬼”的纠缠,可由于和公馆大少爷之间不对等的恋爱关系,她也开始担心害怕,在即将见到要回家的母亲时,她内心的“鬼”开始现形了:我的妈最疼我,我的妈不愿我在周公馆做事,我怕她万一看出我的谎话,知道我在这里做了事,并且同你……,面对既定的事实,作为一名孝顺的女儿,四凤的良心因没听妈妈的话而受到谴责,她觉得背着母亲在周公馆做事而对不起她。四凤的“怕”,源自其内心的良善和一个孝顺子女的本分。爱/怕的纠缠推动《雷雨》剧情的发展,更深刻的则在于这种感情憧憬直接影响着人物的性格形成。
有论者指出,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蘩漪“这类女人总有她的魔”,“蘩漪一方面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经历了苦难,可同时又是一个魔鬼”,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为什么这类女人会“总有她的魔”?为什么说蘩漪是一个魔鬼呢?蘩漪的魔性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生成的呢?显然,“魔性”或“魔鬼”仍是一夸饰性的说辞,它并没有揭示出人物的内在心性本质。蘩漪魔性的存在,说到底还是与她的爱有关,“爱与嫉妒结合时,给人以魔性,甚至把人变为暴君,这在女子那里常可发现。”,在周萍那里,蘩漪激发起一个女人内心强烈的爱,而四凤的出现又让她妒意丛生。与其说魔是自始至终附在蘩漪身上的,不如说爱和嫉妒都是人的原始本能——作为女人的蘩漪有嫉妒的本性并不奇怪:当周萍变心由当初喜欢自己转而喜欢四凤时,蘩漪的嫉妒之心就被激发了出来——四凤的年轻和单纯已不是她所再能拥有的,“假如有人想象着他所爱的对象与另一个人结有相同或更亲密的交谊,胜过他前此独自与他所结的友谊,那么他将恨所爱的对象,并且嫉妒那另一个人。”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蘩漪尽管对周萍已怀有某种恨意,但除了对四凤的嫉妒之外,她仍然抱有期待对方回心转意的幻想,仍一如既往的爱着周萍。换言之,嫉妒并不纯然是否定性的破坏,正如耀斯在分析《追忆逝水年华》时所指出的那样:在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每当期待的东西得以实现,爱情之火总会熄灭,而当嫉妒使人想象心上人为他人所占有时,爱情重又萌发。在乱伦成为既定事实之后,对蘩漪、周萍二人来说,其实最为迫切的已不再是爱情的经营,而是如何来面对他们的家人以及怎样来防止奸情的泄露。四凤的出现让蘩漪妒火中烧,在看到周萍另有新欢之后,于是重又燃起了强烈的爱情火焰,从而将所有的种种顾虑抛之脑后。
如果说嫉妒与爱的结合,只是催生了蘩漪魔性的生成,那么,嫉妒和爱的结合似乎还不足以导致其魔鬼邪恶本性的充分展露。对蘩漪来说,从魔到鬼进而成为一个不管不顾的“魔鬼”,除了嫉妒的天性外,她还被一种怕笼罩,如前所述,她时刻都在担心害怕她和周萍的奸情被知情的鲁贵给败露出去,“最可怕的人就是被怕所控制的人。怕的作用是破坏性的。”,由前所述,她的怕源自对触犯禁忌所招致惩罚的本能害怕。也就是说,是魔的召唤导致了鬼的现身,是爱、嫉妒、怕三重情感的混合交织让蘩漪最后沦为了一名有着“复杂人性、充满魅惑性的魔鬼”。
爱和怕的纠缠构成《雷雨》作为叙事诗的诗性结构法则。正如曹禺所说的“怕是个诱惑”那样,对于《雷雨》里的周家人来说,不惟怕是个诱惑,其实还有个比怕更大的诱惑,那就是爱。“爱”和“怕”互为加强,爱愈浓,则怕愈深,反之亦然。当“爱”和“怕”的缠绕开始加速加深并越出常规,走向了非理性的失控也就在所难免了。
“怕”和“爱”的赎救
处在畸形的爱与非常态怕的缝隙间的人,堕入了痛苦的深渊,也沦为了情感的奴隶,服膺于一种虚空的幻觉,丧失了本真的主体性。如何恢复人自在的主体性来获得赎救性的自由,《雷雨》一剧在最开始就对此做了暗示性的回答。
在话剧的序幕中,曹禺精心设置的背景音乐是巴赫的“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rmini”,亦即著名的《b 小调弥撒曲》,这支宗教意味很浓的名曲在最后一幕收尾的时候再次奏起。对于背景音乐的选择,曹禺曾说过“那点音乐是有点用意的,请设法借一唱盘,尔便会明白这点音乐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的境界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的”,因此实有必要厘清这支曲子的纹路。
众所周知,被誉为近代音乐之父的巴赫是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也是最后一位把为教堂创作音乐视为最大关怀的伟大天才。在他的创作中,教会音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虔诚的新教教徒的巴赫,他一共创作了5首弥撒曲,6 首经文歌;为教会创作了5 年内每周礼仪所用的康塔塔(一种大型声乐套曲)共200 首;在其创作的大量管风琴曲中,有144 首圣咏调。巴赫对教会音乐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这些作品中,被视为巴赫代表作的就是《b 小调弥撒曲》。这首弥撒曲被认为是同类音乐中最深刻、最壮观、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它包括传统的《天主矜怜颂》、《荣福经》、《信经》、《至圣经》、《羔羊经》5 个部分,共24 首分曲。其中渗透著新教的改革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综观全剧,不难发现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其实这种安帖人心的宗教赎救意味贯穿了全剧始终。
我们看到在话剧第一幕的大幕拉开时,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这样一幕:
开幕时,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滤药,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一面在揩汗。
煎药作为话剧人物动作来说或许并不称奇,但背着观众煎药这种刻意的设计作为话剧的第一个场景出现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也就是说作为话剧关键情节线索的“药”一开始就被置于隐匿的场境,而其随后所展开的剧情也的确如此:面对四凤端上的药,蘩漪感到莫名其妙,“谁说我要吃药”,生病的人既然不知道自己有病需要服药,这着实有点匪夷所思。既然是背着当事人抓药,那么抓错药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赋予了“药”在剧中的另一个特性——错位。《雷雨》中的药因而就获具了它的多重隐喻意味。现实生活中的“药”是一种悖论性存在:既是病痛和不健康的征兆,而本身又寄予一种拯救和希望,生活中人们希望远离它,但必需之时又不得不依靠它。我们知道蘩漪事实上的确有“病”,但并不是“老爷说的肝郁”这一生理疾病。作为一个正值中年盛期的女人,周公馆的太太其实是心里有病。蘩漪年龄上比周朴园小一圈,两人志趣又不尽相同,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女人,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蘩漪都处于生命中的旺盛期,可在周公馆她正当的生命欲求无从得以释放,久而久之也就郁积成病。蘩漪病急乱投医,她抓的是周公馆的大公子这根救命稻草,并天真地以为周萍就是她的希望、是医治她心病的最好的“药”,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就在蘩漪身心暂时性地获得疗救的同时,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乱伦包袱成了她心头的新病,而这“病”又多了一个受害者——周萍。周萍“病”发之后感到后悔了,为医治疗伤他也开始了寻找救药的过程:
“他见着四凤,当时就觉得她新鲜,她的‘活’,他发现他最需要的那一点东西,是充满地流动着在四凤身里”,“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他要死心塌地地爱她,他想这样忘了自己,当然他也明白,他这次的爱不只是为求自己心灵的药”。
很显然,周萍不过是用一种逃避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病情。如果说蘩漪是有意地背着世人抓错药,那么周萍则是无意识地在毫不知情地情况下抓错了药。
对周萍和蘩漪这两个触犯乱伦禁忌的大胆肇事者而言,其触犯禁忌所受的惩罚非但关涉他们自己,还牵连到了无辜的他人,“在早期,破坏禁忌所遭受的惩罚,无疑的,是由一种精神上的或自发的力量来控制:即由破坏的禁忌本身来执行报复。稍后,当神或鬼的观念产生以后,禁忌才开始和它们结合起来,而惩罚本身也就自动地附随在这种神秘的力量上了。”,《雷雨》中乱伦的再度发生——周萍和四凤间的兄妹乱伦,即是由破坏的禁忌本身来执行的报复——这是周萍事先所没意识到的。“随着文化型态的改变,禁忌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同时,也慢慢的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成了法律,可是‘埋藏在所有禁忌里的那种无言的命令,虽然因为随着时间和空间而造成了无数的变异,可是它们的起源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即:当心魔鬼的愤怒!’”,如果说禁忌里包含着“魔鬼的愤怒”,那么周萍和蘩漪对禁忌的触犯显然是惊醒了魔鬼的愤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雷雨”为“魔鬼的愤怒”似乎再贴切不过。
周萍和蘩漪一样也没对症下药,也就是说这两副病急乱投医所抓的药都错了位,也因此注定是无效的,而服错药的后果是当事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随着剧情的推动,周公馆里病人们的病情也愈加深重,而在人间药物和救星都宣告破产无效的情况下,处在爱—怕深渊中的人究竟还有没有得救的可能?会不会存在一种根本不同的新的救药呢?我们发现当话剧的序幕大幕拉开时,观众所看到的背景布景恰恰是一座教堂附属医院,那是“药”的集散地:不仅有作为实物的中药西药,更有精神救赎的药方药剂——弥撒和《圣经》。也就是说,在人间的药物失效之后,作者试图寻找一种天上的药来医治《雷雨》里有病的人们,用宗教的救赎来弥合有罪人的伤口,“倘若在刑罚和罪恶之间没有某种使污浊净化的东西,那么什么事情就不会有什么不同。这某种东西只可能是上帝。”,而对没有信靠的人来说,怕是种永恒的生存状态,“怕是被上帝遗弃的产物”,这就自然地把话剧主题由拯救上升到了救赎的高度。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能震慑魔鬼愤怒的也只能是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雨》是越过了传统民族文化的固有疆界,在寻求普世意义的人的终极救赎。
结 语
迫于情感需要以及被“怕”所诱惑的曹禺或许不仅仅在于通过一部《雷雨》来言明某种“郁热”的生存困境,《雷雨》在触及某一悲剧性人类境况的时候,其作者是否又想到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呢?换言之,在《雷雨》中,曹禺是否想通过某种诗意的方式来暗示为诱惑所劫持的人的出路和希望所在呢?
人不惟是理性的动物,理性/非理性之类的二分之于人固然有认识论的意义,但显然涵括不了人的本然存在。作为有着丰富情感的灵性存在,人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天起直至归附尘土的那一刻,无不行进在悲欢离合、生死爱欲的情感场域之中。“怕”和“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作为世间最灵动的情感主体,人体验着情与欲的深度以及爱和恨所能企及的广度,人性的复杂聚启蒙与愚昧于一体,集此世的实在与彼岸的超然于一身。而对国人来说,人性除了熟知的理性和感性维度外,陌生的是,人性的深处其实还潜藏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另一维度——神性。
畸形的爱与非常态的怕,在《雷雨》的诗性悲剧构成中起到一种结构性作用,依话剧的剧情发展来看,两相融合交织而成的爱—怕情结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枢纽,“曹禺每个人物的心灵历程,其实都是心灵辩证法的一个展示过程”,重要的或许不止在于指出一个笼统的心灵辩证法或人性纠结,且还在于分析并论证是怎样的心灵和人性,及又是怎样的辨证和纠结。
当怕和爱的纠缠失控之后,作为人之根本性的“药”的宗教救赎也就成为可能。从这一意义上说,《雷雨》隐喻的又何止是那一代人的“怕”与“爱”?也恰恰是从这一层面上我们说《雷雨》是一部世界级的文学经典。如果说《雷雨》之于其诞生的那个时代具有社会/政治学参照的历史镜像功能而被当作“社会问题剧”来读的话,那么在远离那个时代的今天,话剧所探讨的个人生存伦理或许应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1〕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杨庸一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3〕陈思和.细读《雷雨》——现代文学名作细读之三〔J〕.南方文坛,2003(5).
〔4〕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5〕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 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M〕.张百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9〕S·薇依.在期待之中〔M〕.杜小真、顾嘉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