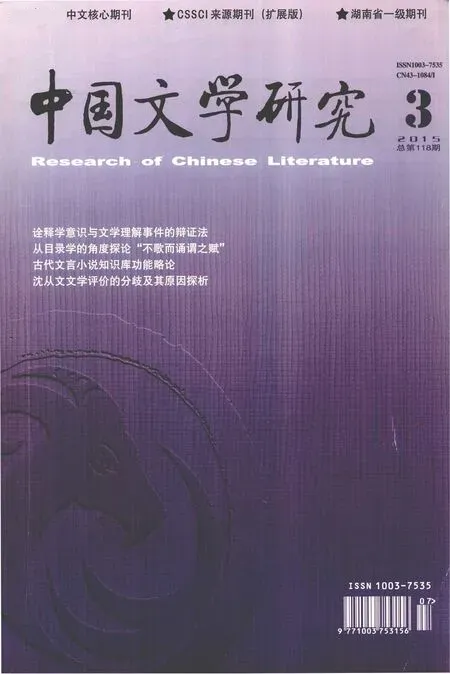桐城派文化生态建构刍议
2015-11-14施旭升
施旭升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4)
一、从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谈起
毋庸置疑,学术研究的起点应该是概念的界定。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自然概莫能外。其中,我们大概经常遇到的几个概念,比如“桐城派”、“桐城文化”等,就曾经广为人们所沿用甚至相混同,以至于产生概念意义的伸缩,甚至出现某些误解和歧义,形成鸡同鸭讲或者自说自话,从而也就很有必要加以明确界定。
关于“桐城派”,自然是有其具体所指的,也就是崛起于清代而开宗立派的桐城古文,大概学界暨坊间于今都没有什么异议。“桐城派”以古文闻名,而旁涉诗词、经史、书画等。作为中国明清文化的重要代表,桐城文人结为门户,世代相传,其传人遍及全国各地。它不仅自明末清初以来绵延200 余年,而且其影响所及,响应者众,形成巨大声势;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承继秦汉以至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文统流脉,而且,遵奉儒学特别是宋元以来程、朱道统余绪,成为明清文化之集大成。“桐城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久,在中国文化史上确是少有匹敌的。
至于“桐城文化”,却是与“桐城派”相关又相互区别的一个概念。“桐城文化”也许更应该是关于一座城市的传统、当下以至未来的,属于地域性的。它关乎这个地域的自然,更关乎其历史,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桐城文化”当属于一种典型的地域人文景观。其地域范围以老桐城(包括其四乡)为中心,而向外辐射;其载体就是桐城的大地、山水世态和人情,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对于“桐城文化”的较为准确的界定应该是:“它应包括桐城历史名人、文献典籍、桐城教育、科技、医学、戏曲、书画、仿徽派建筑、风俗民情、方言、饮食、宗教信仰、动植物资源等。凡与桐城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属桐城文化范畴,是桐城旧有地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然而,这种“桐城文化”的界定,事实上却由于地域的区隔、历史的演变以及现实利益的纠葛,又难免有画地为牢之嫌,不仅其价值指向很明显地趋向实用化,而且其利益相关者则多是不以为然的。
如果说,“桐城派”的概念凸现的是一个辉煌的“过去”,“桐城文化”的概念彰显的则是一个有限的地域,那么,这里也就需要我们提出第三个概念,即“桐城派文化”;也就是以“桐城派”古文及其精神义理为核心,并以其兴衰演变为根本,旁涉其广泛影响及转型历程。“桐城派文化”概念的提出,虽然是出自本文的新撰,但却有其现实针对性和历史必然性。
具体说来,“桐城派文化”的内涵既离不开“桐城派”,却又不是局限于桐城的地域(特别是现有的行政区划)之内的“桐城文化”。如果说,作为有清一代最大的古文流派的“桐城派”,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史现象,也并非单一的地域文化现象,那么就应该看到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前传以及其各种文化的基因;同样,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桐城派”不只是一个苍凉的背影,那么就应该把它看成是至今仍旧存活的文化生命体。因为,“桐城派文化”在其历史发生、发展以及传承的过程中,虽主要出自于桐城的地杰人灵,但是又远远突破了一时一地之局限,而成为一种贯通古今、远播海外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以往的文学、经学发展到今天的哲学、美学,“桐城派文化”虽属于古典文化范畴,却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虽然20 世纪以来,“桐城派文化”也是命运坎坷,甚至历经史无前例的“文革”而几乎荡然无存,但是,正所谓“有石在,火就不会灭”,新时期以来,“桐城派文化”又得以重续前缘,不仅是“桐城派”传人认祖归宗,也不仅是桐城故里需要建立一个地域文化的品牌,而更为重要的还是“桐城派文化”的精神价值的重建,也就是在现代学术文化的视野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上来建构起“桐城派文化”的概念范畴及其符号和价值体系。
基于以上的概念辨析,本文选取“桐城派文化”作为论述的对象,显然主要还是基于其学术价值的考量。换言之,本文所讨论的“桐城派文化”,更侧重于构建其理想形态并发掘其精神的价值,从而需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的范畴,需要对其历史发生、现代转换以及价值形态加以进一步辨析。
二、桐城派文化的社会历史价值
追根溯源,“桐城派文化”离不开桐城这方古老的土地,更离不开“桐城派”古文及其精神义理作为其文化的根基。
从桐城地域的山水大势来看,桐城“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与其“外江内湖”的开放性相并存的地理位置,使得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勤劳而又智慧,民风淳厚却不抱残守缺。长期以来,其内陆交通封闭与其通江达海的便利相结合的特征,既使得人们视野开放、安居乐业,同时也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有效的抵御。诚如戴名世所言:“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这种土壤所孕育出“桐城派”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他们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不仅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多有建树,更有着经世致用方面的艰苦努力,以至于成为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种集大成式的文化样态。
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生成与扭转往往就是在一个又一个事件和段落中完成了。众所周知,“桐城派”的崛起既得益于千年的道统,其衰落却也是随着这种道统的损毁而沉沦乃至消弭。事实上,归结起来,“桐城派”衰落乃至沉沦的命运大致与两大历史事件分不开:其一是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其二是20 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乃至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有人曾认为:“桐城派”的衰落早在1840 年的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了,殊不知鸦片战争所涉及的区域大致局限于东南沿海,对于地处一隅的桐城并无直接的影响。而随后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桐城派”则几乎是毁灭性的。特别是地处江淮之间的桐城甚至直接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拉锯的战场。连绵不绝的兵火所带来的不仅是家园被毁,生民涂炭,而且恪守千年的道统根基似乎已经被深深地动摇了。
到了1917 前后的“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新文化运动人士,曾经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上批判“桐城派”,蔑称其“桐城谬种”,以至于这一恶谥流传甚广,使得“桐城派”彻底地被污名化,以至于长时期无人敢加以声辨。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桐城派”作为地地道道的“四旧”更是在劫难逃,以至于在桐城本土都已难觅其遗迹。直至1985 年11 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该研讨会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戏曲等多方面给予“桐城派”文化以全方位的探讨。至此,“桐城派”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才得到了人们较为客观的认知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问题是:“桐城派”的消沉衰亡就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尤其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桐城派文化”?或者,归根结底,“桐城派文化”的社会历史价值究竟何在?今天是否还需要坚守和发展“桐城派文化”?
其实,“桐城派”虽早已风光不再,但是,“桐城派文化”却是作为一种“古典”精神的代表而延续至今。这里所谓的“古典”,无疑是与“传统”分不开,但是,它又并非仅仅意味着过去,并非只配在博物馆里占有一席之地。执着于“古典”,也并非意味着保守和古旧;追求“古典”,更不是不意味着淡泊“出世”、远离现实,相反,“古典”的坚守乃意味着一种人生的执著;“古典”的精神境界往往可以超越现实表象的时空,追求“象外之象”的崇高、明达、澹泊;“古典”的风貌既可能有着市俗文化的赏心悦目,也不排斥浅近通俗,有着细腻、含蓄、优雅、超脱、余味无穷的深邃悠远。“古典”的内蕴既有着平民的品格,又有着贵族的胸襟。惟其如此,古典艺术并不古板,也并非灰暗低沉,而是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调;它不是排斥感官,而是重视感官,对活生生的感性的事物采取欣然享受的态度。它讲究自然、单纯、活泼、安闲、恬静、清明、典雅、平和、条理、秩序,也就是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怨”,所谓“中和有节”、“宁静致远”。可以说,这也就是“桐城派文化”所坚守的堪称“古典”的道统。而且,更重要的,就当今世界而言,“古典世界的每一个遗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这些遗物所共有的问题、故事、疑问和意义,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都有着一个它们所共有的位置。”如果说,一种文明就代表着一种文化模式,那么,这种文化模式的形成就必然有其足以称之为“古典”的积累与遗存。尤其是对于恪守古典立场的“桐城派文化”而言,它的形态、价值及其发展程度、演变历程,并不是以其它文明形式为尺度所能衡量的,而必然表现出其自身独特的古典化的精神特质,而且在当今世界理所当然地拥有它自己的位置。
三、桐城派文化的现代转换
“桐城派文化”虽然有着其悠久的传统并显示其深厚的根基,然而,其现实情态却是不容乐观。如前所述,自鸦片战争以来,“桐城派”先是历经“太平天国”的兵火的焚毁,后又遭遇“西学”大潮的冲击,特别是遭到陈独秀等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批判,遂呈急速衰落之势。然而,20 世纪以来的“桐城派”却并未因其后学凋零走向寿终正寝,而事实上体现“桐城派”的精神传承的“桐城派文化”则能够历经现代文化的洗礼得以重生。
何以言之?
仅就“桐城派”的兴衰过程而言,如果说,方以智、钱田间开创了“桐城派”的先河,方苞则奠定了“桐城派”的理论基础,刘大櫆承上启下发展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到了姚鼐,更是集各家之大成,进一步完善了“桐城派”的学说体系;而吴汝纶、刘开、姚莹等成为“桐城派”后期的杰出人物,那么,到了20 世纪中后期,实则由方东美、朱光潜等的努力而别开生面,使得“桐城派文化”生出新的枝桠。可以说,他们虽然沐浴了欧风美雨,却依然能够在桐城派的精神传承中得以贯通中西,最终成为现代“桐城派文化”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方东美(1899-1977)可谓学贯中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有效地汲取西方哲学的滋养,最终熔铸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譬如,早在留学美国期间方东美所完成的硕士论文《柏格森人生哲学述评》及博士论文《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一条中西文化及哲学的比较研究的路径的探索,而在其后完成的《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等著作中则是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乃至加以融会贯通,其哲学建树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桐城派所尊奉的儒家道统。再譬如,方东美从《易经》哲学出发力倡一种“生生之德”,认为中国文化之注重“品德”(道德),也就是从高度的哲学精神与高度的艺术精神相配合中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并进而追求“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的生生大德,已经揭示出一种中国文化的生态哲学思想。可以说,西方的哲学智慧,道禅的人生意绪特别是庄子的诗意境界深深影响了方东美以后的致思路径,而其士子情怀、国学根基以及桐城古文的训练也形成了他华美丰赡的哲学著述风格,显示出一种“将生命、宇宙和美感圆融相契的广大和谐的全体”的精神情怀,且最终成就了他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的伟业与品行。
另一桐城派文化的重镇当属朱光潜无疑。因为,在朱光潜(1897-1986)的身上,不仅流淌着传统桐城文化的血液,而且更是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现代转换中的桐城派文化风貌。朱光潜从少年时代习读桐城古文传统,到后来接受新文化的影响,投身西学,系统地追求西方文化;从教育学、心理学最终走向了美学。在这一学术生命成长的历程中,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奠基人,朱光潜不仅融汇中西,以《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著作对于中国传统诗学美学进行重新诠释与系统改造,而且,更以一种贴近时代的心灵去阐释中西美学的传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与蔡仪、李泽厚、姚文元、周谷城等人进行美学论争,催生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建构与更新;他是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尽管他关于形象思维、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观点曾屡遭批判,却也因此而彰显出他的学术思想的丰赡及其探索精神之可贵;他曾经在叔本华、尼采那里汲取过非常丰富的营养,却从克罗齐走向了维柯和马克思,从而也更显示出在文化激烈转型的20世纪桐城派文化的悲怆的历史命运。
细究根源,不难看出,遵循道统、文统的“桐城派”,正是因为总是面临着“世变”的挑战,从而不能不浴火重生。在晚清饱受了“太平天国”的战火蹂躏以及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批判之后,“桐城派”确乎已经陷于绝境。但是,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进步,已显示“桐城派文化”经世致用、日新趋变的努力。特别是作为桐城后裔,方东美、朱光潜等能够承前启后,先后留学欧美英法,自觉承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如果说,朱光潜是从桐城派的“文章”之道走向了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而方东美则从对于桐城派“义法”的体悟中走向了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一途。因此,正是在融通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意义上,经过方东美、朱光潜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桐城派文化”具备了一种现在时态,从而真正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
诚然,应该看到,“古典”确乎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古典”与“现代”成为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两者总是相对应而存在。“古典”正是在“现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得以显现;“现代”也正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进化而表现出对于“古典”的传承与超越。而且,本质上,“古典”与“现代”,又并非只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两者不仅代表着某种时代条件下先后出现的文化的形态、样式和风格,而且,更重要的是各自体现为一种精神品格,一种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存在的方式,一种精神的操守,一种文化的立场。故而,在“古典”与“现代”的密切关联中,正如“现代”需要以古典精神相依托,“古典”,在现代精神的映照下,往往会闪现出耀眼的光芒。两者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不走进“现代”,当然就无所谓“古典”;抛弃“古典”,“现代”也就显得无根。在这个意义上,“桐城派文化”已然展开了一种融“古典”于“现代”的价值理想的追求,或者是开启了一场在“现代”文化语境下来重建“古典”价值的思想实践。
四、桐城派文化的生态建构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桐城派”的古文及其实践,而是着眼于一种绵延不绝而又具有开放性的“桐城派文化”的生态建构,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桐城派文化”在当下所应有的多样化的生态样式以及丰富的现代意义。这里,“桐城派文化”不仅超越地域化的山水自然生态而走向一种场域化的人文精神生态,而且,在时间的维度上也明显突破其历史传统的局限而走向一种现代文化生态的建构。
从而可以说,从生态学意义上,重建桐城派文化的生态系统,就是要使其既能上接“桐城派”的历史传统,又能下启现代文化精神的认同;“桐城派文化”不能仅成为一种“标本”,而应该成为一种“活体”,融入当下的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当中。而如何重建桐城派文化的生态体系,如何才能激发出其历久弥新的文化活力,也就成为本文思考的重点所在。
应该说,所谓“超越地域化”,就是说桐城派文化既立足于桐城县域,而实际上又远远超越了地域的局限;而所谓“场域化的人文精神生态”,则是在突破地域限制之后,桐城派文化便不可避免地直面各种现实的文化矛盾的纠葛与缠绕,受到各种文化权力的控制和反控制。或者说,这也就意味着:“桐城派文化”的生态建构遭遇着不可避免的文化矛盾,即传统与现代、本土(地域)化与全球化、审美与功利、精英与大众等多重矛盾。事实上,这些矛盾的揭示与克服,也就是成为“桐城派文化”的生态得以重构的重要关结点所在。
具体说来,关于当下“桐城派文化”的生态建构可以在一种“树状”的结构及其成长当中来加以理解。
首先,“桐城派文化”是一个有根的文化。根的意义,即在于它是生命的源头与象征。从生态学的观念来看,寻本探源,也就在于探寻和培植生命之根;而且一个生命体唯有根深才能汲取大地的营养。这个根,对于“桐城派文化”而言,当然就是诸多前贤所建构起来的精神血脉与思想传统。这不仅在于它深扎在桐城这片的古老土地上,汲取的是风土民情、价值伦理与文化认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老树能否发出新芽,毕竟才是其生命力传承的关键之所在。所以,桐城派文化的根系历经数百年的生长,已然深扎在中国传统的土壤之中,而其生命力的拓展却还是要更多的仰赖于全球化时代的气候与土壤。
其次,“桐城派文化”是一个有躯干、有身体的文化。也就是说,“桐城派文化”不仅拥有其鲜明的文化特色,而且拥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及其丰富多样的文化经典。从绵延数百年的古文传统、教化精神与人情伦理,到现代意义上的方东美的哲学、朱光潜的美学,不仅其精神价值得以一脉相承,而且造就出一个巨大的文化丰碑。虽然其间历经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转换,其文化文本也从古代的经学、文学转向现代的哲学美学,已然发出新芽,开出新枝,然而其文化符号及其价值意义却犹如生命体的血脉,周游不息,传承不已。
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桐城派文化不断调适与其生长环境的关系,长时期内获得了一种自适性的生态平衡;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生态平衡的维系,才是桐城派文化的生命力得以绵延不绝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桐城派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是一开始打破了这种生态平衡,甚至是被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因此继而又是不断寻求并努力建构起新的生态平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平衡与失衡,也就构成了桐城派文化始终难以摆脱的生态矛盾。其实,也只有在这种平衡与失衡的交错之中,才能始终保持桐城派文化的生命活力,显示出一种历史文化演进的动态平衡。
如今,桐城派文化业已从古典文化演变成为一脉虽饱经风霜却又重新枝繁叶茂的现代文化。虽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当中,“桐城派”曾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甚至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但是,“桐城派文化”却能够历经灾变而绵延于今。其原因不仅在于“桐城派文化”自身的强大吸附力量,而且正是在其作用之下,桐城文脉得以代代相传,其营养也滋养了现代文化的躯体与精神。譬如,桐城派原本作为精英文化主要是在知识阶层发挥效应,进而才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日常生活;其民间崇文重教、文风炽盛也才是理所当然的。由此,诸如“黄梅戏”之类民间艺术也才能够在桐城落地生根,乃至发展壮大、蔚为大观,这也足以显示桐城派文化样态的生命力的强悍。进而,“桐城派文化”并不担心与“西学”的交融会通,甚至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刺激之下而主动地去拥抱西方文化,才促成了“桐城派文化”走向世界,重获新生。即便在盘根错节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桐城派文化”也能以其独特的文化资本与价值资源而获得新的精神认同。
总而言之,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绵延不绝的。“桐城派文化”的生态效应及其符号价值正显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即所谓:树大才显根深,根深才能叶茂,才能生机盎然、绵延不绝。
〔注释〕
①“地域文化”论之局限,表现在1949 年以来随着行政区划的划分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甚至区域之争,譬如,原本为桐城县之东乡和南乡的的枞阳县就为“桐城派”的归属而争议不已,所谓“枞阳出人,桐城出名”即为显例。
②当代桐城派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桐城派文化作为古典文化已经终结其生命历程;它随着儒学精神的解体、耕读传统的消失而趋于消亡。其实,这种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消亡观”是值得商榷的。笔者拟另文专门加以论述。
〔1〕蒋越林.桐城文化研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2).
〔2〕戴名世.戴名世集·孑遗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英)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著,董乐山译.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M〕.牛津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
〔5〕方东美.生生之美(封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